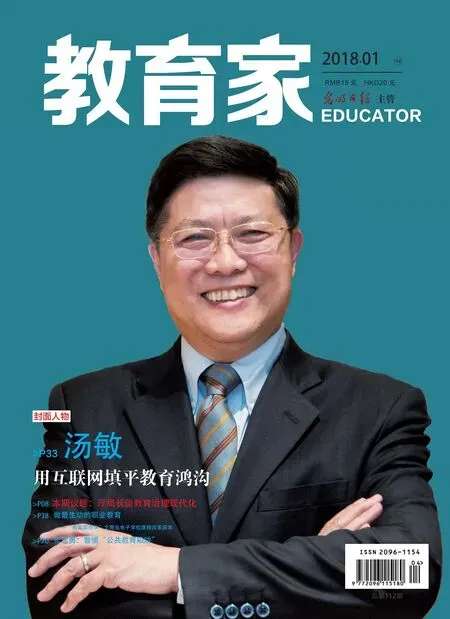比“成功”更有價值的是趣味
吳 非 / 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我讀小學時,全校只有走廊上有個電鐘,教室里沒有誰能知道時間,老師教學枯燥,學生就一節課一節課地“熬”。我的同學曾數數字,上課鈴響就開始默念數字,每數一百在紙上畫一筆,畫到幾十個“正”字正好打鈴下課。還有同學在窗框上刻過日影,大家眼睛不時地瞄那道刻痕——學習無趣時,十一歲的兒童就這樣打發上課時間。之后學生開始有手表或電子計時器,如果學生厭倦教師的課了就頻頻看表。
沒有趣味了就開始生厭,學習更是如此。一旦厭學,輕一些的,滿足于考試及格;嚴重的,能發展到拒絕上學。學生厭學,一部分是家庭原因,也有一部分是教師教學的原因。而壓迫學生最為嚴重、消解學習趣味的,是社會和學校盛行的所謂“成功學”。
把競爭引入學校教學,把屬于完善自我的進德修業當作名利追逐,用考試替代教學,并錯誤地宣揚人生是你死我活的競爭——當學校和家庭合力遵從錯誤落后的價值標準時,作為學生,往往是沒有能力對抗的,他只會在無休止的喧囂中變得麻木,“生活”被拉低為“生存”,生命便失去了趣味。
愛因斯坦曾說:“不要試圖去做一個成功的人,要努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然而,如果價值觀扭曲,教師和家長就會把“價值”解釋回“成功”。家長剝奪孩子學習趣味的主要原因,除了自身文化素養差,還在于不知教育為何物。他們往往受社會風氣影響,認為讀書等同于“刻苦”,“勤奮”等同于“不休息”,任何與做題做試卷無關的事都不是“學習”。部分學生厭學,和家庭提出的過高目標也有關。關注一下以干擾學校教育為能事的“虎媽狼爸”們,就不難發現:這些用極端手段對待子女的家長,自身文明程度并不高,他們常把事業上的失落歸于中小學階段“不夠兇猛”,因而對考試成績不拔尖有種本能的恐懼。
帶著恐懼的情緒學習,不可能享受學習的趣味,更不可能有創造思維。為什么在學生的童年,就給他們灌輸功名利祿意識;甚至警告他們如果不勤奮刻苦,未來就得做牛馬一樣的苦力?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整個社會都在散布對“勞動”的恐懼?為什么要強調“利”而從學習中割裂“熱愛”?沒有熱愛的人生,沒有生命樂趣的人生,有什么價值?
誠然,人生應當盡可能地發展自我,兒童認知能力有限,學習不能僅僅憑興趣;隨著成長,他總得學一些“雖然無味但不能不學”的知識,去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而他憑著童年開始的學習經驗,能在看似平常的過程中逐漸發現趣味,于是有價值的學習出現了。在兒童學習的道路上,始終需要有智慧有恒心的人像燈一樣立在前方,這些引導者就是那些自身也是善于學習的人,有趣的人。
在學校,總得有些讓學生感到有趣的事。我在和小學生、中學生的談話中,能發現以教師本位觀察未必能知道的趣味:因為今天會有某門課,而任課老師每節課上都能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喜;和某班某同學是發小,課間跑去碰頭,擊掌一下,煩惱全消;因為某科的教師比較喜歡他,在走廊里遇上都會給他一個微笑……有趣的事那么多,何必要爭“第一”呢?
教師認為教學無趣,往往在于他做學生時已習慣于無趣的學習,教學在他,是謀生的飯碗,而非有趣的冒險。把教師工作說成是“奉獻”“犧牲”,是對教育的曲解,對職業的誤識。社會把教育庸俗化,教育庸俗化的“成功學”又在影響教師的教學觀,平庸教師的課堂培養出的人群又在構建著平庸的社會,繼而把教師工作尊為“蠟燭式”“春蠶式”“園丁式”,如此何來趣味?學校教育中,最常見的是缺乏智慧的課堂:按部就班的、一成不變的教學計劃,平單調乏味的照本宣科,沒有靈動激情的表達,沒有真正地尊重學生的思考力,等等。學生在這樣的課堂,怎么可能把學習當作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