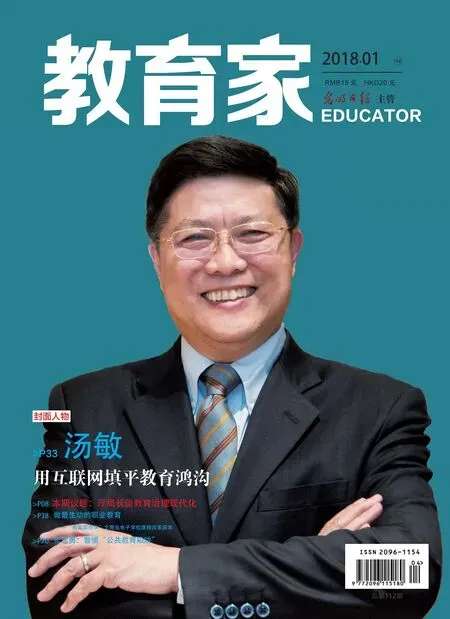我為學生劃“邊界”
劉 宇 / 四川省成都市東城根街小學
在班級管理中,我們常遇到這樣的情景——
情景一:小朋友們七嘴八舌跑到辦公室告狀,說某位小朋友不經過允許動他人的東西。當你去問這個孩子為什么動別人的東西時,他很可能睜著大眼睛,一臉茫然。
情景二:老師不在教室,教室里炸開了鍋,孩子們肆無忌憚地高聲喧嘩。直到老師走進教室,教室才歸于安靜。
這些情景觸發了我的思考:在一個班集體中,我們要帶給孩子們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集體榮譽感嗎?這對于孩子來說似乎太遙遠了。我以為應該讓他們懂得人與人相處的邊界。
什么是邊界?簡而言之,我是我,你是你。這意味著,我們是不同的個體,會有交集,也有彼此獨立的部分。我們應該尊重這個獨立的存在,不隨意侵入,這就是“邊界”。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把傳統中國社會的格局比作石頭擲在水面上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一個多圈水輪的中心,水輪距離石子的遠近好似人與人之間的親疏。因為在中國社會里,人際的親疏遠比邊界要重要。
可是從人的發展來說,孩子從萌生個人意識開始(大概2歲前后),就應該引導他建立邊界感,這是人自我意識發展的重要一步。邊界感能讓孩子充分明白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也不是我的——這是建立邊界感的基礎。只有孩子的邊界獲得了尊重,他才知道去遵守規則,建立秩序。
同理,在班級中,只有每一個孩子的邊界建立清楚,班級才可能形成大家都愿意去遵守和執行的規則,并形成秩序。而這樣的秩序能讓孩子們體會到集體的發展和變化帶來的利益。
幫助孩子建立邊界
達成對獨立空間的共識。雖然教室是公共空間,但是我們有必要引導孩子們確認他們各自在教室中的獨立空間。獨立空間首先保證了在班級中孩子不被他人打擾的可能。
孩子初入學時,我會帶著孩子們討論哪些是班級中的獨立空間。讓孩子們認識到,課桌是自己的獨立空間,老師和同學是不可以隨意打擾這個空間內的人做事的(上課違反規則除外);講桌是老師的獨立空間,老師批改作業時不能靠講桌太近,需要有一個安全距離;當班級的閱讀區和情緒調整區有人時,同學是不可以強行再加入其中的,否則會打擾別人。

教室中獨立空間的建立,讓孩子們透過自身的體驗清楚地在生活中界定“我的空間”“你的空間”,體會了“邊界”一詞的含義。
用外顯的設計幫助獨立空間的建立。邊界的建立,不僅需要孩子的體驗,還需要外部環境的促進。為了保證獨立空間的存在,我們在班級文化建設中設置了“一米線”,并把“一米線”貼在地面和墻面。
吃飯時,排隊舀飯的同學需要站在一米線外等待前一位同學舀飯;老師面批學生作業時,等待的同學要站在一米線外,保證不打擾“一米線”內老師和正在批改作業同學的交流。
為了避免前后左右的課桌擺放侵占他人的空間,我們又設置了班級座位對照標志,孩子們通過對照這些標志就能清晰對自己的空間進行判斷和調整。
有了這種外顯標志的,在班級中如果有同學想要占用更多的空間時,前后的同學就會指指標志說:“嗨,你超過‘一米線’了。”這時,盡管這個孩子不情愿,但是他會退到“一米線”外。
尊重孩子的世界
武志紅先生在《如何毀掉一個孩子?〈黑鏡〉的答案是保護Ta》中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教育需要確定邊界;以“為你好”為出發點而無視邊界,會毀掉孩子;與其自以為是地控制另一個人的人生,不如選擇去相信孩子,相信他們有能力自己長大。對此,我深以為然。在班級中,我們需要給予他們犯錯的權利,更要賦予他們長大的機會。
允許孩子試錯。沒有哪一個孩子不犯錯誤。試錯,才能讓孩子有機會學會獨立,在家不依附于家長,在學校不依附于老師,成長為真正的自我。
有一天,一個孩子對我說:“劉老師,可可吃樹葉啦!”“哦,好的。我知道了。”那個孩子見我一臉平靜又強調了一次:“她在吃樹葉!”“我知道了,乖乖。為什么不可以呢?”“可是她會肚子痛啊!”“也許。但是她不吃怎么會知道不能這樣呢?”當我去問吃樹葉的可可感覺怎樣時,可可說很不好吃,嘴里澀澀的,樹葉的味道不像故事中小熊說的那樣嚼著“那么好”。
貝貝一年級下期時突發奇想,要用奶瓶喝水。媽媽覺得很丟人,于是告訴我,希望我勸勸貝貝。我對貝媽說:“就讓她試試吧。試了就知道該用還是不該用了。”結果第二天,貝貝真的帶來了奶瓶。班上的同學哈哈大笑,貝貝覺得很尷尬。我問她奶瓶喝水方便不?她說一點也不方便,從奶嘴流出來很慢,不能喝個痛快。我問她明天還帶奶瓶不?她說,堅決不帶,太丟人。
有時我們會發現,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總有人“干著急”,替別人擔心,替別人覺得丟人。我認為,這就是超越了邊界。“為什么不可以?”“那就試試吧!”看似是放任,但是我們只要保證不傷害自己,不傷害他人,就不放讓他試一試,而只有當孩子真正經歷了,他才會“吃一塹長一智”。
大空間小主人。童年時的我們總想做很多事。而成年的我們總會忘記自己怎樣長大,忘記曾經那個小小的自己有多盼望能榮耀地站在班級中為大家服務。
在我們的班級里,我和孩子們一起為教室劃分區域,每一個空間和時間都有不同的管理者,班里的孩子人人需要為班級服務,人人都是教室里的小主人。孩子們通過自主申報,最終成為負責區域管理的小主人。管理的空間大到清潔區,小到一個儲物盒、一個開關、一檔書架、一個角落……這些在大人眼中看似毫不起眼的空間,對孩子來說卻是很大的責任。孩子們非常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工作,他們鄭重地寫下作為管理員的承諾,也寫下對同學的溫馨提醒。而老師在班級中的作用則是監督、促進、支持每一個小主人的工作。
推動學生的發展
我注意到,因為懂得了邊界,孩子們在秩序和規則方面有了令人感動的進步:下樓參加大課間鍛煉時,看到一年級的小朋友集合排隊,他們會停下腳步讓弟弟妹妹先走;參加集體朝會時,為了不擋住身后的同學看班級展示,他們會輕輕蹲下身來;班級存錢罐里有一張放了整整一年的一元人民幣,卻沒有一個孩子把它占為己有……邊界的確立為孩子們帶來的是秩序,每天他們很清楚參與班級管理和服務的時間。
良好的秩序感推動著班級規則的形成。在不同的時間,他們會在成長中形成新的規則。我現在所帶班級的孩子們在升入二年級后又形成了新的規則:
出入班級路線:前門進,后門出;喝盒裝牛奶:喝光、壓扁、取吸管;打掃教室:合作、安靜、快速……
當然,盡管孩子們有了很大的進步和變化,但是,他們依然會有越過邊界的時候,也會有不遵守秩序的時候。
可是,更多的日子,他們會把“一米線”記在心中。隨著年齡的長大,他們會發現,“邊界”并不是硬邦邦的,非此即彼,它也是有彈性的,它所帶來的并非淡漠或者隔離,而是一種更加深刻的自由,與親人、和師長、和同學朋友,有了這個邊界,人際關系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