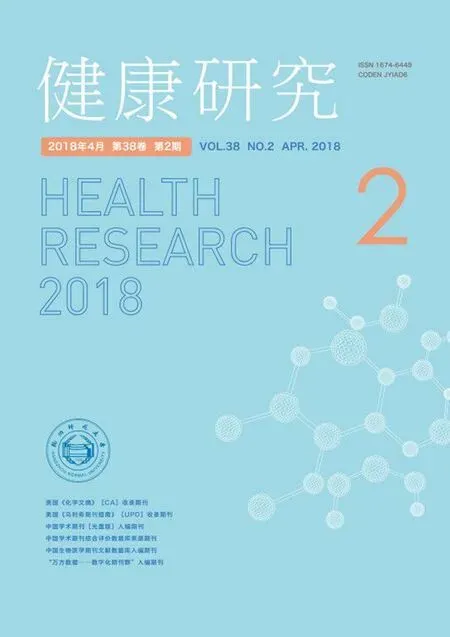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研究進展及展望
童鶯歌,柴 玲,劉苗苗,陳佳佳,楊 磊
(杭州師范大學 醫學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1]將健身在慢性病防治上的積極作用及開展工間健身活動提到了新的國家戰略高度。慢性疼痛作為高發病率的常見慢性病,且多數發病與職業因素有關,不僅危害勞動力,還引發家庭和社會問題,是開展工作場所健康促進的重點關注疾病。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慢性疼痛工作場所健康促進的關注尚少。本文從我國員工慢性疼痛發病概況,開展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積極意義,國內外研究現狀等方面進行論述,并提出我國未來研究和實踐的方向,為實施《“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相關內容提供參考。
1 慢性疼痛的發病概況及對勞動力的危害
根據《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慢性病主要包括心腦血管疾病、癌癥、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和口腔疾病,以及內分泌、腎臟、骨骼、神經等疾病[2]。國際疼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Pain,IASP)將慢性疼痛定義為“持續或間歇性地持續3個月以上的疼痛”[3],屬于慢性病范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全球范圍內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持續性慢性疼痛的發病率約為23%[4]。在我國對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抽樣調查表明,慢性疼痛的患病率高達52.99%[3]。職業人群中慢性疼痛發病率更高,如護士人群下腰痛的發病率為66.8%[5]。頸椎病或頸部退行性病變的發病率在中青年公務員組中高達50.36%,在其他中青年職業組中也高達46.35%[6]。慢性疼痛中最常見的為慢性肌肉骨骼性疼痛(chronic musculoskeletal pain, CMP),指發生在肌肉骨骼系統的慢性疼痛,多為反復拉傷、過度使用以及工作相關的肌肉骨骼疾病所致,主要表現為關節炎性疼痛(主要包括類風濕性關節炎、骨關節炎、纖維肌瘤等)及脊柱相關性疼痛(如頸部和背部疼痛)等[7]。在機械行業中,CMP的患病率高達64%。WHO指出,CMP已成為全球巨大的疾病負擔[8]。
員工指我國企事業、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勞動者和工作人員,慢性疼痛在員工群體中高發,已成突出的社會問題。不恰當的工作方式是員工慢性疼痛發病的主要原因。37%的慢性下腰痛由職業因素所致,與長期重體力勞動、較長時間站立、高強度訓練或長期頻繁彎腰或不良姿勢等因素相關[9]。CMP中的下腰痛、頸部疼痛被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研究列為第一、第四大致殘病因[10]。慢性疼痛是工作缺勤常見的原因,約29%的患者因為慢性疼痛而更換工作,約19%的員工因慢性疼痛失去工作[4]。慢性疼痛不僅對員工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嚴重的困擾,它導致的長期病假、提早退休及社會福利賠償金增加等[11]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員工的健康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都極為重要。
2 開展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積極意義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工作場所指覆蓋工人因工作而需在場或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下的一切地點。工間健身是工作場所健康促進(workplace health promotion, WHP)的重要內容,指采用多學科、多部門、多種干預手段,通過綜合性干預措施,促進員工身體鍛煉的開展及持續進行,以增進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健康危險因素、降低傷病及缺勤率,從而達到促進職工、家屬及其社區居民安全和健康,提高生活質量的目的[12]。
在慢性疼痛員工中開展工間健身屬于二級預防范疇。WHO指出:在工作場所開展二級預防,由于針對的是更少、更確定的人群,可能會非常有效,且具有較好的成本效益[13]。工作場所中的社會支持網絡可以協助慢性疼痛員工改善工作方式(如采取更科學的坐姿、站姿)以及完善工作設備(如提供重物搬運設備);同時企業內的健康專業人員可以參與到健康促進計劃中,通過專業化有針對性地健康指導,改善員工的健康,提升社區的整體健康水平。
根據《全民健康素養促進行動計劃(2014—2020年)》,至2020年我國將建成健康促進企業、健康促進機關、健康促進醫院、健康促進學校各1400個[14];《“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1]將健身在慢性病防治上的積極作用及開展工作場所健身活動提到了新的國家戰略高度,上述兩個文件為在慢性疼痛員工中普及開展工間健身提供了政策支持。針對慢性疼痛員工的工間健身,有著易組織、防控目的明確、預期效果明顯等優勢,可作為我國降低在職員工慢性疼痛發病率的突破口。
3 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研究現狀
3.1 國外研究現狀 WHO將骨骼肌肉系統疾病,如頸腰、背部疼痛等,列為適合在工作場所進行二級預防的疾病[15]。在慢性疼痛中,國外機構開展的工作場所健康促進實踐主要針對肌肉骨骼疼痛,和WHO的指導建議相符[15]。其中有關下腰痛員工工間健身的實踐較多,項目的組織形式多樣化,有單純的鍛煉干預,或在其基礎上加健康教育及個案管理等[16],都取得了積極效果。
國外有關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4個方面:①開展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能顯著緩解疼痛并提高生活質量。如隨機對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發現,慢性下腰痛員工在辦公室開展全身振動操能明顯改善身體功能和生活質量[17]。另一項RCT將200名慢性疼痛患者分別安排在工作場所和居家進行每周5次,每次10分鐘,共持續10周的身體鍛煉干預,結果表明工間健身比居家鍛煉能更有效地減輕肌肉骨骼疼痛,增加肌肉力量,減少鎮痛藥的使用量(P<0.05)[18]。其他研究也發現身體鍛煉,尤其是力量鍛煉可以改善肌肉骨骼性疼痛和身體適應性[19]。②慢性疼痛員工進行工間健身能促進其工作能力的提高。如一項RCT研究[20]通過在兩個工業區對前臂疼痛的工業技術人員進行每周3次共20周的肩部、頸部和手臂部位的特定阻力訓練(訓練組),對照組進行一般的身體活動,結果表明,訓練組較對照組疼痛強度降低更多,且工作殘疾改善更多。此外,研究發現工間健身對減少下腰痛員工的工作缺勤和醫療支出亦有積極作用[21]。③慢性疼痛員工開展工間健身能明顯改善其心理狀態。如一項研究[22]通過對比居家鍛煉和工間健身兩組人群發現,工間健身組可更顯著提高工作活力和疼痛控制力。其他研究也發現,工間健身對慢性疼痛員工的心理健康、人際社交等也有積極促進作用,可改善其焦慮狀態,提高團隊合作能力,促進工作活力等[23]。④探討影響慢性疼痛員工鍛煉行為的心理變量和認知因素。如較多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是影響鍛煉行為的主要因素[24-25],良好的社會支持能提高慢性腰背痛患者的自我效能[26]。此外,研究表明對疾病的認知直接影響慢性疼痛人群的鍛煉行為。如慢性下腰痛患者因缺乏運動鍛煉的意識、對運動鍛煉的長遠利益認識不足、堅持鍛煉的信心不強等,無法堅持鍛煉[27]。
3.2 我國研究現狀 雖然我國慢性疼痛患者開展工間健身的狀況不容樂觀,但我國關于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研究甚少,且主要針對辦公室員工。如有研究者設計了靜力性和動力性拉伸兩套脊柱保健健身操,并應用于銀行辦公人員,結果顯示動力組和靜力組組內干預前后疼痛評分均存在顯著性差異,研究對象的疼痛狀態得到改善[28]。此外,還有研究者突破傳統工間操單一的編排模式,創編了辦公室工間操成套動作,并采用“抗阻”和“有氧”相結合的有氧負重方式應用于 60 名辦公室工作人員,結果顯示,95% 被試者通過該套操的鍛煉,緩解了頸椎部、肩部疼痛; 70% 以上被試者的精神、心理狀態等均得到了明顯改善[29]。
4 展望
4.1 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研究展望 當前研究較多為慢性疼痛員工的力量訓練,但有關鍛煉方式、運動量、工間健身組織方式及健身方案的研究較少。雖然有文獻報道,太極拳能顯著緩解膝骨性關節炎患者的疼痛[30],但太極拳、五禽戲等中國傳統身體活動形式用于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效果尚不甚清楚。《“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出,應大力發展中醫非藥物療法,使其在常見病、多發病和慢性病防治中發揮獨特作用,發展中醫特色康復服務[1]。太極拳、五禽戲等融合了中醫養生之道,建議我國學者可在中國傳統鍛煉形式在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運用上展開探討。此外,后續研究可關注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運動處方庫(包括運動方式、類型、持續時間、頻度等方面)的建立。再者,CMP還是Ⅱ型糖尿病、慢性腎病等慢性病的常見伴發疾病,未來研究可關注慢性疼痛伴發其他慢性疾病人群的工間健身方案及效果。
國內外尚缺乏對慢性疼痛員工堅持工間健身行為機制的深入研究。鍛煉行為機制指影響鍛煉行為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導致鍛煉行為激發、堅持(退出)、恢復的復雜系統,是對鍛煉現象的因果性解釋[24]。在鍛煉行為中,鍛煉堅持(exercise adherence)是有效改善健康的前提,其定義為:長期(>3個月)自覺參加規律性鍛煉(每周鍛煉頻度≥3次,每次鍛煉時間≥30分鐘)的行為[24]。明確慢性疼痛員工鍛煉堅持行為機制,是促進工間健身持續長期開展的基礎。現有研究多針對鍛煉行為的激發,但如何使鍛煉行為持續的心理機制仍不明確。因而,學術界未來可更深入地研究慢性疼痛員工持續及堅持開展工間健身的心理機制。
國外多項研究表明采取經濟上支持措施可以促進員工堅持開展工間健身[31-32]。我國已開展的研究多針對院校教職工、公務員、工礦從業人員等整個員工群體[33-35],鮮見針對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影響因素的研究。建議我國學者可在影響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開展及持續進行的社會人口學因素(如性別、年齡、文化、職業背景、收入、階層等)、企事業單位的場地設施、經濟激勵措施、文化及制度等方面展開調查。
4.2 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實踐展望 進入21世紀以來,WHP在全球范圍內呈現出下列兩種發展趨勢。第一種趨勢為將員工健康的保護和促進措施相結合。在健康促進上,專家側重于鼓勵員工改變不良行為,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在健康保護上,專家希望通過創造安全的工作條件和限制員工的危險暴露來達到保護健康的目的[36]。第二種趨勢為強調對工作場所健康促進和健康保護問責。具體而言,是確定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雇主對員工健康的投資,并對生產力、缺勤率、工作表現等進行監測[36]。
職業因素,包括不恰當的工作方式和不良工作姿勢等因素是員工慢性疼痛發病的主要原因。而高發的慢性疼痛又致頻發的工作缺勤及社會生產力嚴重受損。作為WHP的重要內容,在慢性疼痛員工中開展工間健身,當工作條件有利于員工健康,能使企業的生產力更高。根據WHP在21世紀的發展趨勢,我國企事業單位在開展慢性疼痛員工工間健身的實踐時,可與其他的員工健康保護和促進措施相結合。如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避免員工反復采取不良工作姿勢;向員工開展防范慢性疼痛的健康宣教,使其有機會獲得健康相關信息。此外,建議疾控部門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參與對企事業單位對員工的健康保護和健康促進問責,定期對員工慢性疼痛的發病情況、因疼痛所致的工作缺勤率進行抽查,將工作場所健康促進作為我國公共衛生的重點工作。
參考文獻:
[1]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發布(附全文)[EB/OL].(2016-10-26)[2017-12-05].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6-10/25/c_1119786029.htm.
[2]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的通知[EB/OL].(2017-01-22)[2018-01-0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2/14/content_5167886.htm.
[3] 安傳勤, 劉躍暉. 慢性疼痛病人生活質量的研究進展[J]. 護理研究, 2017, 31(3):259-262.
[4] 童鶯歌,田素明.疼痛護理學[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7:143-145.
[5] 王雅琴, 寧寧, 楊慧,等.四川省三級甲等綜合醫院骨科護士腰痛特征的調查研究[J].中華護理雜志, 2013, 48(5):444-446.
[6] 王立公, 常雙超.廣州市中青年不同人群頸椎病發病率的調查研究[J].中國療養醫學, 2010, 19(5):473-474.
[7] Stanos SP. Topical Ag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Musculoskeletal Pain[J]. Journal of Pain & Symptom Management, 2007, 33(3):342-355.
[8] Kamper SJ, Henschke N, Hestbaek L,etal. Musculoskeletal pai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Brazilian Journal of Physical Therapy, 2016, 20(3):275-284.
[9] 李亨, 鄭軍.慢性下腰痛臨床病因學研究[J]. 亞太傳統醫藥, 2016, 12(20):49-51.
[10] Haukka E, Ojaj?rvi A, Kaila-Kangas L,etal. Protective determinants of sickness absence among employees with multisite pain:a 7-year follow-up[J]. Pain, 2017,158(2):220-229.
[11] Dsc RA, Sheena Derry MA, Taylor RS,etal.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dequately Managed Chronic Non‐Cancer Pain and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J]. Pain Practice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World Institute of Pain, 2014, 14(1):79.
[12] 李霜, 張巧耘.工作場所健康促進理論與實踐[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6:5.
[13] K Proper,W Van Mechelen.Effectiveness and economic impact of worksite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y die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8[EB/OL].(2016-10-11)[2018-03-09].http://www.who.int/Diet physical activity/Proper_K.pdf.
[14] 國家衛生計生委關于印發全民健康素養促進行動規劃(2014-2020 年)的通知[EB/OL].(2014-05-09)[2017-01-05].http://www.nhfpc.gov.cn/xcs/s3581/201405/218e14e7aee6493bb ca74acfd9bad20d.shtm.
[15] K Proper,W Van Mechelen.Effectiveness and economic impact of worksite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y die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8[EB/OL].(2009-01-20)[2018-03-09].http://www.who.int/Diet physical activity/Proper_K.pdf.
[16] Tveito TH, Hysing M, Eriksen HR. Low back pain interventions at the workplac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Occupational Medicine, 2004, 54(1):3-13.
[17] Kaeding TS, Karch A, Schwarz R,etal. 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as a workplace-based sports activity for employees with chronic low-back pain[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2017,27 (12):2027-2039.
[18] Jakobsen MD, Sundstrup E, Brandt M,etal. Effect of workplace- versus home-based physical exercise on musculoskeletal pain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2015, 41(2):153.
[19] Van ED, Munhall C, Irvin E,etal. Effectiveness of workplace interventions in the prevention of upper extremity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nd symptoms: an update of the evidence.[J]. Occupational & Environmental Medicine, 2016, 73(1):62-70.
[20] Andersen LL, Jakobsen MD, Pedersen MT,etal. Effect of specific resistance training on forearm pain and work disability in industrial technicians: cluster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Bmj Open, 2012, 2(1):e000412.
[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hysical activity. Fact sheet 385[EB/OL].(2014-03-28)[2018-02-03].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85/en/2014.
[22] Jakobsen MD, Sundstrup E, Brandt M,etal. Psychosocial benefits of workplace physical exercise: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Bmc Public Health, 2017, 17(1):798.
[23] Andersen, Lars L, Persson,etal.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workplace physical exercise among workers with chronic pain[J]. Medicine, 2017, 96(1):e5709.
[24] 陳善平.體育行為認知決策理論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4.
[25] 王深, 熊猛, 周鳳秀. 鍛煉團體領導行為對成員鍛煉堅持性的影響:鍛煉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J]. 武漢體育學院學報, 2014, 48(11):67-73.
[26] 杜世正, 胡玲莉, 柏亞妹,等.社區慢性腰背痛患者自我效能水平及其影響因素[J].解放軍護理雜志, 2016, 33(12):1-7.
[27] 馬香, 張美芬, 張利峰.慢性下腰痛患者自我管理行為與疾病知識的相關性研究[J].護理學報, 2016, 23(15):42-45.
[28] 劉哲. 伏案型人群脊柱常見病癥的運動干預研究[D]. 鄭州:河南大學, 2012.
[29] 江金澤, 鄭華玲, 王梨,等. 辦公室工間操的實驗研究[J]. 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 17(1):96-101.
[30] Field T. Knee osteoarthritis pain in the elderly can be reduced by massage therapy, yoga and tai chi: A review[J].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Clinical Practice, 2016, 22:87-92.
[31] Losina E, Smith SR, Usiskin IM,etal. Implementation of a workplace intervention using financial rewards to promote adherence to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a feasibility study[J]. Bmc Public Health, 2017, 17(1):921.
[32] Divisón Garrote JA, Escobar CC. Framing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increase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overweight and obese adults][J].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16, 164(6):385.
[33] 張倩. 河南省高校博士學位教師體育鍛煉現狀調查與分析[D]. 鄭州:河南大學, 2016.
[34] 楊飛. 湖北省宜昌市公務員體育鍛煉現狀調查與分析[D]. 武漢:華中師范大學, 2016.
[35] 王澤波. 山西省煤礦企業職工體育發展現狀與對策研究[D]. 北京:首都體育學院, 2012.
[36] 顧沈兵.健康促進項目:從理論到實踐[M].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出版社, 2015: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