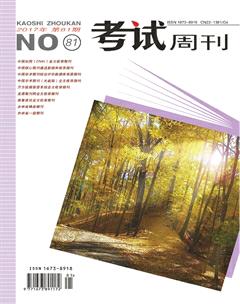論《三國演義》英譯本中比喻的審美補償
張曉紅??
摘要:《三國演義》是部傳世巨著,其中生動多姿的比喻形象是其藝術魅力恒久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浪潮中,如何能夠更好地在英譯過程中對原著的損失進行補償,在英譯本中再現其眾多比喻形象的審美價值?本文試圖應用審美補償理論對這一議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翻譯補償;審美補償;比喻形象
一、 引言
有翻譯,就會有翻譯損失。翻譯損失的存在,在翻譯活動進行之初就被譯者所認識,但是翻譯補償的概念直到20世紀末才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國內第一步全面系統介紹翻譯補償研究的專著是夏廷德于2006年出版的《翻譯補償研究》。他認為:“翻譯損失是指翻譯過程中信息、意義、語用功能、文化因素、審美形式及其功能的喪失。翻譯損失具有不可避免性。”(夏廷德,2006:3)“對上述各種因素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損失進行必要的補償不僅是理所當然的,也是譯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夏廷德,2006:6)而對于翻譯損失的補償,夏廷德也進行了分類,他認為補償分為兩個層面:語言學層面的補償和審美層面的補償。相比于語言學層面的補償,審美補償所受到的關注就更少了。
夏廷德在《翻譯補償研究》中提到文學翻譯必須盡可能再現原作的審美要素,但是,由于語言文化的差異,審美要素時常無法在目的語中直接再現,這就造成了審美層面的損失。導致審美損失的情況主要有三種:一,源語審美形式可以譯出,但功能難以保存,因而導致審美價值部分或全部喪失;二,源語審美形式可以譯出,但與目的語審美功能發生沖突而產生消極作用;三,源語審美形式不能譯出,因而喪失全部審美價值。既然有損失,就要盡量進行補償,那么典籍英譯過程中的比喻的審美損失都是什么形式的?又該怎么補償呢?
《三國演義》的英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進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審美要素也必然會在英譯過程中發生不可避免的損失。如何才能盡量彌補這種損失,如何最大化地在英譯本中展現其審美價值是譯者們孜孜以求的目標。根據夏廷德的審美要素損失分類,依據目前《三國演義》最流行的兩個全譯本的譯文,筆者對《三國演義》中的比喻在英譯過程中的審美損失如何進行補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二、 源語審美形式可以譯出,但功能難以保存,因而導致審美價值部分或全部喪失
1. (關羽)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第1回)
羅譯:He had...eyes sweeping sharply back like those of the crimson-faced phoenix, and brows like nestling silkworms.
鄧譯:He had eyes like a phoenixs and fine bushy eyebrows like silkworms.
上例中的“丹鳳眼”“臥蠶眉”皆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比喻形象。丹鳳眼指眼睛形狀極為細長、嫵媚,像中國傳說中的鳳凰的眼睛,通常指女人眼睛長得美。臥蠶眉指人的眉尾向上高揚,眉身呈現兩段,微彎,眉色烏亮富光澤,如蠶一般。臥蠶眉一般用來比喻男性英武。雖然此句中的比喻的形式在兩個英譯本中都保留了下來,但我們發現實際上,審美元素已經有一部分消失了。鳳凰本就是中國傳說中的神鳥,它的樣子本就是中國人虛構出來的,即使兩個譯本都保留了鳳凰的形象,即使英語讀者注意到了鳳凰眼睛的形狀,但他們能領會phoenix的眼睛是很美的,這個隱含的信息嗎?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保留了蠶這個形象,修飾關羽的眉毛以后,盡管后面有追加的“相貌堂堂,威風凜凜”,但是,對于現代英語讀者來說,把像鳳一樣的眼睛,和像蠶一樣的眉毛和美男子、和威風凜凜的形象聯系起來,恐怕很難做到。汪榕培老先生非常支持直譯,在譯文盡量保留原文的形象:“直譯法可以保留原文濃厚鮮明的民族色彩,再現原文的形象,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所以翻譯時能直譯應盡量直譯。”(汪榕培,王宏,2009:263)但從上述的討論不難看出,文化意象的傳播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保留濃厚鮮明的民族色彩的一個風險就是,這種色彩可能并不會被完全理解和接受。
2. 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第43回)
羅譯:clearly a case of ‘a spent arrow unable to pierce fine silk.
鄧譯: This was the final kick of the crossbow spring, and the bolt was not swift enough to penetrate even the thin silken vesture of Lu.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是個至今生命力仍非常強的表達。縞,是一種白色的薄絹,以古時魯國所產為最薄最細,故稱魯縞。這個名句意思是:即使是強弓射出的利箭,射到極遠的地方,力量已盡時,就連極薄的魯縞也射不穿了。羅譯本根本沒考慮保留這一比喻形象,直接翻譯了它的含義,所以“魯縞”這一審美元素在羅譯本中永遠消失了。而鄧譯本勉強留著了部分形式,譯作:“不能穿透魯的絲織品。”但“Lu”是什么?是一個人?是一個品牌?還是一種工藝?這一細節也無從展現。筆者認為,實際上鄧譯本只要改動一個詞就很好了,比如說:“was not enough to penetrate even the thin silken vesture produced in Lu.”字數并沒有增加,沒有給讀者增加閱讀的負擔。但改動過的譯本在傳達審美價值方面就更加準確和完整了。
3. 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第43回)
羅譯:...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outhland and Jingzhou, a tripodal balance of power will come into being in the empire.endprint
鄧譯:Cao Cao will certainly be broken, and he must retire northwards.Then your country and Jingzhou will be strong, and the tripod will be firmly established.
“鼎”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器物,有三根立腿,用以祭祀,日用,擺設都有,是非常常見且重要的文化元素,“鼎”也代表著權力,鼎足之勢象征三方政權并立、互相對峙。但我們發現在兩個全譯本中,這一審美元素都沒能保留下來。兩位譯者都用了“tripod”這個英語單詞來表達“鼎足”,但“tripod”最容易讓英語讀者聯想到的就是拍照用的三腳架,這根本無法和莊重、大氣、政權聯系起來,所以,“鼎”這個審美元素在兩個譯本中都損失了。對于這種中國特有事物的審美元素在英譯過程中損失的情形,基本上沒有什么特別好的補償辦法。根據英譯本面對的讀者不同,以及定位的不同,也許可以適當考慮加“鼎”的插圖來幫助理解,但即使這樣,其傳達的內在含義也是無法很快就被讀者領會到的。
三、 源語審美形式可以譯出,但與目的語審美功能發生沖突而產生消極作用
1. 策見其人(華佗),童顏鶴發,飄然有出世之姿。(第15回)
羅譯:Sun C observed the man: young of face with hair like the feathers of a crane.He had the light and easy manner of one who no longer belongs to this world.
鄧譯:Shortly the famous HuaTuo arrived, a man with the complexion of a youth and a snowy beard.He looked more like a saint who had passed the gates of this life.
“童顏鶴發”在中國古文中形容老人年紀大了,雖然頭發白了,但相貌依然年輕。“鶴”對于中國人來說非常熟悉,對于“鶴”所傳達的意義也非常了解。在中國古代,人們常把“松”“鶴”“梅花鹿”這三種事物放在一起表“長壽”,表“神仙”。而在英語文化里,“鶴”實際上被認為是一種丑陋的動物,(陳德彰,1999:361)不但與“神”“上帝”沒有任何聯系,而且,也許還會引起讀者的反感。“鶴”這一審美元素的形式固然保留了下來,但其產生的功能卻可能相反。
“在全球化的語境中,認真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價值理念,努力發現彼此不同的思維方式及其存在的分歧,在不損害中國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適的方式來解讀……”(羅選民,楊文地,2012)為了消除“鶴”可能給英語讀者造成的反感,兩個全譯本作者也都根據下文對這一審美元素進行了追加解釋,鄧譯本還用了“saint”一詞,譯作“圣人”“圣徒”來幫助英語讀者接受這一審美形象。應該說,這已經是很好的挽救方式了。但即使如此,由于文化意識根深蒂固,很難改變,筆者建議這種會在目的語中引起審美沖突的比喻形象可以適當放棄。
2. (劉備)面如冠玉,唇若涂脂(第1回)
羅譯:His face was flawless as jade, and his lips like dabs of rouge.
鄧譯:His complexion was as clear as jade, and he had rich red lips.
“面如冠玉”“唇若涂脂”都是中國古文中形容男子的相貌長得漂亮。即使現代中國人中仍有人接受這個標準,但是對于英語讀者來說,恐怕難以接受。當然,歐美歷史上也有過男人戴假發、涂胭脂、涂粉的時期,但對于現代的英語讀者來說,這一形象一時間恐怕還是難以理解。美的標準在變化,不但在中國,在全世界都在變化,不但在文學,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也都不斷發生著變化。德國著名文藝批評家和美學家萊辛曾斷定:“在古希臘人來看,美是造型藝術的最高法律。”(萊辛,2016:15)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拉奧孔雕像看起來并不是非常痛苦,因為如果真實地表現當時承受的痛苦的話,那雕像就會看起來丑陋,而這是古代雕塑家不能容忍的。但是,文學、藝術發展到今天,人們早已摒棄了這一觀點,真實、自然被認為是最美的。對于秉承著這樣的審美思想的現代英語讀者來說,“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的審美元素不但不會引起他們美的聯想,恐怕只會覺得難以接受。“譯文的語體既要考慮其歷史性特征又要側重當代譯語讀者對譯文的可接受性。”(王宏,2012)上述譯文中的審美形式雖然得以保留,但其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所以,同上例,筆者認為可以放棄這一比喻形象而直接譯出其真正想表達的含義就好。
四、 源語審美形式不能譯出,因而喪失全部審美價值
(張飛)豹頭環眼,燕頜虎須,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第1回)
羅譯:a man eight spans tall, with a blunt head like a panthers, huge round eyes, a swallows heavy jowls, a tigers whiskers, a thunderous voice, and a stance like a dashing horse.
鄧譯:a man about his own height, with a bullet head like a leopards, large eyes, a swallow pointed chin, and whiskers like a tigers.He spoke in a loud bass voice and looked as irresistible as a dashing horse.endprint
由于中英文字體系的不同,在典籍英譯的過程中,詩歌和文字內容最常出現由于審美形式不能譯出,因而喪失全部審美價值的情形,由于漢字的詞形組合、韻律、方言都不同于英語,這就導致在這些方面的審美元素根本無法在英語中找到相匹配的事物,因此,也就根本無法體現,那么這些審美元素在英譯過程中也就損失掉了。幸運的是,在比喻的英譯過程中遇到這種損失的機率并不大。比喻的形式基本上都可以譯出,只是其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傳遞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本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多個比喻形象并列,且都是四字的短語,形成了對仗工整、簡潔明快且很有氣勢的排比句式。一旦涉及了文字、句式,比喻的形式反而不是問題了。兩個英譯本都很自然地保留了原比喻的審美元素,“豹”“燕”“虎”“驚雷”“奔馬”所有這些原著的審美元素無一遺漏,都得到了具體的表現。但問題是,原著的那種氣勢卻損失了。不論是羅譯本還是鄧譯本,為了完整地表現原文的審美元素,都不得不使用大量的具體描述來表達,因此形成的譯文不可避免地拖沓、冗長,比喻的審美形式雖然譯出來了,但其審美價值卻全部喪失了。而由于上面討論過的原因,這種文字形式方面的審美損失幾乎沒有辦法得到補償。
五、 結論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不難發現典籍英譯中比喻的審美補償與其他文學形式的審美補償比起來,有其自身的優點,也有其無法回避的弱點,即比喻的審美補償更加依賴于文化的傳播和滲透,中國特有的文化事物和概念,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才能逐漸為英語世界的讀者所接受。這也正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終目的和愿景,而在這個過程中,典籍英譯中比喻的審美補償問題將會一直是一個值得譯者不斷思索,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完善的課題。
參考文獻:
[1] 夏廷德.翻譯補償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2] 汪榕培,王宏.中國典籍英譯[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
[3] 陳德彰.漢英動物詞語的文化內涵[A].郭建中主編 文化與翻譯[C].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
[4] 羅選民,楊文地.文化自覺與典籍英譯[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2(5):63-66.
[5] 萊辛.朱光潛譯.拉奧孔[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6] 王宏.中國典籍英譯:成績、問題與對策[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2(3):9-14.
作者簡介:張曉紅,江蘇省揚州市,南京郵電大學通達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