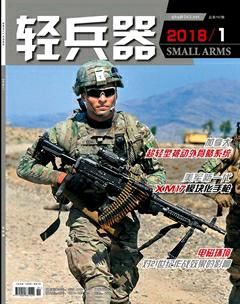一組鴉片戰(zhàn)爭的文物史料
陳傳生+張翼
“一口通商”的黃埔港
兩幅佚名中國畫家的油畫,描繪了19世紀廣州黃埔港百舸爭流千帆滿江的繁盛景象。據(jù)史料記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閉關自守的清政府撤消了江、浙、閩三處海關,只保留粵海關,使廣州成為中國惟一的對外貿(mào)易口岸。清政府還規(guī)定:“凡載洋貨入口之外國商船,不得沿江停泊,必須下錨于黃埔。”黃埔是廣州以南的一個小島,歐洲商人稱之為“河南島”,與廣州相距10余英里,所有來廣州貿(mào)易的歐洲商船都必須在黃埔水域錨泊,然后到島上辦理掛號、報關、繳納稅費等事宜,船員和貨物再由中方的船只運送上岸。展出的兩幅油畫,其中一幅描繪的是離開“河南島”駛進珠江的船只,視角是從廣州珠江岸邊歐洲人開設的工廠面向“河南島”看到的景象;另一幅視角相反,描繪的是珠江中的船只逐漸駛離黃埔港的景象。油畫下面兩段展板文字,內(nèi)容分別是:“中國人非常機智而勤勞”(出自理查德·沃特《環(huán)球旅行》);“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出自1793年乾隆皇帝致英王喬治三世的信)
實行“一口通商”以后,前來廣州貿(mào)易的歐洲商船以英國商船為最多。在1834年以前,由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得了英國對華貿(mào)易的壟斷權,所有來華貿(mào)易的英國商船都是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博物館展出了一幅英國商船油畫和一個按照1:48比例制作的船舶模型,介紹了東印度公司遠洋貿(mào)易使用的布萊克沃三桅帆船。該船由位于泰晤士河畔布萊克沃的格林和威格拉姆(Green and Wigram)家族船廠制造,船長46m,寬7.5m,排水量900噸,是該船廠生產(chǎn)的最后一種型號的東印度貿(mào)易帆船,在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前,這種帆船在英國遠洋貿(mào)易船舶市場幾乎占有絕對的壟斷地位。
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商船是滑鐵盧號,銅版畫《中國港口》描繪了該船在黃埔港錨地停泊的景象。該船排水量1335噸,在1816~1832年間曾先后9次往返于歐亞海域進行商貿(mào)運輸。這幅畫是倫敦的一位畫家根據(jù)英國人約翰·哈金斯的記載于1835年繪制的,從畫面上可以看到水面停泊的眾多歐洲商船和對岸的山川景物以及豐富的人文景觀,滑鐵盧號體積龐大,船上懸掛著東印度公司旗幟,船邊有中國的小船照料,給人以鶴立雞群之感。這幅畫在國內(nèi)有關近代中英海上貿(mào)易和鴉片戰(zhàn)爭的專題作品中被經(jīng)常引用。
一艘中式武裝快艇模型,實際船長70英尺(21.3m),是清政府在珠江三角洲水域用于查緝走私、打擊海盜的武裝帆船,船上裝備6支帶有旋轉座架的火槍和8面盾牌。
中英貿(mào)易摩擦
中英貿(mào)易摩擦最初表現(xiàn)在英國對清政府制定的嚴苛貿(mào)易規(guī)則的不滿。在乾隆皇帝頒布“一口通商”令后,清王朝便以一種封閉甚至敵視的方式對待來到中國的洋人,清政府對洋人在中國的生活和貿(mào)易,甚至言行都做了嚴苛規(guī)定,如“番婦不得進城,洋人不準坐轎不得學漢語”等等。為防止洋人海員喝酒鬧事,還規(guī)定海員平時不得進入廣州城,只能住在黃埔島上,每月只有固定的幾天可以進城在指定區(qū)域內(nèi)活動,結果這條規(guī)定引來了一場糾紛。1807年,去廣州城度假的東印度公司海王星號商船船員在十三行碼頭酒后聚眾斗毆,一名中國人在斗毆中喪生。為了找出元兇,廣州知府在廣州英國商館大廳對曾到廣州度假的52名水手進行調查審訊。這是西方人第一次作為被告出現(xiàn)在中國公堂。調查期間,清政府停止英國貿(mào)易2個月。一連幾天流于形式的審訊后,沒有一名水手承認參與了斗毆,最后官府選定一名表現(xiàn)最囂張的水手給予了輕微的處罰,一個嚴肅的命案最終玩笑般草草收場。博物館展出的一幅油畫記錄了這起所謂的“海王星號事件”,整個畫面內(nèi)容是法庭內(nèi)調查審訊的場景,畫中知名人物除了居于中間位置的廣州知府官員外,坐于庭上右側的是中國行商首領啟官(行商官名,以下同)潘振承、茂官盧觀恒、沛官伍秉鈞、水官潘長耀;坐在庭上左側的是5位重要的英國商人:羅伯特·羅爾斯、約翰·羅伯茨、托馬斯·帕特爾、威廉·巴姆斯頓和喬治·斯湯頓爵士。在這起事件中,由于中國行商茂官盧觀恒是海王星號的擔保人而遭到官府的巨額懲罰,承受了重大經(jīng)濟損失,這也充分反映了清政府的無能和吏治腐敗。
為了避免和減少中英貿(mào)易摩擦,1792年,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政府派遣外交官喬治·馬戛爾尼勛爵出使中國,欲通過談判建立公平的貿(mào)易關系,取得對英國更為有利的交易條件。為了表達誠意,還攜帶了天象儀、地球儀、高倍望遠鏡、鐘表、蒸汽機、遠洋戰(zhàn)艦模型等大量貴重禮物,希望給中國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但清政府對這些禮品并無興趣,馬戛爾尼最終無功而返。鴉片戰(zhàn)爭中,這些禮品有的作為戰(zhàn)利品又被帶回英國。博物館以“外交失敗”為題,展出了幾件當年英國使團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包括天文鐘、望遠鏡等,同時還展出了兩幅與此相關的畫作。其中一幅是1793年中國制作的織錦緙(ke)絲畫,畫面描繪的是英國使團在頤和園準備給中國皇帝送禮的場面,畫的右上角有乾隆皇帝的一首詩,內(nèi)容是:“御制紅毛英吉利國王差使臣馬戛爾尼等奉表貢至詩以志事:博都雅昔修職貢,英吉利今效藎誠。豎亥橫章輸近前,祖功宗德逮遙瀛。視如常卻心嘉篤,不貴異聽物詡精。懷遠薄來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除了這首乾隆皇帝的詩外,博物館對這幅畫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完全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畫面是畫作者根據(jù)道聽途說和憑空想象編造出來的,畫上的英國人穿的是16世紀歐洲人的服裝,抬的兩個天文設備疑似北京耶穌會天文臺的儀器等等,所有細節(jié)甚至地點都與實際不符。另一幅是英國著名畫家威廉·丹尼爾的作品,創(chuàng)作于1794年,表現(xiàn)的是英國外交使團船隊,在伊拉斯謨·高爾爵士指揮的皇家海軍“雄獅號”戰(zhàn)艦護衛(wèi)下,航行至爪哇島安赫爾角錨泊補給淡水的畫面,這幅寫實性的作品曾于1836年在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展出,被認為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其作者是英國畫家威廉·丹尼爾。
邪惡的鴉片貿(mào)易
英國商人向中國傾銷鴉片,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茶葉出口給英國帶來的巨額貿(mào)易逆差。一塊展板以《茶葉貿(mào)易——中國味道》為題,介紹了中國茶葉以及瓷器等商品出口英國的相關史料。
17世紀,茶葉在歐洲是非常昂貴的奢侈品,當時只能從中國獲得。東印度公司從18世紀開始從中國大規(guī)模進口茶葉,使得更多英國人養(yǎng)成了喝茶的習慣。到了19世紀,茶葉已成為英國人最喜歡的飲料。東印度公司進口的茶葉主要有紅茶5種,包括最高品質的白毫、小種、功夫茶、刺山柑花蕾茶和武夷茶,前兩種價格最高,后兩種相對便宜;綠茶3種,按價格依次為熙春茶、松蘿茶、櫻桃茶(御茶)。“茶葉在商業(yè)貿(mào)易史上位居第一”,這是1850年美國商人吉頓·奈耶的一句名言,這句名言被引用在展板文字中。緊隨茶葉貿(mào)易,中國瓷器、絲綢、手工藝品等也進入英國,所有這些都將英國人引入一個新領域。
一個來自中國19世紀的木制茶箱,上面帶有珍珠母鑲嵌,是英國貿(mào)易商高茂(音譯)從中國帶回來的,當時箱子里裝的是復合香味的刺山柑花蕾茶,這是一種產(chǎn)自福建安溪地區(qū)的紅茶,在19世紀的英國最受青睞。一個茶葉罐,使用了木料、玻璃等多種材質,其中的木材來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戰(zhàn)中被俘獲的西班牙圣迪斯瑪特立尼達號戰(zhàn)艦,將戰(zhàn)艦拆毀后用其木材制作了茶葉罐。之所以制作如此高規(guī)格的茶葉罐是因為茶葉最初被帶到歐洲的時候,由于價格昂貴,英國上流社會人士會如同珍寶一樣鎖起來保存,這個茶罐可以盛裝1斤茶葉,“斤”(對應的英文為Caddy,源于Catty一詞)這個中國的計量單位也是隨著茶葉貿(mào)易而進入了英國。3個形狀各異的銀質茶壺,制作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是為飲用高級茶葉而特制的,在18世紀的英國,奢華的茶具已經(jīng)成為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象征。
茶葉貿(mào)易造成了中英之間巨大的貿(mào)易逆差,東印度公司為支付貿(mào)易貨款最終尋找到了非法販賣鴉片這一邪惡的途徑。博物館展出了許多歷史圖片,其中有東印度公司庫房存儲鴉片的成排貨架、中國人蜷縮在煙館吸食大煙的場景,還展出了一桿1900年中國制造的帶有象牙雕飾的大煙槍,展品文字同時指出,東印度公司以藥品的名義向中國出口中國官方明令禁止的鴉片,這個興旺的非法貿(mào)易是英國人對茶葉貪得無厭追求帶來的陰暗面。
英國畫家威廉·約翰·哈金斯繪制的一幅油畫,描繪了英國克萊夫號單桅帆船救助“風精靈號”快船的畫面。風精靈號是英國公司1831年為印度商人Rustomjee Cowasjee建造的一艘快速帆船,1835年裝載了995箱鴉片駛往中國,途經(jīng)馬來半島海域觸暗礁擱淺,結果被克萊夫號搭救。展板文字引用了林則徐的一段話做畫龍點睛之筆:“一些邪惡之人為謀取利益,制造出售鴉片,引誘愚蠢的人毀滅自己。”
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罪證
博物館在最后部分以“英中戰(zhàn)爭”為題,展出了一批反映兩次鴉片戰(zhàn)爭歷史的文物史料。
一段展板文字簡要表述了鴉片戰(zhàn)爭的起因和結果:英國商人越來越多地將鴉片走私到中國,為英國不斷增長的茶葉貿(mào)易提供資金,但嚴重違反了中國政府的律例。1839年,清政府派出官員林則徐摧毀了大量鴉片,由此引發(fā)的爭端導致了戰(zhàn)爭的發(fā)生。英國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中打敗了中國。另一段展板文字是一位英國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對鴉片戰(zhàn)爭的反思和批判:“戰(zhàn)爭的開端愈加不正義,戰(zhàn)爭的過程就會愈發(fā)蓄意妄為……它給我們國家?guī)砹藧u辱,個中緣由我不懂也無法知悉。”
一幅作于1854年的油畫人物肖像為復仇女神號艦艦長威廉·哈奇恩·哈爾爵士(約1797~1878年)。復仇女神號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835~1840年在利物浦建造的遠洋汽輪兵艦,也是英國第一艘鐵殼戰(zhàn)艦(用鐵皮作外殼包裝木船),在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威廉·哈奇恩·哈爾艦長指揮該艦擊沉了大量清軍風帆戰(zhàn)船,為此獲得了多枚勛章,其中兩枚勛章被陳列在展柜中。同一展柜還展出了1842年羅伯特·奧利弗爵士從中國帶回的2把中國寶劍,羅伯特·奧利弗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擔任印度海軍總指揮,這兩把劍是戰(zhàn)爭期間繳獲的。
愛德華·H.克雷醫(yī)生的日記,是鴉片戰(zhàn)爭場景的實錄。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愛德華·H.克雷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擔任軍醫(yī),在此期間他不僅用文字記錄了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和所見所聞,還用畫筆繪制了1700余幅水彩畫和素描,這部圖文并用的日記描繪了戰(zhàn)爭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物質毀滅的真實場景。
銅版畫《南京條約》,是根據(jù)條約簽署的親歷者約翰·普拉特上尉的描述于1846年制作的,該條約簽署于1842年9月29日,地點在英國海軍旗艦康華麗號上,這艘軍艦由著名的瓦迪亞家族建造。《南京條約》的簽訂標志著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結束,條約迫使清政府割地賠款并開放更多的對外通商口岸。展出的這幅銅版畫是采用美柔汀制版方法(美柔汀,歐洲在17世紀發(fā)明的技法,是利用柔和細膩的中間色調表現(xiàn)形象的一種技法,能夠表現(xiàn)極為精細的效果——編者注)制作的。博物館還藏有另外一幅內(nèi)容相同的彩色畫,是在美柔汀版畫基礎上手工上色完成的。在英國人繪制的圖畫上,無論是侵略者還是被侵略者,無論是戰(zhàn)敗的一方還是戰(zhàn)勝的一方,所有人物表情喜悅,好像這場罪惡戰(zhàn)爭的結局對敵對雙方來說都是皆大歡喜。博物館收藏的另外一幅畫作《1840年7月4日中英甲板會議》,描繪的則是另外一種景象,這一天英國將領伯麥率領的主力艦船齊集定海港,定海知縣姚懷祥、水軍首領羅建功等中國官員登上英艦韋爾斯利號甲板,伯麥當面遞交了用漢文書寫的致定海鎮(zhèn)水師總兵的戰(zhàn)書,要守軍于次日獻城投降,結果遭到拒絕。在這幅圖畫中,中英雙方人物表情迥異,英國人的傲慢無理和中國人的憤怒無奈躍然于紙上。
一面鑲在鏡框里的大清帝國飛虎旗,是1857年12月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英法聯(lián)軍攻克廣州城時英軍繳獲的戰(zhàn)利品,軍旗質地為藍色錦緞,上面用金箔絲線縫制了一只綠眼雙翼的金虎和象征風云雷電的圖案,尺寸為1740×1905mm,側邊旗桿套寬75mm。這種軍旗在該博物館藏有多件,其中還有一面為橙黃色綢緞質地,手工刺繡、機器縫制,尺寸1820×1928mm,側邊旗桿套寬95mm。關于飛虎旗正式啟用的時間未見文字記載,在1751年乾隆南巡圖描繪的一艘前鋒艦船上可以看到這面旗幟。
在展品飛虎旗旁邊的展板上,還介紹了大清帝國三角形飛龍旗的相關資料。飛龍旗是1866~1888年清政府使用的旗幟,博物館亦藏有多件。
一門中國制造的“鐵模炮”,制造于19世紀中葉,屬于蘇格蘭卡龍艦炮的仿制品,是一種使用鐵質模具鑄造的射程較近的臼炮,在鴉片戰(zhàn)爭中被英軍繳獲。該炮口徑2.5英寸(65mm),炮管上帶有“鐡模”兩個較大的漢字銘文,是由中國工匠吳亭貴、費君泰(音譯)制作的。
一枚鐵質球型炮彈,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中國軍隊從海岸炮臺架設的火炮發(fā)射的,它擊中了英國皇家海軍配有50門火炮的南京號戰(zhàn)艦,并導致一名英軍士兵喪命。這枚炮彈被南京號戰(zhàn)艦帶回英國收藏起來,并在炮彈上銘刻金色銘文以銘記它的來歷。被南京號戰(zhàn)艦作為戰(zhàn)利品同時帶回英國的,還有發(fā)射這種炮彈的火炮,這是一種體積較大的要塞加農(nóng)炮,現(xiàn)被倫敦塔皇家兵器博物館收藏,在博物館門外露天陳列。另外,英國利茲皇家兵器博物館也收藏有一門相同類型的火炮,也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被英軍繳獲的,該炮炮耳上帶有“蘸”字銘文。
編輯/劉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