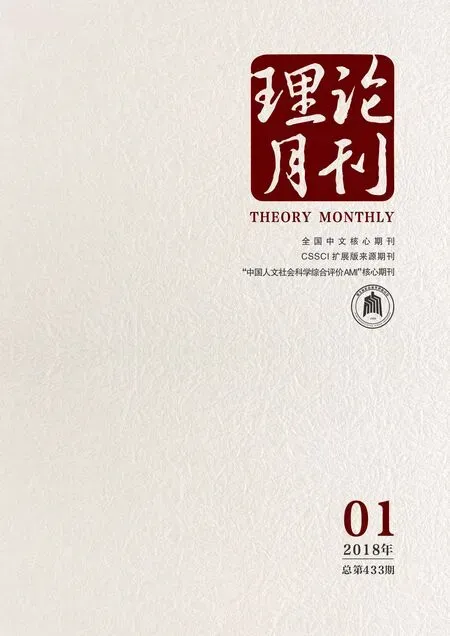文化轉型與文化邊界的守護分析
□劉旺旺,俞良早
(南京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轉型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和民族前進道路上都必然面對的一道難題。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轉型程度與方式也不盡相同,有的快速,有的緩慢,有的激進,有的漸進。近代中國經歷了千年之未有的大轉型,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文化的轉型給國人帶來的震撼最大、爭論最多、選擇最難、任務最重,是否轉、如何轉、轉向何、為何轉成為近百年來國人似乎無法擺脫的糾纏性難題。改革開放以來,文化轉型的頻率之快、波及之廣、挑戰之大、影響之深,使得文化成為無人不能談及但又無人能說清道明的“玄妙之門”。實際上,這是因為人們在文化轉型中未能厘清文化之邊界,未能找到“本我”的文化“棲息地”。
一、文化轉型與文化邊界守護之需
(一)“由慢到快”與文化邊界的“凌空化”
文化作為人之為人的驗證碼,民族精神的標識碼,國家區分的識別碼,伴隨人類歷史發展左右。文化的轉型也并非今日之新事,而是隨著歷史發展主題的轉換而不斷變遷,古已有之。從世界文明發展的大敘事看,人類早期出現的幾個農耕文明,如愛琴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中國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在大航海活動開啟的全球化之前,幾乎處于互相隔絕、各為一方的分離狀態,呈現為分散的原子化分布。不同文明間的沖突與交融在漫長的3000多年中,鮮有發生,但不常有,不同文明借助游牧民族與自身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在時空坐標上進行著各自的刻寫。空間上,不同文明的存在邊界在張力中不斷變更,時間上,不同文明進行著自身的轉型延續,但這些都只是整個世界歷史和全球化進程中一部冗長的文化序幕。自1492年和1498年“這兩個魔幻年”以來,哥倫布和達·伽馬的大海航行揭開了不同文明間更為廣闊深邃、更為深遠影響的交融。從此,原本彼此分散且相對隔絕的文明都被漸漸納入到世界文明中來。歷經15、16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17世紀的科學理性生長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發展,一個率先實現了現代化轉型的西方文明在歐洲誕生。從此,在資本邏輯的強力推動下,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文明或主動、或被動都卷入到現代文明的轉型之中,而且轉型之快是前人所不能比擬的。變化之快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言:“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1](p403)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伴隨著中國這個古老文明大國以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使得全球文化的百花園更加絢麗多彩。但是不同文化間的交匯、交融、交鋒,文化轉型的快速奔馳,使得不同文化間的邊界出現了“凌空化”的趨勢。這種“凌空化”的趨勢主要有兩種表現:一是從國際大范圍看,認為不同國家和民族文化間不存在所謂的邊界,“自由、民主、平等”是所有人都應該向往和追求的目標。“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成為人們反抗一切枷鎖的擋箭牌。實際上,這種論調多是站在西方普世價值的立場,堅持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秉持著資產階級創造了現代文明的優越感,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和理念來“凌空”實實在在的文化邊界,背后的深層意蘊是,其它文明都應積極主動投入到西方現代文明的懷抱。二是從國內小范圍看,認為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不同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應該過多強調文化的邊界,應該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的高度一體化。近年來,保護地方“鄉音”“村落”“民俗”等文化吶喊的聲音不絕于耳正是對這種“凌空化”文化邊界的“抵抗”。實際上,用二元對立的思維分析,這是文化上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較量,自由主義者的軸心原則是崇尚個人自由的文化權利,并且在現代生活中已經融入普通民眾的精神血脈,保守主義者的現代追問強調的是應該為這種文化自由主義設置合理的限度和必要的約束。本質上,它體現的是在“凌空”文化邊界下不同文化間擴張與守護的“張力關系”。
(二)“由淺到深”與文化邊界的“模糊化”
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人們無論是對近代中國面臨苦難矛盾的整體性認識,還是對中國走向未來道路的漸進性探索,由于人們思想認知的固有局限,實際上都有一個“由淺到深”的認識轉變和實踐探索過程。認識轉變體現為,由物質層面的技術不行轉變到政治層面的制度不行,再進而轉變到思想層面的文化不行。探索轉變體現為,由學習歐美到學習蘇俄,再到走中國自己的特色之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文化轉型也追尋著這樣一個變化的軌跡,先由城市再到農村,先由沿海再到內陸,先由精英分子再到普通民眾。今日中國,文化的轉型已觸及到祖國的各個角落,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無論沿海,還是內陸,都能在“同時異地”享受相同文化的盛宴。這絕非是文化發展的壞事,但也帶來了棘手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人們的心理隔閡與思想代溝開始凸顯;二是西方文化“魚龍混雜”地流入尚未做文化準備的農村和偏遠地區。兩方面疊加造成了現代生活轉型和多元文化沖突下文化上的“邊際人”,其文化特質在于跨民族、跨時代的生活要素融于一身,使其人格具有易變性和過渡性,進而導致人們出現文化選擇上的迷茫、文化認同上的惆悵、文化心理上的焦躁。
身處這樣的文化生態中,部分人特別是身處農村和偏遠地區的人,在精神上會有一種“魂不守舍”的痛苦,他們在咀嚼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過程中體味著文化生態的深刻變遷。在這種轉型中,人們的文化情感又需要格外的宣泄和補償,但在多元化、多層化、多樣化、多變化的文化環境中,加之資本邏輯的助推下,宣泄和補償的具體方式往往表現為不分雅俗、不分你我、不分主次、不分美丑,追求及時行樂、偏愛感官愉悅、忽視精神內涵、模糊美雅丑俗。此時,少數人的文化情愫因受西方文化的浸漬和涂抹而逐漸發生變異,認為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國的好,自由觀念、生活方式、民主模式、文化產品等都比中國的好,甚至“月亮都比中國圓”。在這些潛在的文化意識左右下,表現出“模糊”文化邊界的認知傾向,認為文化無國界,更無邊界,只要能夠“為我所用、服務于我”就是好。實際上,這是一種文化邊界“模糊化”的表現,由于認識不清或理解錯位,出現了“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的現象,但內心深處仍常感到“心頭疑云起,無處可拂拭”。人自身的文化存在被零散化、平面化、空心化,成為忘卻記憶、拒絕思考、沒有深度的平面人。文化標準的逐漸模糊化,使得人們無法做出正確的文化判斷和行為選擇。
(三)“由一到多”與文化邊界的“眩暈化”
文化轉型中“由一到多”的變化是近代國人文化體悟最為深刻、最為明顯的文化感覺。從統治長達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文化到國門被迫打開后的中西文化交匯,從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啟蒙到新民主義文化的確立鞏固,從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文化建設到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開放后的文化多元多樣多層化的發展。這其中有所變,有所不變,不變的是“一與多”的張力存在,變的是“一與多”的多重內涵。而身處近代中國,特別是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的人們,無不驚嘆乃至驚奇中國文化轉型的變化之快,這種文化的轉變深深影響人們的文化選擇、文化心態,甚至已經觸及到國人的文化命脈。主流文化的式微、消費文化的崛起、流行文化的興盛、低俗文化的濫觴、大眾文化的發展,各種文化呈現出爭奇斗艷的壯麗文化景觀。人類進入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經》第十二章)的“文化景觀”社會。文化也已不再是統治階級所獨占的,也已不是精英分子所獨享的,而是包括普通大眾所共享的,文化的邊界在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實踐中的內涵已大大擴展。
人作為一種高級動物存在,其根本區別在于人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是各種文化交織且集于一身的“復合體”。文化多樣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動力。文化作為個人生命的存在要素,面對全球化、網絡化、信息化的時代轉變,文化形態的多樣、文化價值的多元、文化審美的多變、文化享有的多層,使得人們思想中出現了文化邊界的“眩暈化”。“眩暈”原本是生物學上的概念,是指因機體對空間定位障礙而產生的一種動性或位置性錯覺,用這一概念來描述今日國人的文化存在可謂是再恰當不過。文化邊界的“眩暈化”,即是指人作為機體對文化轉型之快、文化形態之多、文化選擇之困而產生的一種迷茫、繚亂的錯覺。當人們內心的文化邊界出現“眩暈化”之后,在文化的選擇與實踐中就會出現散光、游移、虛幻現象,造成思想游移不定,態度不夠堅決,時而認同,時而懷疑,出現文化選擇“困難癥”“迷茫癥”等弊病。因此,在多元中把握主流,在多樣中重塑主態,在多變中探求穩定,在多層中達到統一,通過“多”達到更高層次的“一”成為文化發展的潛在訴求。
二、文化轉型與文化邊界守護之困
(一)“快”節奏與文化的“慢”
“時間就是金錢”是近代資本邏輯下市場經濟的座右銘,對速度和效率的片面追求,讓“快文化”占據了人們的潛在意識和價值觀念。文化在近代轉型中表現為前所未有的“求快”,而其背后是資本邏輯的強力推動。資本自誕生以來,便以不同的方式在其逐利秉性的支配下表現出擴張性,或通過武力征服,或通過政治變革,或通過文化滲透,其終極目的是對利潤永不知足的貪婪、對欲望永不知足的追求。也正是在資本邏輯的助推下,“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p405)。這里有一個時間概念的對比,即“不到一百年”與“過去一切世代”。可見在資本邏輯下,追求的是“快”,唯有此才能彰顯資本自身的存在價值。在現代社會呈現出一種“快文化”的景象,即人們似乎都在追求速成、速度、速效,忘卻了深厚積累和內在價值的文化底蘊,呈現出“快而不精”“快而不厚”“快而不高”“快而無質”的文化亂象。“快文化”使人們生活節奏加快,成名要早、致富要快、快餐果腹。
對于國家和個人發揮“潤物細無聲”之用的文化本意是“以文教化”。因此,文化有其自身特殊的發展演進規律,其發展速度上強調的是漸進性。無論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培育,還是個人文化素養的提高,切忌犯急躁冒進的毛病。對此,列寧在領導蘇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針對革命后廣大人民群眾表現出文化建設上的“盲目革命熱情”指出:“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2](p784)為此,他多次警告提醒文化建設“最好慢一些”,“文化任務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那樣迅速”[2](p591)。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建設又何嘗不是如此,“心急吃不了熱豆腐”,要讓文化發揮其社會效益,帶動經濟發展還需“久久為功”。但在文化實踐中,隨處可見對“快”的崇拜,“快”本身并不可恥,但當被政績、被利益所捆綁,被民眾、被政府所曲解,出現多快好省建設、急功近利上馬等現象,變成占絕對優勢的、無處不在的生活法則時,它便是人類的淺薄。這背后是被“資本”所綁架,“揠苗助長”的文化實踐不僅無益反而有害文化健康持續穩定發展。
(二)“浮”氛圍與文化的“重”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無論是經濟生活,還是文化面貌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但物質生活的提高改善并無如影隨形地帶來精神生活的歡心愉悅。當今,激烈的競爭、快節奏的生活、繁雜的社會現象、強烈的物質欲望給人們增加了無形的壓力,使部分人的心態浮躁得宛若煮湯,身上或多或少充斥著俗氣和躁氣,心煩意亂者有之,神不守舍者有之,著急上火者有之。今天的文化場域,正迎來一個百花齊放、爭奇斗艷的春天,同時也彌漫著“浮躁不安”之氣。迎合市場盈利的低俗創作、揣摩評委口味的獎項創作、缺乏獨特創意的跟風創作、短小精悍快速的網絡創作、標題驚艷引人的點擊創作、追求形式美觀的空心創作,上述等等都是沉浸于描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或以剪貼拼湊模仿為寫作生存的方式。許多人都愿意用一個詞來形容當今的文化生態:“浮躁”,這個詞無比精準地刻畫了人們的文化生活現狀。“浮躁”背后是文化內涵的空洞化,文化價值的低廉化,文化審美的平庸化,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失去了發展的方向,使道德失去了存活的基礎,使人們失去了生活的目標,使文化失去了應有的靈氣。
文化作為連接古今的精神命脈,是人之為人的生命基因,具有一種內在的特質,即追求的沉與穩。實際上,在傳統的道德和宗教領域中,總是對“浮”進行猛烈的鞭笞。隨著誘惑資本主義的興起,當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規約都日漸寬松,但唯獨人們的心靈好像卻變得愈加沉重。一方面是人們在物質充裕條件下持續獲得短暫的感官刺激和滿足,另一方面是人們在文化繁榮表象下出現了心靈麻木、精神迷茫、道德失范等文化病癥。而當“誘惑代替強制,享樂主義代替嚴苛的義務,幽默代替莊嚴,消費世界趨向表現為一種卸除所有思想重量、所有意義厚度的世界”[3](p3)。要化解這種文化的“浮躁”,就要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或者說在多元文化中找回國人的文化之根、文化之魂,在文化邊界的變與不變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找回人們心底那份文化之重,喚起國人內心對文化的敬畏之感。
(三)“滿”追求與文化的“魂”
文化轉型中的“滿”追求主要是指人們在文化延續和文化創造中表現出的“文化濫造”。我們正處于一個文化產品流通與消費急劇快速發展,多種文化景觀遍地開花,處處上演的“非常”時期,處于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化資源富裕乃至“過剩”時期。人們無論是在現實日常生活中,還是在網絡虛擬社會中,終日受到各種文化產品、文化景觀、文化消費的誘惑和刺激。人類的視覺、嗅覺、聽覺、味覺從未像今天這樣忙碌,各種欲望也從未像今天這樣的強烈。特別是以網絡化、數字化、電子化為主要特征的新媒體的出現,造就了一種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文化井噴”現象,即作為文化依附存在“器具”的新媒體已在社會上無處不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泛濫程度,成為人們向社會和全部人類生活世界展示自己的櫥窗。新媒體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一種近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存在者”!它們似乎既是給人們以各種指導和“忠告”的神仙和大師,又似乎是人們信手可得的、對人百依百順的工具和“奴仆”。[4]這勢必會導致文化喪失原本的意義和功能,成為沒有靈魂的商品符號和文化軀殼。文化產品的精神屬性越來越被擱置,打著“怎么都行”的旗號,顛覆一切權威和經典,各種文化垃圾由此催生,“三俗”充斥著人們的文化生活,空耗了文化精神,削減了文化審美,最終必將喪失文化的自信。
文化不僅是一個國家的精神底蘊,而且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氣魄,是人類審美地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體現了一個民族的國民品格、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深層次的東西,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精髓和根基。”[5](p160)文化之魂決定了文化的立場、文化的取向和文化的選擇,其本質上體現為“形神統一”,“神”就是文化的精神實質,是文化之魂;“形”就是文化的現實樣態,是文化載體。而在當前文化領域出現了失魂、失序、失守、失諧、失控的現象,冠之以“大眾文化”之名,掌握著濃烈的話語霸權,以致任何對它們的挑戰都有可能被指認或判定為落后和保守。實際上,大眾文化原本無可厚非,但在資本邏輯的強力推動下,如果沒有精神的內核支撐,只是附上“娛樂”的標簽,欲望的無阻礙永續流動和隨意擺弄,必然會導致文化邊界的失控,繁榮的表象背后潛藏著內心的空虛,價值的多元背后暗流著迷茫的惘然,最終走上“娛樂至死”“失魂落魄”的邪道。因此,能否守住文化之“魂”是文化自覺的一種考驗。否則,“無拘無束的叛逆沖動和一味求新的經驗探奇,在撕裂傳統紐帶的時候會斬斷生存的意義根基,而根基被斬斷的個人,只能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文化漂泊者”[6](p144)。
上述在文化轉型中出現的“快”節奏、“浮”氛圍、“滿”追求等現象,實際上與近代中國的國情和民族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國人對近代中國落后挨打原因的認識發端于器物落后,深化到制度落后,再到最后認識到文化的落后,這樣一種思想認識歷程使得國人在圖強復興的探索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的短視”。失去了文化的靈魂,就會出現“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不講對錯,不問是非,不知美丑,不便香臭,渾渾噩噩,窮奢極欲。”[7]而真正的文化啟蒙或文化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慢”過程,需要“沉”下來,找到“魂”。人們越來越體悟到,一個社會的良性發展,需要堅持最低的文化標準,捍衛基本的文化原則,用文化之道構筑最后也是最堅固的屏障。
三、文化轉型與文化邊界守護之道
(一)文化樣態上:處理好“一”與“多”的關系
任何國家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任何民族的理想信念、精神信仰,任何個人的文化寄托、核心價值觀,都應當是一元的、一致的,具有穩定性、持久性,這是國家、民族、個人保持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必備條件。在中國,居于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因為它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我們立黨立國和治黨治國的指導思想,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會改變前進的方向、就會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信息化、開放化的時代,文化樣態上多樣、多元、多變、多層的存在是社會發展的客觀不爭事實。精英文化、消費文化、流行文化、低俗文化、網絡文化等等在異常喧囂的文化市場上“爭奇斗艷”。精英文化堅守著文化的高雅陣地,試圖維護文化的那份純真;消費文化伴隨著經濟的增長異軍突起,通過引誘欲望牽引著大眾的審美;網絡文化借助電子科技的發展大行其道,通過網絡平臺客戶端推送著繁雜的信息。而“多元文化的有序和諧發展必然要有一元化思想的指導和核心價值的引領,否則就會出現文化上的‘千人千面’,形不成文化上的凝聚力、向心力,而只會助長離心力、消解力”[8]。因此,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文化景觀中,正確處理“一元指導”與“多元并存”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元指導,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來引導和協調社會各種文化價值取向,使社會上的各種文化樣態能夠符合良性的發展要求,但是它并不否認文化的多樣多元存在。“陽光有七種顏色,世界也是多彩的”[9],堅持文化的多元存在,就是要讓各種有利于人類文明進步、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精神素養提升的文化并存,在多元文化價值取向中保持合理的張力,但是它并不是文化的“無邊無界”。正確處理“一”與“多”的關系,就是要通過一元化的指導思想提升多樣文化形態的品質,過濾掉伴隨著多樣文化浪潮而出現的某些落后腐朽的文化殘渣,有效整合多元文化,在以一統多、以一導多、以一帶多的動態互動中,達到和而不同、互相補充、統一于社會共同理想,在文化邊界的“堅持”與“寬容”的動態平衡中實現文化的繁榮興盛。同時要防止理論和實踐上的極端化、偏執化現象,唯“意識形態”化和去“意識形態”化是不可取的,用多元來否定一元、用多元來消解核心同樣也是不可取的。
(二)發展速度上:處理好“慢”與“快”的關系
社會的轉型有快有慢、有急有緩,但文化作為社會存在整體的精神內核,轉型更多表現為慢。傳統社會中,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過著田園般的詩意生活。近代以來,在資本邏輯的強力推動下,速度和效率成為引領人們生活的不二法則,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踏上了“快節奏”的列車匆匆向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變化之快舉世稱奇,“快”已成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價值標尺,甚至營造出一種“快文化”的氛圍。“快文化”片面化、非理性地追求娛樂快感,容易導致歷史理性的匱乏和美學理想的沉落。“快文化”在今日中國的盛行有其復雜的時代背景,是多種因素的凝聚,如近代中國在國際比較中“追趕”的境遇,國人在掙脫“窮怕了”記憶陰霾中“求變”的心態等等。以“大眾文化”為標識的“快文化”日益橫行,以“精英文化”為標識的“慢文化”日漸式微,使得人們不禁發出“守護文化之神”“守護詩意的心境”“精神返鄉”等吶喊。
“快”是一把雙刃劍,不越邊界,合乎規律,遵循科學之快,將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好處。文化的發展和繁榮要面向且進入市場,但千萬不能放低品格而順從和依附于市場。“快文化”幕后的操盤手是資本及其擴張增值邏輯,資本給現代生活裝上了一個無法停轉的輪子,使原本詩意的生活成為一部永動機,由此產生了現代性的“文化焦慮”和“騷動不安”。而文化的生成、發展和培育決非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慢下來、沉下來、靜下來,更需要耐心、虛心、實心。但文化的靈韻在工業化時代不斷喪失,不當快而求快,必受其害,會背離初衷,適得其反。適度,“快文化”將上升為美感,養眼更養心。過度,“快文化”將淪落為宣泄,傷力更傷情。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快”與“慢”的關系,既要堅持“快有規律、快要適度”,又要防止“快”對文化生態的破壞,對精神世界的侵蝕;既要堅持“慢有品質、慢有韻味”,又要防止“慢”對文化發展的懈怠,對變化世界的抵制,達到一種“快中有慢、慢中有快、相兼有度、和諧共生”的文化發展狀態。
(三)審美取向上:處理好“雅”與“俗”的關系
雅者,正也。雅文化是在人類活動以及勞動過程中,產生的以“高雅、典雅、幽雅、儒雅”為顯著特點的文化,多與精英知識分子的審美創造和嚴肅思考有關。中國乃是禮儀之邦,崇尚“雅正”乃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知識分子乃至一般民眾的人生準則和審美理念,影響到人們的文化修養、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各方面。俗文化多指通俗化、大眾化、平民化的文化,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多與底層民眾的樸素表達和消遣休閑相連。俗文化自古有之,其特點是樸素易懂,便于流行,如俗語、諺語、歇后語、民謠、民歌等等。文化發展史中的“雅”與“俗”是一對“孿生姊妹”,雅文化源于俗文化,精于俗文化,高于俗文化。俗文化是雅文化的基礎,脫離俗文化的雅文化是不存在。實際上,任何一種理想的文化形態必須是“雅俗兼得、和諧相融”的,單向度的追求“雅文化”或“俗文化”是背離文化規律的,也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
但在當下,消費文化、網絡文化、景觀文化盛行,“文化消費”“大眾娛樂”等成為窺探社會現狀的關鍵詞。急功近利的文化浮躁大行其道,“三俗”(庸俗、低俗、惡俗)文化隨之泛濫,雖飽受詬病,但屢禁不止。應該說,在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現象的出現有其正當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但是對于文化中出現的“越界”行為及其表征出的“娛樂至死”“盲目狂歡”“拒絕崇高”“反諷經典”的現象,必須敢于“亮劍”。文化是人生命的構成要素,不可能是“無菌的真空”,文化的發展也不可能完全杜絕“三俗”。只是“三俗”文化不能溢出界域,更不能成為大眾文化市場的榜樣,甚至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化。一方面,精英知識分子試圖通過文化批判將雅文化拉回“高堂之廟”,但面對俗文化的廣泛享用卻顯得“無力回天”。另一方面,普通民眾試圖通過追求雅文化以提升自身文化素養和品味,但面對雅文化的“金科玉律”卻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實際上,雅之于俗的意義在于,以廟堂之正糾江湖之偏,俗之于雅的意義在于,以江湖之活糾廟堂之僵,最終達到一種“雅俗兼得”的美好狀態。
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文明的升華,需要秩序的守護。秩序是一種有組織、有條理安排其自身內在結構或要素以求達到正常運轉的良好狀態。自然生態平衡要有秩序,社會持續發展也要有秩序,文化作為人之為人的生命要素和國之魂脈的精神要素更要有秩序。但對于中國這樣的后發展國家,在社會大轉型期,呈現出某種無序性或過渡性狀態,人們的文化棲息地變得不安和浮躁。而文化對于國家和民族來說是千秋偉業、大業和雄業,必須著眼于長遠和未來,必須舍得花時間和精力,必須守得住邊界和底蘊,讓文化之光在民族復興的征程中更加熠熠生輝。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法]吉勒·利波維茨基.輕文明[M].郁夢非,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
[4]李鵬程.文化危機三題[J].江海學刊,2014(3).
[5]田旭明.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7]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10-15.
[8]劉旺旺,俞良早.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文化思想的形成根據論析[J].探索,2017(4).
[9]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