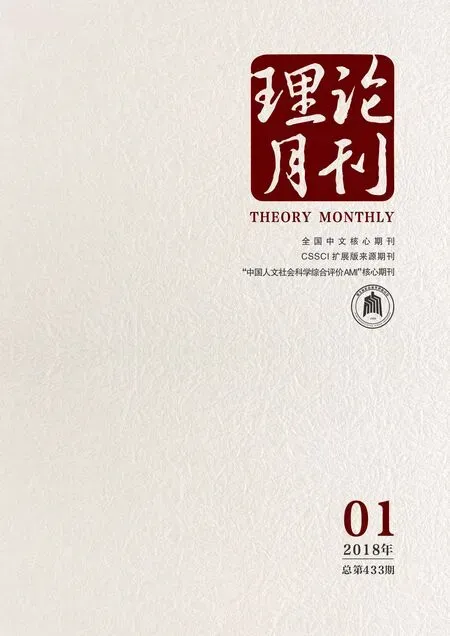翻譯研究的文化概念問題
□熊 偉
(武漢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對“文化”這個關鍵詞進行歷史語義學考察時指出,文化是英文里兩三個比較復雜的詞之一,主要原因是“在一些學科領域里以及在不同的思想體系里,它被當成重要的觀念。”[1](p101)文化的概念雖然重要,但其意義卻隨語境的變化而不同。其中,學科、理論和話語對文化概念的確切意義和適用范圍影響較大[2](p18)。翻譯是一種跨語際、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動,文化自然是翻譯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然而,由于翻譯研究具有多學科和跨學科特征,且學科內部理論流派眾多,話語駁雜,因而對文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各不相同。這種不一致性容易引起混亂和誤解,甚至濫用和亂用。為此,本文的研究問題是:文化是如何成為翻譯研究的核心概念的?翻譯研究中不同的文化概念源自何處?不同的文化概念對翻譯研究產生了什么影響?文化概念在翻譯研究的使用中存在哪些不當之處?為此,本文擬通過對人類學、文化研究和哲學視角的文化概念在翻譯研究中的呈現,及其在使用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來厘清文化概念在翻譯研究不同語境中的意義,為準確理解和使用相關的翻譯理論提供一點啟示。
一、人類學視角的文化概念與翻譯研究
語言與文化是翻譯研究與人類學共同關注的議題。人之為人能言也。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稟賦,因而人類又被稱為語言人。人類學家通過對他者語言獨特結構的描寫,來了解某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而在理解、描述和闡釋自身和他者的過程中,必定存在著廣義或狹義的翻譯。于是,翻譯研究與人類學找到了榫合點,人類學的文化概念便水到渠成地被引入到翻譯研究中。
早在1952年,美國人類學家Kroeber和Kluckhohn就列舉了人類學文獻中文化的164種定義[3](p36),彰顯了人類學對文化概念的重視以及文化的多義性。此后,新的文化定義仍舊層出不窮,角度各異。盡管定義眾多,但人類學的文化概念大致圍繞著一種基本思想,即文化是一種將某一群體統一起來,并賦予其社會身份的系統性思想和情感,影響或制約著人們的行為。同屬一種文化就是共享語言或意義的框架,借此人們的身份得以確立,其行為得以理解和預見。然而,當文化與某一群體(種族、民族或國家)捆綁在一起時,不同的生活方式往往會產生“所有像我們的人是‘我們’,其余的人是‘他們’”(吉卜林:《我們與他們》),這種文化排他性極易滑向種族中心主義和偏見。發軔于西方的人類學,創立之初因其更加關注原始時代和異族文化,而帶有西方種族中心主義色彩。遺憾的是這種特點為殖民主義所利用,成為殖民和征服的工具。正如薩義德所言:“在所有的現代社會科學中,人類學在歷史上是與殖民主義關系最為密切的,因為人類學家和人種學家時常就土著的規矩與習俗向殖民主義統治者提出建議。”[4](p216)
Nida在探討語言、文化和翻譯之間的關系時,將“文化”簡明扼要地定義為“某一社會信念和實踐的總和。”[5](p78)該定義與人類學的文化是某一群體生活方式的總和的定義相似。Nida的動態對等理論,意在超越不同群體語言和文化的疆界,達到“交流等值”,即強調原文讀者對原文和譯文讀者對譯文反應的等效性。為此,在翻譯策略上就要超越語言層面的對等,進行文化語境的置換,如將英語的“上帝的羔羊”譯成愛斯基摩語的“上帝的海豹”。安妮·布莉塞特(Annie Brisset)稱其研究“把雅各布森‘差異中的對等’原則從狹隘的現實命名領域提取出來,應用于廣闊的社會實踐與世界觀領域。……在結構主義如日中天的時候,奈達的民族文化學視角可謂獨樹一幟。”[6](p74)
然而,Nida的翻譯理論也遭遇質疑和批評。他的《風俗與文化》(Customs and Cultures)一書的副標題是“為傳播基督教的人類學”,且開篇第一句為“好的傳教士總是好的人類學家”[7],表明他試圖通過翻譯《圣經》來皈依非基督徒的目的。為了幫助目標語讀者不費力地跨越文化障礙,理解和接受宗教文本,動態對等的提出便順理成章了。但是,王東風認為,不能泛用奈達的《圣經》翻譯理論,文化的差異決定了等效反應的不可能性,用目標語文化的文化標記來置換源語文化的語義內容,是一種“文化蒙蔽”[8](p203-220)。這種以隱蔽形式抹平文化差異的策略,正是后殖民批評的矛頭所向。
Nida還認為語言間的共性大于差異,并且語言文化不存在優劣之分。但是,在與中國文化語言學的代表人物申小龍的論戰中,他又表現出歐洲語言和文化的優越性。申氏認為中國人的語言、文化和思維方式具有“深層通約”,與西方沒有“公約數”。高一虹等將申氏理論譯成英文并求教于奈達。始料未及的是,奈達對申小龍的批評猶如老師對學生的訓斥,而后者的反應也頗為激烈:“點評者的批評是典型的西方話語中心,他說的一切都是以西方的范疇為前提。……這種思維習慣上的‘無意識’深刻體現出西方人面對世界時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意識。”[9](p156)其實,雙方的爭議只不過是西方語言文化的一元論和二元論之爭的延續,但當討論的對象變成東方的語言文化時,Nida還是流露出西方種族中心主義情緒。Nida的矛盾說明,他難逃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魔咒。德里達認為,將發音字母凌駕于其他書寫形式之上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是種族中心主義的一種重要表現。由語言推及文化,我們便不難理解Nida“傲慢與偏見”的根源了。
當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以后,瑪麗·斯耐爾-合恩比(Mary Snell-Hornby)摒棄傳統翻譯研究中以“等值”為核心概念的研究,強調翻譯與文化密不可分,將翻譯視為一種跨文化活動。她明確指出其使用的“文化”概念來自人類學:“這里說的文化并非是指其狹義,即人類在人文科學上取得的高度知識發展,而是其更廣的人類學意義,即人類生活里所有受社會制約的方方面面。”[10](p39-40)她進一步闡述:“第一,文化這個概念成了知識、熟練程度和理解的綜合體;第二,它直接與行為(或行動)和事件相聯系;第三,它靠不管是社會行為中的還是語言使用所接受的期望和規范來維系。”[11](p41)可見,她的文化概念與人類學的文化是觀察和理解的框架,是影響和制約人們行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不僅如此,她還指出,德國功能主義翻譯研究者將美國人種學家Ward Goodenough的文化定義視為標準[12](p55-56)。然而,在其著作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的中譯本《翻譯研究:綜合法》的《譯序》里,斯內爾-合恩比被稱為是“促進了翻譯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的向文化方面的轉向。”[13](p2)令人疑惑的是,不知這里轉向的是何種意義的文化?《譯序》下文繼續寫道:“在修訂版中,她刪去了對她稱之為操縱學派,這一盛行于歐洲的翻譯研究學派的批評。這其實也含蓄地表明了她對操縱學派(以Toury,Lefevere,Hermans,Zohar等人為代表)所強調的翻譯研究應從譯文及目標語環境出發,研究翻譯與目標語文化之間的各種互動關系的觀點的認同。”[14](p2)從此處表露的信息來看,上述文化指向的應該是文化研究視角的文化,因為操縱學派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重要內容。可見,這里人類學和文化研究視角的文化概念有混淆之嫌。
意大利翻譯學者Katan堅持相對主義立場,認為文化語境是感知、理解文化并影響交際的一個重要框架。由于不同文化中的個體理解、歸納和建構現實的方式不同,于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就必須充當文化中介者在不同的文化框架中切換。他將文化定義為一個共享的心理模式,“一個具有一致性和相關性的信念、價值觀、策略和認知環境的系統。在這個系統里,文化的每一個側面相互連接構成一個統一的文化語境,以此標明一個人及其文化。”[15](p17)這種將文化看作是一套理解現實和組織經驗的共享體系顯然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然而,在Katan的Translating Cultures(《文化翻譯》)一書引進版的《出版前言》中,他的研究被置于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背景下加以介紹,這似乎不太合理。
其實,Bassnett曾提醒人們,“翻譯研究早期‘文化主義者’所用的術語來自于歐洲中心主義的人類學視角,并不是文化研究視角。”[16](p130)不僅如此,后來傾向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的人類學視角翻譯研究,也不是文化研究視角。遺憾的是,在很多關于翻譯的文章、著作和教材中,文化的概念被混淆和誤用了。
二、文化研究視角的文化概念與翻譯研究
那么,文化研究到底研究的是什么“文化”呢?在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文化研究中,一些學者如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格特、E.P.湯普森等,反對之前的阿諾德和利維斯將文化只是等同于高雅文化,而忽略大眾文化。他們認為不存在超階級、全領域的同一性文化。在特定的社會和文化中,有一個支配文化群體決定著該文化的主導意識形態,被支配文化群體則被有意或無意地要求遵循。另一方面,被支配群體則力圖挑戰支配群體強加的單一“文化”概念。他們運用各種策略來打破沉默,獲取權力。簡言之,文化不再被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多元性的文化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展開博弈。約翰生總結了文化研究的三個特征:第一,文化研究與社會關系密切相關,尤其是與階級關系和階級構形,與性別分化,與社會關系和種族的建構以及與作為從屬形式的年齡壓迫的關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權力問題,有助于促進個體和社會團體能力的非對稱發展,使之限定和實現各自的需要。第三,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的決定的領域,而是社會差異和社會斗爭的場所[17](p8-9)。
文化研究廣泛涉及階級、性別、種族、權力和社會斗爭的特點,使之在文學、哲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得到廣泛應用,翻譯研究也不例外。Mona Baker雖然不同意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說法,但也承認翻譯研究的發展動態與人文科學中其他學科的發展動態存在聯系和互動[18](p12)。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攜手的契機在于,“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異軍突起的非精英學術話語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體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這一點與翻譯研究的‘邊緣性’、對傳統的學科體系的反叛和對原文文本的‘創造性叛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19](p10)自此,翻譯研究的焦點轉向文本轉換過程中的操縱性因素,如權力、詩學、規范、贊助人、意識形態等等。
多元系統理論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一個重要成果。在某種程度上,該理論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反映了翻譯研究轉向的是何種意義的文化。Evan-Zohar、Toury等將目光投向文學翻譯與目標語文化的互動機制。他們認為,一個特定社會中的文學是多種系統的集合,是一個系統的系統,即“多元系統”。在此系統中,各種文類、學派、流派等相互競爭,以贏得讀者、獲取地位或權力。作為對多元系統理論的繼承和發展,Toury在描述翻譯學里闡述了翻譯在目標文化中的功能。他的“文化”意為抽象的系統或網絡,是指“與翻譯有關的整個社會語境,包括規范、規約、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或‘接收系統’。”[20](p49)Bassnett和Lefevere合編的《翻譯、歷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被認為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正式宣言,宣告翻譯研究從“文本”轉向“文化”。在這本書里,文化的意義進一步被拓展,比Toury“更加寬廣和具體,包括后殖民領域、女性主義話語和翻譯中的意識形態誤讀等研究的新進展。”[21](p50)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評述1980年代的翻譯研究時,Snell-Hornby將描述翻譯學、目的論、翻譯行動模式和解構主義都置于“1980年代的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 of the 1980s”)標題下。她指出“文化是目的論的核心概念,于是1980年代中期德國就產生了‘文化轉向’”,這里的文化是指“知識、精通和感知的統一體(特別是規范和規約觀念),它是功能主義路徑翻譯研究的基礎。這種路徑將翻譯視為一種交際和社會行動的特殊形式,而不是抽象的符碼轉換。”[22](p55)在她那里,來自文化研究和人類學的文化概念都歸屬于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不知這樣是否會導致概念的模糊和理解的混亂?其實,她自己也有所覺察,“對文獻的仔細閱讀顯示,實際上,同一術語經常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文化’。”[23](p64)Bassnett在討論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之間的關系時,也曾指出了文化概念的演化,“翻譯研究業已擺脫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逐步走向多元文化的概念。”[24](p133)
雖然文化研究具有跨學科、多學科特征,但其主要的研究對象“文化”卻更多地是指向具有非精英性和邊緣性的大眾文化,而不是泛泛而指各種意義的文化。如果將來自不同學科和理論體系的文化概念,統統不加區分地納入到文化研究中,就會造成文化研究的話語通貨膨脹,包羅萬象卻又模糊不清,這恐怕也是文化研究飽受詬病的原因之一。同理,當我們在討論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時,也必須澄清轉向的是何種“文化”。
三、哲學視角的文化概念與翻譯研究
上述提及的文化,無論是單一的,還是多元的;精英的,還是大眾的,文化間的邊界始終存在。換言之,文化A之所以是文化A,是因為其不是文化B,A與B相互對立和否定。德里達認為,二元對立是西方哲學和文化的基本結構,成對的雙方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如黑—白、好—壞、男—女、東方—西方等。他抓住觀念可同時存在于對立雙方中這個要害,建立了他的解構主義思想,并借此對從古希臘綿延至20世紀的西方哲學中的絕對二元對立思想發起了挑戰。他指出,如果去掉二元對立間的“—”,雙方就會彼此包含對方的某些成分,形成以二元為兩極的連續體。
解構主義思想啟迪人們重新思考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問題。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認為,翻譯要么讓讀者靠近作者,要么讓作者靠近讀者。兩種方法涇渭分明,不能混雜,否則會產生非常不好的結果,導致作者和讀者永遠碰不了頭。施氏翻譯思想影響深遠,余蔭不斷,以不同名稱成對出現在眾多的翻譯理論中:Nida的“形式對動態”(formal versus dynamic)、Newmark的“語義對交際”(semantic versus communicative)、Levy的“反虛幻對虛幻”(anti-illusory versus illusory)、Evan-Zohar和Toury的“充分對接受”(adequate versus acceptable)、House的“顯性對隱性”(overt versus covert)、Nord的“文獻對工具”(documental versusinstrumental)、Venuti的“阻抗與透明”(resistant versus transparent)等等[25](p181)。這些成對概念反映了眾多西方翻譯理論在源語文化與目標語文化兩極間交替的模式,體現了深嵌在西方邏輯思維中的二元對立觀,表明了不同文化的排斥性和離散性。Pym對這種思想進行了批評,“邊界只有兩邊,沒有中間地帶,沒有交集。”[26](p178)人類的跨文化交流史證明,文化之間并不存在清晰可見的“邊界”或“斷層線”,而是存在著重疊的“灰色”區域。居于其間的譯者(翻譯)則被視為具有“文化交互性(interculturality),或某種程度的文化交互性。”[27](p177)
后殖民理論中的“雜糅”(Hybrid)概念就體現了這種文化交互性。Homi Bhaba認為,這種雜糅存在于相互沖突的文化間,通過在文化“中間”地帶(“in-between”space)穿越和棲居的人們,對建立在種族、階級、性別和國籍之上的身份認同發起挑戰乃至顛覆。因為雜糅必定同時分屬于二元對立的雙方,實際上也就解構了二元對立。巴西食人主義翻譯理論是一種文化翻譯理論,也體現了解構主義意義上的文化概念。為了重拾被歐洲文化壓制的本土文化,巴西于20世紀20年代爆發了“食人主義”政治抵抗運動,即通過吞噬和吸收歐洲文化的“肉體和精血”來滋養、發展和壯大本土文化,并以此反抗歐洲的文化霸權。兩種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相互否定、相互取消。受此啟發,1960年代巴西坎波斯兄弟(Augusto de Campos與Harold de Campos)提出了食人主義翻譯理論。原文的終極意義被消解,吞噬的原文拌之以本土文化元素,為再造的譯文提供了養分。“食人主義”隱喻式反映的不僅是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還體現了文化間相互依存、相互轉換和相互斗爭的關系。
那么,當文化邊界變得模糊甚至消解時,又如何去定義“文化”呢?從解構主義思想出發,Pym建議不去定義“文化”,以留下更多可供發現的空間和避免單一文化(monocultures)帶來的種種草率設想。他進一步從翻譯的角度解釋道,“單一文化可以通過否定的方式來定義,不是用源文本和目標語文本來定義文化,而是將其定義為是文本從一種翻譯到另一種翻譯,從輸入到輸出運動中所遭遇到的阻抗……,如果沒有文化,信息流通也就沒有阻礙,信息也會保持不變。于是,我們可以通過轉化進出文化間的文本(語詞、觀念和概念)來使文化顯身。這樣,建立在跨文化基礎上的翻譯史就會告訴我們什么是文化,而不是反過來。”[28](p191)簡言之,跨文化先于文化。
四、結語
作為一種跨語際、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動,翻譯尤其注重對文化因素的考察。由于翻譯研究的多學科性和跨學科性,來自不同學科和理論話語的文化概念都紛紛進入各種翻譯理論中。任何理論體系的構建,必須對其關鍵概念進行界定,否則就會導致理解的混亂、使用的隨意以及理論的漏洞。因此,對于翻譯研究中文化概念的涵義、使用語境及范圍的爬梳,有助于準確把握和使用相關翻譯理論。
[1][英]雷蒙·威廉斯著.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M].劉建基,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
[2]蕭俊明.文化的語境與淵源[J].國外社會科學,1999(3).
[3]Samovar,Larry,Richard E.Porter&Lisa A.Stefani.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Asia,2000.
[4][美]愛德華·W·薩伊德.文化與帝國主義[M].李琨,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
[5]Nida,Eugene A..Language and Cultur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1.
[6][加]安妮·布莉塞特.文化視角下的翻譯[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11(1).
[7]Nida,Eugene.Customs and Cultures[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4.
[8]王東風.文化差異與讀者反應[M]//郭建中.文化與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9]高一虹.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與超越[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10][德]瑪麗·斯耐爾-合恩比.翻譯研究:綜合法[M].李德超,朱志瑜,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11]Snell-Hornby,Mary.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2006.
[12]Katan,David.Translating Cultur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13]Bassnett,Susan&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4]林堅.文化概念演變及文化學研究歷程[J].文化學刊,2007(4).
[15]徐方斌.關于翻譯研究及各種“轉向”[J].上海翻譯,2009(3).
[16]王寧.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17]Pym,Anthony.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