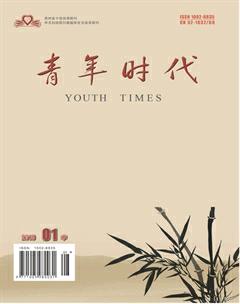視域對文本解讀的影響
宮聿香
摘 要:生活中人們在解讀某一歷史史料或文本的過程中,總是會對古人的想法或是做法產生一種迷惑或是不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所處時代與古人有著很大的不同,自然使古人的視域與當代人的視域有所差異;然而對于同時代文本等的了解,人們也是會產生不同的看法,這則是因為除時代背景這一因素的影響外,作者與讀者及讀者與讀者之間的視域也是有差異的,從而造成了對于文本解讀差異的出現。筆者就讀者與作者的視域差異及影響讀者誤讀的因素等進行探討,使人們可以在對文本進行解讀時盡可能的減少兩者視域間差異所造成的影響,最大限度地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及加深對歷史的認識與了解。
關鍵詞:文本解讀;視域;視域差異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總是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當別人在說一句話時會就自身存在的視域去理解他的意思,從而得出自己的理解,但這往往會使聽者與說者之間產生一定的誤解,這就是所謂的“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正如人們常說的大人是不能理解或是很難去理解小孩子的思維,因為兩者在視域上有著較大的差別,因此當一個大人用他的視域去理解小孩子的世界時,總是難以懂得其中的意義,然而誤解的造成不僅僅是對于話語如此,對于對文本的解讀也是如此,且影響理解的因素并不是單一存在的。2009年央視春晚相聲《我有點暈》闡述了一則有趣的現象:三十年前,大街上騎自行車的,羨慕那開小轎車的,三十年后,開小轎車的羨慕那騎自行車的;三十年前,人能吃粉絲,現在弄不好粉絲能把人吃了。歷史在不斷地更迭,人們的觀念也在不斷地變化,僅僅三十年的時光,社會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人們對于同一事物的解讀就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縱觀歷史的長河,人們經歷了幾千年的文明變遷與演變,處于當代的人們,對于歷史史料的解讀過程中,如果是用當代的眼光去研讀歷史,那么歷史的真面目恐怕就物是全非了,這就要求人們在解讀歷史史料的過程中,去了解其所處時代的特殊性與其所具有的時代特色,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史料,正如施萊爾馬赫所言每個話語只有憑借對它所屬歷史的整體生命的認識或者憑借對與它相關歷史的認識才能被理解。但不能忽略的是,不論人們怎么身臨其境的去看待史料,在解讀它的時候總是與其本身所要表達的內容有著一定的差距,因為人們是擁有這個時代所賦予的視域,從出生起,就是為適應這個社會主導的觀念而存在,在解讀文本的時候,人們自身的視域總是在左右著自己的思想與認識,從而也使對史料的解讀迎合了讀者所處時代的主流觀點。正如,三十年前,人們看到粉絲首先想到的自然而然是吃的粉絲,而三十年后,說起粉絲,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粉絲人員的粉絲而非吃食,這就是時代觀念的變化所賦予人們觀念的變化,所以讀者在解讀文本的時候應通過它的時代進行理解。
人們總是只從每個話語所屬的整個生命理解它,換言之,因為每個話語只有作為處在自身所有生命環節的規定中的言論者一個生命環節才是可認識的,而這只來自他的將規定他發展和繼續存在的整個環境,所以每個言論者只有通過他的民族和時代才是可理解的。在解讀文本等符號過程中,讀者如果不能時時提醒自己考慮文本等所處的歷史環境等因素,人們自然而然的會用自己所處時代的主流觀念先入為主的去了解文本,易產生一定的誤讀,而年代越久遠所產生的溝壑越寬,易使自己解讀出與文本所要表達的內容南轅北轍的認識與結論,這就是兩個視域不同所導致的。施萊爾馬赫指出:“我們必須想到,被寫的東西常常是在不同于解釋者生活時期和時代的另一時期和時代里被寫的;解釋的首要任務不是要按照現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認識作者和他的聽眾之間的原始關系。”
這就要求人們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歷史文本,但讀者與文本(符號)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容易導致誤解,因此施萊爾馬赫甚至明確地把詮釋學看成是一種“避免誤解的藝術”。正如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談到,“如同語言是一種社會及歷史的產物,疾病就相當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眾多歷史文件里所謂的‘圣者假使活在今日的美國社會,恐怕難逃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命運,相反的,現代我們認為對封建社會不算有害的近視眼及嗅覺遲鈍很可能會被我們的狩獵祖先視為生理殘疾。”可見,在不同的時代中,對于事物的要求與資格的限制等情況是不同的。
正如每個話語都有雙重的關系,與語言整體的關系以及與其創造者的整個思想的關系,所有理解也由兩個環節構成,將話語理解為從語言中派生出來的,以及將它理解為思想者的一個事實(Tatsache)。所以僅僅是對于歷史大背景的整體把握是不夠的,也必須對文本著者的生平經歷等有一定的了解。因為文本的著作是作者在其自身視域的運用下所得出的,對于文本的認識就有著獨特的觀點等,對史料進行編寫的過程中,則會賦予他所著文本自身所帶有的認識即作者在用自己的視域在對文字進行斟酌挑選與記述,對于某一個事物的描述,也許會帶著些地方性的特色(如當地的俗稱),基于此,如果缺乏對于作者生平的了解,會有對文本誤讀或是不懂的情況。
可見在讀者看待歷史時,除了主體本身對于自己解讀史料的影響之外,作者本身的視域也對讀者認識行為的發生潛在的起著一定程度的引導作用,從而完成使讀者更易于接受作者本人所要表達的思想這一目的,導致讀者在了解歷史的過程中,得出的認識與歷史事實本身有著一定的出入。正如19世紀所興起的蘭克學派,其主張史學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不偏不倚,如實客觀,該學派倡導秉筆直書,通過史料批判如實地再現歷史,否認史家對史料及史著的滲入。但是其自身的表現并非完全如其所主張的那樣,在蘭克自身對史料的記載過程中,其是有著自身偏好的,其對于史料的詳細與否的書寫這一行為就說明了其并非能做到完全的置身事外而去完整的還原歷史。
那么,其所著的書籍當讀者接觸到時,就已經受到了作者自身偏向的一種引導,從而使讀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作者的喜惡與想要表達的思想,抑或是引導讀者對某一事物看法的改變,如某些史料中對于某一文明的忽略或者惡意的描述,則會使讀者對于某一文化先入為主的產生一種不良盜匪印象,從而達到其所潛在的目的。正如,同是一副007電影的畫報,但是對于男女主角的位置變化及服裝等因素的調整,讀者在看到時,所受到的影響就是不同的,這就是媒體在運用畫報在潛意識中,對讀者的思想進行了引導,從而宣傳了社會的主流思想。endprint
再如前段時間筆者身邊所發生的一件小事,有一位學姐來宿舍為其論文研究做調查實驗,將筆者及室友作為樣本測試每個人的習得問題,她說已經在其自己院系里面做過一些測試,大多的答案偏向了A方向(回答者中有2種偏向),看一下筆者及室友會偏向哪個,測試完成的結果卻是出乎意料,因為筆者及室友又給出了第三種、第四種偏向等意料之外的結果,更有的同學給出了令人費解的答案偏向,有的答案的給出與學姐本要測試的要點還是有所差距的,這就是生活中的“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雖然是同樣的問題,當學姐用了不同的語氣表達時,同一個人卻給出了兩種不同的答案,這就是讀者在解讀文本的過程中,受到了著者的影響。
從這一實踐,人們就可以看出,個人的生活經歷與視域對于個人對于事物的判斷與事物的解讀是有著巨大差別的,這樣人們在解讀前人寫作的歷史史料的過程中,自然會產生與歷史所謂的真相有著一定差距的認識,人們并不能用自身的視域完全的認識到史料、文本等的視域。而在生活中,人們可以做到的就是盡可能的去了解作者所存在的時代背景與生活經歷等去解讀史料,理解歷史的真相。作者在對文本進行表達的時候也會導致其言語與作者的意圖有差異,從而加劇了讀者與文本間誤讀的可能性。正如利科所言即“文本所意味的東西不再與作者所意指的東西一致:語詞的意義和精神的意義具有不同的命運。”
在施萊爾馬赫看來,盡管讀者和作者之間存在釋學距離,存在視域的差別,但這種距離和差別卻是可以消除的:“在一個人想理解另一個人的任何情況中都存在這樣一個前提,即這種差別是可消除的。心理學解釋任務就是精確地進入講話者和理解者之間區別的根基里。”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視域上的距離與差別真的能消除嗎?筆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讀者總是作為一個第三者在看待史料及其作者,讀者總是被自己的視域所左右,會對事物產生喜歡或厭惡之感或是對事物敏感程度的差距,這也是歷史史料解讀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每個人一方面是一個地點,在那里一個給定的語言以獨特的方式形成自身,并且只能從語言的整體理解他的話語,另一方面他自身也是一個持續發展著的精神,而他的話語只是這種精神的一個與其余行動之事相關的行動之事。
因為人們是這個社會中的存在者,是被涂鴉過的而非一張白紙,讀者本身是不可能完全與自身的視域相割離,其總會在潛意識中影響著人們,因此在解讀文本的過程中總是會添加上自身視域的理解使與原作者的意圖有著些許的差距。但這種差距的存在是有益的,并且是利于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的,正如在某年人們對某件事物的認識是這樣的,幾年后,對某件事物的認識可能會有一個新的發展,而這種發展也許會與作出的認識是截然相反的,但人們不能一味地對最初的認識進行批判,因為事物的發展及人的認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沒有前面的鋪墊,就沒有后續的發展,正如沒有牢固的地基又怎會有高樓大廈的建立,對歷史解讀就是一個在不斷更新自己認識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如馬克思所說發展是一個呈螺旋狀不斷上升的過程,期間會有曲折,但總體呈現一種上升的態勢。
兩者的視域不斷地碰撞、融合從而形成了一個新的視域,這就使作者在解讀完作者的史料過程中,在自己視域的指導下,從而形成了具有作者特色的新的作品,正因為這樣才造就了豐富多彩的世界,如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如果人人對史料的解讀都是一樣的,那么就不能帶來史學界精彩紛呈的大辯論。人們正是在彼此間的矛盾與差異的基礎上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推動著歷史、思想及文明的不斷演變。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若是其一味地聽從老師柏拉圖的教導,又怎會有對后世的偉大貢獻。視域在彼此的接觸與對矛盾的解決過程中,交叉地帶不斷地擴大,從而使對各自內容的解讀更能符合原視域所要表達的主旨,人們對于史料的解讀也就更能反應歷史的事實。
參考文獻:
[1][德]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張云濤.1819年解釋學綱要通論[J].德國哲學,2013(1).
[2]洪漢鼎.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3]彭啟福.視域融合度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論批判[J].學術月刊,2007(8).
[4][美]威廉·麥克尼爾.疾病與瘟疫[M].余新忠,畢會成,譯,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
[5]洪漢鼎.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