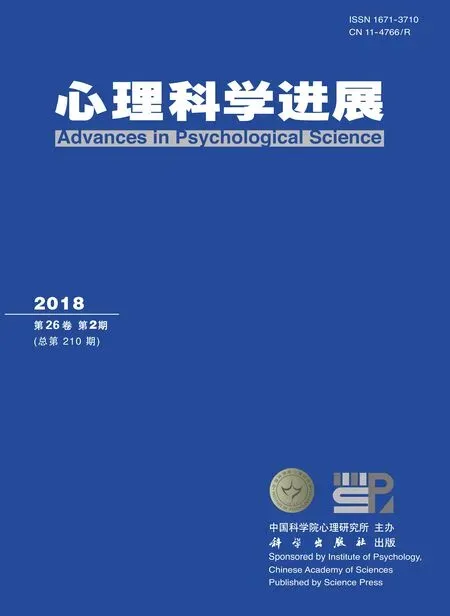交流語言認知特征*
張恒超
(天津商業大學法學院心理學系, 天津 300134)
1 前言
交流(communication)是以語言為核心媒介的一種社會人際互動方式, 即基于某種目的, 交流者圍繞特定任務和對象進行溝通, 以最終做出分類、命名、解釋和抉擇的行為操作或處置; 交流的典型特征表現于, 語言媒介的核心性、交流目的的共同性、交流認知的互動性、交流行為的合作性, 以及交流責任和個人責任的共存性(張恒超,2013; Krauss & Weinheimer, 1964)。語言心理學中交流語言的使用可以概括為:語言發出者或指導者(director)產生某個表述, 語言接受者或操作者(matcher)對表述做出符合交流共同意圖和期望的解讀; 語言在交流者間不斷輪換和傳遞思想的過程(語義), 功能性地解決了合作的共同任務或問題(語用) (Brown-Schmidt, 2009; Christensen,Fusaroli, & Tylén, 2016)。與個體頭腦中的個體語言不同, 個體私語是個體自我認知過程的媒介;而交流語言更表現為社會性特征, 是一種以交流者共同理解與使用為基礎的社會行為, 主要通過深思熟慮的過程驅動, 交流者不僅要時刻監控交流語言過程, 還要時刻參照同伴的知識、思想并推理同伴即時發生的心理狀態(信念、假設、期望、意圖、態度和情緒等), 該過程有助于彼此交流認知的共享性和交流合作行為的限制性、共同性(Shintel & Keysar, 2009; Zwaan, 2014)。
歸納而言, 以往交流語言認知研究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交流語言內容特征(Arnold, Kahn,& Pancani, 2012; Davies, 2011; Rogers, Fay, &Maybery, 2013), 交流語言加工理論(Brown-Schmidt,2009; Galati, 2009; Shintel & Keysar, 2009), 交流語言與非語言因素的關系(Brennan, Chen, Dickinson,Neider, & Zelinsky, 2008; Goldin-Meadow & Alibali,2013; Shintel & Keysar, 2009; Vanlangendonck,Willems, Menenti, & Hagoort, 2013)。接下來將分別一一述評。
2 交流語言內容特征
交流語言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對象的“指示性”,指示性表述是基本的交流語言單元之一, 方便于交流者指代、挑選特定的對象; 從交流語言內容特征出發, 交流語言的指示性表現為對對象普遍或基本語義的傳遞, 以及交流語言針對交流目的和任務的適當性表達(Davies, 2011)。Grice (1975)指出交流語言的內容最終依賴并決定于交流合作規則, 交流者彼此期望并假定對方會遵守該規則,因為規則的違反將導致雙方交流關系的不和諧性,隨之交流語言的表達和理解均會產生“言外之意”。進一步而言, 交流語言內容特征影響到其在特定交流情境下的現實功能性, 具體表現在交流語言內容的信息特征(張恒超, 2016; Arnold et al.,2012; Rogers et al., 2013); 受交流情境影響的同伴特定性特征等方面(張恒超, 2013; 張恒超, 陰國恩, 2014; Levinson, 2016; O’Carroll, Nicoladis,& Smithson, 2015)。
2.1 交流語言信息量
交流語言信息特征的探討不可避免地需要考慮語言使用的情境, 即從語用觀點出發, 交流語言絕不是在一個語境完全自由的條件下發生的;交流情境的制約性決定了語言發生和理解過程中的推理特征。交流語境一方面涉及的因素非常廣泛, 如交流者經驗的共同性、共同或相似的團體成員身份、交流視覺信息、交流目的和方式、交流的時間、交流者間的物理距離等等; 另一方面交流語境具有相對不穩定性, 尤其是在陌生的交流情境下, 交流語言受到交流者認知互動和交流時間進程的影響(張恒超, 2017; Davies, 2011; Sacchi,Riva, & Aceto, 2016)。Clark 和 Marshall (1981)提出一個概括而廣泛的交流情境因素的分類系統,具體將“交流情境因素”分為:交流對象物理特征的共享性、交流語言、交流中的非語言信息; 并強調交流情境限制下的語言發生和理解過程是交流者間認知和行為共享性水平的表現之一。鑒于交流情境限制下的語言認知過程和個人私語認知過程的差異性, 研究者指出交流語言信息量的特征具體表現在:相對于交流對象的內涵或特征,交流語言信息過多(如詳細的描述性的解釋和說明)、信息過少(如使用缺少外延限定性的上位概念表達對象, 或者對象及其功能等特征的表述不完整)、信息恰當; 簡言之, 交流語言信息量的評定決定于交流情境因素明顯或不明顯對于語言表述的限制性(Arts, Maes, Noordman, & Jansen, 2011;Gatt, Goudbeek, & Krahmer, 2010)。
對于交流語言信息量, 以往一部分研究支持交流語言是對交流對象的一種精細化解釋, 包含了相對于恰當內容或指稱的過多信息(Galati &Avraamides, 2013; Heller, Gorman, & Tanenhaus,2012); 過多信息有助于向交流同伴傳遞多種溝通線索, 也有助于消除語言交流中的歧義, 并且過多信息的呈現不會導致交流同伴對說者心理狀態和交流意圖做額外的精心推論, 相反, 交流者對語言信息過少或不足的敏感性相對更高, 其拒絕與同伴就信息不足的語言達成認知共享(Katsos,2009)。Vanlangendonck等(2013)強調這是由于實際交流中交流者并非總能很好地排除個人信息,而實現與同伴對等共享信息所導致的, 設想“如果語言表達者看到尺寸不同的兩個瓶子, 而此時同伴看不到小的瓶子; 或者交流者面對的是一個大瓶子和一個小茶杯”, 表達者要求對方“遞給我‘大’瓶子”, 盡管這樣的語言表述可能會使同伴略顯遲疑, 但并不妨礙交流意圖的正確傳達。反之,如果交流情境中存在兩個不同特點的瓶子, 僅說“遞給我瓶子”, 同伴將無法做出正確的判定。另一部分研究則認為交流語言相對于特定情境中對象的準確描述而言, 表現出信息過少的特征, 因為交流語言的信息過多將會引發交流者對情境的無關性推理, 比較推理是人們日常交流中的一種習慣性思維過程和特點(Sedivy, 2003; Snedeker &Trueswell, 2004); 相比之下, 從交流情境的豐富性特點出發, 交流者間的互動和溝通不僅通過語言實現, 還通過與特定情境有關的多種可能線索來實現, 交流情境線索會自覺地為交流者提供語言之外的參照信息和反饋信息, 因而導致語言信息相對簡約(Hanna, Tanenhaus, & Trueswell, 2003;Nappa & Arnold, 2014; Zwaan, 2014)。比如, 當Alex對Elise說“I need to sign this”, Elise可能即時預測到并清楚對方的需求, 相應作出“取筆”行為的傾向性, Alex接下來可能表述“Can you hand me the pen?”, 交流者間這種語言之外的互動默契性(交流情境限制、非語言信息的反饋等), 決定了Alex不需要對筆的特征、用途等做深入澄清, 甚至語言表達中會進一步弱化“the pen”的語音強度,甚至只表達“Can you hand me” (Arnold et al., 2012)。
兩相對照, 以往研究觀點之爭一定程度上源于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差異性:首先, 考慮到交流認知研究的相對復雜性和實驗控制的困難性, 交流實驗任務傾向于設計的簡單而明確。如, 交流的靶對象和比較對象同時呈現, 交流者通過語言辨別并指導對方完成挑選等操作(Buz, Tanenhaus,& Jaeger, 2016); 從大量非對象中搜尋目標對象,像O-in-Qs視覺搜尋任務(Brennan et al., 2008); 先將交流對象(如積木)命名和分類, 再語言指導同伴組建特定模型(Markman & Makin, 1998; Sidera et al., 2013); 交流者指導同伴完成生活物品的特定擺放任務(Arnold et al., 2012)等等。此類設計便于實驗控制和變量指標的探查, 并且交流語言的記錄和分析相對容易, 共同性在于交流者明確而有針對性的對實驗任務中的特定對象做出說明和界定, 這樣對象內涵的參照是明確的, 可以直觀解釋交流語言內容是信息過多還是信息過少, 亦或信息恰當。但是, 不足在于這類實驗任務難以展現現實交流行為的時間進程和語言變化性、豐富性。Bezuidenhout (2013)指出交流語言認知的分析應考慮兩點:一是任何交流行為都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二是簡單的視覺情境范式便于聚焦于即時交流語言的分析, 但不利于反映交流語言的動態變化性, 這類似于“照片”和“錄像”的關系。因此, 交流語言信息量分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于:時間動態進程中語言建構過程是以即時交流為基礎而不斷增量形成的, 換言之, 交流語言信息量分析應同時兼顧即時交流任務和長時交流任務的影響差異(Brown-Schmidt & Heller, 2014)。
其次, 簡單對立交流語言信息過多和信息過少, 即以交流對象的概念內涵為參照, 特定交流語言或者屬于信息過多、或者屬于信息過少, 二者必居其一。這實際上是實驗任務簡單化的必然結果。例如, 將“菊花”和“康乃馨”同時呈現, 交流語言描述“康乃馨”為“花”則屬于信息過少, “紅康乃馨”屬于信息過多, “康乃馨”屬于信息恰當(Barr& Keysar, 2002)。然而, 現實中的交流情境和交流對象可能更為復雜, 在一些人們不熟悉的情境中,交流語言內容可能同時表現出信息過多和信息過少, 簡言之, 針對交流對象, 語言內容可能既提及一些與交流目的無關的信息, 而表現出信息過多, 同時也可能未充分解釋與交流目的有關的對象信息, 而表現出信息過少。比如上例, 還可以假定出現一種不同的語言表述“漂亮的花”, 針對特定對象并置的交流語境, “漂亮”是多余信息, “花”由于無法區分“康乃馨”和“菊花”, 因此信息不足。這樣一個回合的交流語言可能僅僅表現出信息過多或過少, 也可能同時表現出信息過多和過少。Grice (1975)的交流語言信息規則(Grice’s Quantity maxim)兼顧到了交流者間的互動合作關系, 參見表1。Grice重點指出這些規則遵循了語言交流者間的合作性、互動性, 合作依賴于這些規則的期望, 這不僅限定了交流語言的信息特征, 同時有助于交流者互動合作中對于交流語言隱含義的解釋和共享。
總之, 交流語言和個人私語本質上是不同的,交流中不僅語言和對象間存在特定的限定關系,而且語言解釋的限定性也源于特定的交流情境、同伴間的互動關系等(Beyer & Liebe, 2015; Duran& Dale, 2014)。因此, 交流語言不是一種靜態語言,其核心在于表現為一種動態性的思想聯系和交流者間的認知碰撞與契合, 其在交流進程中將隨時因交流情境、認知變化等而相應調整, 特定交流中語言信息量恰當性的評定, 不是一個孤立標準的參照過程, 而需要充分考慮交流任務特征、交流目的、同伴特點等多種因素。

表1 Grice的交流語言信息規則
2.2 交流語言內容的“同伴特定性”
交流語言研究的另一個焦點是語言內容的“同伴特定性”特點, 這涉及到交流情境下交流者利用同伴身份特征限制語言內容信息。當前研究者一致認為, 交流語言的同伴特定性特征來自于交流中的“聽者設計” (audience design)現象。“聽者設計”表現為交流活動中, 交流者為了聯合彼此認知形成目標的共同理解, 而表現出的不斷調整彼此語言和行為的現象, 同伴特定調整的目的在于形成共同的交流基礎(共同的交流信念、期望、意圖等) (張恒超, 2013; Brown-Schmidt, 2009;Rogers et al., 2013; Shintel & Keysar, 2009)。具體在交流語言方面表現出說者根據聽者的需要設計語言內容, 聽者參照與說者的“約定”解釋語言信息。同伴特定性特征使交流語言以高共享的形式溝通信息, 節省認知努力并提高交流效率和準確性, 比如, 語言“參照慣例”的形成和認知協調作用(Brown-Schmidt, 2009; Malt & Sloman, 2004;Rogers et al., 2013); 參照慣例是交流者間彼此共享和理解的特定語言表述, 其一旦形成則相對穩定地存在特定交流者的語言互動中, 并在之后相似的交流情境下在特定交流者間重復出現, 語言的相對穩定有助于彼此特定理解的一致性(Barr &Keysar, 2002)。Brennan和Clark (1996)的研究指出參照慣例的交流認知含義在于, 暗示了交流同伴間以一種特定方式概念化并約定對象, 這種同伴特定性交流語言有助于雙方交流認知和行為的協調一致, 該研究要求交流被試雙方觀看一些抽象圖形, 比如交流者采用“ballerina”而不是“skater”稱呼一個對象, 這種約定不僅體現彼此認知的共享性, 實際上包含了特定同伴間對對象形狀細節的某種理解, 進而影響交流記憶的編碼過程, 當相似交流情境再次出現時, 交流語言的“同伴特定性”特點將穩定保持, 表現為參照慣例在特定交流者間的重復運用。
“同伴特定”交流語言是交流者概念化交流對象而形成的靈活協議, 其映射和包含了特定情境和同伴信息, 沒有參與交流的個人無法分享該信息; Markman和Makin (1998)發現, 在經歷了2-5天的延遲后交流者在記憶中仍然保留該特定語言表述, 說者再次使用該表述時聽者表現出對相應知識狀態的敏感性。交流者對于同伴特定交流語言的這種敏感性被進一步證實僅發生在真實交流情境之下, Yu, Schermerhorn和Scheutz (2012)的研究中交流條件分兩種, 與真人交流, 與人形模型交流, 同時分析了眼動數據、交流語言, 結果發現只有在與真人交流條件下, 交流被試的語言才表現出同伴特定特征, 并且被試對同伴的偶發細微行為表現出敏感性, 表明特定語言內容中包含了真實交流情境下彼此共同的交流經歷和記憶。Horton (2007)先安排被試分別根據兩個實驗同謀給出的類別線索產生類別樣例; 接下來, 一個同謀在場的條件下再分別完成圖片命名任務, 發現圖片對象與在場同謀有關聯時命名更快且語言簡潔。Duff, Hengst, Tranel和Cohen (2006)以七巧板為實驗材料, 采用遺忘癥患者為被試, 發現他們一定程度上也對交流同伴曾經發生的交流語言敏感, “同伴特定語言”的記憶包含了無意識的成分。總之, 以上共同證明了:交流情境下語言“同伴特定”效應受真實交流中的一般認知過程的調節。
伴隨著交流語言“同伴特定”特征的探討, 部分研究著眼解釋“同伴特定”特征發生的認知過程和特點, 即“同伴特定”信息什么時候進入交流語言認知加工系統的。由此產生了兩種研究觀點和解釋:一種觀點認為, 同伴特定信息在交流的最早時刻就開始引導語言加工決策, 該觀點支持交流語言加工“基于限制”的理論:交流發生時語言即受到情境中雙方特點、對象基本表征等因素的限制(Bezuidenhout, 2013; Metzing & Brennan,2003)。另一種觀點則認為, 交流初期交流者的語言加工以自我為中心, 交流進程不斷發展, 雙方逐漸根據情境因素對語言內容作出調整, 表現出“同伴特定性”特征, 即交流語言認知加工過程的“兩階段模型” (Bromme, Jucks, & Wagner, 2005;Brown-Schmidt, 2009; Pickering & Garrod, 2004):交流即時加工期間交流者重視語境信息將導致認知的繁重性, 因此不會成為交流語言一般加工策略的一部分, 因此交流之始, 語言加工表現出自我為中心, 交流互動角色的感知將延遲影響語言加工, 這有助于解釋交流前期交流者對同伴交流語言產生的“感知不恰當”現象(Keysar, Barr, Balin,& Brauner, 2000)。
歸納而言, 兩種觀點爭論的焦點在于交流語言認知過程中個人認知和共享認知間的關系問題,以往以及未來對于該問題的深入探查, 有助于理解交流者如何使用交流語言加工系統, 和個人私語加工系統比較交流語言加工系統更為復雜、靈活和多樣化, 包含了交流互動的不同子過程:語言發生、語言理解、記憶提取、互動心理狀態、交流認知執行和監控等。誠然, 交流語言認知是復雜的, 這種復雜性決定了交流語言字面上并不總是清晰的、明確的, 交流語言歧義的消除和信息共享離不開“同伴特定性”的交流背景, 也就是說, “同伴特定性”使得語言交流認知負擔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給交流互動的參與者, 因此, 交流者對于模糊語言的限制性解釋, 不一定必須訴諸于認知資源需求和精心的意識推理, 這最終使特定交流者間的語言溝通更為協調和節省, 反之, 如果缺乏“同伴特定性”背景的支持, 交流語言認知加工過程將更為困難和復雜。
3 交流語言加工理論
在交流語言內容特征討論的基礎上, 圍繞著交流語言的“同伴特定性”特征或交流語言的“聽者設計”過程和特征, 以往研究對交流語言加工過程做出了一定的解釋。盡管語言可以是個體頭腦中認知過程的媒介, 但從本質上而言, 交流言語行為本身具有社會性, 其以共同理解與使用為基礎, 語言使用成為共同活動和彼此間認知協調的一種形式(Gahl & Strand, 2016; Rogers et al., 2013)。
換個角度而言, 交流語言“同伴特定性”特征的形成或交流語言的“聽者設計”過程, 即是語言交流過程中交流者間意義和認知的協調過程。那么, 該協調過程是怎樣實現的呢?一種可能是語言認知協調主要通過深思熟慮或精心推理的過程驅動, 該過程需要交流者互動中有意識考慮同伴的思想、觀點、共同的經歷等, 并嘗試推理同伴的心理狀態, 如假設、信念、期望、意圖等。在這一過程中交流者需要精心規劃自己的語言, 并精心解釋同伴的語言, 使得彼此交流中的共同背景和基礎顯得尤為重要, 共同交流基礎可以限制彼此語言產生和理解的過程——說者參照與特定聽者的共同基礎和背景來設計語言, 聽者通過假定說者遵從了“聽者設計”原則以解釋和理解語言(Shintel & Keysar, 2009)。很容易理解交流語言的有意識的“聽者設計”過程提供了一個有力且有效的途徑以最大化提高交流語言的監控和調節, 從而最小化降低錯誤的語言交流。然而, 有研究者也指出, 如此精心的語言認知推理過程需要交流者時刻保持語言加工的不斷更新, 這既耗費時間, 對認知要求又高(Epley, Keysar, van Boven, & Gilovich,2004)。相比之下, 交流者間語言認知的成功高效協調可能借助了交流情境中的特定談話模式, 即語言認知協調利用了交流互動中多種可能的情境線索。與完全有意產生交流語言信號不同, 這些交流情境線索不是有意被關注和考慮以適應聽者信息需要的, 該過程表現為一種無意識認知加工過程(Brown-Schmidt, 2009; Roberts, Langstein, &Galantucci, 2016)。這樣, 關于交流語言認知加工過程特征形成了兩種理論解釋:交流語言加工的經典理論(Classical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交流語言互動校準模型(The Interactive Alignment model) (Clark & Carlson, 1982; Hellbernd & Sammler,2016; Rogers et al., 2013)。
3.1 交流語言加工的經典理論
交流語言加工的經典理論認為, 交流語言加工過程涉及認知策略性調整, 交流者互動中有意識計劃和設計語言, 以滿足聽者的信息需求, 該過程是外顯的(Brown-Schmidt, 2009; Clark & Wilkes-Gibbs, 1986; Rogers et al., 2013)。經典理論認為交流語言互動中彼此的換位思考是語言信息策略性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們通常會考慮到自己聽者同伴的信念和知識經驗來建構語言信息, 互動中聽者的反饋會使他們進一步調整和完善語言的這種聽者設計, 隨著彼此交流語言共享性水平的不斷提高, 交流者間的合作努力逐漸降低, 典型的表現為語言信息簡潔性提高, 最終, 交流者間會形成一個特定的語言交流模式——語言參照慣例, 語言參照慣例標示了特定交流者間如何標識共同的交流對象(Brennan & Clark, 1996; Clark &Wilkes-Gibbs, 1986; Jacquette, 2014; Kronmüller &Barr, 2015)。
從交流語言加工的經典理論出發, 交流語言的聽者設計過程和同伴特定性特征源于交流者互動中更高的注意水平、動機水平, 這有助于思維發散和啟發, 因此可以假設:意識性、策略性的語言認知加工過程將受到認知資源的限制和影響,特定任務條件下交流語言加工帶來的認知資源的過度損耗將給交流活動帶來不利影響(張恒超, 陰國恩, 2012; Berezan, Yoo, & Christodoulidou, 2016;Brennan et al., 2008; De Ruiter, Bangerter, & Dings,2012; Epley, Keysar, VanBoven, & Gilovich, 2004;Koppensteiner, Stephan, & J?schke, 2016)。Brennan等(2008)將交流因素分為注視信息、語言信息, 借助眼動儀創設了“共享注視(交流者可以在自己屏幕上即時觀察對方任務搜索中的注視信息)”“共享語言”“共享語言和注視”不同的交流方式, 在O-in-Qs交流任務中發現, 共享注視交流方式下的任務效率最高, 盡管共享注視方式現實生活中難以實現, 但研究結果證實了交流語言導致交流者間更高的認知協調“成本”。張恒超和陰國恩(2012)的研究通過創設三種復雜性學習材料, 發現語言交流學習效率顯著受到任務材料復雜性或難度的影響, 具體和個人學習比較表現出, 隨著材料復雜性的提高語言交流學習效率由顯著更高轉變為顯著更低。De Ruiter等(2012)進一步研究指出交流情境下非語言信息互動始終相伴于語言互動同時發生, 即非策略性、非意識性調整過程導致了策略性、意識性語言交流的相對贅余, 由于語言交流意識性過程對于認知資源的要求較高,因此, 交流者能夠借助非語言信息實現交流活動時, 則不借助或較少借助語言交流。
其實從交流價值出發相對容易理解和接受交流語言加工經典理論所強調的“意識性”“策略性”加工特點。交流互動中語言表現出的“同伴特定性調整”根本上是在于強有力地避免或最小化交流的錯誤性, 這需要交流進程中時刻保持意識的清醒和不斷更新, 即對于交流語言的即時監控; 如此精心的加工和推理使得交流者時刻注意區分和監控自我認知過程和交流同伴認知過程的異同性和變化性, 這是交流者間語言協調性建立的基礎,因此, 交流語言加工過程的意識性特征對交流者的認知要求更高。有研究從不遵從或打破交流語言“同伴特定性”規則的交流中探查發現, 如果交流者中的一方在交流互動過程中試圖打破或違背語言參照慣例, 交流同伴會明確認為說者在向自己傳達交流對象發生了變化或更換的信息, 將有意識重新更新和協調原有的認知(Yu et al., 2012)。Rogers等(2013)研究的實驗 1中采用了一種不同的設計思路, 檢驗人們是否策略性地設計交流語言以滿足聽者的信息需求, 以語言信息長度操作性定義交流語言認知努力程度, 具體而言, 要求被試寫出對一系列抽象形狀對象的描述, 語言解釋分別是針對自己和其他人, 結果針對他人設計的語言信息內容顯著更長, 以期為交流同伴提供更為準確的語言理解, 即人們策略性地為交流同伴設計語言信息, 以滿足其信息需求。
誠然, 交流語言加工經典理論對于交流語言認知加工過程的“意識性”解釋是正確的, 但是,這并不能絕對排除交流語言認知加工中的“非意識性和非策略性”過程的同時存在。交流語言認知和個人私語的最大不同在于交流情境以及交流者間認知互動過程的現實存在, 言語過程的社會性特征也決定了交流語言認知加工過程不可能在一個忽視情境和同伴的單純情形下發生, 研究也證實隨著交流進程的不斷發展, 交流者對交流情境中非語言信息的利用程度會越來越高, 對于交流語言的依賴性相對降低, 對于非語言信息的利用使得交流者的交流效率顯著提升, 且認知負擔顯著減少, 此時, 交流者對于交流語言認知加工的監控程度隨之降低, 但是彼此會保持交流語言模式的相對穩定和簡潔, 以保證不對交流互動認知和行為形成額外干擾, 這種情形下, 語言參照慣例的穩定性不完全代表語言信息的準確性, 而更多代表了一種交流特定情境和特定同伴的關聯性。
3.2 交流語言互動校準模型
交流語言互動校準模型認為, 交流者語言的生成是自動的、內隱的, 是在特定交流情境下交流者間互動引發的非策略性結果。交流語言加工經典理論強調語言認知加工過程是一個策略性的、自上而下的個人層面設計過程; 而交流語言的互動校準模型則強調語言認知加工過程是非策略性、自下而上的互動層面設計過程(Epley, Morewedge,& Keysar, 2004; Ferreira & Dell, 2000; Rogers et al.,2013)。
相比之下, 交流語言互動校準模型認為, 在語言加工過程中人們幾乎不會有意識注意聽者的觀念、知識、期望等, 交流過程中說者采用特定的句法結構和表述方式, 主要是為了自覺易化交流互動中內容的溝通表達(Ferreira & Dell, 2000);同樣聽者對于交流語言的解釋過程也是自覺完成的, 而不需意識性推理說者的信念、意圖等(Epley,Morewedge, & Keysar, 2004)。同樣, 互動校準模型針對性的指出語言參照慣例形成和持續使用的過程也是非策略性的, 具體而言, 交流中交流者表現出默契使用相同的語言信息、語言表達方式甚至語調等, 說者生成的特定語言表述會自動激活聽者的相似表征, 而這些表征會自動保持在交流者的記憶之中, 當交流回合持續發展, 說者變為聽者時, 這些表征傾向于重復使用以方便雙方的共同理解, 因此, 與策略性、意識性、認知損耗的經典理論觀點不同, 互動校準模型強調非策略性互動和認知節省性(Pickering & Garrod, 2004)。與經典理論一致之處在于, 互動校準模型也認為說者對聽者的信念可以調節交流語言生成過程, 例如, 當說者知曉他們是在和電腦而不是人玩一個圖片命名游戲時, 出現了更復雜的語言生成過程,原因是其認為自己是在與一個沒有能力的計算機進行交流互動, 說者對聽者交際能力的信念和推斷影響了語言互動過程和特征(Branigan, Pickering,Pearson, McLean, & Brown, 2011; Green, Wilhelmsen,Wilmots, Dodd, & Quinn, 2016), 表明說者對于聽者的知識信念會影響交流語言表達方式和信息內容的設計。兩種理論的區別在于:經典理論認為“聽者設計”過程是意識性、策略性的; 而互動校準模型認為是非意識性、非策略性的。
Rogers等(2013)更傾向于整體上認可, 交流語言加工過程可能存在意識性和策略性調整, 也同樣有可能存在非意識性和非策略性的調整, 考慮到經典理論和互動校準模型對于交流語言聽者設計是個體層面的策略性調整還是互動層面的非策略性調整的爭論焦點, Rogers等(2013)認為澄清問題的關鍵在于分析交流互動對于交流語言認知加工的影響程度和特征, 因此, 從兩個方面改進實驗設計以檢驗該問題, 一是對比限制互動交流任務和自由互動交流任務, 二是變化交流情境中互動人數的規模, 這兩方面與交流互動性直接相關, 研究采用七巧板拼出的圖案作為實驗材料。
實驗1設計了一個限制互動任務, 要求被試描述一系列圖片; 并告知被試, 他們的描述是針對自己、或針對1個、4個、9個其他人。結果表明,被試為他人設計的信息均顯著長于為自己設計的,聽者數量不影響語言描述, 支持了經典理論的策略性語言認知加工觀點。實驗2采用了真實互動交流的實驗任務, 結果發現聽者群體規模顯著影響交流語言加工的努力程度, 聽者數量越多, 描述語言越多, 這是互動條件下的非策略性調整過程,聽者數量增加導致了社會互動的增多, 自覺誘發交流語言加工變化以適應小組合作交流情境。
綜合歸納而言, 交流語言互動中策略性調整和非策略性調整均是真實存在的, 這是源于交流情境中個人認知和公共認知的共存性特征, 各研究爭論的焦點在于實驗設計、實驗任務等的差異性, 并且各研究在強調一種交流語言認知加工特征的前提下, 并不完全否認另一種語言認知加工特征的伴隨性。此處, 本文認為在真實交流互動情境中, 語言加工的非策略性認知過程更為突出,因為真實交流中交流情境因素對交流語言潛在的影響性更大, 如交流者人數、非語言交流方式的多寡(注視、面部表情、手勢等)、交流任務的復雜性程度等等, 這決定了自下而上的互動層面設計過程更為顯著突出; 反之, 在控制性不同的限制互動交流情境中, 語言加工的策略性認知過程相對顯現出來, 因為互動水平的降低直接導致策略性的、自上而下的個人層面設計過程更為突出。誠然, 現實交流情境下, 交流的目的、交流方式、交流者間的人際特征等均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性, 既然是交流互動就一定存在非策略性語言認知加工過程, 同時既然交流者間交流中的心理狀態、個體認知、對交流活動的認識程度等差異也是真實存在的, 就一定也存在策略性語言認知加工過程。
4 交流語言與非語言因素的關系
交流中語言的顯著地位得到研究者們的一致認可, 與個人語言認知過程相比, 交流語言認知加工的復雜性和靈活性更大, 這一方面在于互動語言自身, 另一方面也在于交流中存在眾多非語言交流媒介, 并且和語言交流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作用。在實驗研究條件下對于非語言因素的控制程度使得交流實驗情境的自然性不同, 這一直也是研究者爭論的一個重要方面(Bezuidenhout,2013; Brown-Schmidt & Heller, 2014; Overall &McNulty, 2017)。
從現實生活中的語用觀點而言, 交流語言的發生發展和理解始終是處于一個相對語境背景之下, 交流情境特征是多樣化的并貫穿在語言交流的全程中, 譬如, 交流者的個性特征和社會群體身份, 已有的經驗和知識背景, 彼此的交流目的、時空條件(面對面交流、遠程交流等)等, 這些因素綜合影響交流語言認知加工過程(張恒超, 2013;張恒超, 陰國恩, 2014; Barnett & Johnson, 2016;Buz et al., 2016; Clark & Wilkes-Gibbs, 1986; Rogers et al., 2013)。誠然, 交流語言的現實自然觀察最為真實, 然而現實交流復雜性極高, 并且隨著交流時間進程的發展交流語言認知受非語言因素的不確定性影響可能即時發生各種變化, 因此, 無實驗控制的交流語言認知研究是困難的, 交流實驗控制允許研究者相對科學界定和解釋交流語言認知特征, 有助于揭示語言認知加工的一般特征和交流語言使用的一般特點(Brown-Schmidt, 2009;Clark & Schaefer, 1989)。
在語言心理學的實驗研究領域中, 當前大量研究主要關注了兩類非語言因素:語言交流中的對象共享性(Gahl & Strand, 2016; Galati, 2009; Vesper,Schmitz, Safra, Sebanz, & Knoblich, 2016; Yoon,Koh, & Brown-Schmidt, 2012; Zwaan, 2014)和表情共享性(手勢表情由于具有顯著的非語言交流特征和可觀察可量化性, 成為研究的熱點) (Beaudoin-Ryan & Goldin-Meadow, 2014; Goldin-Meadow, 2015;Graziano & Gullberg, 2013; Koppensteiner et al., 2016;Novack & Goldin-Meadow, 2015; Perniss, ?zyürek,& Morgan, 2015)。
影響交流語言認知的一個非語言因素是“交流對象的共同可視性”。當前研究較一致認為, 在語言交流過程中, 交流對象物理感知特征的共享將導致交流語言的顯著簡化, 然而, 對象感知特征和交流情境中的表情因素不同, 其不具有獨立的交流性, 所以語言的簡化會使交流者彼此間認知和行為的協調效率和水平顯著降低。Galati (2009)的研究采用了卡片匹配任務, 研究將對象可視性作為研究變量, 結果發現雙方是否共享交流卡片的感知特征影響交流語言認知加工的過程和特征,具體而言:交流者彼此共享交流卡片感知特征的條件下, 交流語言的信息顯著更少。Vesper等(2016)的實驗任務是交流者雙方通過語言交流同步移動屏幕中的相應對象, 一種條件下彼此語言交流溝通和操作中不能同時觀察對方的屏幕內容(“hidden condition”), 另一種條件下語言交流中可以即時觀察同伴的屏幕內容(“visible condition”), 結果也證實:語言交流對象可視條件下, 交流語言顯著更為簡單, 信息更為片段化。
關于交流對象共享性對語言認知的影響特點,研究者們一致解釋為, 交流語言認知在即時交流過程中時刻包含和體現了交流者的自我認知和與同伴共享信息的公共認知, 兩者對交流語言認知過程的影響特征和程度取決于實際的交流情境特點(Crossley, Woodworth, Black, & Hare, 2016; Gahl& Strand, 2016; Yoon et al., 2012; Zwaan, 2014)。具體而言, 當交流者彼此共享交流對象的物理特征時, 表面上這似乎有助于易化語言交流過程, 而實際上交流對象的共同可視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流性, 并不能獨立促進交流者的交流公共認知過程,相反這種共同可視性相對增強了交流者對交流對象的自我認知過程, 因此, 交流對象的共同可視性在弱化交流語言認知加工過程的同時, 也弱化了語言媒介的交流性, 由于無法提高和促進交流的公共認知過程, 而使得交流者間語言認知和交流行為的協調過程相應增長。
影響交流語言認知的另一個非語言因素是“交流表情的共享性”, 表情是相對概括和可以從不同方面進行精細劃分的, 這對于交流語言認知實驗研究相對而言的困難的, 部分研究以語言交流過程中“同伴可視性”來整體上操作性定義表情變量:Arnold等(2012)研究中交流者面對面交流,實驗要求一方(說者)語言指導對方(聽者——研究者同謀)對物品做出指定的擺放, 研究者控制了聽者(操作者)的任務反饋行為, 以探討指導者語言認知加工受聽者反饋性表情的影響特征, 結果發現:如果聽者在說者語言指導前預先拿起了相應物品, 說者的語言表達變得快速而簡潔。Brown-Schmidt (2009)的研究通過控制交流情境的真實性也證實“真人交流互動情境下”交流語言中包含了特定交流者間豐富的經歷和經驗信息, 相反,“非真實互動情境下” (人與錄音交流)語言的交流共享性特征減弱甚至消失。Yu等(2012)則將“與錄音交流”替換為相對形象的“與等比例人偶交流”,結果仍然證實, 真實互動情境下交流者語言溝通中表現出對同伴表情細節或細微動作的顯著敏感性。O’Carroll等(2015)進一步在同一交流任務中將交流過程分為前后兩個部分:交流前半期交流者面對面交流, 后半期進行無表情交流(以隔板分開), 交流前后期語言對比發現:前半期的交流語言顯著更為簡潔而高效, 后半期的交流語言則更為精細和全面。Koppensteiner等(2016)從交流語言理解性的角度也證實, 當政客的演講視頻表情豐富時, 有助于聽者觀點的理解和接受, 反之亦然。概括而言, 表情整體上是一個復雜而綜合的交流系統, 在實際交流過程中其不僅輔助和促進語言交流, 而且其自身也具有一定的獨立交流性,因此對于語言發生過程和理解過程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當前, 大量研究關注了手勢表情對交流語言認知的影響特征, 交流中手勢表現出和語言的共同發生特點, 甚至先天盲人的語言交流也會伴隨大量的手勢表達(Novack & Goldin-Meadow, 2015)。語言交流中手勢的使用一方面輔助揭示語言中的不明確信息, 鑒于語言認知加工的“深思熟慮”特征, 手勢有助于澄清語言的模糊表達, 或傳遞不便于語言解釋的信息; 另一方面手勢不是交流語言的附屬品, 其擁有獨立的交流特征, 手勢表達的自動化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語言加工的認知負荷(Goldin-Meadow, 2015; Goldin-Meadow & Alibali,2013)。關于交流語言和手勢關系特點的研究形成了兩種觀點:其一, 手勢的表達方式雖然不同于語言, 但在特定交流活動中兩者相伴發生, 多角度表達相關聯的交流信息。例如, Graziano和Gullberg (2013)實驗發現:在易于交流的任務中,交流語言的流暢發生伴隨著手勢的自然連貫表達;反之在難以交流的任務中, 交流語言模糊、贅余,且表達斷續, 手勢也不自然不連貫。交流的“相互作用模型” (the interface model)認為, 手勢和語言分別由行動發生器和信息發生器計劃、啟動和支配, 兩者發生機制雖然不同, 但交流中卻彼此互動和限制(Kita & ?zyürek, 2003)。其二, 手勢具有獨立的交流性, 可以促進語言交流。比如Alibali,Kita和Young (2000)以及Pine, Bird和Kirk (2007)發現語言流暢表達時, 手勢發生相對減少; 反之,手勢頻繁發生, 以彌補語言交流的不完整性和不準確性, 手勢獨立的交流性表現出來。交流的“詞匯性手勢生成模型” (lexical gesture process model)認為, 手勢可以配合語言交流表達共同的交流意圖, 但是手勢不是簡單的語言伴生品, 手勢的發生并不總是滯后于語言的發生, 其發生、發展過程甚至影響著語言的發生和理解——激活說者的語言發生過程和聽者的語言理解過程, 并且手勢可以使交流者共享語言之外的交流信息(Alibali &Nathan, 2012)。
隨著科學心理實驗技術的應用, 如眼動儀,使得交流注視成為實驗控制因素之一。交流注視優勢假說(gaze advantage hypothesis)認為, 在某些交流情境下, 如陌生對象交流、視覺空間交流任務等, 交流語言難以清晰而完備地解釋對象, 并且語言信息的展開需要耗費時間和認知努力, 這便形成一個交流語言弊端, 相反此時共享的注視信息更具有交流優勢(Hanna & Brennan, 2007)。Brennan等(2008)在“O-in-Qs”視覺搜索任務中, 借助眼動儀使交流者彼此實現注視共享, 證實了搜尋任務中, 與共享語言相比共享注視交流的顯著高效性; 當僅語言交流時, 交流者語言不僅復雜且表述時間更長。Hanna和Brennan (2007)強調尤其是在交流早期共享的注視信息提供了消除交流語言歧義的直觀線索。然而, 現實交流中, 僅依靠注視的沉默交流不是普遍現象; 并且, 依賴眼動儀實現的共享注視在現實中難以完全實現(雖然像交流者共同鑒賞一副畫作等交流情境可以發生,但注視信息不可能像眼動儀那樣實現直觀呈現)。
張恒超(2017)研究中在以往探討基礎上進一步系統性設計了交流情境中的語言和非語言因素,以交流語言為核心, 通過因素遞加分別創設了“共享語言、共享語言+對象、共享語言+對象+表情”三種交流方式, 探查了交流情境中雙方共享因素對參照性交流雙方學習的影響特征, 結果表明:參照性交流學習過程中“共享語言+對象+表情”方式下交流者學習水平最高, 集中表現于低成績一方的學習效率更高, 交流雙方學習協調水平最高; “共享語言方式和共享語言+對象+表情方式”下被試選擇性注意水平顯著高于“共享語言+對象方式”。從各因素彼此影響關系的角度證實:在交流語言互動的基礎上, 表情共享性顯著促進參照性交流認知和行為水平, 對象共享性則表現出不利性影響效應; 研究進一步指出表情對于交流語言認知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交流信息的互動溝通過程, 還表現在表情傳遞了語言之外的交流情緒特征(如:肯定、否定, 支持、拒絕以及期望鼓勵等), 這對于交流雙方語言信息的辨別、確認等互動過程至關重要。
綜上, 交流語言認知過程是復雜的、多變的,語言交流的意識性、策略性認知過程和非語言交流的非意識性、非策略性認知過程并行不悖且相互依存。語言是交流的核心媒介和典型特征, 以語言為媒介的交流認知協調過程, 需要交流者精心推理彼此的認知狀態并時刻更新, 該策略性調整過程對認知資源提出了相對更高的要求, 與此相應, 非語言媒介的非策略性協調過程來自于交流情境中的多種自發性線索, 這樣就形成了交流認知中語言和非語言媒介間的相輔相承和相互制約的特征, 因此, 這決定了交流認知過程是一個相對龐雜的系統, 以往研究已經嘗試做了一定的研究探索, 一方面, 應當客觀對待各研究結果的多樣性和分歧性, 另一方面, 隨著該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入, 應始終考慮到交流語言認知加工過程的核心特征和媒介作用, 交流語言認知的進一步探查和分析不應離開非語言因素客觀存在的多樣化交流背景。
5 啟示與展望
如上所述, 交流語言認知過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對于交流語言認知特征的探討應持一個相對開放的態度:
特定交流條件下交流語言內容的信息特征,信息過多和信息過少可能同時存在和發生, 不應該也不必要絕對化排斥一方; 盡管交流語言認知過程和個人私語的認知過程存在明顯的差異性,交流語言認知過程帶有典型的“同伴特定性”特征,當存在交流情境便會存在交流語言的公共認知過程, 但是顯然, 交流語言的“同伴特定性”特征不意味著交流者彼此間交流語言認知的絕對同一性,因此任何交流情境下, 交流者的語言認知過程也必定帶有個人認知過程的獨有特征; 語言交流是一種典型的社會行為, 言語行為具有社會性, 交流語言內容是思維過程的一種反映, 因而交流語言的意識性、策略性是客觀存在的, 但也并不應該完全排斥語言認知過程中的無意識認知過程;交流語言認知的復雜性一定程度上源于交流互動認知的復雜性, 語言是交流互動的核心媒介而不是唯一媒介, 因此交流語言認知的探查, 不應該忽視非語言因素的潛在影響作用, 及與語言認知過程的相互作用關系。
在此基礎上, 未來研究應進一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 交流語言認知研究和傳統的個人語言認知研究不同, 其復雜性源于交流情境的多因素共存性和關系的復雜性, 鑒于這種實驗復雜性和語言分析的相對困難性, 以往研究的通常思路是針對性的設計實驗, 集中探查某種單一因素對于交流語言認知的影響, 這有助于語言認知探查和影響因素的評估, 未來研究應在此基礎上嘗試采用多因素依次疊加的方式設計多重實驗條件, 這些因素可以以漸增的方式依次加入實驗設計中,不僅有助于檢驗每個限制因素對交流語言認知的影響程度, 還有助于根據多因素疊加的方式考查彼此間的影響性質和特征。
其次, 對于交流語言認知機制的最終解釋,需要考慮交流實驗情境的自然性和現實性, 只有在相對良好外部效度的實驗情境下, 才有助于真實解釋和對照“即時交流”和“長時交流”中語言加工過程的復雜性, 才有助于真實總結出語言認知加工中各種限制因素的影響等級和關系。交流語言互動的語用特征, 更注重實驗研究結果的現實遷移性, 這是交流語言認知研究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這將有助于更為廣泛和真實的理解現實中社會情境下的交流互動認知特征, 有助于理解教育教學情境下的交流合作學習認知過程, 也有助于解釋和理解隨著科技的發展, 不同現實交流情境下的交流語言認知共同性和差異性(如電話交流、網絡交流; 多媒體互動教學; 廣告宣傳等等)。
最后, 雖然交流語言認知和傳統的個人語言認知比較具有研究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但是共同性在于均涉及到認知過程的不同層次(感知、注意、記憶、思維、個性等等), 未來研究仍然需要從多種思路出發, 進一步擴展研究設計, 在多種子加工過程基礎上完善語言認知過程的全面理解。并進一步嘗試借助眼動儀、腦成像技術等提供多角度的同步證據。
張恒超.(2013).參照性交流中的“聽者設計”.心理發展與教育, 29(5), 552?560.
張恒超.(2016).參照性交流和個人情境對學習雙方選擇性注意的影響.心理學探新, 36(2), 123?127.
張恒超.(2017).共享因素對參照性交流雙方學習的影響.心理學報, 49(2), 197?205.
張恒超, 陰國恩.(2012).關系復雜性對關系類別間接性學習的影響.心理發展與教育, 28(2), 193?200.
張恒超, 陰國恩.(2014).參照性交流中的非策略性認知過程.心理研究, 7(5), 7?14.
Alibali, M.W., Kita, S., & Young, A.J.(2000).Gesture and the process of speech production: We think, therefore, we gesture.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15, 593?613.
Alibali, M.W., & Nathan, M.J.(2012).Embodiment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vidence from learners’and teachers’ gestures.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21, 247?286.
Arnold, J.E., Kahn, J.M., & Pancani, G.C.(2012).Audience design affects acoustic reduction via production facilitation.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3), 505?512.
Arts, A., Maes, A., Noordman, L., & Jansen, C.(2011).Overspecification facilitates object identifica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 43(1), 361?374.
Barnett, M.D., & Johnson, D.M.(2016).The perfectionism social disconnection model: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mmunication style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94, 200?205.
Barr, D.J., & Keysar, B.(2002).Anchoring comprehension in linguistic precedent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46(2), 391?418.
Beaudoin-Ryan, L., & Goldin-Meadow, S.(2014).Teaching moral reasoning through gesture.Developmental Science,17(6), 984?990.
Berezan, O., Yoo, M., & Christodoulidou, N.(2016).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n communication style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for hotel loyalty programs.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echnology, 7(1), 100?116.
Beyer, H., & Liebe, U.(2015).Three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measure the social context dependence of prejudice communication and discriminatory behavior.Social ScienceResearch, 49, 343?355.
Bezuidenhout, A.(2013).Perspective taking in conversation:A defense of speaker non-egocentricity.Journal of Pragmatics,48, 4?16.
Branigan, H.P., Pickering, M.J., Pearson, J., McLean, J.F.,& Brown, A.(2011).The role of beliefs in lexical alignment:Evidence from dialogs with humans and computers.Cognition, 121(1), 41?57.
Brennan, S.E., Chen, X., Dickinson, C.A., Neider, M.B., &Zelinsky, G.J.(2008).Coordinating cogniti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shared gaze during collaborative search.Cognition, 106(3), 1465?1477.
Brennan, S.E., & Clark, H.H.(1996).Conceptual pacts and lexical choice in convers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2(6),1482?1493.
Bromme, R., Jucks, R., & Wagner, T.(2005).How to refer to‘diabetes’? Language in online health advice.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9(5), 569?586.
Brown-Schmidt, S.(2009).Partner-specific interpretation of maintained referential precedents during interactive dialog.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61(2), 171?190.
Brown-Schmidt, S., & Heller, D.(2014).What language processing can tell us about perspective taking: A reply to Bezuidenhout (2013).Journal of Pragmatics, 60, 279?284.
Buz, E., Tanenhaus, M.K., & Jaeger, T.F.(2016).Dynamically adapted context-specific hyper-articulation: Feedback from interlocutors affects speakers’ subsequent pronunciation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68?86.
Christensen, P., Fusaroli, R., & Tylén, K.(2016).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shaping constituent order in emerging communication systems: Structural iconicity, interactive alignment and conventionalization.Cognition, 146, 67?80.
Clark, H.H., & Carlson, T.B.(1982).Hearers and speech acts.Language, 58(2), 332?373.
Clark, H.H., & Marshall, C.R.(1981).Definite reference and mutual knowledge.In A.K.Joshi, I.A.Sag, & B.L.Webber (Eds.),Elements of discourse understanding(pp.10?6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rk, H.H., & Schaefer, E.F.(1989).Contributing to discourse.Cognitive Science, 13, 259?294.
Clark, H.H., & Wilkes-Gibbs, D.(1986).Referring as a collaborative process.Cognition, 22(1), 1?39.
Crossley, L., Woodworth, M., Black, P.J., & Hare, R.(2016).The dark side of negotiation: Examining the outcomes of face-to-face and computer-mediated negotiations among dark personalitie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91, 47?51.
Davies, C.N.(2011).Over-informativeness in referential communication(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
De Ruiter, J.P., Bangerter, A., & Dings, P.(2012).The interplay between gesture and speech in the production of referring expressions: Investigating the tradeoff hypothesis.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4(2), 232?248.
Duff, M.C., Hengst, J., Tranel, D., & Cohen, N.J.(2006).Development of shared information in communication despite hippocampal amnesia.Nature Neuroscience, 9(1), 140?146.
Duran, N.D., & Dale, R.(2014).Perspective-taking in dialogue as self-organization under social constraints.New Ideas in Psychology, 32, 131?146.
Epley, N., Keysar, B., van Boven, L., & Gilovich, T.(2004).Perspective taking as egocentric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3), 327?339.
Epley, N., Morewedge, C.K., & Keysar, B.(2004).Perspective taking in children and adults: Equivalent egocentrism but differential correc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6), 760?768.
Ferreira, V.S., & Dell, G.S.(2000).Effect of ambiguity and lexical availability on syntactic and lexical production.Cognitive Psychology, 40(4), 296?340.
Gahl, S., & Strand, J.F.(2016).Many neighborhoods:Phonological and perceptual neighborhood density in lexical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162?178.
Galati, A.(2009).Assessing common ground in conversation: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and physical co-presence on early planning(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Galati, A., & Avraamides, M.N.(2013).Collaborating in spatial tasks: How partners coordinate their spatial memories and descriptions.Cognitive Processing, 14(2), 193?195.
Gatt, A., Goudbeek, M., & Krahmer, E.(2010).A new computational model of alignment and overspecification in reference production.Poster presented at Architectures and Mechanism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AMLaP), York.
Goldin-Meadow, S.(2015).From action to abstraction:Gesture as a mechanism of change.Developmental Review,38, 167?184.
Goldin-Meadow, S., & Alibali, M.W.(2013).Gesture’s role in speaking, learning, and creating languag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4, 257?283.
Graziano, M., & Gullberg, M.(2013).Gesture production and speech fluency in competent speakers and language learners.InTilburg Gesture Research Meeting (TiGeR)2013.Tilburg University.
Green, T., Wilhelmsen, T., Wilmots, E., Dodd, B., & Quinn,S.(2016).Social anxiety, attribute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self-disclosure across private and public Facebook communication.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8, 206?213.
Grice, H.P.(1975).Logic and conversation.In P.Cole & J.Morgan (Eds.),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pp.41?58).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anna, J.E., & Brennan, S.E.(2007).Speakers’ eye gaze disambiguates referring expressions early during face-to-face conversa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7(4),596?615.
Hanna, J.E., Tanenhaus, M.K., & Trueswell, J.C.(2003).The effects of common ground and perspective on domains of referential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9, 43?61.
Hellbernd, N., & Sammler, D.(2016).Prosody conveys speaker’s intentions: Acoustic cues for speech act percep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8, 70?86.
Heller, D., Gorman, K.S., & Tanenhaus, M.K.(2012).To name or to describe: Shared knowledge affects referential form.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4(2), 290?305.
Horton, W.S.(2007).The influence of partner-specific memory associations on language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picture naming.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22(7), 1114?1139.
Jacquette, D.(2014).Collective referential intentionality in the semantics of dialogue.Studies in Logic, Grammar and Rhetoric, 36(1), 143?159.
Katsos, N.(2009).Evaluating under-informative utterances with context-dependent and context-independent scales: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In U.Sauerland& K.Yatsushiro (Eds.),Experimental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pp.51?73).London: Palgrave.
Keysar, B., Barr, D.J., Balin, J.A., & Brauner, J.S.(2000).Taking perspective in conversation: The role of mutual knowledge in comprehension.Psychological Science, 11(1),32?38.
Kita, S., & ?zyürek, A.(2003).What does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in semantic coordination of speech and gesture reveal?: Evidence for an interface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thinking and speaking.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48(1), 16?32.
Koppensteiner, M., Stephan, P., & J?schke, J.P.M.(2016).Moving speeches: Dominance, trustworthiness and competence in body mot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94, 101?106.
Krauss, R.M., & Weinheimer, S.(1964).Changes in reference phrases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of us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A preliminary study.Psychonomic Science, 1,113?114.
Kronmüller, E., & Barr, D.J.(2015) Referential precedents in spoke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3, 1?19.
Levinson, S.C.(2016).Turn-taking in human communication–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rocessing.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 6?14.
Malt, B.C., & Sloman, S.A.(2004).Conversation and convention: Enduring influences on name choice for common objects.Memory & Cognition, 32(8), 1346?1354.
Markman, A.B., & Makin, V.S.(1998).Referential communication and category acquisi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7(4), 331?354.
Metzing, C., & Brennan, S.E.(2003).When conceptual pacts are broken: Partner-specific effects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referring expression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49(2), 201?213.
Nappa, R., & Arnold, J.E.(2014).The road to understanding is paved with the speaker’s intentions: Cues to the speaker’s attention and intentions affect pronoun comprehension.Cognitive Psychology, 70, 58?81.
Novack, M., & Goldin-Meadow, S.(2015).Learning from gesture: How our hands change our minds.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7(3), 405?412.
O’Carroll, S., Nicoladis, E., & Smithson, L.(2015).The effect of extroversion on communication: Evidence from an interlocutor visibility manipulation.Speech Communication,69, 1?8.
Overall, N.C., & McNulty, J.K.(2017).What type of communication during conflict is beneficial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1?5.
Perniss, P., ?zyürek, A., & Morgan, G.(2015).The influence of the visual modality o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Insights from sign language and gesture.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7, 2?11.
Pickering, M.J., & Garrod, S.(2004).Toward a mechanistic psychology of dialogue.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7(2), 169?190; discussion 190?226.
Pine, K.J., Bird, H., & Kirk, E.(2007).The effects of prohibiting gestures on children’s lexical retrieval ability.Developmental Science, 10(6), 747?754.
Roberts, G., Langstein, B., & Galantucci, B.(2016).(In)sensitivity to incoherence in human communication.Language & Communication, 47, 15?22.
Rogers, S.L., Fay, N., & Maybery, M.(2013).Audience design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during group discussion.PLoS ONE, 8(2), e57211.
Sacchi, S., Riva, P., & Aceto, A.(2016).Myopic about climate change: Cognitive style, psychological distance,and environmentalism.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5, 68?73.
Sedivy, J.C.(2003).Pragmatic versus form-based accounts of referential contrast: Evidence for effects of informativity expectations.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32(1),3?23.
Shintel, H., & Keysar, B.(2009).Less is more: A minimalist account of joint action in communication.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1(2), 260?273.
Sidera, F., Serrat, E., Serrano, J., Rostan, C., Ca?o, A., &Amadó, A.(2013).Let’s share perspectives! Mentalistic skills involved in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3), 325?352.
Snedeker, J., & Trueswell, J.C.(2004).The developing constraints on parsing decisions: The role of lexical-biases and referential scenes in child and adult sentence processing.Cognitive Psychology, 49(3), 238?299.
Vanlangendonck, F., Willems, R.M., Menenti, L., & Hagoort,P.(2013).The role of common ground in audience design:Beyond an all or nothing story.Post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the Production of Referring Expressions: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omputation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Reference the (PRE-CogSci 2013), Berlin,Germany.
Vesper, C., Schmitz, L., Safra, L., Sebanz, N., & Knoblich, G.(2016).The role of shared visual information for joint action coordination.Cognition, 153, 118?123.
Yoon, S.O., Koh, S., & Brown-Schmidt.(2012).Influence of perspective and goals on reference production in conversation.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 699?707.
Yu, C., Schermerhorn, P., & Scheutz, M.(2012).Adaptive eye gaze patterns in interactions with human and artificial agents.ACM Transactions on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Systems, 1(2), 1?25.
Zwaan, R.A.(2014).Embodiment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Reframing the discuss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18(5), 229?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