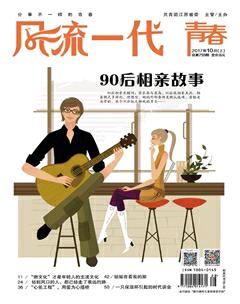“破廟專業戶”連達,千里獨行手繪古建
白露


在眾多的古建筑愛好者中,有人喜歡用攝影的方式來記錄和珍存古建,有人喜歡用文字來記載和描述古建,而像連達這樣,作為一個最底層的打工者,一個人,一支鋼筆,千里獨行手繪古建的,還真是不多見。
十多年來,連達利用業余時旬在山西、山東、河北等地尋訪古建和進行古建筑的鋼筆寫生,并集結出版《尋訪山西古廟》《觸摸,廟宇》《山西古建寫生》等書,在國內文化界和建筑界引起深刻的反響。一見鐘情成“破廟專業戶”
今年38歲的連達,生長于黑龍江,現居大連,網名小虎。因醉心手繪古建,被人戲稱為“破廟專業戶”。
18歲時,因為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連達揣著3000元錢,開始了自己的第次獨自旅行。首站,他選中了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一周,后聽聞山西有很多古建,于是買了一張車票,直指平遙。
第一次站在雙林寺、鎮國寺等古建筑前,連達全身的血液都開始興奮和沸騰,感覺自己似乎被召回到了久遠的家園。置身于這種古樸傳統而幽雅的環境里,身心無比舒暢。他突然意識到“這才是我們自己的文明瑰寶,是我生追尋的目標。”在平遙城墻下,他繞行了好幾圈,根本不想走,便租了輛自行車,日日到附近村莊里轉悠。
當時連達還是個窮學生,手中連最廉份的傻瓜相機也沒有,雖然對眼前的古建筑群極度喜愛,可連張照片也無法留下,不知如何宣泄對古建筑的情感。忽然想到自己還會畫上兩筆,他找了幾張白紙、一支鉛筆,憑著美術課上的那點水平,顧不得好不好看,把看到的古建勾勒出個樣子,只想離開這里后,可以拿出來看看。后來,隨著對素描的不斷自學和研究,他終于用鋼筆手繪這種方式開辟了一條獨特的記錄古建之路。
走出城市的鋼筋水泥叢林,回到詩歌般悠然的古老意境中,描繪心中的美好圣殿,沒有什么比這更令連達陶醉的了。平時他就找些底層的工作養活自己,只要有長點的假期就往有古建筑的地方跑。
連達這種邊游覽邊繪畫的旅行方式,早期其實有些漫無目的,北京、河北、山東、山西都畫過些。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山西最終成為他系統手繪古建的不二之選。連達說“三晉的歷史緊緊聯系著中華的興衰,山西因而遺留下了眾多文物古跡,現在全國僅存的四座唐代木構建筑都在山西境內,僅存的四處五代時期木建筑中有三處在山西,這里元代以前古建筑的保有量超過全國總量的70%,而明清兩代的古跡更是浩如煙海,難以計數。擁有這樣無可比擬的優勢,想領略中國古建筑的風采只能是非山西莫屬了。”
每年,連達都要在山西逗留兩個月,家里人乜習慣了,一到時間,如果他還在家里,就奇怪,怎么這么乖,不去山西了?
千里獨行追趕古建
消逝的速度
每次出行,連達都會攜帶一只重達50多斤的背包,裝有各種用具、畫具以及衣物等必備品,用老鄉的話講,比袋子白面還沉。他背著行囊奔走在山西的廣大農村,在沒有班車又租不到車的時候徒步十幾里直至鞋底脫落,在荒村被成群的野狗追擊過……
一些廟荒廢已久,里面的草都長得及腰深了,廟門都坍塌淤埋了。這時候他只能翻墻,甚至從墻洞鉆進去,從破爛的門扇下面爬進去,真是想盡了切辦法。2013年的夏天,連達在高平和陵川 帶數次慘遭暴雨天氣,人被淋得全身濕透倒不說,接連不斷的雨天實在是影響寫生,只能望天興嘆。后來,他索性將手繪工作改在了每年的春秋兩季行動。
有次,連達曾經從某個鄉鎮路向北,一天跑了五個村,沒有座廟能進得去,相當遺憾。有的村民認為他把那些滄桑破敗的古廟畫下來會給當地抹黑,拒絕他的到來。不過相比這些,一些古建筑和古村落日益殘毀消逝的現狀更叫連達傷心和無奈。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著名古建筑受到有效保護以外,大量散落在鄉間名氣不大的古建筑正面臨著毀滅和凋零,很多古廟宇處于無人保護自生自滅的狀態,有些古建筑雖然立著國家級或省、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實際的境遇也是相當堪憂的,漏水塌方,構架腐朽,缺乏維修和保護的現象比較常見。一些地方自籌資金進行維修,卻因為缺乏對古建筑深入的了解相懂得古建筑維修的專業人員參與,把好端端有幾百年歷史的古廟修成了嶄新如影視外景地般的假古董,實際上這樣的維修也是種毀壞。
很多廟宇,連達屢次前往都無法得見,等過段時間再來,卻已經被粗劣翻修成慘不忍睹的模樣,甚至坍塌、被燒毀。將其畫下來不僅滿足了連達對古建筑的喜愛,更多的是種追趕古建筑消逝速度的努力。連達更愿意將自己的作品當作份給歷史的禮物,若干年后,那些廟沒了,那些樹死了,那份蒼涼消失了,依然可以從畫中感知那時那刻的細節以及建筑的無窮魁力。
情系古長城,給現在和未來的交代
這些年,連達的事跡也引起了文化界的關注。201 7年6月,連達的第三本書《尋訪山西古廟》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不僅收錄連達尋訪晉東南、晉南1 09處古寺廟繪制的1 85幅寫生畫,還有十余萬字的行記,記錄著他的行跡和心跡他匆匆走過的黎明和黃昏,他眼里古建筑所在的山川、地貌和人,還有他對自己摯愛的山西古建筑保存現狀的擔憂、惋惜。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李志榮說,連達并非科班畫家,也沒有受過系統的古代建筑教育,卻是目前中國描繪山西古建筑彘好的畫家。他對山西古建筑年代、類型、風格特征刻畫之準確、生動和細致,令人贊嘆。
2017年5月6曰,由中國建翁學會和北京建筑大學聯合主辦的“帶路”歷史建筑攝影·手繪藝術展在中國建筑師作品展示館開幕,連達的20多幅手繪作品被選中參展。他還被吸納為中國文物學會會員、中國長城學會會員。
連達對于長城也是癡迷的。長城打動他的更多是那種磅礴的氣勢,那種蒼涼到讓人心疼的殘缺之美,那種孤懸于荒野山巔不為人知的神秘,激發連達不斷地去接近它、探究它、了解它、感受它。他多次背著數十斤重的帳篷等露營裝備穿越在古長城上,把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山西的大部分明代長城都走過了。許多野長城修筑在人跡罕至的崇山峻嶺,想要到達并不容易,披荊斬棘風餐露宿是家常便飯。
隨著對長城了解的深入和行走長度的積累,連達發現長城的現狀實在不容樂觀。現存的長城本身已經是劫后余生,殘垣斷壁,更嚴重的是許多人肆意破壞拆改長城建筑,盜挖長城磚石,盜賣珍貴的碑刻、匾額和文字磚。
從第一次接觸古長城到現在,十多年間,連達拍攝和記錄了大量的長城現狀資料,手繪了不少長城的作品,搜集和制作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散佚長城碑刻拓片以及文字磚拓片,也把自己青春的記憶留在了滄桑的古長城上。他曾經帶著妻子(那時候尚在戀愛)走了許多地段的古長城,后來他們的婚禮也是在長城上舉行的。那種患難與共的經歷是常人無法企及的寶貴財富,也是妻子至今理解和支持他的堅實基礎。
令人欣慰的是,連達以他精湛的技藝和行者的實踐,感動和吸引了很多的人為他點贊,與他同行。連達也正在走進學校課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他的粉絲,加入他的行列。連達選擇做 名行者,行萬里路,繪萬卷圖,就是為了記錄曾經的中國的真經用木、磚、石、瓦在自然山川間建構的精神世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