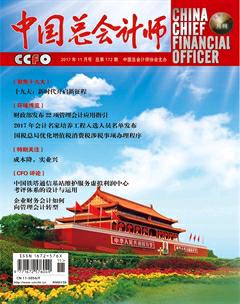高成本的形成動因及“降成本”面臨的困難
前文分析了我國企業面臨的高成本問題,闡述了“降成本”的內涵、外延和重要意義,回顧了“降成本”工作取得的巨大進展。下面就我國企業高成本的形成動因、“降成本”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探討。
一、高成本的形成動因
我國企業高成本的現實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有經濟發展階段的原因,有市場本身的原因,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企業內部的原因。從我國發展階段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來看,導致成本趨勢性上升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能過剩、杠桿率高、庫存多
“三去一降一補”的“三去”都是和成本關聯在一起的:產能嚴重過剩意味著有大量的無效成本,無效成本不能帶來增值;杠桿率很高意味著財務費用很重,成本自然升高;庫存多顯然導致資金周轉慢,成本也會升高,這些都會導致高成本。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由這些問題導致的成本是經濟成本,是資源錯配的成本。僵尸企業就是典型的資源錯配現象,大量寶貴的社會資源消耗在這些企業里,產能不能有效發揮出來;杠桿率高實際是資金的配置出了問題。從經濟成本的角度來說,這還帶來很高的機會成本。社會資源是有限的,不能用在合適的用途上,實際上就是資源錯配,經濟運行成本就會很高。當前企業成本高,與資源錯配密切關聯,與市場扭曲有深刻聯系。
(二)研發投入不足
研發的短缺會導致成本的增值效率低。企業如果沒有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新模式,一方面,生產過程消耗就會很高,單位產品的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管理費用等,都會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成本的增值率,或者說轉化率低,帶來的附加值低。這樣的成本是低效成本,甚至可以說是無效成本。這同時產生兩個結果:企業成本高、產品附加值低。因此,企業技術進步緩慢導致的這種高成本、低利潤,是研發不足的結果,是長期跟隨、模仿形成路徑依賴而產生的結果。靠跟隨、模仿而生存、發展的時代已經從整體上結束了。沒有研發,沒有創新,企業成本就會越來越高,利潤越來越薄,直至被淘汰而退出市場。從現實來看,越是重視研發的企業,日子越是好過;相反,陷入困境的企業,都是不重視研發的企業。這也證實了研發與企業成本的相關性。
(三)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也會帶來高成本。我國在不到20年的時間之內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一般用長達幾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時間。我們在還沒有富起來的時候就進入老齡化社會了,而這些養老的成本是由全社會來負擔的,最終是由企業來承擔的。不僅如此,老齡化的另一面是適齡勞動力減少,勞動力市場發生逆轉,從買方市場變為賣方市場,企業雇工不愁的時代結束了,用工荒時常發生,工人的工資越來越高。當這種現象變為一種普遍現象時,不只是企業雇工成本上升,而且還會衍生擴大,使各項企業成本同時上升,如人工貴導致物流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銷售費用上升,等等。
(四)資源匱乏
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生產、生活所需的資源不斷增長,我國自有資源已遠遠滿足不了發展的需要。相對于我國的生產規模和生活水平,我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當資源供應越來越依賴于國際市場時,必將導致資源成本上升。例如我國石油、鐵礦石對外依存度超過60%,國內的資源不夠,要到國際市場上去購買,這不僅決定于國際市場供求狀況,還取決于國際政治格局以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其中既有市場風險,也有國際政治風險,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國內資源不足,國際資源爭奪加劇,全球風險水平上升,整體導致資源使用成本提高。
(五)環境污染
環境污染帶來的是環境成本。環境成本一部分是由社會來承擔的,付出的是大眾健康代價和政府治理代價;一部分是由企業來承擔的,轉變為企業的成本。隨著環保要求越來越高,企業用于環保方面的支出會不斷增長,企業承擔的環境成本也就越來越多,以達到生產不污染,或者盡可能少污染環境,降低社會成本。這就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的過程。環境成本內部化,體現多個方面,如繳納環保稅、環境保護的研發投入、環保設備購置、更換工藝流程,等等。在其他條件不變時,這方面的成本開支多了,企業利潤就減少了。有的企業因此而陷入虧損,最終退出市場;有的企業會被迫轉型升級,轉向清潔生產,得以生存發展。我國生態環境污染日積月累,已經形成很高的污染存量,對現有企業來說,意味著再也不能通過外部化的方式來轉嫁環境成本。環境污染的存量現在不得不靠政府大量投入來治理,而環境污染的增量治理勢必將由企業來承擔。企業承擔的環境責任越來越大,其承受的環境成本也將越來越高。
(六)社會誠信缺失
社會誠信缺失,整個經濟社會運行成本就會全面提高。比如契約意識淡薄,簽了合同不履行,導致企業之間的相互拖欠增加、法律訴訟增多。經濟運行是一個大系統,企業與企業之間通過投入產出鏈、供應鏈、價值鏈緊密地拴在一起,相互依存。其中一個企業不守契約,會影響一串企業。若企業普遍不講誠信,則企業之間的關系將會面臨不確定性程度的整體上升,風險擴大,交易成本會大大增加,由此導致企業高成本。
融資成本高,就與誠信不足直接相關,這導致過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擔保、認證和公證,這些都不是免費的,最終都會添加到融資成本的賬單上。
勞資關系同樣如此,無論是資方、還是勞方,一旦雙方之間契約關系因社會誠信而受到不良影響,不只是給企業帶來成本,也會給收入分配、居民收入增長以及消費需求帶來不確定性影響。政府的誠信水平對經濟社會運行的不確定性影響,具有類似于基礎貨幣那樣的乘數效應。若政府誠信水平下降,會增大公共風險,導致生產、生活成本全面提升。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誠信缺失,信用不足,風險上升,最終都會轉化為企業成本。
資源錯配的成本、養老的成本、資源的成本、環境的成本以及誠信缺失帶來的成本,等等,之所以會越來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變遷滯后。這里所說的制度變遷滯后是相對于風險而言的,制度變遷跟不上風險的衍生、擴大,而風險會轉化為生產、生活的成本。前面所說的六個方面的成本,其實都是風險凝結沉淀的結果。今天的結果,是因為昨天沒看到風險,制度沒有有效跟進,風險沒有及時化解,甚至風險還在衍生擴大。風險水平的整體上升,全社會的整體成本就會上升,微觀主體的成本也就會水漲船高。endprint
事實上,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風險社會”,全球經濟及我國的經濟也進入到“風險經濟”狀態,這也是經濟新常態的一個基本特征。
從定價的角度來看,過去說的定價就是按照歷史成本來定價,或者說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而現在的定價機制已經改變,是按照風險來定價的,或者說是以未來風險為基礎的。企業的成本也不是過去的歷史成本,而是轉化為風險成本。按照歷史成本定價與按照未來風險定價,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定價機制。一旦按照風險來定價,就不是以前那種所謂的供求規律——供大于求就會降價,供小于求就會漲價,而是供求雙方的風險判斷,風險上升,就會是漲價,風險下降,則會是降價。比如現階段的資金是相對過剩的,但是當銀行給企業貸款的時候,首先要評估企業的風險狀況,中小企業風險大,利率就要高,大企業風險低,利率就低。除此之外還有抵押,抵押要評估,擔保還要有再擔保,這就產生了交易費用,所以整個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就很高。
當定價機制不是按照歷史成本,而是按照未來風險在定價的時候,風險水平全面上升,這就意味著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會變貴。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實體經濟在內的成本就都會提高。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風險社會意味著有很多的風險要內部化,比如說老齡化的風險要企業承擔,就是社保繳費,導致企業的成本上升。還有環境污染的風險要內部化,也會導致企業的成本上升,不能讓企業去污染,而讓政府來治理。社會領域的風險都在內部化,內部化就意味著轉化為企業的成本,這些都會導致成本上升。社會誠信水平下降,信用風險普遍增高,所有企業的成本都會由此而增加。
對于經濟、社會各種各樣風險的擴大,也就是不確定性的增加,會使整個經濟的運行成本上升,會使整個實體企業的成本上升,由此進入了一個高成本的時代。
要降低整個社會的公共風險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創新,推進制度變遷,使制度和風險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匹配,充分發揮制度及時防范化解風險的功能,避免風險累積和集聚。
二、“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項難度大、影響廣、挑戰性強的系統工程。
由于降成本牽涉方面眾多,容易受到內外部復雜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導致降成本的任務仍然很艱巨。
當前存在多頭監管、監管過多、重復監管等現象,加重了下一級政府部門和企業的工作負擔和運行成本。
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方面,一些銀行采取大額授信權限上收總行的集中管理模式,推行“一刀切”的限貸政策,抽貸、斷貸現象嚴重,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緩解,“短貸長用”現象非常普遍,帶來了不小的金融風險。
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多式聯運和信息化水平偏低、貨物中轉裝卸消耗過大、運行效率低等問題,也亟待關注與有效解決。
總體來看,政府降成本目前面臨著高成本時代降成本的有限性,與階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實體經濟企業健康發展更需要標本兼治的長效機制,特別是在完善金融組織體系、推動物流模式創新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等方面。
三、“降成本”存在的主要問題
“降成本”雖然取得了重要進展,但也面臨不少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降低稅負和財政收入減少的矛盾
2015年財政支出增速15.8%,財政收入增速8.4%,二者增速差7.4個百分點,創多年以來新高。2016年1-10月,公共財政收入增速為5.9%,公共財政支出為10.0%,收支增速差4.1個百分點。隨著減稅和穩增長力度加大,財政收支矛盾可能進一步加大。
(二)降低勞動力成本與擴大內需的矛盾
中國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占比偏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但降低勞動力成本會降低收入增速,不利于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盡管在減稅、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和矛盾,但供給側改革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在減稅、簡政放權、推動要素改革和發展直接融資等方面,政府可作為的空間仍然很大。
四、“降成本”的誤區
1.認為所有成本都要降
不少企業將降成本理解為所有成本都要降,所有的成本都能夠下降,有些地方政府也將降成本理解為做“減法”,就是將各個環節的成本都降下去,這就容易陷入“成本普降”的誤區。事實上,有些成本非但不能降,反而基本趨勢是上升的。比如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這需要加強環境保護,意味著以前在企業外部由社會承擔的一部分成本要內部化,即更多地由企業去承擔環境成本,那么,對企業來說就不能放松對排污和環保的要求,否則就會陷入環境成本也要降低的誤區。降成本需避免陷入“成本普降”誤區,政策性降成本不能妨礙正常的市場競爭,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相結合。
2.以行政方式降成本
不少企業把降成本簡單理解為“政府為企業”,寄希望通過降成本來擺脫企業面臨的生產經營困境,一些地方政府確實也推出了“一對一”的救助式幫扶政策。政府在出臺降成本政策時,也沒有“一盤棋”考慮,而多是通過下指標、定任務,以行政方式“運動式”降成本,導致“政府沖在第一線,企業不急政府急”的異化現象。事實上,企業才是降成本主體,政府可通過更好地發揮自身作用,為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財科院認為,政府降成本舉措要尊重市場規律,以引導為主,推動實現企業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
3.為降成本而降成本
不少企業管理者將降成本的目標界定為“車間班組”式的目標,即通過采購、生產、銷售等環節控制成本,為降成本而降成本。無論企業還是政府,應首先明確降成本的目標,不能為了降成本而降成本。企業降成本的目標應是將各個環節成本與整體成本結合起來,提高成本利潤率和成本轉化率,提高盈利能力和附加值。
4.孤立地降成本
成本是系統性的,無論從企業各項成本構成來看,還是從上下游企業來看,抑或是從政府、企業與居民關系來看,成本都是相互關聯的,孤立地降成本會導致“抓住一點,不計其余”,易引發新的問題。
經濟運行本身具有系統性,一個環節既會是供給方,也會是需求方,不能孤立地去看待降成本問題。當前,學術界和實際工作部門,都有將降成本拆分為各個單項成本分不同的部門進行的傾向和做法,這些降成本措施是基于一種直線的、單維的、片面的“線性思維”方式,微觀層面和短期來看能夠降低一些成本,但從宏觀層面和長期來看效果不佳,企業應盡量避免進入這種誤區,應以非線性思維,整體、系統地看待降成本問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