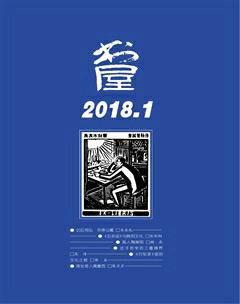文史擷珍(三題)
善哉,“一個人”
被譽為“第一個占領近代科學重要位置的中國人”──數學大師陳省身晚年答記者問時說:“大家都鼓吹交流,講科學需要合作,需要相互幫忙,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對。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個人做出來的。一個人的創見是自己努力和靈感的結晶,很少是一群人討論的結果。”錢穆說:“學問之事,貴能孤往”(“孤云”是其為數不多的筆名之一)。錢鍾書說“學問是荒江野嶺中幾個素心人彼此間的事”,流布甚廣。一個頂尖數學家,一個國學大師,一個“學者中的學者”,在業內皆“第一流”。無論他們的夫子自道,還是一生的學術歷程,其“第一流的工作”都“是一個人做出來的”。“第一流”的業績和“一個人”的“孤往”,大有關系存焉。
抗戰時,錢穆隨西南聯大南遷到昆明,但他有意在省城外圍的小縣擇居而住,有課務才趕到昆明,平時便在此獨居著書,近五十萬字的《國史大綱》歷時一年而成。陳寅恪到此訪友,嘆道:“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后來錢穆回蘇州,借耦園隱居一年,撰成五十萬言《〈史記〉地名考》。晚年他回憶這兩段經歷,自稱“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其“孤往”之深,連陳寅恪也為之嘆服。
笨功夫
現代詞學奠基人夏承燾,晚年回顧學術道路時說:“笨是我治學的本錢。”在其眼里,讀書沒有捷徑,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才能漸入佳境。夏老對“笨”字有一別開生面的解釋:“笨”,從“竹”從“本”,頭上頂著竹冊(冊是串好的竹簡,即古代書籍),這是教人勤奮用功。
在楚辭學、敦煌學上卓有建樹的姜亮夫,晚年在《自傳》中說:“最近一位友人給我的信上說‘先生甘淡泊,耐勤勞,為學術貫通,治學求謹嚴,老老實實作學問……云云。贊賞我的話,慚不敢當……實在只是一個‘笨字了得。”姜老治學,肯下笨功夫。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在巴黎看到流散出去的敦煌文物和經卷,用最笨的方式抄錄、描摹。很長一時期,每天從上午抄到晚上博物館關門,午飯喝白開水吃點干面包充饑。完成此項工程時,其視力下降了六百度!真是“一個‘笨字了得”。
如今學界“聰明人”滿天飛,肯下笨功夫治學的“笨伯”越來越少。胡適說:“這個世界聰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數人。”錢鍾書說:“越是聰明人,越要懂得下笨功夫。”聰明人肯下笨功夫,多不同凡響。
“刪詩如殺賊”
如今,出書的門檻越來越低,自費出版很常見。有人在編選自家作品集時,敝帚自珍,覺得自己的文章篇篇都好,編書時不肯割愛。結果所出之書貌似厚重,但因少精選反而顯得很“輕薄”。抗戰時期有“浙西詩人”之稱的俞楚石,自編《西苕溪詩稿》。地方官劉能超在為其作序時說:“顧茲編悉經其嚴自汰剔,刪詩如殺賊。”可見詩人編選時自我把關很嚴。因為“傳人吟句不須多,至性文章永不磨”。
魯迅于1933年應上海天馬書店之約,從《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五書中選編了一本《自選集》,是其生前唯一的“自選集”。內中僅收小說、散文、散文詩二十二篇,堪稱魯迅雜文之外文學創作的精華。他在自序中說:“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其自選標準是不同“材料、寫法”的代表性,以便“可供讀者參考”。
在1995年出了厚達五百多頁的《王朔文集》后,2004年又有《王朔自選集》。王朔在“自選集”自序中說:“老《文集》收得全,全就不免濫,好比一條魚不洗不開膛就上了桌,讓人出了全魚價,一口沒留神還添了惡心。”自編詩文集時,“刪詩如殺賊”,或可免此“惡心”。
(范一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