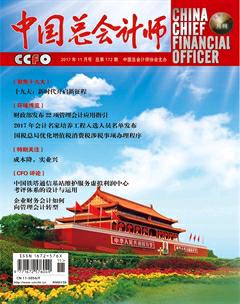我是怎樣堅(jiān)持“坐而不待斃”的:忍饑減肥
減肥,似乎是由年輕女士為追求骨感美而興起的,后來影響到男性擴(kuò)大到職場,但是,如果提出老年人尤其是肥胖老人的減肥問題,而且認(rèn)為在某種意義上比年輕人減肥更重要,恐怕很多人都不會贊同。
中國人習(xí)慣于將老年人的肥胖褒贊為“發(fā)福”,總愛贊曰“心寬體胖”。因?yàn)槔夏耆艘呀?jīng)轉(zhuǎn)入“頤養(yǎng)天年”階段,往往離不開吃得好、喝得好,生活舒適愉快,即使體重增加了,也無傷大雅。如果人到老年還要接受減肥折磨,不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嗎?
果然,我提出準(zhǔn)備減肥首先遭遇來自家庭的反對。反對意見一,你并不肥胖;反對意見二,你本來就沒有什么享受嗜好,如果再節(jié)食減肥,老年生活還有什么樂趣呢?
這里,再對自己的身體情況做一點(diǎn)說明。
我在13-15歲(小男孩長身體階段)時恰逢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災(zāi)害”),時至今日,內(nèi)行人士一眼就能看出我的身體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嚴(yán)重的發(fā)育不良,后來又被群毆暴打至“重傷”(1967年),家里也沒有增補(bǔ)營養(yǎng)的經(jīng)濟(jì)條件,以致直到2015年心腦血管大病爆發(fā)時,我其實(shí)都不胖。帶著“極高危”的出院報告回家后,一度心境低落,結(jié)果,2016年5月體檢時,體重達(dá)到81.5公斤(身高1.68米),結(jié)論為“肥胖”,體檢醫(yī)生提出“減肥”建議,而我也開始感覺到體重正在悄悄地成為我的負(fù)擔(dān)。
有一次,看到舉重運(yùn)動員在最后一次增加重量時失敗,我突然聯(lián)想到,如果把舉重運(yùn)動員最后一次的失敗看作是一個人心腦血管抗壓失敗的極限,那么應(yīng)當(dāng)就不難理解,他的失敗其實(shí)并不是舉起總量“XX公斤”的失敗,而是舉起“XX+1”的那一公斤的失敗。因?yàn)椋灰返裟且还锷踔涟牍铮\(yùn)動員就可以重新成功地舉起“XX公斤”的杠鈴。同理,如果把人的體重看成是一個杠鈴,那么,人的心臟就相當(dāng)于一天24小時里分分秒秒都在舉著這個杠鈴,如果能從這個杠鈴上減少一公斤甚至半公斤,對于健康機(jī)體來說,可能感覺不到什么,但是,對于曾經(jīng)患病的心腦血管來說,當(dāng)意外悄悄到來時,這一公斤或者半公斤,就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減去,“駱駝”就可能安然無恙。
由此意識到,減肥對預(yù)防心腦血管“卒中——猝死”的重大價值就在于,哪怕體重只是減輕了一公斤甚至半公斤,就有可能在某種預(yù)想不到的情況下,保護(hù)自己平安度過一次“卒中——猝死”的危險。
于是,我決定減肥而且從保持一日三餐的飯量不超過7成做起,同時嚴(yán)格控制正餐以外的進(jìn)食(包括不吃宵夜)。因?yàn)楝F(xiàn)在的飲食構(gòu)成已經(jīng)高度營養(yǎng)化,自己人到老年,身體消耗減少,需求相應(yīng)減少,沒有必要攝入過量營養(yǎng)任其在體內(nèi)變成脂肪徒增體重負(fù)擔(dān)。
2017年5月體檢,我的體重降為76.5公斤,結(jié)論從“肥胖”改為“超重”。而在體檢之前,自己已經(jīng)開始感覺到了這種減肥方式的效果,其中最為鮮明的,是伴隨著體重的減輕,每天堅(jiān)持定時定量分組運(yùn)動完成后第一分鐘的即時心跳,已從100跳出頭降為90幾跳,顯然,這一降低與減肥有關(guān)。
之所以將“節(jié)食”減肥稱之為“忍饑”減肥,則是這種減肥開始后,首先要面對的就是隨著三餐攝入食物量的減少而引發(fā)的一種持續(xù)的饑餓感。一開始這種感覺很強(qiáng)烈,老是想著再吃點(diǎn)什么,這時就需要自己的減肥意志了。
在堅(jiān)持了一年以后,我把健身鍛煉和節(jié)食減肥總結(jié)為一種“雙向合力”:一方面通過每天定時定量的體能鍛煉,保持心腦抗壓的功能力;另一方面減肥則以減輕心腦血管的負(fù)擔(dān),通過這種雙向結(jié)合來防止心腦血管的“卒中——猝死”爆發(fā)。兩年多來的明顯效果是:它守護(hù)著自己在帶著“極高危”的診斷結(jié)論出院后,在奔七的“高齡”依然能夠堅(jiān)持每天在電腦前不少于4個小時的工作。而每天堅(jiān)持“坐而不待斃”的工作并且絕無虛夸的證據(jù),就是2016-2017年兩年里往返北京與上海之間的6起公開判決生效的原創(chuàng)著作被抄襲的自主維權(quán)案例,還有同一期間內(nèi)獨(dú)立完成的三部重要著作的第三版修訂,以及2017年新出版的兩部重要的專著:《劉伯奎談創(chuàng)新讀書——怎樣跨學(xué)科讀書》和在美國學(xué)術(shù)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劉伯奎猜想——從“火星探索”猜想“人類的由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