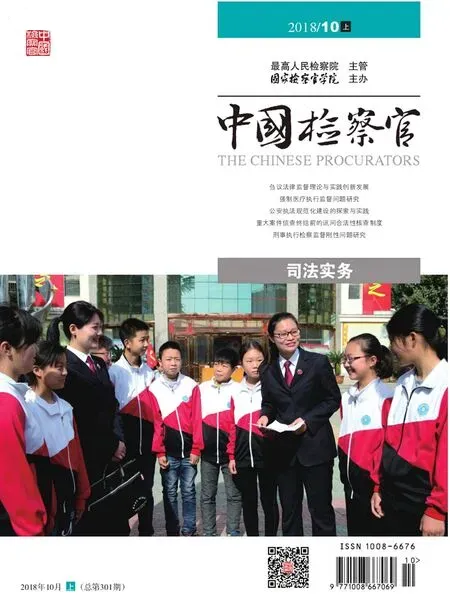毒品犯罪嫌疑人辯解引發的司法認定問題
●曾泉生 蘇 靜/文
毒品犯罪一直是我國刑事法律嚴厲打擊的重點犯罪,部分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為了逃避法律制裁,到案后仍然想方設法推脫罪行,人為地、故意地增加毒品犯罪案件辦理難度,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辯解中的合理成分也為司法工作者規范辦案行為、推動立法完善、提升司法公信提供了思考路徑和解決方案。
一、當場查扣毒品實物的收集與固定
案例一:2017年某日晚,經與購毒人員吳某某事先聯系,被告人張某某攜帶一包凈重10.205克的冰毒(甲基苯丙胺)竄至某賓館房間。被告人張某某倒出凈重3.293克冰毒交給吳某某,自己留下其余的6.912克冰毒并暫時放在桌上,吳某某當場支付人民幣1000元。交易完成后,被告人張某某離開,在房門口被公安人員當場抓獲。公安人員從該房間內查獲上述冰毒。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張某某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建議法院對其在有期徒刑七年至八年幅度內處刑,并處以罰金。
被告人張某某在偵查、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的供述一致且穩定,庭審時對指控的罪名和販毒過程也無異議,但對販毒數量提出辯解,稱自己向上家購買的冰毒僅為9.8克,公安機關用于稱重的電子天平顯示數值不準確,導致多出0.405克。實踐中,為了減輕罪責,毒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往往會對毒品數量提出異議,這是其辯解最集中的問題,給毒品案件查扣環節收集證據工作提出了更高標準和更嚴要求。
查扣毒品實物是查辦毒品犯罪過程中較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案件的其他偵查活動大多要從查扣毒品具體展開,查扣毒品實物的重量也是量刑環節最重要的參考因素。實務中,毒品交易上家不明、重量種類不清、檢材混同等案件證據問題,均源于查扣環節的疏忽大意。因此,毒品查扣環節作為固定毒品犯罪案件證據的最佳時間點,司法機關要予以充分重視,注意從盤問、稱重、封存、勘驗、檢查等方面具體落實。
(一)毒品稱重保管行為應當場進行
查扣毒品的重量直接影響量刑,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圍繞這個焦點進行集中辯解,上述案例就是這方面突出體現。過去,有些地區的偵查機關多在毒品鑒定時對查扣毒品進行稱重,并在鑒定意見中體現重量,之后再將稱重結果等告知嫌疑人,由此容易導致嫌疑人不直接參與稱重過程。且因為告知時距離查獲毒品已經過較長時間,面對嫌疑人提出的數量(重量)異議,偵查人員很難擺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或證據,導致工作存在被動性。因此,除非因情況緊急無稱重條件的(但也應當場封存毒品并妥善保管,盡快履行告知職責),查扣毒品應當進行現場稱重。同時需要明確現場稱重與鑒定稱重的關系,不是選擇其一,而是并行不悖,現場稱重是鑒定稱重的必要前置,也是對鑒定結果予以佐證的重要依據。允許上述二者之間存在合理誤差,即誤差不對基本事實的認定以及量刑幅度等造成重大影響,因而不會引發嫌疑人的異議,或即便有了異議也能進行合理解釋。
(二)毒品查扣現場盤問應重點突出、內容簡潔
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是偵查機關偵破毒品犯罪案件過程中收集的主要證據,根據經驗,距離案發時間越近的詢問、訊問筆錄,采信度越高。由此可見,在毒品犯罪查扣現場直接訊問取得的筆錄,可信度較高,應當予以充分重視。在確保現場盤問不會引發重大危險的前提下,偵查人員可以在查扣毒品的犯罪現場對涉案人員進行詢問、訊問,制作筆錄并利用執法記錄儀等設備對該過程進行全程錄音錄像。 同時應當注意,現場盤問的內容應當重點突出,適當簡化,主要了解查扣毒品的來源、歸屬、用途等關鍵問題,堅持安全性和必要性原則,無需求全求備。一旦現場盤問內容以某種方式作為證據固定下來,對于案件后續偵破、定罪量刑以及應對被告人翻供都十分有力。
(三)稱量儀器應當保證準確性和精密性
上述案件嫌疑人對偵查機關用于稱重的電子天平提出異議,這在實踐中也屢見不鮮,尤其在影響量刑幅度跳檔的情況下,其辯解雖然存在無理攪三分之嫌,但為了嚴格訴訟程序、確保證據“三性”,對稱量儀器的使用仍應予以充分重視。具體操作時,針對不同重量的毒品要選擇適當分度值的衡器,使用適當精度和稱量范圍的衡器。
為保障稱量儀器處于正常的工作狀態,稱量人在稱量前應將衡器示數歸零,并確保衡器處在質量有效期內。稱量所用衡器應當經過法定計量檢定機構(如當地計量所)的檢定,并具備計量檢定證書,計量檢定證書復印件應當歸入證據材料卷,隨案移送。稱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在場并有見證人的情況下進行,并制作稱量筆錄;對兩個以上包裝的毒品,不得混合后稱量,應當分別稱量,統一制作稱量筆錄。稱量筆錄應當由稱量人、犯罪嫌疑人和見證人簽名,犯罪嫌疑人拒絕簽名的,應當在稱量筆錄中注明。
上述案件中,針對被告人張某某就稱重數量做出的辯解,檢察機關進行了有力地駁斥。 一方面舉證出示當地計量所出具的檢定證書,證實公安機關進行稱重的電子天平合格;另一方面,請本案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對抓捕過程和現場提取、稱重、扣押過程等相關情況進行說明,充分證實偵查人員在抓獲被告人張某某的現場,當面對兩包毒品進行了提取和稱重,稱重結果為10.205克。結合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多次對毒品重量供述的一致性,法院最終認定被告人的辯解與事實不符,不予采納,最終判決其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并處罰金。
二、持續性誘惑偵查引誘次數的法律認定
案例二:黃某于2016年8月15日電話聯系被告人白某,提出購買冰毒的要求。隨后被告人白某駕車前往約定地點,將1包重約0.4克的冰毒 (甲基苯丙胺)交給黃某,后者隨即支付給被告人白某人民幣400元。
同年8月17日晚,公安人員安排黃某與被告人白某電話聯系,提出購買冰毒的要求。雙方在電話里約定了交易價格和時間。隨后,被告人白某前往約定地點,以人民幣200元的價格將1包冰毒賣給馬某某,之后公安人員從黃某繳獲該包冰毒。
同年8月18日晚,公安人員再次安排黃某向被告人白某提出購買冰毒的要求。在約定地點,被告人白某以人民幣600元的價格將2包冰毒賣給黃某。隨即民警將白某當場抓獲,并從黃某處繳獲上述冰毒。經鑒定,被告人白某販賣給黃某的3包冰毒共重1.2克,均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本案三起犯罪事實中,后兩起系在偵查人員控制下產生的毒品交易,涉及是否屬于犯罪引誘和控制下交易等誘惑偵查情形。偵查人員原本計劃在被告人白某第二次販賣毒品時將其立即抓獲,但白某作案后迅速開車混入車流;偵查人員雖然立即組織追蹤抓捕,但當時正值交通擁堵高峰期,加之白某的反偵察能力較強,追捕未果,只好再次安排黃某向白某約購毒品。最終在第二次特情引誘后,將被告人白某抓獲歸案,并在客觀上造成了被告人白某販賣毒品三次的犯罪結果。
(一)特情引誘的次數影響被告人犯罪事實認定
本案中,假設偵查人員第一次“引誘”即抓捕成功,被告人白某可能僅會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但因偵查人員第一次未抓捕成功,只能再次部署特情引誘,導致被告人多次販賣毒品,客觀上構成被告人犯罪“情節嚴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第3條第4款,“多次販賣毒品”的,可認定為《刑法》第347條第4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即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白某對販賣毒品三次的案件事實沒有異議,但辯稱是受偵查人員誘惑才多次販毒,不應將偵查人員特情引誘的次數全部計入其販賣毒品的次數,只能認定其販賣毒品一次。
作為一種特殊的偵查手段,誘惑偵查(又稱“特情引誘”)目前正普遍地運用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偵破過程。為應對毒品犯罪多環節、跨地域、職業性、隱蔽性強、反偵查意識強等特點給偵查工作帶來的挑戰和困境,誘惑偵查作為偵破毒品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偵查手段,在實踐中非常必要。但這一偵查手段的運用,具有侵害公民私權利的高度危險,極易引發國家公權力與被告人私權利之間的沖突和碰撞。因此,本案中,數次引誘應否計入被告人販賣次數,既是被告人辯解的重點,也是司法實務中爭議的焦點。
(二)特情引誘的次數不宜予以限制
由于持續性引誘在一定程度上讓被告人承擔與其罪責不相適應的刑罰,極有可能嚴重影響被告人的私權利,學界有觀點提出要嚴格限制持續性犯意引誘的使用,具體做法就是必須限定特情引誘的次數。但在當前毒品犯罪形勢依然嚴峻的情況下,筆者認為,考慮到當前毒品犯罪案件的查辦現狀,對于因客觀因素影響導致偵查人員一次特情引誘沒有抓捕成功的,應當準許其繼續使用特情手段,以確保打擊毒品犯罪的高壓態勢。
(三)特情引誘的次數不宜計入毒品犯罪次數
類似本案的特情引誘,屬于印證既存犯罪的“機會再次提供型”的引誘,對于佐證被告人實施了毒品販賣行為有重大作用,被告人不能以此作為自己免責的理由。因其原本就有毒品犯罪的故意,客觀上也再次實施了毒品犯罪行為,即便被告人辯稱自己本無繼續販毒的意圖,其也應對擴大犯意下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因此,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應當依法計入其販賣毒品的數量,但在量刑時應從輕處罰;如果經引誘后的毒品數量剛達到或者超過判處死刑數量標準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至于因抓捕不成功而導致持續性引誘,導致被告人多次販賣毒品的,販毒次數則要謹慎評價。實踐中,由于毒品犯罪所具有的個案差異,加之受到抓捕時機、地形、人群環境甚至偵查人員判斷力、反應力、執行力等具體因素的影響,不同偵查人員實施抓捕行為,就可能出現素質高、反應快、身手敏捷的偵查人員能一次將販毒犯罪嫌疑人成功抓獲,其他人員則可能要多次特情引誘才能抓捕成功。因此,如果將特情引誘的次數全部計入被告人販賣毒品的次數,就可能會出現被優秀偵查人員一次成功抓獲的犯罪嫌疑人會面臨相對較輕的刑罰,而多次引誘才被抓獲的,則會面臨更重的處罰,甚至觸動法定刑升格。這對被告人有失公平,其接受刑罰的程度受不確定因素影響過大,屬于公權力機關特情引誘手段的運用不當侵害公民私權利的情形。因此,為避免出現由于偵查人員辦案水平、執法素質不同而導致違背刑法“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情形發生,有效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偵查人員特情引誘的次數不應計入被告人販賣毒品的次數。
三、同一犯罪前科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法律適用
案例三:被告人蔡某某因犯販賣毒品罪于2014年2月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2014年9月刑滿釋放。被告人鄭某某因販賣毒品罪于2000年5月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2001年2月刑滿釋放。2017年3月偵查人員抓獲上述二被告人時,從二人身上分別查獲13包共計凈重40.11克的冰毒(甲基苯丙胺),以及一包凈重42.68克冰毒(甲基苯丙胺)與麻古(甲基苯丙胺片劑)的混合物。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蔡某某、鄭某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建議法院分別對蔡某某、鄭某某在有期徒刑七年三個月至八年三個月幅度內處刑,并處以罰金。
本案被告人蔡某某曾因販賣毒品罪被判處10個月有期徒刑,刑罰執行完畢后5年內又因販賣毒品罪被提起公訴,屬于同一犯罪前科同時構成毒品再犯與累犯;被告人鄭某某前罪執行完畢至本次犯罪已經超過5年,其犯罪前科情況法律評價為毒品再犯。鄭某某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提出異議,辯稱其只有毒品再犯情節,而蔡某某同時具有累犯和毒品再犯情節,自己僅有一個從重處罰情節,但在量刑上卻與蔡某某一樣。
(一)法律適用之依據
累犯和毒品再犯的關系問題,學界有很多探討,司法實踐中也頗多爭議。但目前基本一致的觀點是:毒品再犯是對再次從事毒品犯罪的行為予以從重處罰的特別規定,不是累犯的特殊形式。關于同一犯罪前科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法律規定,主要有以下四個依據:一是《刑法》第65條關于累犯的規定;二是《刑法》第356條關于毒品再犯的規定;三是《大連會議紀要》第8條關于對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從重處罰的規定;四是《武漢會議紀要》第6條關于不得重復予以從重處罰的規定。
(二)法律適用之沖突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具有不同犯罪前科的被告人,若同時構成毒品再犯和累犯,理應同時適用毒品再犯和累犯的規定進行從重處罰。但如果是具有同一犯罪前科的被告人同時觸犯毒品再犯和累犯,若對被告人同時適用刑法第65條和第356條的規定進行從重處罰,被告人經常會以其樸素的法律認知提出異議,司法實務中也存在較大的爭議,普遍認為其違背刑法禁止重復評價及罪刑相適用的原則。
本案中,蔡某某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若按照《大連會議紀要》的規定,就會因同一個犯罪前科被重復評價并被兩次從重處罰;若按照《武漢會議紀要》的規定,蔡某某在量刑時就不會被重復予以從重處罰。因此,《武漢會議紀要》實際上解決了重復從重處罰的問題,使被告人不因被重復評價而受雙重處罰,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如本案中,蔡某某同時具有累犯和毒品再犯情節,而鄭某某只有毒品再犯情節,若適用《武漢會議紀要》規定,最終兩人的判決結果極有可能會一樣;那么鄭某某就會提出疑問:“為什么自己僅有一個從重處罰情節,卻與有兩個從重處罰情節的蔡某某量刑沒什么兩樣?”裁判文書公之于眾后,公眾也會對此產生疑問,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必將損害司法權威。
(三)立法完善之建議
根據《刑法》規定,累犯和毒品再犯都是“應當從重處罰”的情節,即都必須從重處罰,但《武漢會議紀要》規定不得重復予以從重處罰,這便有違背上位法之嫌,況且運用不當就很可能破壞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囿于對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法律規定不盡完善,應從《刑法》層面上加強對法律的規范適用,正面回應目前司法實踐中遇到的這些難題。
為針對性地解決上述矛盾,有效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以及法律尊嚴,建議修改《刑法》第356條,將該條內容修改為:“因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本節規定之罪的,從重處罰;同時觸犯本法第65條規定的,依照本法第65條規定從重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