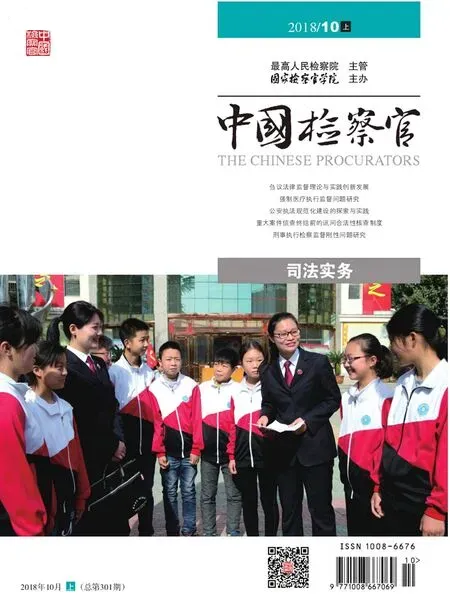大數據司法辦案下的公益訴訟
●張薰尹 許士友/文
一、“智慧檢務”與公益訴訟
“智慧檢務”階段,是推進檢察事業智慧創新發展的新引擎。智慧檢務是新時代檢察工作的一項全局性、戰略性工作創新、也是影響深遠的檢察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的重大革命。“智慧檢務”的核心是通過構建智慧檢務理論、規劃、應用“三大體系”、打造“全業務智慧辦案、全要素智慧管理、全方位智慧服務、全領域智慧支撐”的檢察機關智能化應用平臺,推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和檢察工作深度融合,推進檢察工作創新發展。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深化智慧檢務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中指出,深化智慧檢務的建設目標是加強智慧檢務理論體系、規劃體系、應用體系“三大體系”建設,形成“全業務智慧辦案、全要素智慧管理、全方位智慧服務、全領域智慧支撐”的智慧檢務總體架構。到2020年底,充分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推進檢察工作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躍升,研發智慧檢務的重點應用。到2025年底,全面實現智慧檢務的發展目標,以機器換人力,以智能增效能,打造新型檢察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1]
檢察公益訴訟,是指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或發現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在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履行訴前程序未實現公益保護之目的,進而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法院予以裁判的法律監督活動。[2]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是在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產生的重要舉措。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后,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5年12月出臺《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提出檢察機關對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的行政違法行為進行監督,行政機關應當配合。
綜上,檢察公益訴訟是由國家頂層設計、自上而下推動的一項檢察機關新增業務,系屬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制度的重要環節。智慧檢務是新時期新技術下檢察工作的一項工作創新和革命。如果說“智慧檢務”下的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是工具、是手段,那么公益訴訟則是重要載體,實現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發展則是目的。“智慧檢務”讓檢察公益訴訟機制建設更加健全,例如建立健全一體化辦案機制。安徽、福建、陜西在全省推行公益訴訟一體化辦案機制,通過督辦、參辦、領辦等方式,發揮內部合力,加大辦案力度。探索成立公益訴訟辦案指揮中心,統一管理案件線索、統一研判監督策略、統一指定案件管轄、統一調配辦案力量、統一指揮辦案工作,統籌協調重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二、實踐中公益訴訟面臨的困境
(一)理論共識不足
檢察公益訴訟制度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項法律監督制度,與傳統的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相比,其在理論層面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和充分,缺乏表要的理論支撐。如:檢察公益訴訟作為客觀訴訟與一般民事、行政訴訟等主觀訴訟的主要區別和制度差異問題;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起訴資格與訴權問題;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與公益訴訟的關系;訴訟的訴訟地位訴訟權利義務以及具體程序構建問題;具體程序構建中涉及的理論問題:如證據規則、訴訟請求,裁判形式以及不作為的認定等深層次的行政法實體問題等。
(二)公益訴訟案件線索匱乏
公益訴訟屬于被動型工作,有效的案源是工作順利開展的基礎和前提,但由于宣傳不足等原因,公益訴訟案源匱乏的問題一直制約著民行檢察工作的開展。例如,破壞生態環境案件線索主要來源于行政執法機關的移送以及受害人或知情人的舉報。當前檢察機關在生態環境檢察監督領域中的案件線索獲取困難,雖然“兩法銜接”機制已經建立,但行政執法機關主動共享行政執法信息及相關案件數據積極性不高,多個行政執法平臺并存運行,存在行政執法信息平臺使用率低、案件不錄、少錄、遲錄等問題,案件線索主要是通過主動出擊、受害人、知情人舉報以及聯合專項檢查等手段獲得,檢察監督缺乏剛性,監督信息渠道不暢,阻礙立案監督線索發現。
(三)公益訴訟案件取證論證困難
從公益訴訟的發起過程看,辦理公益訴訟案件中最大的困難是取證。造成這一現象有主客觀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觀因素,例如環境污染類案件,為了取證,可能要找到污染源和水源,由于污染源比較隱蔽,水源發源在山洞中,人力根本無法觸及;二是主觀因素,因為公益訴訟案件,很大一部分是對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職和失職行為的糾錯,所以大多數行政機關不愿配合,這也造成了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取證困難;三是技術因素,一些證據需要運用專門的技術進行鑒定,如果請專門的鑒定機構也需要資金支持。所以,取證難,特別是基層檢察機關的取證更加困難。基層檢察機關,應以信息化建設插上公益訴訟“智慧翅膀”,建立公益訴訟智慧數據分析系統,加強涉公益類信息數據的采集。綜合運用大數據、區塊鏈、導航系統、無人機等高科技手段,解決公益訴訟調查難、取證難等問題,提升檢察公益訴訟工作的規范化和專業化水平。
(四)公益訴訟案件證據的證明力問題
檢察機關作為檢察公益訴訟案件的原告,雖然檢察機關自身有一定的辦案能力,但是由于公益訴訟案件的復雜,很多案件取證難度大,所以所以公益訴訟案件證據的證明力的大小對案件會有重要影響。例如,破壞生態環境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往往要積累一段時間后才會顯現,具有很強的滯后性,但隨著時間推移,滅失證據的可能性以及證明因果關系存在的難度隨之增大。同時,破壞環境資源案件的因果關系證明往往需要司法鑒定作為重要依據,現有法律對環境損害鑒定規定較為籠統,司法實踐中存在鑒定機構、鑒定人員資質以及鑒定意見的法律效力不明確等問題,生態環境領域的鑒定評估專業性強,具備相應資質的鑒定機構和人員較為稀缺,辦案機關常常不知道應該委托哪個機構進行鑒定。
三、大數據破解公益訴訟的困境
一是通過大數據將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突破檢察公益訴訟理論共識不足的困境。法律分析主要專注于定性分析上。通過大數據引入定量分析,可以使原有的分析更加具有說服力,也會發現原來沒有關注到的問題點和解決對策,從而為理論層面的深入分析提供支撐。例如檢察公益訴訟作為客觀訴訟與一般民事、行政訴訟等主觀訴訟的主要區別和制度差異問題,在對這個問題研究時,可以將現有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古今中外的案例,拿來比較分析,數據總結兩者在訴訟主體、訴訟客體、制度等等諸多方面的比較,在進行分析,從而更好地為理論研究提供支撐,發現與原來沒有發現問題點,從而找出對策,解決當下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無疑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
二是將“兩法銜接”平臺打造公益訴訟的活水源頭。公益訴訟案件案源匱乏,因為公益訴訟很多是糾錯,特別是在行政公益案件中,很多時候是對行政機關的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糾正,也因此行政機關不愿配合,檢察機關發現案源更加困難,實踐中不容易發現案件線索。為解決此問題,一方面可以運用大數據,通過將“兩法銜接”平臺中錄入的行政執法案件進行集中摸排,篩選出屬于公益訴訟范圍的案件,然后及時進行跟蹤調查,跟進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職,發現問題,定期跟蹤,從而實現了案件線索成倍增長。另一方面,也要通過數據分析,根據“兩法銜接”平臺中的案件情況,數據分析出容易發生公益訴訟案件的領域和類型,然后重點關注這些領域、類型,既有助于提前預防,也方便及時發現案件線索。
三是利用大數據對公益訴訟案件進行統計分析指導工作方向。數據分析,能夠為工作開展提供數據支撐,做出合理預測。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國家的發展、行業的進步、部門的提升,更過地時候體現在對信息的掌握、對數據的分析上。公益訴訟能夠通過大數據,對公益訴訟案件的數量、構成情況、判案情況、審理情況等等做出數據分析,既解釋先前公益訴訟情況的原因,同時也能對公益訴訟未來發展做出預測,從而更好地指導公益訴訟的發展。例如,圖1中近幾年公益訴訟案件數情況,通過數據統計,我們不難發現2017年行政公益訴訟案件量激增,自2015年開始開展為期兩年的檢察機關公益訴訟試點,正好2017年試點結束,公益訴訟案件的激增正說明了試點方案的成果。

四是采用電子筆錄,規范言詞證據。書面的言辭筆錄,很容易造成證據效力確實,存在主客官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客觀原因,隨著時間的推移,字跡、紙面都會老化和不清晰,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另一方面主觀原因,在記錄的時候,并不可能把證人的所有言辭都記錄下來,而且有時候也會馬虎造成筆誤等等。電子筆錄同書面筆錄相比還有一個優勢,書面筆錄只能記錄言辭內容,但是電子筆錄除了能完整記錄下內容,行為人的說話語氣、態度也會記錄下來,這對庭審中判斷言辭證據的效力和真實性也有重要作用,保證證據的完整和客觀性。[4]所以,建議為改變過去詢問筆錄、調查筆錄字跡不清晰、涂改而影響證據效力的問題,委隨時隨地都能夠調查、詢問、固定證據,公益訴訟應多采用電子筆錄的方式,從而規范言辭證據,這樣既方便了群眾,也提高了工作效率,還能在公益訴訟出庭時得到法院的肯定。
五是人工智能、無人機拍攝等成為公益訴訟取證的利器。調查公益訴訟案件,很多證據很難取證,特別是在環境污染類的公益訴訟案件中,有的污染源頭在深洞中,在深山中,甚至是在無人區,這無疑給取證帶來了巨大困難。俗話說,君子性非異也善假于物也。這時候,人工智能就能派上用處了。運用無人機、機器人到這些地方去拍攝取證,收集到證據,保證公益訴訟能夠順利開展。例如近日,河北省投入無人機配套設備用于公益訴訟取證工作,無人機能遠程拍攝固定重要證據,并通過動態跟蹤、細節捕捉等優勢,避免了傳統攝像記錄的盲點。
注釋:
[1]參見趙志剛,金鴻浩:《傳統檢察信息化邁向智慧檢務的必由之路——兼論智慧檢務的認知導向、問題導向、實踐導向》,載《人民檢察》2017年第12期。
[2]參見王煒:《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理論與實踐》,載《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
[3]參見鄭鷹翔:《“互聯網+”環境下的“智慧檢務”工程進路》,載《楚天法治》2017年第30期。
[4]參見劉藝:《檢察公益訴訟的司法實踐與理論探索》,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