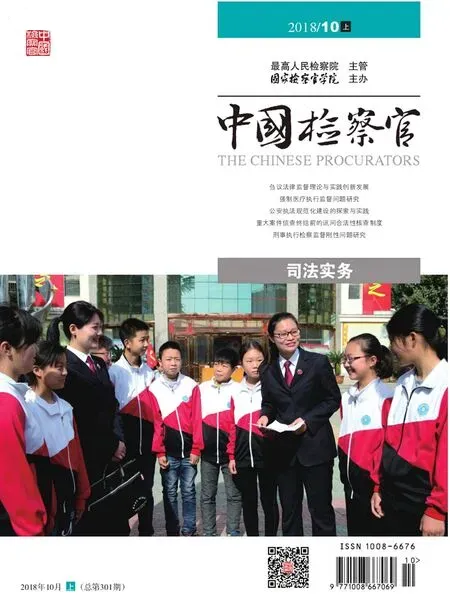刑事和解檢察監督的路徑選擇
——以當事人自愿原則保障為視角
●章 蓉 單家和/文
刑事和解就是一種以合作的形式恢復原有秩序的糾紛解決方式,它是由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賠償、道歉等形式達成諒解后,國家機關不再用更嚴厲、更苛刻的方式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或者對其從輕處罰,包括不適用逮捕、強制羈押、不起訴和非監禁刑等處理方式。[1]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對傳統刑罰理論側重犯罪懲罰、預防的刑事司法價值的有益補充,其更加注重社會關系的修復,方式更加靈活、個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傳統司法難以撫慰被害人心靈傷害、賠償難以兌現等社會詬病。然而,基于自身價值的考量,刑事和解各方的行為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刑事和解自愿原則的實現。
一、自愿原則的近景觀察:多方博弈,被迫客觀存在
刑事和解的是經濟賠償與精神諒解合意的綜合體,與此相適應,刑事和解自愿原則保護中的“自愿”,不僅僅是達成賠償協議的自愿,更應當涵括被告人的真誠悔罪和被害人諒解的自愿。[2]然而,司法實踐的“異化”,一些刑事和解案件中的和解協議的達成、悔罪和諒解可能并不是完全出自當事人的自愿:
(一)被害人的“艱難抉擇”
從經濟層面看,為了解決因犯罪行為導致的家庭經濟困難,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作出同意與加害人刑事和解的意思表示,更進一步說,在一些案件中,即使被害人不存在家庭困難,但加害人提出的賠償數額不足以彌補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損失,一旦案件進入訴訟程序,被害人可能無法獲得與實際損失相當的經濟賠償,基于此而不得不選擇接受和解。從傳統價值觀來看,中國人注重人情和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強調以和為貴,因而在部分案件中就出現了道德綁架,社會公眾,尤其是周邊熟悉的人認為被害人應當參與刑事和解,必須原諒犯罪嫌疑人,否則就會被貼上缺乏愛心、報復心太強等負面標簽。而與此同時,通過刑事和解化解矛盾也是被政府所鼓勵和弘揚的,為數不少的被害人正是基于社會道德綁架、政府提倡而參與并同意了刑事和解,這些被害人參與刑事和解雖然不能說是完全被迫的,但也不是完全自愿。
(二)加害人的“被迫選擇”
從刑罰期待可能性來看,在許多案件中,加害人由于擔心不選擇刑事和解可能導致在后續的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從重處罰,或是出于想被從輕處罰的目的,加害人選擇了參與刑事和解;從刑事案件雙方的社會地位來看,由于當前外來人員犯罪比例居高不下,部分地區超過60%以上,在本地人(被害人)與外地人(被告人)的司法博弈中,雙方擁有的社會資源不均衡,尤其是獲取法律幫助資源極為不均衡,在很多情況下,外來罪犯迫于無奈,不得不接受被害人提出的(不合理)經濟賠償要求,以期“破財消災”。從被害人訴訟地位看,被害人的參與是進行刑事和解的前提,其自愿是最終能否達成和解的決定因素之一,其被部分賦予決定犯罪人責任的權利,“被害人擁有了決定犯罪人命運去向的巨大權力,犯罪人及其社會關系網絡對被害人的潛在危險也會隨之增大。”[3]犯罪人會采取種種措施甚至違法手段來影響被害人,迫使其同意和解,迫使其同意加害人提出的和解方案。
(三)司法機關的“運作困局”。
司法機關掌握著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的逮捕權、起訴權、量刑權等,對于加害人而言,司法機關一定程度上掌控著刑事和解的運作進程;對于被害人而言,司法機關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可以敦促加害人積極賠付,甚至更高賠付。和解不成,加害人將身陷囹圄、被害人一無所獲在所難免,由于被害人、加害人與司法機關并不是平等的參與者,當事人出于這樣的擔憂而違心接受調解結果,這對刑事和解案件的雙方都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實質的強制。[4]進一步說,有的當事人為了減輕刑事處罰,可能鉆空子、拉關系,甚至威脅案件承辦人,司法人員一旦動搖,就極有可能喪失其公正立場,不能做到秉公執法,必然影響當事人自愿原則的實現。從程序正義角度看,我國目前律師參與刑事和解的比例還不是很高,加之大多數加害人的法律知識欠缺,導致刑事和解中當事人對自身的行為導致的法律后果不明知。每一個人活動主要是為追求其私利的最大化,在對自身行為后果不明的情況下,當事人所做的意思表示可能并非真實自愿。
二、自愿原則的價值保障:規范運作,強化檢察監督
正如前文所言,諸多原因使得刑事和解自愿原則難以保障,有人甚至認為刑事和解是為富人設置的制度,“以錢買刑”、“以罰代刑”放縱犯罪,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和統一性。我們必須正視,刑事案件的性質和類型具有復雜性,即涉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涉及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的重要方式,刑事和解是在綜合權衡的基礎上,國家對其公權力向案件當事人的有限讓渡,但基于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均衡保障的考量,加強刑事和解的法律監督也是其應然之意。
(一)建立傳統與現代并重的信息共享機制
當前,對刑事和解案件法律監督的難點在于信息不通,尤其是對公安機關偵查階段實施的刑事和解的情況不明,底數不清。我們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充分發揮基層檢察室、檢察官工作室等貼近基層、貼近一線的位置優勢,主動融入刑事和解案件辦理過程中,做到刑事和解案件的辦理與法律監督同步啟動,實現法律監督的全程化。二是對于基層檢察室等未能全面覆蓋的基層司法機關辦理的刑事和解案件,公檢法司要建立刑事和解信息同步通報制度。刑事案件的和解程序啟動后,辦案部門應當向檢察機關遞交案件相關材料及和解當事人和解意向相關證明材料,以便檢察機關及時了解刑事和解辦理情況,確保法律監督工作及時介入;更為重要的是,在構建“互聯網+智慧檢察”、“互聯網+司法公開”、“互聯網+社會治理”的背景下,要充分發揮互聯網大數據優勢,構建檢法數據聯通共享機制,如通過利用公安局提供的數字證書,登錄公安辦案信息系統,及時查看刑事和解案件辦理情況。
(二)建立案件與罪犯并重的法律監督機制
一方面要加強對當事人雙方影響當事人自愿原則的潛在因素的社會調查。影響刑事和解自愿原則的風險指標可分為正向指標和負面指標兩類。正向指標主要有:當事人家族民風淳樸、為人正派,當事人為未成年人、初犯、從犯、自首、立功、悔罪態度好、積極退贓或主動賠償、沒有不良嗜好和成長經歷良好等。[5]負面指標:當事人家族社會資源不均衡,甚至一方多人或多次有黑惡性質的犯罪活動,當事人無固定住所、犯罪動機卑劣、社會影響惡劣、教育背景等有缺陷等。另一方面,在履行法律監督的過程中,要與加害人、被害人所在工作單位、社區街道、派出所聯系,客觀聽取第三方意見,以公開促公正,同時,綜合考量當事人影響自愿原則指標情況,權衡比較,確保當事人意思自治,案件處理符合大多數人的普遍期待。
(三)建立回歸與和解并重的跟蹤監督機制
刑事和解的目的在于化解當事人雙方的糾紛,由于意思表達不完全、經濟賠償履行不到位、當事人雙方思想變動等原因,雙方有可能發生新的沖突。為真正促進矛盾的化解,一方面,要構建定期回訪制度,采取電話、信函、上門了解等方式了解刑事和解協議的履行情況,當事人雙方的關系狀況,尤其是對當事人較多的案件,當事人經濟困難的案件等。另一方面,對當事人達成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作出寬緩處理后,基層檢察室、檢察官聯絡室等要與當事人所在村(居)民委員會、工作單位、學校以及監護人共同制定幫教計劃,并監督相關措施的落實,確保被告人能夠早日回歸社會。同時,要適當結合案件實際情況抽查與巡回回訪,加強對重點案件監督。
三、自愿原則監督的遠景展望:以人為本,兼顧多方利益
法律監督是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責,其具有很強的政策性、法律性和實踐性。對刑事和解的法律監督一定要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要以當事人中心為主軸,同時兼顧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司法資源等,具體而言,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一)堅持當事人主體地位原則
刑事和解的根本目的在于修復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和被犯罪損害的社會關系,必須建立在當事人各自內心自然表達的基礎上,不能受到任何因素的誘惑和干擾。[6]檢察機關不能喧賓奪主,過于干涉,甚至大包大攬,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在監督過程中,檢察機關不僅要保障當事人意思自治,更要確保刑事和解的規范運行,只要和解沒有出現違反法律法規、違反社會公德和公序良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等情形,一般情況下不應隨意撤銷,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被害人要求的經濟賠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正常范圍值,但只要經濟賠償內容的達成是基于雙方當事人自由意志的體現,還沒有達到極端無理,明顯違反法律的程度,如超過法律規定賠償數倍以上,也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雖然刑事和解一般具有刑罰替代手段的性質,意味著犯罪嫌疑人不再承擔刑事責任或減輕刑事責任,但若行為人具有再次實施侵犯公共利益的可能的,則應當禁止允許和解。
(二)堅持與訴訟職能融合原則
刑事和解程序并非是一種獨立的程序,它是在整個訴訟程序之中依賴于其他訴訟程序的一種非必須的程序,對刑事和解程序監督的高效運作,必然要借助于其他訴訟程序來完成。在履行刑事和解案件的法律監督職責過程中,一方面,刑事和解的監督必須緊緊圍繞訴訟職能開展,要積極融入訴訟職能之中,而非游離于訴訟職能之外。伴隨刑事訴訟程序的推進,根據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協議情況、履行情況等,通過依法履行審查逮捕權、審查起訴權等方式,如提起公訴、批準逮捕等方式開展法律監督,促進訴訟職能與監督職能的有效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對刑事和解的監督要服務訴訟職能,而不能影響,甚至削弱訴訟職能的實現。對刑事和解的法律監督要和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審判程序等訴訟程序有機融合,而不能人為的將刑事和解的監督職能和訴訟職能割裂開來。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刑事和解中的被害人和加害人雙方都可能出現對和解協議“和解→反悔→再和解→再反悔”迂回反復的情形,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過程中,要對各種情形有充分的認識,不能輕易的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的意志所左右,輕易的使刑事程序反復,否則會陷入被動,不利于訴訟推進的尷尬境地。
(三)堅持重點監督原則
鑒于檢察機關資源的有限性,不可能對刑事和解中包含的所有事項都要監督,既不現實也不利于節約司法資源,要堅持重點論,要因地制宜,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恰如其分的監督力度,以統一執法,更好的實現公平正義。在刑事和解的檢查監督中,要整合司法系統內外監督資源,集中監督力量,一方面,要對一段時期內,刑事和解中不符合法律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精神相違背行為開展專項的法律監督,另一方面,要針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影響較大的刑事和解案件開展法律監督,以監督提升司法公信力。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明確司法機關的目標統一于打擊犯罪,保護人民,以此為法律監督的導向,積極與被監督單位的溝通和協調,以期取得被監督單位的認同與配合。更為重要的時,要理性認識和正確對待刑事和解檢察監督的局限性,避免不適當的夸大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功能。
(四)堅持及時全程救濟原則
對刑事和解的檢察監督,是國家刑罰權的讓渡的必要限制,是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平衡和互動過程,其目的在于追求當事人權益最大化,增加社會公眾的福祉,不斷滿足人民在公平正義方面日益增長的新需求,彰顯司法為民的檢察主旨。然而,由于相關配套制度不完善,案件久調不決,案結事了人不和,“以錢贖刑”等負面影響也屢有發生。要積極推進律師介入刑事和解制度,發揮律師的專業優勢,實現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減少和防止反悔的出現。要推進刑事和解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防范和杜絕處于優勢經濟地位的犯罪人以高額賠償作誘餌,鼓動被害人接受刑事和解,防止和杜絕因被害人擔憂無法獲得最低限度的賠償,而違背自己的意愿接受和解。對于當事人在刑事和解中,收到外力脅迫和解向檢察機關控告、申訴的,要及時予以處理;對于違反自愿原則的案件,應當建議公安機關撤銷原決定,重新移送起訴;對于辦案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的,應當將有關線索移交職能部門。
博登海默曾經說過:“正義有著一張普羅修斯似的臉,變化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7]。刑事和解制度是國家權力和個人權利全面衡量的一種折衷,其實質是在追求相關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增進公共福祉。刑事和解最大限度的滿足了被害人的利益訴求,消除了社會對立面,實現了多贏的良好局面,在司法實踐中大放光彩。在對刑事和解案件的監督中,檢察機關要敢于監督、善于監督、勤于監督、依法監督,使刑事和解成為化解社會矛盾、修復社會關系,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劑良藥。
注釋:
[1]參見賀恒揚:《加強檢察監督實現刑事和解的價值回歸》,載《第三屆國家高級檢察官論壇論文集》2007年11月。
[2]參見黎曉婷:《游走于邊緣的雙刃劍:刑事和解中法官暗示性話語的探究與規制》,載《法律適用》2013年第2期。
[3]湯火箭:《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與論證》,載《人民檢察》2004年第10期。
[4]參見 楊曉靜:《刑事和解:自愿抑或強制》,載《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5]參見單家和、劉赟:《刑事和解中當事人自愿的司法保障》,載《法制與經濟》2010年第6期。
[6]參見 王才遠、金鑫:《檢察機關參與刑事和解的職能定位》,載《人民檢察》2012年第21期。
[7][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