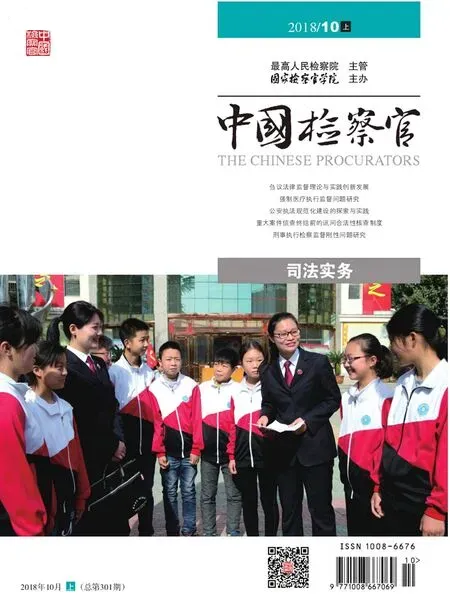審查起訴階段退回補充偵查實證分析
●丁彩彩 雷 閃/文
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對于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這是我國刑訴法對于退回補充偵查制度(以下簡稱“退查”)的具體規定。在當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背景下,庭審活動對事實和證據的要求日益嚴格,當事人主義的色彩更加濃厚,控辯雙方各自承擔的舉證責任更加清晰。公訴機關為了順利完成代表國家指控犯罪的職責,必須使案件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才可提起公訴。因此,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減少法庭審判中出現的種種風險,在審查起訴階段應充分利用退查方式來獲取庭審所必需的證據材料。筆者通過對2017年度J市人民檢察院辦理的公訴案件進行調研,分析退查數據及背后原因和退查實效,以期為進一步充分發揮退查制度的作用提供參考。
一、審查起訴階段退查案件的特點
(一)退查率較高
2017年,J院共受理公訴案件1151件1490人,經過退查案件數量共計242件448人,占全部受理案件數量的21.03%。其中,經過一次退查案件數量共計168件268人,占全部案件數量的14.60%;二次退查案件共計74件180人,占全部案件數量的6.43%。可見,審查起訴階段退查相對比較普遍,退查率較高。
(二)涉及罪名廣泛,又相對集中
退查案件涉及案件類型范圍較廣,如故意傷害罪、販賣毒品罪、集資詐騙罪、盜竊罪、強奸罪等。其中,有67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盜竊罪退查,人數最多;有41人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退查,居為其次;有33人以涉嫌販賣毒品罪退查,有31人以涉嫌故意傷害罪退查,涉嫌詐騙罪的有24人,涉嫌容留吸毒罪的有16人,涉嫌職務侵占罪的有12人,其他罪名相對較少。
(三)退回補充偵查時間以一個月期限屆滿為常態
在基層檢察院,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數量并不多,絕大部分案件都能夠在一個月內按照退查提綱補充偵查完畢并補充材料。但實務中仍然存在個別案件超過一個月的現象,甚至有偵查機關以種種理由“借用”公訴機關的審查起訴期限。事實上,基層院辦理的大部分審查起訴案件,補充偵查的工作量和難度并不大,實際補充偵查工作時間根本用不了一個月,但幾乎所有的退查案件都在一個月期限屆滿時再行重報,第一時間退查結束重報的案件極少,嚴重影響訴訟進程。
(四)退查后起訴率不理想
在筆者統計的退查案件中,有167件提起公訴,所占比例僅為69.01%;同意公安機關撤回34件,所占比例為14.05%;有6件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作存疑不訴處理,所占比例為2.5%;有1人作附條件不起訴處理;有27件正在辦理過程中,所占比例為11.16%。低于70%的起訴比率和超過14%的撤案率足以說明補充偵查的質量不高,退查效果并沒有達到預期狀態。
二、退查率偏高背后的理論與實證反思
(一)退查制度功能的異化現象在一定范圍內存在
現代司法改革以實現公正與效率兩大刑事訴訟價值為目標,而退查制度就是公正與效率的訴訟價值在相互博弈與平衡之后的最終結果。所以,偵查、起訴機關在退查工作中必須時刻圍繞公正與效率的目標,對案件是否需要退查,需要補充哪些證據,如何進一步補充固定證據等等,都要嚴格把握深入分析,不可隨意退查。然而,筆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在退查率偏高現象的背后,有相當部分的案件在實際上違背了退查制度設計的初衷和價值追求,功能發生了異化。具體表現在:
一是借用退查制度互借審限現象突出。法律規定檢察機關退回補充偵查以一個月為限,但實踐中卻變成以一個月為常態,“名退補,實不退”或者“名重報,實未歸”的互借審限現象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這種所謂互相行便利的退查行為,已經嚴重違背了退查制度的初衷,失去了公訴引導偵查的價值,異化為偵查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在程序上的一場獨角戲。
二是偵訴雙方相互掣肘現象頻發。經過調研,公訴人普遍反映,偵查人員對于退查案件存在相當大的抵觸情緒,退查提綱中約50%以上的取證要求往往以“無法查實”為由重報。這其中固然有部分內容確系無法查實,但不排除偵查人員消極應付退查,以“無法查實”作為理由搪塞檢察機關。而另一方面公訴人認為偵查人員缺乏正確的證據意識,取證能力有限,即使明知退查后偵查機關也不可能查到新的證據,公訴人仍然利用退查程序來表明自己對案件當前證據情況的懷疑甚至否定態度。這種現象導致的后果之一便是退查率偏高而起訴率并未相應提高。
(二)退查率偏高和退查效果不佳的實證反思
筆者對正常情況下需要退查的案件進行了深入對比分析,發現退查率偏高的背后有諸多因素的影響,具體包括:
1.偵查水平和偵查質量不理想。一是偵查人員本身偵查意識和偵查水平不高。一方面,在基層偵查機關,承擔辦案任務的偵查人員多為年輕干警,取證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剛入職的年輕干警,經驗相當匱乏,取證工作存在很多不足,難以經得起檢驗。另一方面,基層偵查機關的干警人員流動性很快,很多案件從立案到移送審查起訴這一過程中,因原承辦人提拔、抽調、上專案等各種原因經常需要更換承辦人,承接案件的偵查人員因為不熟悉案情、不了解證據收集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偵查質量。
二是偵查人員對于依法、全面取證關注度不高。一方面,偵查人員大多將重點關注在破案上,對取證重視程度不夠。受偵查機關內部考核機制的影響,偵查人員對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尤其是對檢察機關已經批捕的案件,極少關注是否順利起訴以及順利判決。這也導致了對退查不重視,敷衍了事。另一方面,過于依賴口供、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言詞證據的收集,對實物證據收集不足。在案件進入到審查起訴階段,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原本完整的證據鏈遭到破壞,公訴部門難以起訴,只能將案件退回補充偵查。這種現象在盜竊、尋釁滋事、故意傷害、販賣毒品、強奸等案件中非常突出。
三是偵查精力投入不均。在調研中,筆者發現,越是重大案件,偵查人員的取證水平越高,各方面證據的收集、固定和儲存等都很規范、全面;越是普通刑事案件,甚至是扒竊、危險駕駛這種相對簡單的案件,偵查人員往往存在疏漏之處,需要退查補充證據。究其原因,偵查人員在普通案件和重大案件上傾注的警力和精力存在明顯的差異,對大案要案的重視程度更高。實踐中出現部分偵查人員只關注重大刑事案件,對普通刑事案件取證不重視甚至走過場的傾向,導致案件無法達到事實清楚和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在時限的要求下,偵查人員將這些不具備移送審查起訴條件的案件予以移送,必然導致退查案件數量大幅度增加。前述被退回補充偵查最多的罪名依次是盜竊罪、尋釁滋事罪等相對簡單的案件,恰恰說明這一點。
2.起訴引導偵查效果不理想。退查的功能在于公訴機關以提起公訴的標準對案件當前證據情況進行分析衡量,對需要補充的證據提出指導性意見,引導偵查機關繼續補充相關證據。但在退查案件中,我們發現起訴引導偵查功能的發揮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退查提綱缺乏明確性和可操作性。公訴機關的意見主要體現在退查提綱中,因此提綱要有引導性和可操作性。調研中筆者發現,部分案件的退查提綱過于含糊,內容指向不明確,導致兩次退查的退查提綱內容基本一致,二次退查率相應提高。二是訴偵溝通機制存在障礙。部分案件需要補查的內容并非必需辦理退查手續,完全可以在審查起訴期限內補充完畢,例如前科判決及釋放證明、到案經過、是否有自首或者立功情節等等,但是因為溝通機制的不順暢、不合理,偵查機關補正不及時,導致案件期限屆滿必須退查,甚至還要經過二次退查才能補充完畢。三是提前介入偵查機制不完善。雖然刑訴法規定,對于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件,人民檢察院認為確有必要時,可以派員適時介入偵查活動,但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對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界定標準卻沒有明確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檢察機關很少主動提出介入偵查,最后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時,經審查發現案件存在事實不清或證據不足的情形,就直接將案件退查。這種事后審查、被動式審查、書面審查的模式,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案件退查率。
3.退查制度缺少配套制度的保障。一方面,刑訴法及刑訴規則對退查制度都作了明確規定,但并沒有具體的監督機制予以保障退查效果,導致“退而不查”的現象普遍發生。司法實踐中,對于部分簡單刑事案件,如果需要補充的證據要耗費較大的人財物資源,偵查機關往往避重就輕,補查一些無關緊要的其他材料應付了事,甚至直接以情況說明的形式證實證據無法補充。監督制約機制的缺失,已經成為制約退查效果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檢察機關的監督意識不強,不敢監督、不愿監督的思想傾向依然存在。雖然刑訴法對司法機關的要求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約,但實務中重配合輕制約的思維普遍存在。部分公訴人對于退查案件基本上持消極放任態度,不過問、不追問、不反饋,任由偵查機關自行補充,對于結果也是被動接受。這種觀念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得退查的目的落空,退查率居高不下。
4.檢察機關缺乏自行補充偵查的主動性。根據刑訴法規定,對于需要補充偵查的案件,檢察機關可以退查,也可以自己主動補充偵查。但我國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何種情形下應適用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何種情況下應由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因此,檢察機關更愿意通過相對便捷的退回補充偵查來節省時間和精力,同時減緩辦案壓力,規避法律風險,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退查率的增加。
三、退查制度的規范與完善
(一)轉變辦案思維,強化業務學習,提升偵訴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履職能力
首先,要樹立證據規則意識,提升偵查水平。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大背景下,法庭審判對證據標準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因此對證據的收集、固定和保存,直接關系到案件的定罪量刑。取證合法規范全面,自然就會降低退查的概率,辦案效率自然會獲得保障,而效率的提升本身又符合正義的內在追求。
其次,要加強崗位練兵,提升履職能力。組織多層次多角度的業務學習、崗位培訓和技能比武等,持續深化辦案人員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理解、分析和把握能力,為偵查和補充偵查水平的提升奠定堅實牢固的根基。要結合刑事案件偵查的實際需要,提高基層辦案人員對一般刑事案件的偵破取證能力,減少審查起訴環節退查的適用率。
再次,細化退查提綱,強化檢察機關自行補查的力度。退查提綱要明確有針對性,更要有可操作性,要詳細列明當前案件事實和現有證據存在哪些問題,需要從哪些方面補充偵查,采取何種手段補充偵查,要實現什么樣的補查效果,在補查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項等,并要根據補查進展隨時調整下一步補查的方向與內容。另外,公訴人員要提高自己的偵查水平,擴大檢察機關自行補查的適用范圍和機率,在并非必須退查的情況下,強化自行補查力度,減少盲目退查率,提高辦案效率。
最后,規范健全提前介入機制,變被動審查為主動引導。偵訴兩機關要加強溝通協調,對重大、復雜、疑難等案件的范圍盡量達成共識,作出相對明確的界定。對此類案件的偵查,偵查機關要第一時間通知公訴機關派員到場,通過提前介入引導取證;公訴機關要牢牢把握主動引導偵查的機會,通過提前熟悉案情,分析證據情況,以提起公訴的標準衡量偵查取證的現狀和下一步計劃,并適時跟進監督確保科學規范取證。
(二)建立健全退查制度的監督制約和保障機制
首先,要建立退查跟蹤與反饋制度。公訴人員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樹立敢于監督、善于監督的辦案思維,對待退查案件要“一跟到底”,及時掌握退查進度,適時作出方向和內容的引導和調整,提高退查質量和效果。對待偵查人員消極退查甚至退查超期等行為,要及時予以糾正,并向其主管部門書面通報。
其次,要善于利用績效考核機制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對于退查案件,偵訴兩機關均可納入考核機制予以考量。無論是公訴人員濫用退查或者放任退查案件,還是偵查人員“退而不查”甚至超期退查等不良行為,都作為考核指標之一納入績效評價體系。同時,可以將退查率納入考評機制。對于退查率偏高的辦案單位,在遵循司法規律的基礎上,核實其背后原因,在無法做出合理解釋的情況下,可視為辦案質量不高的指標之一予以扣分,反之則予以加分獎勵。
再次,完善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偵查人員與公訴人員在辦案思路和把握標準上的認知差異,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前者對退查案件的排斥與不認同。因此,角色體驗不失為解決問題的良策。刑訴法規定,對于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通過偵查人員出庭作證,親身經歷庭審過程中法庭對事實和證據的把握尺度,更能督促偵查人員在以后的偵查過程中依法規范取證,確保案件達到起訴標準,更能提升偵查人員對于退查案件的認同感。
(三)加強溝通協調,增強辦案合力
提高退查質效和降低退查率并非靠某個辦案機關單槍匹馬就能實現,也并非一日之功,必須通過多方聯動配合共同努力方能實現。一方面,偵訴兩機關可以通過會簽文件或者聯席會議等形式,加強溝通協調,制定統一明確的證據標準并嚴格執行,減少對證據標準的認知分歧。通過加強溝通交流,相互闡述對案件事實、證據的認識和理解,把事實和證據吃透弄懂,找出分歧和問題,有針對性地研究和解決。另一方面,注重經驗積累與分享。建立退查總結通報制度,通過對一段時間內退查案件進行綜合分析對比,查找共性問題,解決個性問題,總結經驗和教訓,為下一步改進工作方法、提升案件質量奠定基礎。同時,可適時建立精品案例庫,對于提前介入偵查、公訴引導偵查以及合力偵查成功的典型案例予以提煉升華,形成一套成熟的補查思路與方法,作為模板供借鑒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