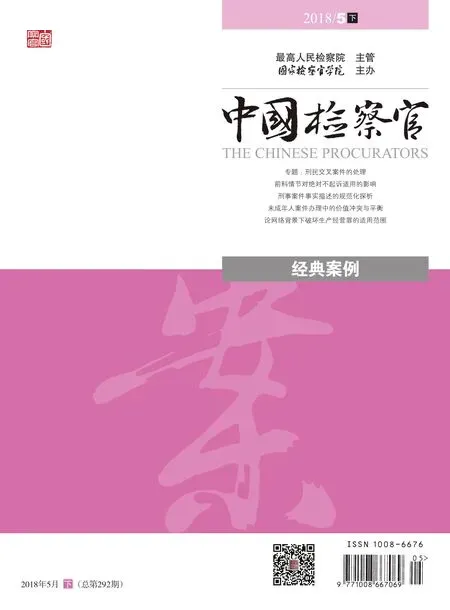刑事案件事實描述的規范化探析
文◎柏屹穎 卓 凱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是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的刑事司法基本原則,“無行為則無犯罪”的刑法格言也揭示了案件事實在刑事案件中的基礎性作用。司法實務中,事實不準確不僅會影響案件承辦人的法律判斷,還會誤導相關決策者作出不當意見,致使案件訴訟程序難以順利進行,影響個案司法公正的實現。近年來出現的冤假錯案與事實認定不無關系。雖然多數司法人員能夠認識到案件事實的重要性,但部分法律文書中案件事實描述卻不甚規范,單純通過法律文書中案件事實陳述難以掌握具體案情,難以作出合理合法的判斷。因此,有必要對此專門予以探討。
一、刑事案件事實描述存在的問題
(一)有些案件事實描述不全面
案件事實描述的基本要求是要素齊全 (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原因、過程及結果,俗稱七個“W”)、陳述完整。但是,實務中有些法律文書的事實認定并未達到應有的要求。(1)有的事實描述不完整,影響此罪與彼罪的判斷。如,王某盜竊案中,公安機關在提請逮捕書中僅描述為“王某潛入被害人李某某家中盜竊”、“王某被返回房間拿資料的被害人李某某發現,并在逃跑中被保安抓獲”,未提及該房屋系剛剛裝修完畢、尚未入住的情況,也未提及王某被發現后拿著鐵錘指著被害人恐嚇的情況,就此無法得出王某是否系入戶盜竊以及是否轉化搶劫等罪名的問題。(2)有的事實描述遺漏關鍵情節,導致罪或非罪截然不同的結論。如,陳某故意傷害案的提請逮捕書認定“因瑣事發生口角,黃某等3人沖入陳某姐姐家中追打陳某,后黃某在追打過程中被陳某連續捅刺腦、頸等重要部位而死”,而客觀事實則是因陳某不愿意出借其車輛給黃某,黃便糾集張某(持刀)、王某追打陳某,陳某躲避不成逃入小巷,追在最前面的黃某被陳某捅刺兩刀(胸部創口達皮下組織)后自行走出巷子。可見,遺漏對案發起因、打斗雙方力量對比、捅刺細節等具體描述可能會影響陳某是否系正當防衛的判定。事實上,諸如此類涉及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被害人重大過錯等事實,因多種因素容易成為法律文書中事實描述忽略的節點。
(二)有些案件事實描述的用語不規范
法律文書中的案件事實絕非主觀臆造,但也不是純碎的客觀存在,而是相關訴訟主體通過對在案證據的分析論證與篩選后的結論,是主觀認知與客觀證據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此,案件事實描述的準確性就要求訴訟主體具有較強的文字表達能力,事實描述的用語也顯得尤為考究。司法實務中也存在一些不規范情形。(1)有些案件事實描述的用語不妥當,如在盜竊犯罪類提請批準逮捕文書中,時常見到“犯罪嫌疑人某某竄至某處實施盜竊”的表述,“竄”明顯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在客觀中立的案件事實描述中,使用該類具有評價功能的語詞并不妥當。(2)有些事實描述的用語有口語化的傾向,如使用“很火”這個詞來表達被告人“很氣憤”,使用“放電影電視劇”替代“播放電影電視劇”等表述。(3)有些事實描述使用抽象的刑法規范用語替代具體的案件事實描述也不合理。如我們習慣使用行為人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替代具體事實的描述,既有提前預設行為人行為性質之嫌,也不符合事實描述的客觀、中立、平和用語等特征。
(三)有些案件事實描述的用語不準確
案件事實的描述不僅要全面、規范,而且務必要詳實、準確。如此,案外人才能通過對案件事實的閱讀了解案件的全貌與整個經過。司法實務中存在一些不準確的情況。(1)有的法律文書中事實描述習慣使用抽象性的概念,而非具體的、敘述性的表述。如對于案件起因的描述往往使用 “因瑣事引起糾紛”、“因小事發生矛盾”等語句,對于故意殺害或傷害多人案件經過的描述,認為類似“某某持刀連續捅刺致使多人死亡、輕傷”足以,殊不知對于傷害順序、時間空間的間隔等準確陳述對于判定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尤為重要。(2)有的法律文書描述的事實也有證據印證規則貫徹不好的情況,比如對于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者被害人陳述而無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認定為案件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后又翻供的、在未作供證矛盾分析情況下輕易采信未經印證的孤證。
二、刑事案件事實描述失當的原因
(一)部分司法人員對案件存在不當“先見”
案件事實多存在不同的評價側面,不同角度的評判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故客觀中立的事實描述尤為重要,人們會根據認定的事實結合自己的認識得出相應的結論。實踐中,存在事實描述不全面或者遺漏關鍵細節的情況可能與相關訴訟主體存有不當的預設性的認識有關,即有的司法人員先對案件事實予以定性分析,根據自己的判斷,結合刑法關于具體罪名構成要件的規定進行案件事實描述。實際上,事實描述就是呈現案件的全貌及具體發生經過,其本質應是敘述性的,而非評價性的。相關訴訟主體不能先對其評價,再將個人認知強加于中立的事實陳述中。比如,不能預設尋釁滋事罪名而將行為人動機描述為逞強耍橫,更不能因為欲置行為人有罪境地而忽略可能存在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刑法阻卻事由的陳述。
(二)有些司法人員建構事實能力稍顯不足
證據分析能力、事實認定能力與法律適用能力等是司法工作人員應當具備的核心能力。由于事實認定需要以證據分析為基礎,對案件事實描述的偏差就突顯相關司法工作人員對證據的把握及運用證據鎖定事實的能力不夠嫻熟、事實描述的文字表達能力也需要進一步提升與規范。比如,不熟悉或者不能嚴格貫徹判斷證據的印證證明方法的可能會將未經印證的孤證情況作為案件事實,缺少一定實務工作經驗的司法人員可能無法充分運用經驗法則對在案事實進行認定,生活閱歷欠缺的司法人員可能也不能自如地運用自由心證的證據判斷法則。又如,對語句修辭不夠敏感、文字表達能力不夠自如的司法人員可能無法準確區分“抄起鐵鍬砸向他人”與“拿著鐵鍬砸向他人”的文本意義,更不會注意到“竄至某處”可能帶有的對行為人人格貶低色彩的意味。
(三)少數司法人員的認識問題
司法責任制特別是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像懸在司法人員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警醒著人們不能觸犯司法的底線。本意良好的制度設計,帶給一線辦案人員的壓力邊界卻無限延伸,體現在案件事實描述上就會出現以抽象的、剪裁的修辭替代具體細節的陳述,刑法規范用語大量存在的情況。本文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多數由于一線辦案人員的自我保護意識導致的:一是司法人員因簡潔明快已習慣使用抽象表達方式,輕易不會打破這種局面,且抽象用語更有利于將剪裁的案件事實與刑法規范“強行并攏”;二是使用抽象表達方式會給后續復核復查留下足夠的解釋空間。除了自我保護之外,也不排除有部分司法人員故意裁剪案件事實,在案件事實描述時不認真、不仔細,遺漏對關鍵證據的審查判斷,在案件討論與匯報時故意隱瞞案件的關鍵細節,以達到支持自己觀點或者其他個人目的。當然,有些辦案人員刻意將孤證事實列入相應法律文書的認定事實,目的是強化下一階段司法人員有罪推定的內心確信,這對于事實認定本身影響不大,并非本文關注的重點。
三、刑事案件事實規范描述的合理路徑
(一)合理把握案件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遞階關系
從法律方法論角度看,裁判結論無非是邏輯三段論推導的結果,大體是先確定作為小前提的案件事實,后尋找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范,再將事實涵攝于規范之下進行判定。實際上,“案件事實具有不同側面與不同性質,如果離開可能適用的刑法規范,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必然得出千差萬別的結論。”[1]據此,案件事實的認定當然離不開可能適用的構成要件的指導,無法與法律規范截然區分。可是,本文所關注的“案件事實”并非在于其如何形成,而是在于其確定后如何表達。盡管“為決定某一生活事實是否可能為某一法律規定所規范,為判斷之人實際上必須做各種不同的先行判斷”,[2]事實形成的過程需要“不斷往返于事實與規范之間”,但事實確定后的文本建構卻與規范判斷不能等同視之。因為案件事實是訴訟主體基于在案證據形成的判斷,著重解決“有沒有,有什么”的問題;而法律適用是司法工作人員基于自身的法律知識形成的認定,著重解決“是什么”的問題。應當說,案件事實部分與法律適用部分的功能是存在差異的,如果在法律文書的事實描述時,大量使用具有評價功能的規范用語替代中立的文本敘事,抑或帶有預設性的抽象價值判斷進行事實描述,便會混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遞階關系。
此外,事實描述總是由具體的訴訟主體通過語言進行的,而訴訟主體的認識能力必然有其自身的主觀性與局限性,這一過程也會表現出一定的隱蔽與非公開性,這就決定了事實描述主體思維認知、表達方式的重要性。所以,刑事法律文書中事實描述的合理做法便是,根據在案證據判定案件事實后,全面概括案件的具體經過,不能刻意回避或者剪裁重要事實,也不能混淆平和、中立的文本敘事與價值判斷的界限。
(二)提升司法人員建構案件事實的能力
個案的公正離不開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法律適用等核心能力的嫻熟把控。在法律文書的事實描述方面,我們不僅要學習各種證據的判斷方法與運用規則,也要注重文本修辭的選擇運用。固然,司法工作人員可能會基于不同的背景知識、生活閱歷等對既定的客觀事實作出不同的法律判定,也應尊重“法官”這種自由裁判,可是司法官員“不是一位隨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俠。他應從一些經過考驗并受到尊重的原則中汲取他的啟示。他不得屈從于含混不清且未加規制的仁愛之心。他應當運用一種以傳統為知識根據的裁量,以類比為方法,受到制度的紀律約束,并服從社會生活中秩序的基本需求。”[3]具體而言,在事實描述時應注重以下規則的學習與運用:
首先,應確保事實認定的證據基礎扎實。在確保單個證據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基礎上,嚴格貫徹證據的印證證明等規則實現證據的綜合分析,從而確保事實認定的客觀準確性。如即使內心確信犯罪嫌疑人系流竄作案,在未進行查證核實時,也不能將犯罪嫌疑人供述的“x年x月x日,在x小區入室盜竊一部蘋果5S手機”作為報捕書中案件事實一部分。
其次,應注重事實描述的完整性要求。依照事實陳述的“七要素”要求,依照一定的邏輯順序完整表達案件整個經過,不能以點帶面、以偏概全,更不能無中生有或刻意隱瞞關鍵事實。如,一起三人共同盜竊案件的事實,應該這樣表述:“x年x月下旬,無業人員王某在幫助宏發貿易公司經理吳某搬家時,得知吳某在盛大花園小區的房子正在裝修、尚未入住,于是起意到該房子內盜竊家電。x年x月x日下午,王某糾集劉某、李某二人,約定由王某負責盜竊,劉某負責在樓下接應,李某開面包車在小區東門外等候。x月x日晚11時,王某等3人開車來到盛大花園東門外,王某爬上二樓持長柄液壓鉗夾斷防盜網鐵條后進入屋內,發現臥室有聯想手提電腦一臺,于是將液壓鉗和電腦從窗戶交給樓下守候的劉某。隨后王某在拆客廳平板液晶電腦時,被返回房間拿東西的被害人吳某發現,王某隨即亮出大號扳手指向吳某稱“再喊就弄死你”,然后從大門跑走。吳某下樓追趕并大叫抓小偷,王某跑向小區南門時被保安曾某、石某抓獲。劉某聽到叫喊后,將所盜筆記本電腦和液壓鉗藏于小區綠化帶后往東門跑,與李某會合后二人逃至乙縣。公安機關根據王某的交待,于x月x日將劉某和李某抓獲歸案。所盜筆記本電腦被小區群眾拾得后交給公安機關,經鑒定價值3000元。”如此表述,可以清晰地看到案件的全部過程,包括犯罪預謀、實施過程、歸案情況及作案工具、贓物處理情況,比較符合事實描述完整性的要求。
最后,需要注意文本表達的規范性,強調語句修辭準確性。由于案件事實是在整合物證、書證、鑒定意見、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與辯解等證據材料基礎上得出的,在這種整合過程中,必須借助語句的表達實現證據信息的轉化,而轉化的過程就可能出現表達的多樣性。如在一起涉及故意殺人案的事實表述中,版本Ⅰ描述為:“x年x月x日,小商販王某在馬路邊非法擺攤被城管人員查處,在勤務室接受處罰時,王某與城管執法人員李某、陳某發生爭執,用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將城管人員李某捅死、陳某刺傷”;版本Ⅱ描述為:“x年x月x日,小商販王某(身高1.6米)在馬路邊非法擺攤被城管人員查處,在勤務室接受處罰時,王某與城管執法人員李某(身高1.8米)、陳某(身高1.82米)發生爭執,李某首先毆打王某,接著陳某也毆打王某,王某被迫用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將城管人員李某捅死、陳某刺傷”。盡管版本Ⅰ和版本Ⅱ均來自同樣的證據材料,但信息轉化的處理不同,呈現的文本效果截然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實踐中個案辦理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不僅僅在于證據、邏輯等,還在于公正的文本表達方式。所以,注意語句的規范表達與具體修辭的慎重選擇就尤為重要。
(三)強化事實認定的公眾參與,注意“法律真實”的規范表達
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不是同等的概念。作為中立的司法人員因不具有親歷性,對于“事實”是否發生的判斷就需要借助證據進行,而證據大多由訴訟參與主體提供或者獲取,必然就會存在失真的可能,故司法人員的重要職責便是靈活運用各種方法實現對證據的鑒真。由鑒別后的證據構建成的事實就是法律真實,這就要求司法人員在事實陳述時應以證據論,既不能隨意使用“自由心證”分析方法、錯將客觀真實當作法律真實,更不能將沒有任何證據基礎的“閑言碎語”或“個人臆測”當作案件事實予以陳述。畢竟,雖然案件的法律事實不完全等同于客觀事實,但是案件事實的描述也絕不能有虛構的成分。
對此,相關訴訟主體應時刻注意對“法律真實”底線的堅守,既不能故意虛構案件事實,也不能憑個人主觀臆斷認定案件事實。當然,在個案事實認定中,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會忽略其他訴訟主體的參與作用,故強化事實認定的公眾參與也非常重要。如在疑難復雜案件討論時,確立事實判斷與法律判斷并重的理念。案件承辦人員在匯報時應列明各訴訟主體提供的證據名錄,讓參與討論人員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證據規則及生活經驗進行案件事實的判斷,各參與人經過充分討論得出的結論也成為最終事實認定的重要參考,如此案件的“法律真實”也能實現規范表達。
注釋:
[1]張明楷:《案件事實的認定方法》,載《法學雜志》2006年第2期。
[2]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頁。
[3][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蘇力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