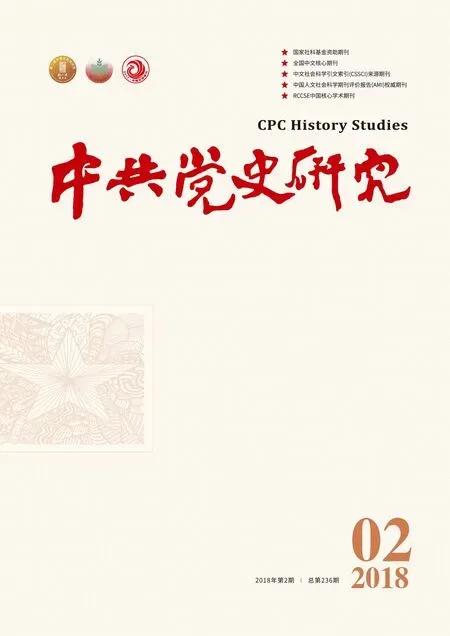在“統戰”與“敵后游擊”間徘徊:中共東江抗日武裝的建立及發展(1938—1943)*
楊 新 新
1943年初,根據新成立不久的中共東江軍政委員會內部統計,在東江等地進行敵后游擊戰爭數年的曾生、王作堯部隊(即1942年更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主力),經歷了“東移”*即1940年初,為避免被國民黨方“圍剿”,曾、王二部由東江等地向粵東海陸豐地區轉移的行動,下文對此有專門討論,此處不再贅述。與大嶺山、陽臺山“反頑”、反“掃蕩”戰爭洗禮后,已由建立之初不足百人且毫無任何軍事經驗的游擊武裝,擴展至擁有1300余人槍,初步形成一定戰斗力,并正在“向正規軍發展”的“主力部隊”*《林平給中央轉恩來電——關于東江與三角洲兩區的工作總結》(1943年2月21日),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8, 1986年,第224頁。,成為廣東戰場上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獨立抗日武裝力量。
然而就在同一時期前后,由時任中共東江軍政委員會主任尹林平發給中共中央并南方局的報告,以及部分干部戰士的后來回憶中表示,當時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非但未公開打出中共領導的旗號,僅以“愛國青年和華僑、港澳同胞自發組織的群眾抗日武裝的面目”活動,*《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83頁。且部隊中的部分干部、戰士對國共間可能發生內戰沖突的“殘酷性”“長期性”不夠警惕,始終對廣東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抱有一定的“樂觀”與“幻想”情緒*《東江區一年工作報告與今后工作方針》(1943年2月21日),本書編委會編:《東江縱隊志》,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第501頁。。
對此,后來者不禁要問,1943年前后,中日戰爭已進行數年,中共在華北、華中等地公開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已成氣候,*參見楊奎松:《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日軍事戰略方針的演變》,《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為中日戰場上各方所矚目,何以唯獨廣東一隅中共領導之抗日游擊武裝,卻遲遲未公布旗號?此外,隨著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到1943年前后,國共兩黨雖仍然互有合作需求,但實際關系已大不如前。在此情況下,東江等地之中共軍事武裝人員,又為何對廣東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始終抱有“樂觀”與“幻想”?
根據現有研究可知,盡管學界已就抗戰時期東江等地中共領導下的游擊武裝之建立與發展過程等問題作了一定程度的討論,然而為數眾多的分析,基本屬于就事論事式的平鋪直述,并未對廣東中共抗日游擊武裝不同于其他地區的路徑演變特征等問題作較為深入的闡述與解釋。*主要相關論著參見《東江縱隊史稿》,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廣東人民武裝斗爭史》第3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東江縱隊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1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本書編委會編:《中國共產黨東江地方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深圳市史志辦公室編:《中國共產黨深圳歷史》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丁身尊主編:《廣東民國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方志欽、蔣祖緣主編:《廣東通史·現代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等。換言之,較之華北、華中等地,華南抗戰爆發以來,中共廣東黨組織在東江等地主導之敵后抗日游擊武裝斗爭,經歷了何種大相徑庭的歷史發展過程,以致進入抗戰相持階段中后期,其仍然呈現出上述不一樣的問題與特點,值得后來者進一步研究。
一、“統戰地方”與華南抗戰前中共廣東黨組織的“抗日武裝工作”策略
從現有可見的相關材料來看,盡管早至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未久,中共中央便已提出并在華北等地展開了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參見楊奎松:《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后游擊戰》,《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2期。。然而考慮到1937年七八月前后,華南的中共廣東地方黨組織正著手于組織的重建與恢復,重點工作仍在健全并鞏固“南方黨組織的基礎”*《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報告——關于政治形勢、黨組織概況、群眾運動和目前重要工作》,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6,1986年,第84頁。,則可知這一時期,廣東等地雖有個別黨員與部分進步青年學生被派往參加了廣州、東江等地國民黨當局舉辦的壯丁隊、軍政干部訓練班以及民眾自發成立的各類抗日武裝自衛團體等,為未來之敵后游擊戰爭培養了“軍事骨干”,*《中國共產黨東江地方史》,第266頁。但整體而言,中共廣東地方黨組織對敵后游擊武裝斗爭等工作卻并無太多實質性的準備。
中共廣東地方黨組織開始對抗日軍事武裝斗爭等問題有所考慮,大約在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加緊進攻南部中國之后。一方面,根據駐武漢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長江局聯席會議的決定,兩廣地區中共地方黨組織工作中心由香港轉移至廣州,長江局派組織部干部黃杰巡查兩廣,加強對華南等地群眾抗日救亡運動與抗日軍事武裝斗爭的領導與準備。*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04頁。同時通過國共雙方以及周恩來與英國方面的協商,中共中央又分別在廣州、香港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積極開展對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余漢謀、香翰屏及其所部的軍事統戰工作*《東江縱隊史》,第7—8頁。。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遲至1938年4月中共廣東省委正式成立以前,中共廣東地方黨組織的抗日軍事武裝斗爭準備,并非側重于敵后獨立武裝游擊戰爭的動員與發動,而主要著眼于通過各類統戰關系以及成立“抗先”(“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等抗日青年統一戰線組織,輸送青年學生投考國民黨官方舉辦的各類“軍校訓練班”,并組織青年隨軍服務隊,在國民黨地方正規部隊中開展以“堅持抗戰”“鞏固統一戰線”為主的“模范軍人”運動,*《張文彬關于廣東工作的綜合報告——關于廣東共產黨的工作環境和群眾運動、武裝斗爭、反托斗爭》(1938年),《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6,第333—336頁。以求促成廣東國民黨軍抵御外患,擴大中共在本地的組織與影響力。
而這一時期,中共廣東黨組織的軍事武裝斗爭工作之所以著重于通過各種合法運動形式,努力在本地國民黨軍隊中建立統一戰線關系,推動廣東抗日救亡運動發展,與以下兩方面存在一定的聯系:一方面七七事變以來,廣東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內部派系傾軋,余漢謀等人有意借用中共力量與統一戰線口號,以壯大聲勢,故大膽啟用進步青年,放開民眾運動*《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6,第299—300頁。;另一方面國共再次攜手后,中共中央要求活動于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各白區地方黨組織應放棄此前的地下黨式的關門主義態度,在“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旗號下,團結“一切各黨各派各階層各實力派”與“最廣大的中間群眾”,改造國民政府及其軍隊“使之走向實現民族獨立、民主自由與民生幸福的革命三民主義道路”*《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1937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224—228頁。。
事實上,就當日之情勢來看,正處于組織重建中的中共廣東黨組織,的確也一度因部分干部、黨員的“‘左’傾關門主義情緒”,以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執行不力,黨組織恢復與發展工作出現不同程度的阻礙與滯后。直至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后,毛澤東秘書張文彬調至華南,轉變本地黨組織革命策略,放手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建立統戰關系后,中共廣東黨組織在國民黨地方部隊中的軍事統戰工作方才顯露成效。*《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1卷,第387頁。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因為張文彬等人來粵后,不遺余力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并且中共廣東黨組織遠離中共中央,也未如華北、華中等地的中共黨組織一般掌握諸如八路軍、新四軍一類的正式軍事武裝,這也造成一段時期內,部分本地干部黨員在華南抗日軍事武裝斗爭工作的開展與認識上,出現了重視對國民黨正規軍的“兵役”統戰運動,而相對輕視建立敵后獨立武裝游擊戰等傾向。
華南等地中共黨組織將開展敵后獨立武裝游擊戰爭正式提上議事日程,則要晚于1938年4月中共廣東省委成立。遵照中共中央與長江局的指示,新成立的中共廣東省委設立了專門的軍事委員會,任命省委常委尹林平擔任省軍委書記,并就黨員參加各地自衛團體,組織群眾抗日武裝等問題作了初步討論。*參見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廣東黨史大事記(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第184—185頁。
同年夏秋,隨著日軍進犯華南地區計劃的加速,以及中共敵后游擊戰爭總體“政略”的確定,廣東省委又在廣州召開了武裝工作會議,并就發動敵后抗日武裝斗爭等問題作了具體部署,要求各地黨組織應“將武裝工作提到第一位”,利用各種方式,建立并加強對地方抗日自衛武裝的掌握,實現黨內的“軍事化”,以為將來全面展開敵后抗日游擊戰爭預做準備。*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7頁。同時,廣東省委還擬定了日軍入侵廣東后,以東江地區為中心,開展敵后游擊戰的計劃,并調派部分有軍事經驗的干部返回東江等地,加強對當地抗日武裝工作的領導*參見《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1卷,第401—402頁。。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由于華南抗戰爆發前,中共廣東黨組織部分干部黨員在本地的“抗日武裝工作”中較為重視與國民黨地方正規軍“交朋友”、建立統戰關系。加之此時廣東黨組織多數黨員為學生、知識分子出身,并無軍事斗爭經驗,部分省委負責干部又因擔心中共廣東黨組織力量薄弱,東江等地可供回旋余地較小,不適于敵后游擊戰爭的開展,以致出現信心不足等問題。這使得廣州武裝工作會議后,東江“幾個中心縣委”雖根據省委要求,開始建立起軍事武裝部,并著手于“地方自衛武裝團體的工作”,但總體上而言,廣東黨組織對游擊戰爭的實際領導,卻依然是各項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環”。*《張文彬關于廣東工作的綜合報告——關于廣東共產黨的工作環境和群眾運動、武裝斗爭、反托斗爭》,《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6,第316頁。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廣州淪陷后中共領導下的華南敵后游擊戰爭的發動與展開較之華北、華中等地更顯曲折與復雜。
二、重“統戰”傾向影響下中共東江抗日游擊武裝的初建及其“反復”
1938年10月12日,日本華南派遣軍第21軍在海軍的配合下,從惠陽大亞灣登陸,開始進犯廣州。面對日方的突然進攻,由于國民黨軍政當局在情報研判上出現失誤,未作有效防范,使日軍得以長驅直入,數日內直逼廣州城郊。中共廣東黨組織部分干部領導此前在抗日軍事問題上“過分信賴廣東當局的力量”,強調抗日統一戰線的作用,應對戰爭爆發的準備不足。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此時赴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未歸,事發后省委又缺乏統一的行動計劃與部署,致使部分黨員干部一度出現了“彷徨失措”等情況。*《目前形勢與斗爭任務——林平在區黨委干部會議上的報告》(1945年7月7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8,第435頁。
廣州淪陷前后,中共廣東省委因在廣東各地“沒有真正可以掌握的武裝”,不得不計劃隨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撤往粵北*《楊康華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頁。。10月13日,日軍登陸大亞灣的第二日,負責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廖承志召集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恒、海員工委書記曾生等,研究部署在東江敵后開展武裝游擊斗爭,決定派通曉客家語言、熟悉惠陽等地情況的曾生,以及有一定軍事斗爭經驗的謝鶴籌、周伯明等,率部分惠州籍黨員干部與華僑、工人等返回惠陽坪山,組織抗日游擊武裝,成立“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并將相關決議電報中共中央*參見《曾生回憶錄》,第94—96頁。。幾乎與此同時,10月15日,在未接到上級黨組織指示的情況下,中共東莞中心縣委亦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在此前本地黨組織部分掌握的“東莞常備壯丁隊”的基礎上,通過本地統戰關系,成立名義上隸屬國民黨縣政府,實際由中共東莞中心縣委領導、縣委武裝部長王作堯任隊長的“東莞模范壯丁隊”,展開敵后抗日游擊斗爭*參見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歷史的閃光——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的回顧》,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頁。。
面對廣東局勢的變化,在接到廖承志等來電后,11月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給廣東省委、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回電,同意了廖承志等人關于在東江敵后獨立開展抗日游擊戰的計劃,*《廣東工作報告摘錄及談話記錄》(1940年6月11日),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4,1987年,第269頁。同時指示中共廣東黨組織應積極利用國民黨方同意各地成立自衛軍的訓令,發展“人民抗日武裝”,在東江、海陸豐等“日占區后方開拓游擊區”,建立抗日根據地,爭取并推動廣東國民黨地方當局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廣東黨統戰、群眾工作的意見》(1938年11月1日),轉引自《東江縱隊史》,第21—22頁。。
事實上,盡管在接到中共中央關于同意開展華南敵后抗日游擊戰指示以前,惠陽、東莞等地的敵后游擊武裝工作實際已在部分黨員干部的領導下鋪開,然而因受到此前中共廣東黨內“重統戰工作,輕武裝斗爭”傾向的影響,部分干部黨員卻對獨立開展敵后抗日軍事游擊斗爭出現信心不足,以致消極執行等問題。 直至張文彬返回廣東,向廣東各地黨組織傳達了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要求廣東黨組織必須把“發動與組織敵后及前線上廣大群眾游擊戰爭,配合正規軍作戰,作為黨的中心任務”之后, 組織發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方才真正成為廣東黨組織“第一等重要工作之一”。從此后一段時期內曾生、王作堯等人在惠陽、東莞等地動員并發展敵后民眾游擊戰之情況來看,由于中共廣東省委此前將工作重點放在對廣州、香港等大城市中國民黨軍政當局之統戰與青年抗日民族救亡運動等的發動上,相對忽視在鄉村地區的組織發展與民眾動員工作,導致中共當時在廣東的影響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區,鄉間一般民眾不但不清楚共產黨為何種組織,且對曾、王等人發展游擊武裝有所顧忌*《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6,第331頁。。甚至連部分農村地區的黨員亦“只知抗日”,不清楚黨的具體政策,一味緊跟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走*王作堯:《東縱一葉》,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頁。。這也給東江等地中共初期的敵后抗日游擊戰之發動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為解決上述問題,同時注意到國共雙方在廣東力量對比懸殊,中共廣東省委對積極開展支持以余漢謀、張發奎等部為中心,建立“模范統戰省”的工作方針尚未改變,*《張文彬關于廣東工作報告——抗日戰爭發展、各政治派別關系、黨的工作》(1940年4月23日),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7,1986年,第170—173頁。出于減少雙方間“摩擦”的考慮,曾生、王作堯等人一方面根據中共中央要求,并未公布其黨員身份,而是以組織民眾自衛隊、群眾抗日武裝等面目活動,以爭取本地國民黨軍政當局的支持*馮鑒川:《華南抗日縱隊的建立及其歷史貢獻》,《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另一方面他們又依靠本地人的身份優勢,利用宗族與同鄉關系,以及“抗先”、“惠青”(“香港惠陽青年會回鄉救亡工作團”簡稱)等中共外圍青年組織此前在東江地區宣傳抗日救亡時打下的人脈基礎,動員本地青年學生與民眾參加并支持敵后抗日游擊戰,并積極與本地民團、土匪等武裝搞好關系*王作堯:《東縱一葉》,第78—79頁。。
同時,受益于東寶惠邊地區靠近香港的便利條件,曾、王二部又得到經由香港地方黨組織、“海委”“八辦”以及海外華僑等轉來的經費與物資的支持*中國海員工會廣東省委員會編:《廣東海員工人運動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頁。。這使曾、王二部在東寶惠邊等地的活動,終于打破了此前一度被動的局面,得到了國民黨方面與地方社會的支持,獲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由于曾、王二部在建立敵后抗日軍事武裝初期,中共廣東黨組織部分領導干部一再強調敵后游擊武裝斗爭必須同對國民黨方的統戰工作相配合,故其并未公開打出中共領導的旗號,而是接受國民黨方頒發的番號,隨國民黨正規軍行動*參見《歷史的閃光——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的回顧》,第6—7頁。。加之此時曾、王游擊隊中成員以返鄉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乃至本地婦女、“老媽媽”居主,多無任何軍事斗爭經驗,不適應游擊作戰,對堅持敵后武裝游擊戰爭信心不足*參見陳文慧:《東莞模范壯丁隊的女戰士》,《南粵紅棉》,廣東省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東江組,1983年,第47—48頁。。1938年12月前后,日軍占領廣州后“回師掃蕩”東江地區,國民黨駐軍迅速潰敗,撤往香港新界等地,曾、王游擊隊中不但出現了成員開小差離隊等問題,曾生部與姚永光率領的東莞模范壯丁隊部分游擊武裝人員,甚至出現了丟掉武器,隨國民黨軍一道撤至香港“避難”等情況,*周伯明:《投筆從戎,鏖戰東江——憶曾生同志》,《懷念周伯明同志》,廣州地區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東江縱隊分會、珠江縱隊分會,1999年,第215頁。致使中共領導的東江敵后抗日游擊戰在發展初期遭到了一定的挫折與反復。
1938年12月底,廖承志、梁廣等以新成立的中共東南特委的名義在九龍彌敦酒店召開會議,會上廖承志批評了曾生、姚永光等人隨國民黨軍撤至香港的錯誤行動,要求曾生等人帶隊重返東江敵后,堅持敵后游擊武裝斗爭。同時,廖承志等還要求其應設法運用統戰關系,取得國民黨方的支持,公開打出抗日部隊的旗號,以便獲得民眾的支持與“港澳愛國同胞和華僑的支援”。*《楊康華回憶錄》,第83頁。
會后,根據廖承志與東南特委的安排,一方面,曾生等人借葉挺在東江等地與國民黨軍中的影響力,*1938年10月前后,葉挺因與項英意見上出現分歧,離開新四軍,返回廣東,擬接受余漢謀委任,赴東江惠州老家發動抗日游擊戰。后因蔣介石擔心余漢謀與葉挺等人在地方做大勢力,堅決反對,而不得不作罷,葉挺重新回到新四軍任軍長。但葉挺滯留廣東期間,通過廖承志的從中牽線,卻也為曾生等人重返東江敵后提供了不小幫助。參見袁鑒文:《懷念老隊長王作堯同志》,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懷念王作堯將軍》,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25頁。收容部分潰散到新界等地之國民黨士兵,并收集其丟棄之武器,帶隊重返東江敵后*參見《曾生回憶錄》,第108—109頁。;另一方面,堅持東江敵后的王作堯等人,亦從大嶺山轉移至東寶邊地區,與由當地中共黨員黃木芬等人掌握的抗日自衛隊匯合,連同阮海天等從增城等帶來的“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第三區常備隊”一起,整編為“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參見葉龐:《東寶邊區工委》,東莞政協編:《山鷹之歌——東莞路東三區革命斗爭紀實》,廣東經濟出版社,2015年,第62—63頁。。此后,曾生、王作堯等部隊遂再次在東江敵后逐步站穩了腳跟。
鑒于曾生、王作堯二部中多數成員缺乏必要的軍事斗爭經驗,就在曾生等率部重返惠陽后不久,東南特委一方面電告中共中央,請求調來部分有實戰經驗的粵籍軍事干部梁鴻鈞(除外)、盧偉如、李振亞、鄔強等人,分派至曾生、王作堯二部,開辦軍事訓練班,加強對部隊干部、戰士軍事素養的提升*黃業:《深情懷念鄔強同志》,中共英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懷念鄔強同志》,1994年,第28頁。;另一方面廖承志與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又積極聯絡南洋英荷屬惠州僑胞,成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簡稱“東團”),返回東江敵后,與“惠青”等中共外圍組織合并,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從物資捐募、民眾動員等方面,配合曾、王二部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之展開*葉鋒:《活躍在大亞灣沿岸的惠青救亡工作團》,中共惠陽縣委員會、惠陽縣人民政府編:《大亞灣風云》,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6頁。。
與此同時,曾、王二部亦積極利用當地“響馬”曾鴻文等人的關系,籌集錢糧武器,收編土匪、自衛武裝等,壯大自身力量,并通過統戰與地方宗族關系,再次取得國民黨軍給予的正式番號,分別被編為“第四戰區第三游擊縱隊新編大隊”(曾生部)、“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挺進指揮部第四游擊縱隊直轄第二大隊”(王作堯部)*參見王作堯:《東縱一葉》,第78—79、83—88頁。。1939年5月,中共東江軍事委員會(簡稱“東江軍委”)成立之時,曾、王兩部已擴張至數百人槍,初步建立起槍械修理所、醫務室、鞋廠和被服廠,*《廣東人民武裝斗爭史》第3卷,第103頁。并在部隊內部秘密成立了黨組織*曾文:《回顧“東縱”基層部隊的政治工作》,中共惠陽縣委黨史辦公室、東縱惠陽縣老戰士聯誼會編:《東縱戰斗在惠陽》,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頁。,成為東江敵后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游擊武裝。
三、“東移”受挫與中共東江抗日軍事武裝策略的部分調整
正當曾、王二部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東江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局面初步有所打開之日,1939年底1940年初,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國共合作關系出現波折,雙方軍隊在各地摩擦不斷*參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9—391頁。。曾、王二部此時亦因在東江等地擴張過快,受限于物資供給不足等問題的影響,不得不開始執行較為激進的“打土豪”等政策,影響到部分本地勢力的利益,進而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發生沖突*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p.24.。1939年11月,陳誠到廣東韶關攻訐中共在敵后戰場“游而不擊”,表示要“嚴防共黨活動”。此后,國民黨東江地方當局開始限制中共外圍組織“東團”等在東江地區的抗日救亡活動,并以勾結土匪、擾亂治安為由,逮捕了“東團”博羅隊成員楊德元等人*《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事件紀實》,《廣東華僑港澳同胞回鄉服務團史料——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1985年,第277頁。。同時,國民黨第四戰區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香翰屏亦以“協助工作”為名,要求派人到曾、王二部中擔任副隊長等職務,并調集部隊包圍曾、王二部,要求其前往惠州城內進行整編、集訓,妄圖予以繳械并消滅之*《梁廣關于坪山事件經過的報告——事變發生的經過、影響及應解決的幾件事》(1940年4月12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7,第133頁。。
面對局勢的惡化以及國民黨方面逐漸轉變的態度,由于中共廣東黨組織內部就是否繼續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并長期與國民黨方合作等問題產生了認識上的分歧;加之“發展敵后游擊戰爭”工作雖已成為這一時期中共廣東省委的“四大任務”之一,但部分干部黨員對此一直信心不足,“武裝斗爭經驗缺乏”等問題長期存在*黃業等:《真鋼火煉,光輝一生》,《懷念曾生同志》,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6年,第88頁。。
1940年初,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明確指示,且內部爭議頗多的情況下,為免活動于東江敵后的中共游擊武裝因力量薄弱,被國民黨方一網打盡,中共東江軍委根據潛伏在國民黨方游擊指揮部中的地下黨員送來的情報,匆忙作出決定,曾、王二部暫時脫離東寶惠邊地區,向粵東海陸豐等地轉移*參見《東江縱隊史稿》,第34—35頁。。
6 作者投稿時須從郵局匯20元稿件處理費,請勿在稿件中夾寄。稿件確認刊載后,將按標準向作者收取版面費(版面費請從郵局寄給本刊編輯部)。我刊收到版面費后,將出具正式收據,以掛號信形式寄給作者。稿件刊登后酌致稿酬,并贈當期雜志1冊。稿件及匯款請勿寄給個人。
由于部隊在轉移前動員、準備工作不足,轉移過程中又遭國民黨方圍追堵截,隊伍抵達海陸豐地區后,更因語言不通,不熟悉當地情況,缺乏地方社會與民眾的支持,*王作堯:《東縱一葉》,第114頁。以致傷員無法得到有效救治,彈藥、物資極度匱乏,部隊減員較為嚴重,從出發前的800余人驟減至100多人,且“軍事上完全陷于被動”,干部戰士情緒低落,處境十分艱難。*《東江縱隊史》,第57頁。
1940年5月,在從梁廣與東南特委處獲悉曾、王二部“東移”后出現上述困難后,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廖承志與東南特委等,指出曾、王二部脫離東江前線,轉入“后方停留”,在政治上是“絕對錯誤的,軍事上也必失敗”,要求其必須重返東寶惠邊地區,大膽堅持敵后抗日游擊戰,不怕與國民黨方“摩擦”,以求得“生存發展”*《曾、王兩部應回防東寶惠并注意行動事項》(1940年5月8日),《東江縱隊志》,第486頁。。同年8月,在接到中共中央命令后,曾、王二部克服重重困難,陸續從海陸豐地區返回惠陽、寶安前線,并在寶安上下坪召開干部會議,總結“東移”的經驗教訓,確定未來東江敵后抗日游擊戰的基本方針與任務*《廣東人民武裝斗爭史》第3卷,第128頁。。
會上,按照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等關于“糾正對廣東環境特殊的樂觀估計”*《中共中央關于時局逆轉與黨的應付措施給粵委的指示》(1940年4月1日),南方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設》,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17頁。,以及“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3頁。會議決定返回東江敵后的曾、王二部,放棄此前國民黨方發給的番號,部隊更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曾部為第三大隊,王部為第五大隊),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并建立抗日根據地與民主政權。同時對國民黨方實行“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名義上暫不公布中共領導的旗號,以便獲取更多的支持與同情,避免與國民黨方的公開決裂。*參見《東江縱隊史》,第63頁。
上下坪會議后,針對曾、王二部中因“東移”分歧出現的“干部不團結”以及部分黨員“消極逃避,軍事政治均采取被動”等問題,為加強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以及東江敵后和前線工作的領導,根據此前中共廣東省委執委會的決議,中共東江軍委又任命曾擔任過紅軍團長與八路軍延安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有較豐富軍事斗爭經驗的尹林平、梁鴻鈞等,分別出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政治委員與軍事指揮,同時尹林平兼任東江特委、前東特委書記。同年10月,在尹林平等人的指揮下,第三大隊開赴東莞,創建以大嶺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留在寶安的第五大隊,則在王作堯等人的領導下,建立起以陽臺山為中心的路東抗日根據地。*參見《廣東人民武裝斗爭史》第3卷,第130—136頁。
到1941年年中,盡管受內外形勢的影響,廣東黨組織內部仍有部分干部黨員,對中共能否在華南等地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抱有疑惑,其在本地抗日軍事武裝斗爭策略問題上相對重視“統戰”國民黨正規軍的傾向并未全然轉變*參見《目前形勢與斗爭任務——林平在區黨委干部會議上的報告》(1945年7月7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8,第432—433頁。。然而在廖承志、梁廣等領導的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粵南省委以及華僑、東寶等地地方勢力的支持下,初步積累了一定游擊經驗的曾、王二部,擋住了國民黨地方部隊與日偽軍的“圍剿”,并逐步走出了“東移”失敗的“陰影”,使隊伍再次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與發展*吳克輝:《中共領導的東江抗日武裝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歷程和基本經驗》,廣東省人民武裝斗爭史編纂委員會編:《廣東人民武裝斗爭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8頁。。
四、香港淪陷、廣東國共關系公開破裂與中共東江游擊武裝的大發展
1941年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受益于尹林平等軍事干部的指揮,愈發能夠靈活運用游擊戰術,避實就虛,給“圍剿”“掃蕩”東江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日、偽、頑各方予以有效打擊,戰斗力逐步提升,初步建成以東寶惠邊地區為中心的東江抗日游擊基地*參見《東江縱隊史》,第90—91頁。。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駐寶安等地的日軍,渡過深圳河,進入新界,向香港發起進攻。25日,英軍宣布放下武器,港督楊慕奇(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向日軍投降,香港遂告淪陷。
香港被日軍占領后,由于日軍為將香港“變成海空軍輔助港,太平洋戰爭的后方根據地”,加緊了對各項戰略資源的控制,這導致活動于東寶惠邊地區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武裝一直通過香港獲取地下黨、海外華僑等經費、物資支持的渠道就此被截斷,使得部隊經濟緊張等問題開始顯現*參見《林平給中央轉恩來電——關于香港淪陷后的一般情況》(1943年2月),《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8,第233—234頁。。
為使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早日擺脫上述困難局面,1942年1月,轉入東江游擊區的中共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在寶安縣白石龍村召開干部會議。會議在總結了此前東江地區敵后游擊斗爭的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為“加強和統一東江地區敵后游擊戰的軍隊和地方黨的領導”,決定成立東江軍政委員會,任命尹林平為主任,同時建立直接與延安、南方局以及南委聯系的電臺。*參見《曾生回憶錄》,第239頁。
鑒于東江等地的游擊部隊較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擴展,會議另決定,對東江抗日游擊武裝進行整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更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下轄一個主力大隊和四個地方大隊,任命梁鴻鈞為總隊長,尹林平兼任政治委員。同時,為解決部隊經濟緊張等問題,張文彬一方面去電中共中央,請求通過秘密渠道撥給經費予以支持*《張文彬報告東江情況》(1942年1月10日),《東江縱隊史料》,第41頁。;另一方面他希望借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共關系有所調整,加強對國民黨地方當局的統戰工作,促其能夠恢復東江等地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隊之“名義”與“番號”,并重新“劃分防地,發給經費”,以使之繼續“配合國軍”作戰。*參見張文彬:《我們的主張》(1942年1月下旬),《東江縱隊史料》,第43—44頁。
就在張文彬等人積極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溝通協商,試圖再次通過統一戰線關系,努力使廣東敵后游擊戰爭走出困谷時,1942年4月,“南委”與“粵北省委”事件相繼案發,中共廣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廖承志、張文彬等人陸續被捕,國共兩黨在廣東關系公開破裂,幾無再繼續合作的可能。華南國統區各中共黨組織被迫停止活動,轉入隱蔽狀態。*有關“南委”“粵北省委”事件詳細經過的討論,可參見《“南委事件”與華南共產黨組織的應變措施》,林天乙:《中共黨史論叢》,岳麓書社,2005年,第228—246頁。
與此同時,隨著1942年夏秋以來,廣東各地久旱不雨,災情不斷,出現嚴重糧荒,日偽與國民黨方等加緊了對東江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封鎖與“圍剿”*參見《林平致中央并恩來電——關于今年一月后敵、我、友、頑的情況》(1943年3月),《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8,第251頁。。失去香港與各地方黨組織支持,對處于“保存力量,長期埋伏,等待時機”中的地下黨施以援手,使原本便經濟緊張、陷入發展困境中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更是“雪上加霜”,進入前所未有的困難期*參見《林平給中央并周恩來電——一年來政治形勢的總結與今后時局的動向》(1943年2月7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8,第218頁。。
面對愈發嚴峻的形勢,在已無法依靠統戰關系與外部渠道維持敵后武裝游擊戰爭的情況下,1943年初,周恩來致電東江游擊隊負責人尹林平等,指出國民黨方對東江中共武裝“勢在必打,志在消滅”,要求廣東各地干部黨員必須破除此前對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不切實際的幻想,克服困難,艱苦奮斗,同日偽與國民黨方作針鋒相對的斗爭,粉碎其對根據地與游擊隊的封鎖與“圍剿”。*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562頁。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與中共南方局的決定,1943年2月,“南委”事件后兼任新成立的廣東省臨時委員會(簡稱“省臨委”)書記,統管廣東各地黨組織的尹林平在香港九龍烏蛟騰村召開省臨委與東江軍政委員會聯席會議。會上,敵后軍事斗爭經驗較為豐富的尹林平提出,廣東黨與東江等地的敵后游擊隊應改變此前礙于同國民黨方的“統戰關系”而不得不“固守已有根據地”的保守做法,需采取靈活多變的運動游擊戰戰術,主動出擊,深入敵后,發展新區,進行徹底、堅決的敵后獨立抗日武裝斗爭。*王作堯:《尹林平同志在廣東武裝斗爭中的貢獻》,《尹林平》,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頁。
針對游擊隊與根據地經濟緊張、物資短缺以致隊伍發展相對停滯等問題,會議決定,一方面東江軍政委員會精簡上層機關,減少不必要的開支,領導干部分散各地,充實并加強基層戰斗部隊;另一方面,又調得力干部專門負責根據地“經濟發展”以及稅站建立等“財經工作”,以增加部隊收入*《東江革命根據地稅收史概述》,《東江革命根據地稅收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頁。。同時,利用宗族、同鄉等社會關系,收編土匪、偽軍等,建立“白皮紅心”政權與外圍武裝組織,并派出小股武裝深入港九敵后等交通要道,建立海上游擊隊,為部隊主力收集情報、籌集物資、安置傷員等*《林平給中央并周恩來電——一年來政治形勢的總結與今后時局的動向》(1943年2月7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8,第226頁。。
烏蛟騰會議后,由于受內外形勢再次變化的影響,華南抗戰以來中共廣東黨組織內部長期存在的“重統戰工作,輕武裝斗爭”的傾向得以基本祛除,獨立自主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的軍事方略最終確立并得到較好執行。東江等地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武裝也因此打破了國民黨方的封鎖進攻以及日偽方的“萬人大掃蕩”,渡過了“籠罩著悲觀、失望”情緒的最艱難歲月*《東江縱隊工作報告——對敵戰斗及黨的建設情況和經驗教訓》(1944年10月),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6,1987年,第56頁。。到1943年底,經過一年左右發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擴至3000余人槍,部隊戰斗力、政治覺悟等有了明顯提升。東江敵后根據地建設與財經工作水平亦有了顯著提高,基本實現了游擊隊與地方黨組織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參見林平:《東江游擊區目前情況》(1943年11月23日),《東江縱隊史料》,第77—78頁。。
鑒于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已在東江敵后“站住腳跟”,并通過營救港九等地文化名人與盟軍戰俘等行動為各方所熟知,且其接受中共領導的事實已為公開秘密,再無隱瞞必要。根據尹林平等人的請求與建議,遵照中共中央隨后的指示與要求,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正式更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同日,東江縱隊在成立宣言中明確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擁護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宣言》,《東江縱隊史料》,第88頁。。此后,東江敵后抗日游擊隊開始以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的名義公開活動,中共東江縱隊遂成為華南抗日戰場上一面重要的旗幟。
五、結 語
無論是華南抗戰期間曾出任過中共東江縱隊司令的曾生,還是曾兼任東江縱隊政委與東江軍政委員會主任的尹林平,在其后來關于中共東江敵后抗日游擊隊的發展歷程及其經驗教訓的回憶與檢討中皆認為,遲至1943年初烏蛟騰會議前后,中共廣東黨組織在抗日軍事武裝斗爭問題上“獨立自主依靠人民開展和堅持敵后游擊戰爭”的策略才最終得以全然確立,*參見尹林平:《東江縱隊統戰工作的回憶》,中共寶安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回顧東縱統戰工作》,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17頁。部隊各方面形勢此后也邁入了新局面,有了較大程度的進展*《曾生回憶錄》,第286頁。。這表明,1943年前后是中共東江敵后抗日游擊武裝朝著良性方向轉變的重要時間節點。在此之前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共廣東黨組織內部在對獨立自主開展本地敵后抗日游擊戰等問題上可能并未達成一致,缺乏明確的“斗爭方針和路線”*尹林平:《東江縱隊統戰工作的回憶》,《回顧東縱統戰工作》,第15頁。。廣東的中共抗日游擊武裝的發展過程并不順利。
事實上,通過本文的前述分析可知,誠如曾生、尹林平等人的回憶所言,由于華南抗戰爆發前后,重建后不久的中共廣東黨組織自身力量較為薄弱,未掌握諸如八路軍、新四軍一類的正式軍事武裝,加之其反需要利用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的統戰關系,加緊組織的鞏固與發展,這導致中共廣東黨組織內部部分干部黨員在本地抗日軍事武裝策略問題上始終存在著“重統戰工作,輕武裝斗爭”等傾向,這使得東江等地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武裝的建立與初期的發展,充滿了反復與挫折。直至香港淪陷,國共兩黨關系在廣東公開破裂,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后,廣東黨組織內部“害怕統一戰線破裂,不敢對國民黨作堅決的自衛斗爭”等問題才得以基本解決,中共東江抗日游擊武裝此后也迅速改變了之前的被動地位,實現了部隊的大發展。*《中國共產黨深圳歷史》第1卷,第136頁。
當然,也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自華南抗戰以來,到1943年前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抗日軍事武裝策略始終在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開展統戰與獨立自主地進行敵后游擊戰之間徘徊,這一方面雖然也一度造成中共東江抗日游擊武裝的建立與發展過程充滿了跌宕起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另一方面本地黨員干部與部隊戰士也在這一曲折復雜的過程中積累了軍事游擊戰的實際經驗與教訓,逐步堅定了開展抗日武裝游擊斗爭的信心與決心。因此,或可認為,到1943年前后,中共廣東地方黨組織徹底走上獨立自主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之路,中共東江抗日游擊武裝較之從前實現了跨越性的發展,無疑是各種外在條件變化所使然,也是其自身內在演變邏輯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