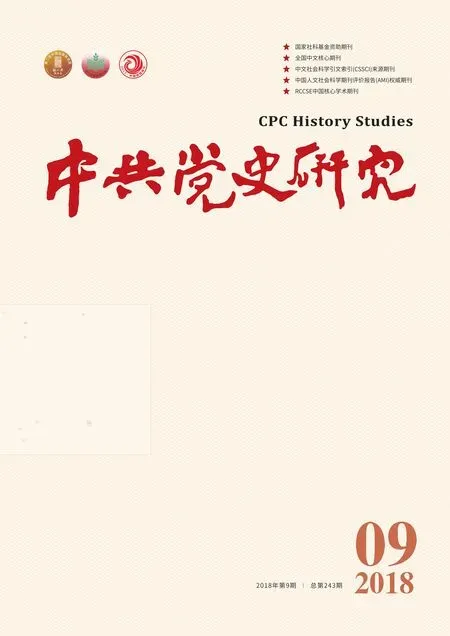紀(jì)念李新同志
金 沖 及
現(xiàn)有的中國(guó)史學(xué)史著作,大抵只寫(xiě)到晚清和民國(guó)時(shí)期。對(duì)新中國(guó)的發(fā)展即便講到,也十分粗略。此中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再過(guò)若干年,總會(huì)有比較詳備的包括新中國(guó)在內(nèi)的中國(guó)史學(xué)史著作問(wèn)世。拿文學(xué)界來(lái)說(shuō),不是已有不少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之類(lèi)的著作出版了嗎?以論述和剖析歷史為己任的史學(xué)工作者,決不會(huì)長(zhǎng)期對(duì)這幾十年來(lái)中國(guó)史學(xué)自身的歷史置之不顧,不去對(duì)它的發(fā)展歷程進(jìn)行嚴(yán)肅認(rèn)真的分析研究。
到那時(shí),我想,在這類(lèi)著作中應(yīng)該講到李新同志,尤其是他主持開(kāi)拓的中華民國(guó)史研究工作,因?yàn)樗a(chǎn)生的影響對(duì)史學(xué)界來(lái)說(shuō)是全局性的,而且過(guò)些時(shí)間后會(huì)看得更清楚。
李新同志是我尊敬的前輩學(xué)者,我知道他的名字已經(jīng)將近70年了,但最初聽(tīng)說(shuō)他,并不是因?yàn)槭穼W(xué),而是因?yàn)榻逃ぷ鳌I鲜兰o(jì)50年代后期,我在復(fù)旦大學(xué)擔(dān)任教務(wù)部副主任。全國(guó)的高等學(xué)校在院系調(diào)整后都在努力建設(shè)新的教學(xué)體系和制度。但是,應(yīng)該怎么做,大家心里卻沒(méi)有數(shù)。我們?cè)S多人認(rèn)真讀的是蘇聯(lián)學(xué)者凱洛夫的《教育學(xué)》,想從這里找到依據(jù),但總覺(jué)得同中國(guó)的實(shí)際情況不相符。從解放區(qū)遷來(lái)擴(kuò)建而成的高等學(xué)校只有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李新同志正在幫助吳玉章校長(zhǎng)負(fù)責(zé)人民大學(xué)的教務(wù)工作。那時(shí),上海和北京的交通往來(lái)還相當(dāng)不便,很難有機(jī)會(huì)到人民大學(xué)看看,更不容易見(jiàn)到他請(qǐng)益。但在教育部的內(nèi)部材料上,我多次讀到過(guò)李新同志對(duì)怎樣建立一套中國(guó)自己的新教育制度的談話(huà)或文章,文風(fēng)總是明白曉暢,獨(dú)有見(jiàn)地,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第一次見(jiàn)到李新同志,是1961年10月在武漢參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現(xiàn)在經(jīng)常忙于參加各種學(xué)術(shù)會(huì)議的中青年學(xué)者也許很難想象,那時(shí)全國(guó)性的學(xué)術(shù)會(huì)議是極為罕見(jiàn)的。在上海的復(fù)旦大學(xué)不算閉塞,我在復(fù)旦給學(xué)生講中國(guó)近代史的課程也已經(jīng)八年多了,但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全國(guó)性的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那次參會(huì)的前輩學(xué)者很多,如吳玉章、李達(dá)、范文瀾、呂振羽、吳晗、白壽彝、邵循正、何干之等。攝影時(shí),我和戴逸、李侃、李文海、祁龍威、王思治等站在第三排,而時(shí)年43歲的李新同志坐在第一排,可見(jiàn)史學(xué)界對(duì)他的尊重。在這種場(chǎng)合下,我不好湊上去找他,所以那次并沒(méi)有同他說(shuō)過(guò)話(huà)。
會(huì)后,我和胡繩武同志開(kāi)始著手寫(xiě)《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這時(shí),吳玉章同志關(guān)于辛亥革命的回憶錄剛剛出版,我至少認(rèn)真地讀過(guò)五六遍。后來(lái)聽(tīng)說(shuō)它是李新同志幫助整理的,確實(shí)使我肅然起敬。
1965年,我調(diào)到北京工作,但“文化大革命”隨即開(kāi)始,我被審查了五年,自然更談不上和李新同志有見(jiàn)面的機(jī)會(huì)。
我同中國(guó)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今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一些年長(zhǎng)的同志本來(lái)很熟悉。一到北京,最早來(lái)看我的,就有丁守和等同志。王學(xué)莊、劉志琴、朱宗震、丘權(quán)政、呂景琳等是我在復(fù)旦教中國(guó)近代史課時(shí)的學(xué)生。“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和近代史所同志的來(lái)往就很多了,同李新同志也有了接觸的機(jī)會(huì)。那時(shí),我在文物出版社擔(dān)任副總編輯。1980年,近代史所曾兩次來(lái)商調(diào),都沒(méi)有辦成。我心里是很愿意到近代史所做研究工作的,但由于習(xí)慣于工作安排聽(tīng)從組織決定,所以自己完全沒(méi)有過(guò)問(wèn),更沒(méi)有發(fā)表任何意見(jiàn)。后來(lái)有近代史所的朋友對(duì)我說(shuō):“調(diào)你,是‘三駕馬車(chē)’都能接受的。”近代史所的“三駕馬車(chē)”即劉大年、李新和黎澍。由此我才知道,這件事也包含著李新同志對(duì)我的厚愛(ài)。
1985年起,我被聘為近代史所的學(xué)術(shù)委員會(huì)委員(當(dāng)時(shí),所外的學(xué)術(shù)委員還有嚴(yán)中平、胡華、戴逸三位),前后共15年。李新同志當(dāng)然也是學(xué)術(shù)委員。在這段時(shí)間內(nèi),我還有機(jī)會(huì)同他一起參加了不少?lài)?guó)內(nèi)的學(xué)術(shù)會(huì)議。于是,我們的接觸就多起來(lái)了,談得最多的自然是中華民國(guó)史的編寫(xiě),有幾點(diǎn)給我的印象最深:
第一,民國(guó)時(shí)期的中國(guó),同新中國(guó)直接銜接,如果對(duì)這段歷史的方方面面不進(jìn)行切實(shí)的研究,那么,對(duì)新中國(guó)的國(guó)情和它的由來(lái)就難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在當(dāng)時(shí)的特殊條件下,能夠毅然決然地把這項(xiàng)任務(wù)擔(dān)當(dāng)起來(lái),堅(jiān)持到底,做出在國(guó)內(nèi)外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成果,實(shí)在極不容易。
這一點(diǎn),我有切身體會(huì)。前面講到,我和胡繩武同志從1961年起開(kāi)始動(dòng)手寫(xiě)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到1963年,第一卷已經(jīng)完稿,并經(jīng)上海人民出版社審讀后決定出版,編輯部的具體意見(jiàn)也提給了我們。但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的政治空氣已經(jīng)越來(lái)越緊張,聽(tīng)說(shuō)夏衍同志準(zhǔn)備拍攝關(guān)于秋瑾的電影,江青知道后就說(shuō):“怎么?現(xiàn)在還要宣傳國(guó)民黨?”我們寫(xiě)的《史稿》第一卷從孫中山的革命活動(dòng)開(kāi)始時(shí)起,到興中會(huì)成立,再到同盟會(huì)成立前夜,那不更是要被說(shuō)成“宣傳國(guó)民黨”嗎?那不是自己對(duì)準(zhǔn)了來(lái)勢(shì)兇猛的槍口沖過(guò)去?還是把這本書(shū)的出版先擱下來(lái),看看情況再說(shuō)。這一放,就放了18年,到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時(shí)才稍作補(bǔ)充、修改后出版。
一比,就見(jiàn)高下。李新同志主持編寫(xiě)中華民國(guó)史,雖然是周恩來(lái)總理在1972年提出來(lái)的,但那時(shí)“文化大革命”還在繼續(xù),這項(xiàng)工作一做起來(lái),就遇到許多阻力,編寫(xiě)中更會(huì)碰到許許多多原來(lái)沒(méi)有預(yù)料到且不易處理的問(wèn)題,存在許多未知數(shù)。如果不是李新同志下這樣大的決心,既有膽略,又有韌性,那么,拖一拖就可以把這件事拖黃,整個(gè)中華民國(guó)史研究都有可能停頓下來(lái),至少還要經(jīng)歷不少曲折。李新同志在緊要關(guān)頭表現(xiàn)出來(lái)的膽略和勇氣,不能不令人欽佩。
第二,下決心承擔(dān)這個(gè)任務(wù)后,應(yīng)該編寫(xiě)成怎樣的一部中華民國(guó)史,又面臨兩種選擇:匆忙地草草了事,就算完成一項(xiàng)任務(wù),還是堅(jiān)持高標(biāo)準(zhǔn)、嚴(yán)要求,盡力寫(xiě)出一部在當(dāng)時(shí)所能達(dá)到的高水平的著作來(lái)?
李新同志有過(guò)主持編寫(xiě)多卷本《中國(gu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通史》等的豐富經(jīng)驗(yàn),一開(kāi)始就提出很高的要求,強(qiáng)調(diào)不能急于求成,必須首先扎扎實(shí)實(shí)地掌握豐富可靠的歷史資料,進(jìn)行具體分析,盡力弄清事實(shí)真相,在此基礎(chǔ)上才能動(dòng)手進(jìn)行論述。中華民國(guó)史的編寫(xiě)就是這樣起步的。
他對(duì)編寫(xiě)中的中華民國(guó)史的結(jié)構(gòu),提出了一個(gè)氣魄宏偉的構(gòu)想,即要包括《中華民國(guó)史》《中華民國(guó)人物志》《中華民國(guó)大事記》《中華民國(guó)專(zhuān)題資料》等幾個(gè)部分。這既體現(xiàn)了他先把有關(guān)史實(shí)弄清楚、弄準(zhǔn)確,以避免出現(xiàn)“硬傷”或流于徒發(fā)空論的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中國(guó)史學(xué)著作的編寫(xiě)傳統(tǒng)。大家知道,中國(guó)號(hào)稱(chēng)正史的“二十四史”,大體上是由紀(jì)、傳、志、表幾部分組成的。《中華民國(guó)史》是主體,類(lèi)似正史中的“紀(jì)”。《人物志》在體裁上就是“列傳”。《大事記》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表”的作用。缺少的是“志”,《專(zhuān)題資料》原來(lái)設(shè)想在這方面起些補(bǔ)充作用,但沒(méi)有做完。當(dāng)然,民國(guó)史研究這樣巨大的工程本來(lái)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研究也很難說(shuō)有止境,但前人篳路藍(lán)縷的開(kāi)啟之功是永存的。
第三,參加中華民國(guó)史編寫(xiě)工作的學(xué)者人數(shù)眾多,組內(nèi)人員最多時(shí)達(dá)40多人,以后有些人分散到其他高等學(xué)校和研究單位去;參加協(xié)作的單位和人員更多;不少編寫(xiě)成果和副產(chǎn)品陸續(xù)在學(xué)術(shù)刊物上發(fā)表。這些對(duì)新時(shí)期史學(xué)界的學(xué)風(fēng)所起的“潤(rùn)物細(xì)無(wú)聲”作用是很大的。
編寫(xiě)中華民國(guó)史這件事,既是許多學(xué)者眾志成城的成果,反過(guò)來(lái),也培育出為數(shù)不少的人才,他們活躍在今天的史壇上,成為史學(xué)界后起之秀的骨干力量。這是一項(xiàng)無(wú)聲的重要成果。
李新同志知人善任,能夠把可以掌握的力量迅速組織起來(lái),各盡所能,既大膽放手,又嚴(yán)格要求,使參加這項(xiàng)工作的年輕人明白自己的任務(wù),心情愉快,比較快地投入其中并得到成長(zhǎng)。他十分關(guān)心參加這項(xiàng)工作的成員在工作和生活上的甘苦,幫助不少年輕人解決了他們難以解決的重大困難。許多人都對(duì)此有過(guò)感人的描述,我就不再多說(shuō)了。
這里只補(bǔ)充一個(gè)我親身經(jīng)歷的例子,從中可以看出他對(duì)中青年學(xué)者取得研究成果是多么喜悅,并希望這些成果被更多人所了解。
在《中華民國(guó)史》有一個(gè)分卷剛出版的時(shí)候,一天,他突然到我家里來(lái)。我實(shí)在惶恐不安,對(duì)他說(shuō):“李新同志,您老人家怎么自己來(lái)了?只要打個(gè)電話(huà),我立刻會(huì)趕到你家來(lái)的。”他就拿出這本近60萬(wàn)字的書(shū)來(lái),叮囑我寫(xiě)篇介紹文章,書(shū)上還有他自己的簽名。這件事使我很感動(dòng)。我一直把這本書(shū)放在我對(duì)面的書(shū)柜中,也是對(duì)李新同志的紀(jì)念。
今年是李新同志百年誕辰。民國(guó)史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不斷走向深入。研究民國(guó)時(shí)期方方面面歷史的史學(xué)工作者,在中國(guó)史學(xué)界占有很大比重,這已成為引人注目的事實(shí)。此時(shí)此刻,曾在李新同志領(lǐng)導(dǎo)下工作過(guò)的學(xué)者寫(xiě)出一批懷念他的文章,匯成《踏遍荒山罕見(jiàn)松——李新百年誕辰紀(jì)念文集》。陳鐵健同志囑我也寫(xiě)幾句話(huà)。這是我應(yīng)該做的。雖然寫(xiě)得很匆忙,但多少也表達(dá)了我對(duì)這位前輩的緬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