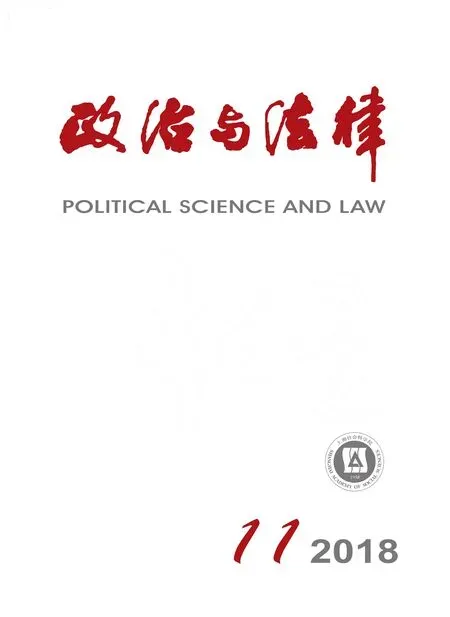從民國時期判例造法之爭看法典化時代的法律場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北京 100088)
從各國的經驗看,民法典的編纂往往是“法典化時代”的巔峰。在法律淵源領域,“法典化時代”意味著法典成了所有法律淵源的核心,其他的法律淵源的地位取決于其與法典的關系。*參見于飛:《民法總則法源條款的缺失與補充》,《法學研究》2018年第1期。我國《民法總則》第10條的規定就體現了這種認識。即便學者中始終不乏呼吁立法機關承認更多法律淵源者,這一條文仍只承認了習慣的補充性淵源地位。在法律概念領域,法典化意味著“法律來自人的創造而非發現”的觀念占據主導地位。既然立法者可以通過法典創造法律,那么其他的法律職業是否也以自己的方式創造法律?這就引出了“判例造法”。筆者于本文中所稱的判例造法,是指司法機關以判例創造規范,它既包括了法律的續造,也包括了改變法典規則的情況。無論立法者是否承認,學說(la doctrine)與判例(la jurisprudence)在各個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中都成了事實上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淵源。這背后的時代因素其實非常簡單。首先,本來用于保證法律秩序之內在價值統一和規范融貫性的法典,因為特別法漸次增加而逐漸喪失其規范整合功能。[注]參見陸青:《論中國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現象》,《中外法學》2014年第6期。其次,伴隨全球化產生的法律碎片化現象越來越普遍和明顯。[注]參見高鴻鈞:《法律全球化的理論與實踐——挑戰與機會》,《求是學刊》2014年第3期。最后,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大量新事物,不但挑戰著現有法律規范,也挑戰著法律知識體系。以上三個時代特征導致學說和判例更積極地參加規范創造的過程,并在實質意義上改變著法律的內容。因此,不能僅僅因為法律中沒有規定,就否定判例與學說之法律淵源地位,也不能認為司法裁判只是將立法者的規定具體化、學說只是對不同形式的規范進行體系整合。于是,在大陸法系國家以法典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當代法學理論體系中,出現了重新審視學說與判例在規范創造方面之作用的潮流。其實,在是否承認學說與判例之規范創造力背后,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到底是什么因素決定了一個法律體系中法學與司法的功能?
如果不回答這個問題,人們就無法正確認識學說與判例在法典化時代如何創制規范。實際上,晚近國內的研究已經提出了類似的疑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的規定》(法釋〔2009〕14號)對判例只字不提,最高人民法院卻發布指導性案例。學者們在關于判例對指導性案例的引用、效力的討論中,又不斷提出其法律淵源地位的問題。同時,法學研究者應當如何對待指導性案例也成了一個逐漸浮出水面的問題。理解決定學說與判例之間關系的因素能夠幫助人們分析和理解兩種法律淵源以及與其相對應的兩個法律群體在規范創制方面的作用與能力。
基于以上實踐關切,筆者擬于本文中以民國時期關于判例造法的爭論為素材,研究學說與判例的關系。民國時期是我國法律與法學現代化的一個關鍵時期。以民法為例,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到1931年中華民國《民法》(以下簡稱:《民法》)全部施行,這十九年是希望編纂一部體系化的成文法典卻一直沒有真正實現該目標的階段。在此期間,大理院、司法院實際上先后發揮著規范創制的功能,并為日后的法典編纂奠定了堅實基礎。其工作的材料除了《大清現行刑律》中不與共和政體相悖的民事部分和其他單行法規則以外,還有通過法學繼受的歐陸法系概念和原理。[注]參見黃源盛:《中國法史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20-421頁。在《民法》生效之初,司法上又涉及新舊規范融合問題。不妨以此考察學說和判例在中國民法典早期施行中的互動,并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社會學(sociologie réflexive)作輔助性理解。研究者把法律實踐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場”(champ social),不同的法律職業從業者在此場域中競爭關于“說出法律”的壟斷權。[注]Cf. Pierre Bourdieu, “La force du droit. éléments pour une sociologie du champ jurid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6, vol.64, no°1, p. 3-19.民國時期的相關論爭展現了立法、司法、學說三種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判例造法的雙重屬性
所謂判例造法,指的無非是司法機關在解釋立法時實質上創造規范。其載體既包括了對具體案件的個案裁判(“判”),也包括了一般性發布的解釋例(“例”)。關于判例造法的論爭之所以在民國時期的法學界產生,正是因為成文法規范將判例和解釋例作為權力和法律淵源來處理,卻在權力之行使和淵源之位階等問題上留下了過多的不確定性。
(一)作為權力的判例造法
民國的最高司法機構之沿革,大略可以劃分為1912年到1927年的(北洋政府)大理院時期和1928年到1949年的(國民政府)司法院時期。[注]參見張生:《民國初年的大理院——最高司法接管兼行民事立法職能》,《政法論壇》1998年第6期。1927年大理院改為最高法院,后成為1928年《司法院組織法》所設立之司法院的一部分。參見聶鑫:《近代最高司法機關的新范式》,《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1914年的《平政院編制令》將行政訴訟和公務員懲戒交由平政院掌理。直至1928年《司法院組織法》生效,其第1條重新把民刑事案件、行政案件與公懲案件的最高審判權都劃歸司法院掌握。兩個時期變易之際,自然于司法權和司法行政權歸屬、行政訴訟管轄權等方面有顯著的變化。如果說大理院大體上是最高司法機關的話,司法院則因為審判權和司法行政權集于一身,表現出更復雜的性質。[注]參見上注,聶鑫文。為了行文方便,筆者于本文中仍以“最高司法機關”統稱大理院和司法院。司法機關不僅有權就具體個案解釋法律之適用,也有權一般性地發布對法律的抽象解釋。這些解釋就是判例造法的具體表現形式。
無論是在大理院時期還是在司法院時期,只有最高司法機關方能以判例造法。從大理院時代到1947年“行憲”之后,民國司法系統的規范創制權僅能以“法律解釋”之名規定在各部法律之中。它一方面抽象地對法令發表意見、進行解釋,并統一法律適用;另一方面以裁判的形式在具體個案中解釋法律。《暫行法院編制法》中著名的第35條便規定了“大理院卿有統一解釋法令必應處置之權”,并有因為審檢衙門或其他國家機關之質問而統一解釋法律之權。其第37條更具體地規定:“大理院各庭審理上告案件,如解釋法令之意見,與本庭或他庭成案有異,由大理院院長依法令之義類,開民事科或刑事科或民、刑兩科之總會審判之。”可見判例和解釋例對大理院及地方各級審判機關有拘束力。[注]參見“十五年抗字第二〇號”,載郭衛編:《大理院判決例全書(下)》,上海法學編譯社1933年版,第823頁。在大理院時期,民庭在具體的判決中進行的解釋雖然裁斷的是個案中的權利和義務,其判例的寫作模式卻是提出一般性的規則。[注]參見前注⑥,張生文。并且,大理院各庭在解釋法令的意見與成案有異的情況下可以開“總會”審判,這也就意味著“總會”可以變更之前的判例。可見,大理院除了統一解釋法律,亦以判例和“總會”的方式經由具體的個案解釋法律。劉恩榮解釋《修正暫行法院編制法》第35條時認為該條“既著有‘統一’二字,則當然有拘束一切之效力,縱事實上或有反對之見解,而法律上不能認反對為有效”。[注]劉恩榮:《論大理院之解釋與其判例》,《法律評論》第37期(1924年)。所以,此處所說判例可以普遍性地確定法律的意義。就算是借判例而進行法律解釋,其結果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到了司法院時期,1928年《司法院組織法》第3條規定:“司法院院長經最高法院院長及所屬各庭庭長會議議決后,行使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之權。”可見,司法院保留了對法令進行統一解釋和通過判例變更調整對法律之解釋的權力,和大理院時期幾無二致。這一時期的判例繼續保持了提出一般性規則的風格。黃源盛于是認為1922年以前幾乎“有一判即有一例”,乃至“有謂此種判例的產生即不啻于大理院的立法矣”。[注]黃源盛:《民初法律變遷與裁判(1912-1928)》,政治大學法學叢書(臺北)2000年版,第74頁。至于解釋例,則如芮沐所言,司法院解釋法律的制度安排令“其所解釋者,規定當為抽象的疑問,解釋例之效果自與判例之為某某切實案件所關系又不同”。[注]芮沐:《司法院對行政法令之解釋》,《明日之中國》1936年第1卷第2期。袁家珹也強調:“既存之法律,一經有權者解釋,其義遂定,不能更為他之解釋,即所解釋之意義,視為法律之真正意義,有一定效力,違反之者,須受制裁。”[注]袁家珹:《論法律解釋權(續)》,《越旭》1926年第6期。
由此可見,民國時期司法機關所發布的個案裁判和解釋例其實都是抽象性的規范創造。因此,以判例造法又在實踐中成了一種由司法機關所掌握的規范創制權。后來,1935年國民政府的《憲法草案》(“五五憲草”)第79條也為統一解釋提供了基礎:“司法院有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權。”同年生效的《法院組織法》第25條進一步確定了變更判例會議制度:“最高法院各庭審理案件,關于法律上之見解,與本庭或他庭判決先例有異時,應由院長呈由司法院院長召集變更判例會議決定之。”到了1947年《司法院組織法》通過后,在司法院內再設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并統一解釋法律、命令。
綜上所述,民國最高司法機關對法律的解釋可以約束下級審判機關。大理院和司法院進行法律解釋的途徑都有三種:以解釋例統一解釋;以個案裁判解釋法律;以變更判例會議改變此前的法律解釋。可見,法律中規定的“法律解釋”之權實際上是一種規范創制權。黃源盛敏銳地意識到了民國司法機關“創例視同立法”。[注]同前注,黃源盛書,第73頁。乍看之下,最高司法機關以判例造法的權限和程序都已經很明確了。然而,事實是司法機關的權力在內部和外部兩方面都不穩定。內部的不確定因素是不同的法令應由哪個機關解釋。如行政法令的解釋權應當屬于行政法院還是最高法院的爭議,便是上述不確定因素的一個面向。[注]參見前注,芮沐文。外部的不確定因素是最高司法機關也一直面臨著來自立法者對解釋權的競爭。事實上一旦把解釋作為一種“權力”,各機關之間相互競爭必然難以避免。《民法》生效后,圍繞判例產生的疑惑不但沒有消除,而且增加了。正是在此契機下,出現了圍繞法律解釋而展開的一系列討論。
(二)作為法源的判例造法
最高司法機關無疑通過在判例中解釋法律而創造規范。其爭議在于這種實質上存在的(de facto)規范創制權力是否使判例在法律上(de jure)也具備了法律淵源的地位。筆者認為,如果細致考察《民法》的第1條,就可以認為立法者有意把判例排除在正式法律淵源之外。
法律淵源理論是19世紀歐洲民法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增長點。[注]Cf. Alain Papaux, “Aux sources du droit: L’autorité et la ruse”, Revue interdisciplinaire d’études juridiques, 1 mai 2013, Volume 70, no°1, p. 207-223.民國時期的民法學者也受了這一風潮的影響。其表現就是在法典中對法律淵源采取了列舉式規定。然而,歷來法典的列舉規定中均不見“例”的字樣。于是,學者對民國時期判例是否為法律淵源、與其他法律淵源的關系等問題爭論不休。[注]參見黃源盛:《民刑分立之后——民初大理院民事審判法源問題再探》,載柳立言主編:《中國史新論——法律史分冊》,經聯出版公司(臺北)2008年版,第313-366頁;黃圣棻:《大理院民事判決法源之研究》,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2002年碩士論文。筆者認為,與基本上同時期其他國家成文法中關于法律淵源的規定相對比,中國的法典化進程中關于法律淵源規定的沿革將展現其獨特的意義。
《大清民律草案》第1條規定:“民事本律所未載者,依習慣法,無習慣法者,依條理。”大理院時期,在廢棄了《大清民律草案》的情況下,“三年上字第七〇號”判決中的表達是“法律無明文者依習慣法,無習慣法者依條理”。[注]“三年上字第七〇號”,載郭衛編:《大理院判決例全書》(上),上海法學編譯社1933年版,第29頁。后來生效的《民法》第1條的表達是“民事,法律無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通說認為,該規定來自《瑞士民法典》第1條。[注]參見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頁;蘇永欽:《民法第一條的規范意義——從比較法、立法史與方法論角度解析》,載蘇永欽:《跨越自治與管制》,五南圖書出版社(臺北)1999年版,第283-321頁。有論者進而認為《大清民律草案》也效仿了《瑞士民法典》第1條。參見李敏:《〈瑞士民法典〉“著名的”第一條——基于法思想、方法論和司法實務的研究》,《比較法研究》2015年第4期;德美:《探索與抉擇——晚清法律移植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頁。然而,這種說法無法成立。無論時人作如何聲明,通過與《瑞士民法典》和其他可能出處的對比可以看出,其實中國法典中對法律淵源的規定應當另有出處。對這一規定的來源辨析將揭示法典起草者對規范創制權配置的考量。
首先,類似條款并非《瑞士民法典》所獨創。1874年的《德國民法典草案》曾規定:“裁判官應依照本法進行裁判,本法沒有規定的依習慣法;不存在習慣法的情況下,裁判官依照法理進行裁判。”[注]參見張生:《清末民事習慣調查與〈大清民律草案〉的編纂》,《法學研究》2007年第1期。1875年的日本《明治八年太政官布告第百三號》關于法律淵源的表述是:“于民事裁判,無成文法者,依習慣;無習慣者,推考條理而裁判之。”就時間上看,不可能認為1875年的日本太政官布告承襲自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就19世紀末法律學說交流的情況而言,似乎也不太可能認為《瑞士民法典》的起草者效仿的是日本太政官布告。更合理的解釋是兩者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淵源——《德國民法典草案》。《德國民法典草案》啟發了日本的上述太政官布告,而《瑞士民法典》的起草者除了《德國民法典草案》以外,可能還參照了惹尼(Fran?ois Gény)1899年的著作《實在私法的解釋方法與法律淵源》。[注]至少惹尼在該書再版的附錄文章中不無自得地提到了《瑞士民法典》對其理論的肯定。Fran?ois Gény, “Les pouvoirs du juge d’après le Code civil suisse du 10 décembre 1907 (Chapitre troisième de l’épilogue)”, in 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 : essai critique,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1919, vol. II/II, p. 308-329.當然,幾份文本之間的繼承關系還需要更多的史料支持,不能僅憑猜測,但無論如何,《瑞士民法典》肯定不是《大清民律草案》和《民法典》唯一的參考資源。
其次,從文字上看,中國的法典與上述太政官布告的相似性更高。《瑞士民法典》第1條規定:“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釋上有相應規定的任何法律問題,一律適用本法。如本法沒有可以適用的規定,法官應依據習慣法,無習慣法時,應依據他作為立法者所規定的規范裁判之。于此情形,法官應遵循公認的學理與判例。”[注]《瑞士民法典》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本中第1條的表達稍有不同。筆者于本文中暫且使用謝懷栻從德文文本翻譯的中文版本。參見謝懷栻:《大陸法國家民法典研究(四)》,《外國法譯叢》1995年第2期。如果瑞士法是藍本,那么民國政府制定的《民法》在第1條中不但否定了裁判者可以取得立法者的地位,而且有意把“公認的學理與判例”替換成了“法理”。如此一來,起草者反而把時間順序上較晚、規定也更為細致的瑞士法變回了19世紀末較為粗糙的表達,這樣的假設顯然不合理。相反,將前引有關法律淵源的不同表述加以比較,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是東亞國家的三個條文之間無論是在結構上還是在用詞上相似程度都更高一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瑞士民法典》第1條背后的法哲學和其他的規范都有所不同。認為《瑞士民法典》更重要的觀點可能因為《大清民律草案》也使用了極具特色的“本法”(La loi; Das Recht)表述而得到支持。然而,對比之下,至少有兩點理由說明后來的研究者可能高估了《瑞士民法典》對我國的重要性,也低估了其特殊性和創新性。其一,無論是從表達上還是從結構上看,東亞的三個文本和1874年《德國民法典草案》的相似程度顯然更高。這種相似性令人不得不猜測,上述太政官布告可能直接受益于1874年《德國民法典草案》,并在《大清民律草案》和《民法》關于法源的規定的形成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其二,《瑞士民法典》采取了不同于其他規范的法哲學觀點和立法技術。《瑞士民法典》的起草過程和“自由法運動”的風起云涌在時間上重合,在“自由法運動”的積極倡導者眼中,其第1條也確實是該運動的果實。起草者意識到法典和對法典的解釋是兩種相對獨立的事物。同時,他們還承認法律可能存在無論如何解釋也無法填補的漏洞。為此需要超越制定法的法律淵源。不過,最具革命性的見解是,在窮盡成文法和習慣法仍無法解決法律問題時,允許法官在個案中取代立法者創制法律。[注]參見前注,李敏文。“公認的學理與判例”雖然可以作為一種對法官權力的限制,法官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行判斷哪些學理和判例是“公認的”。東亞的三個文本都相當明確地拒絕了法官取代立法者地位的可能性,所以它們和《瑞士民法典》第1條有實質的、法哲學立場上的不同。
對法源條款來源的辨析顯示,民國時期的法典起草者有意識地希望限制法官在適用法律時進行“造法”以填補漏洞的權力。不管法典起草者最終是從日本還是從瑞士獲得啟發,無可爭議的是他們一定都同時知道兩種可能的選項。就算最后《瑞士民法典》“著名的”第1條是來源,拒絕讓裁判官享有立法者的地位和把“判例”移除出列舉的法源,也顯然是起草者有意為之。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刪除了“或解釋上”的字眼也是有意否定通過法律解釋創制規范的可能。可是,擁有著悠久制定法傳統的帝制中國一直存在著通過判例形成的案例法,參考甚至還未經“通行”而著為定例的先例,以至于在影響力上不次于英國司法上的先例。[注]參見陳新宇:《帝制中國的法源與適用——以比附問題為中心的展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頁;王志強:《中英先例制度的歷史比較》,《法學研究》2008年第3期。到了共和時代,北洋政府時期需要法院于法典不存、法制并不完備之時采取更積極的態度;南京政府時期又需要法院調和外來規范與本土實踐之裂痕。就算不強調散見于各種法院組織法上對判例與解釋例之拘束力的規定,法院——特別是最高司法機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制定規范也是不爭的事實。
民國時期,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條文創造了一個廣闊的可能解釋空間,讓判例與解釋例的性質變得晦暗不明。從民法典文本看,判例和解釋例最多作為“條理”或“法理”的組成部分而成為法律淵源。各法院組織法卻又強調最高司法機構的判例具有“拘束力”。《民法》明確地拒絕了司法取代立法者地位的可能性,但判例又實際上創造著新規范,且判例與解釋例確實是司法上賴以回答法律問題的資源。“本院歷來判例”“本院判例所屢經說明者”“本院采為判例者”“本院著為判例者”等類似的說法廣泛出現在大理院的判例中,此種語言樣態確實能“充分證明大理院是直接以判例作為審判依據,承認其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注]同前注,黃圣棻文。那么,一個疑問旋即產生,并重新落至法律淵源理論的規范性面向:司法機關創制規則具有正當性嗎,或者說,法官可以在某個時刻擁有立法者地位嗎?如果說,民國時期的成文法對此并沒有明確答復,那么,當時的學說卻給出了相當肯定的答案。
二、學說肯定判例造法
民國時期的法學家幾乎一致支持司法機關擁有創制規范的權力,并肯定判例是一種法律淵源。許多法學家甚至在《民法》生效后仍主張法官可以脫離實定法的約束而自行發現社會中的法律。當實定法為判例之地位創造出如此多可能性時,不但司法實踐確實利用了這種可能性的空間創制規范,而且學說的立場也出人意料地統一。法律理論在意識到判例造法的困難之后仍合力通過強調判例造法的現實必要、擴張法律的定義,從而使法官的造法權正當化,讓最高司法機關的法官實際上具有了《瑞士民法典》第1條所規定的法官之權力。關于法律解釋方法的論著中,則有重要的流派主張法律解釋不能拘泥于文義。正是在這種合力中,可以發現法典化時代的學說與判例之間存在的微妙關系。
(一)判例造法的合理性
1.判例造法的現實必要性
學者對司法造法之肯定,最直接地體現在學術作品中引用造法性判例,而學者在引用判例時,又總是把它作為法律的一部分來處理。早在大理院時期,以《法政雜志》為代表的期刊便匯集出版大理院關于某一事項的判例。如在《民法》生效前爭議較多的妾之身份問題上,該刊即錄大理院刑事判決元字第29號,并加以評價:“此案大理院以不認一夫多妻制之存在為前提,而法律上又不能以人為目的物,故廖禮耕之對于陳五妹遂成絕無關系之人,而不能取得告訴權。觀之此案,吾國之多妻者當知所警矣。”[注]《大理院關于妾之判例》,《法政雜志》1913年第8期。可見,成文法雖未對妾之身份統一解決,大理院卻不妨創造規則,而學界對這種由大理院創設的規則是欣然接受的。相對于期刊,教科書肯定更為重要。《民法》生效后,許多具體的制度尚未細化落實,而法學(特別是民法學)的體系又必須在課堂上講授,法學家也就不可避免地把一些判例看作法律的規定,作為講解具體內容的素材。如胡長清就在講解關于外國人權利能力之限制時,舉大理院1919年上字919號判決和1920年上字593號判決為例,說明外國人在土地所有權、資源所有權等方面的限制。[注]參見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法條中只說外國人權利能力得為“法令”所限制,胡長清此舉無異于以判例為法令了。史尚寬在其《親屬法論》中亦常出于實質平等考慮而收錄以例破律的判決。[注]參見史尚寬:《親屬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頁。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民國時期的法律教科書中并不罕見。
然而,在民國前期,人們并未完全理解法律解釋的性質。令最高司法機關頭痛的解釋提請濫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寵惠曾經批評下級法院把具體個案改頭換面直接詢問大理院的意見,導致解釋提請實際上成了大理院代替下級法院做出判決。[注]王寵惠:《改良司法意見》,《東方雜志》1920年第20期。雖然南京民國政府時期《司法院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請求解釋以抽象之疑問為限,不得臚列具體事實”,但實際上“請求解釋之公牘無不多少列述具體事實”。[注]同前注,芮沐文。由此可見,在整個民國時期,雖然從規范的意義上可以強調統一解釋并非針對具體個案,但實踐中請求最高司法機關解釋往往成了下級法院解決個案的一種手段。
雖然最高司法機關以此為苦,學者卻表現出了對下級法院的一定程度理解。如果法律適用不可避免地涉及法律解釋,又如何能把法律的解釋之“權”統一于最高司法機關從而排除其他司法機關的法律解釋活動呢?所以制定法中的規定本來就無遵守之可能。對此,袁家珹就認為:“或謂法律一經解釋,即不免有多寡之變更,既有變更,即為立法;故釋法者表面雖無立法權,而實際則有之。”[注]同前注,袁家珹文。對此,他雖然“頗認為不正當”,卻也承認這種思潮并非全無根據。采同樣立場的還有劉恩榮。他認為大理院有權以新判例取代舊判例為解釋就是讓其判例具有拘束一切的效力,嚴格按照《法院編制法》,“此種見解,固難謂當”。因為《法院編制法》第45條(“大理院或分院,發交下級審判廳之案件,下級審判廳對于此案,不得違背該院法令上之意見”)應解釋為:大理院對上訴案件所為之裁判僅能拘束受發交的下級審判廳,而不能拘束其他的下級審判廳,而且受發交的下級審判廳對于其他案件亦不受該判例拘束。他卻也承認:“但從實際論之,亦非無相當之理由。蓋我國法典,多未編訂,不啻不文法國……有判例作為準則,法院與人民,均有所依據,不致感下無法守之苦。”[注]同前注⑩,劉恩榮文。可見彼時法學家多認可最高司法機關的確有必要以判例造法克服規范缺失之弊。
一方面,釋法提請泛濫,使對法律的抽象解釋實際上變成具體個案中的解釋,另一方面,無論判例還是解釋例,司法機關又確確實實在創制法律,規范中存在區分的兩種解釋形態反而邊界模糊。今天的觀察者可以認為民國時期最高司法機關的解釋形同立法,當時的法學家也有類似的認識。劉恩榮就說,大理院所為的解釋“性質為抽象的,與法規性質完全相同,故又有謂解釋權為立法權者,雖與三權分配之旨,似有抵觸,要亦非無因之論,此可見解釋效力之廣大也”。[注]同前注⑩,劉恩榮文。大理院和司法院的解釋例和判決要旨都具有極高的抽象性,所以外觀上與立法相似。劉恩榮也意識到,根據權力分立的原則,不能把解釋作為一種立法權,只不過在國家政制和法律時刻處于變動中的時代,允許解釋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可以肯定的是,法律解釋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立法權和司法權之間的界限。如此,學說的立場就昭然若揭了:雖然最高司法機構的法官沒有明確像《瑞士民法典》第1條所稱的“作為立法者”,但實際上行使著并出于實踐的必要性應該繼續行使規范的創制權。
2.判例造法的理論可能性
當然,反對把判例作為法律淵源(至少反對作為正式法律淵源)的主張并非不存在。朱顯楨從實證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在法律生效后法律解釋本身并非由“國權而擔保者”,因而不能具有法律淵源的地位,[注]朱顯楨:《法律解釋論》,《社會科學論叢》1935年法律專號第2卷第8、第9號合刊。不過,實證主義的主權觀未必一定反對司法造法,關鍵還是在于如何理解主權。羅鼎就舉奧斯丁學說,把司法權也作為主權的一部分。[注]羅鼎:《法律解釋上之英美法源》,《法律評論》1923年第17期。那么,不可分的主權如果真的通過司法活動創造規范,于理論上也無滯澀之處。司法與立法之間的界限最終因為它們都統一于主權而被羅鼎繞過了。于實踐中,最高司法機關也在判例“二年上字第三號”中明確了習慣法的判斷標準和效力。這樣一來,本來明確列舉在《大清民律草案》中作為法律淵源的“習慣法”,最終卻僅僅因為判例的承認而獲得實證法的地位。[注]參見“二年上字第三號”,載郭衛編:《大理院判決例全書》(上),上海法學編譯社1933年版,第29頁。并且,前述“三年上字第七〇號”更是先于《民法》確定了法律淵源的位階。于成文法而言,在民法典生效之前,“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固然是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法律淵源,卻借由大理院的判例和解釋例才解決了適用和民刑事規則之間的轉換問題。[注]參見段曉彥:《〈大清現行刑律〉與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對“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適用》,《法學研究》2013年第5期。因此,最高司法機構的解釋豈止是法律淵源,簡直是最重要的法律淵源之一了。正是它在法典的籌備階段(也就是法典化的時代)決定著法律淵源的種類和位階。無怪乎蔡樞衡會如此強調法律解釋在事實上的效力:“可是條文本身只是法律的形式,法的本質之一屬性,全法律的一因素;不是法律的全本質,尤其不是全法律。成文法國家的條文以及六法全書的內容只是認識法律的指南針,發現法律的一個條件。法學的結論是裁判的判斷之源泉,裁判之判斷是法學之深刻化或發展了的法學。法學的結論和裁判的判斷互為因果,法律便在這中間益趨完全。”[注]蔡樞衡:《中國法治的根本問題》,《當代評論》1941年第6期。
于是,判例不僅與成文法和法學并列組成“全法律”,更與法學一道,以法學為源泉,成為發展了的法學,從而是法律能夠益趨完全的關鍵一步。在這個意義上,司法與法學“合謀”,超越了成文法,成了真正創制法律的力量。
在學說的解說下,成文法的語義范圍內地位曖昧的法律解釋竟然成了重要的法律淵源乃至形同立法,甚至具有了超然于其他法律淵源的地位。民國時期的法學家在關于法律解釋的討論中從法律條文、實際需要、司法現實等角度全面捍衛法律解釋的規范創制權,可謂煞費苦心。實踐中司法院統一解釋變成了對個案中法律適用的解釋,并且在個案中也采取抽象、普遍的解釋。學說證成了法律解釋之實際拘束力,法官儼然以立法者的形象于司法實踐中登臺。《大清民律草案》和《民法》的起草者有能力在文字上避免《瑞士民法典》第1條的設計,卻無力阻止司法和學說合力讓實踐展現出甚至比“著名的第1條”更自由的司法造法權。如此說來,《瑞士民法典》第1條到底是不是“民事,法律無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的源頭變得無足輕重,重要的是,時人大多如此想象,又確實經由實踐和理論的循環往復使《瑞士民法典》的條文確實成為了理解中國實踐的鑰匙。
(二)源于社會的判例
前文分析了學說如何在論述中肯定司法機關以例造法的實踐,但這種形式意義的結論并不足以展現學說與判例關系的全貌。從理論上說,既然學說認為司法之例本質上是法律解釋,如果法律解釋不能偏離文義或者不能偏離立法者的主觀目的,那么判例仍然只是立法的派生作品。相反,如果學者認為司法不必拘泥文義和立法者的主觀目的,那么可以說學說在形式和實質兩方面都支持司法權確實擁有創造法律所沒有的規則或者改變法律中的規則的權力。因此,判例之規范創造力又轉化成了法律解釋理論的問題。下文將說明,中國的法學家恰恰在法典化的時代孜孜不倦地提醒法律的解釋者,正在準備中或剛生效的法典同樣會和社會生活脫節,從而需要解釋者自行判斷是否受文義拘束。
此處或許可以選擇一個傳承脈絡相當清晰、在民國法律解釋討論中具有普遍代表意義的“派別”為例。筆者權且稱之為“石坂系”,因為其立場表達要么來自對日本民法學家石坂音四郎作品的翻譯,要么來自受他啟發的中國法學家自身的作品。石坂音四郎早年留學德國,是德國學說(特別是自由法學)在日本的代表人物。剛從日本明治大學回國從教于朝陽大學的胡長清復述了石坂的一些觀點。1934年,同樣收錄于石坂音四郎的《民法研究(改纂·上巻)》的部分文字也由自復旦大學畢業后留學日本,后任教于北平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彭時整理并翻譯成《法律學與法律之解釋及其適用》,發表于《法律評論》。[注]參見[日]石坂音四郎:《法律學與法律之解釋及其適用》,彭時譯,《法律評論》1934年第3期、第5期。彭時的譯文在《法律評論》上連載發表時未署原作者的名字,因該文的日文原文收錄于石坂音四郎的《民法研究(改纂·上巻)》,筆者得以通過對比原文和譯文而確定原作者。時任中山大學教師的朱顯楨在他1936年發表的論文《法律解釋論》“法律解釋之方法”部分也指出:“日本民法學大家石坂音四郎頗有詳細精到之研究。茲特介紹其概略,聊以代吾人之意見。”[注]同前注,朱顯楨文。這一系列作品恰好出現在從1926年到1936年之間這一段從大理院時期到司法院時期的變革過程中,中間還有《民法》起草頒行等重要事件。
胡長清在其中篇幅最短的《常識的法律解釋》中強調:“所謂文章解釋,即以闡明法文所表示之意思與實質為目的之解釋。欲達此目的,應并用文理解釋與論理解釋,自不待言。”[注]胡長清:《常識的法律解釋》,《法律評論》1927年第44期。這種分類也是石坂音四郎的觀點,盡管他用的是“文字解釋”和“論理解釋”的術語。他認為,其中“論理解釋之意義,殊欠明了”,其實,兩者并不彼此獨立,論理解釋只是要求解釋者參考立法材料、歷史沿革、從體系出發、依據法律理由、依法律原則、制定法律的原因、實際之結果諸種。石坂接著又指出:“其中多半,實無何等價值可言。”[注][日]石坂音四郎:《法律解釋論》,涂身潔譯,《法律評論》1926年第143期。在法律解釋方法上幾乎對石坂音四郎全文照搬的朱顯楨也同意,只有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是真正重要的,因為“前者形式的依據法規之互相關系而解釋法律,后者實質的觀察法律之目的與實際生活之關系而解釋法律;前者依論理方法,后者依價值判斷”。[注]同前注,朱顯楨文。
這一場學說繼受最終讓解釋者的價值判斷成了法律解釋時的決定性因素。簡單的梳理便可看出,用今天的話說,石坂系的法律解釋論無非把法律解釋方法分成了文義解釋和非文義解釋兩種。它把今天的研究者獨立討論的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立法目的解釋等方法一概放在了后一個大類中。與文義解釋相比,倒是依價值判斷而解釋的非文義解釋更能引起民國時期學者的興趣。朱顯楨認為:“立法者意思探究說,既受上述之種種攻擊非難,則其說之無價值,當可想見,近來關于法律解釋之目的,除少數學者而外,一般皆已唾棄此說而不顧了。”[注]同前注,朱顯楨文。官費留學日本并加入同盟會的羅鼎也曾提到:“吾人固主張立法與司法應取同一之態度,然非謂法律應對的依從立法者之意思以解釋也。”[注]羅鼎:《法律解釋上之英美法源》,《法律評論》1923年第19期。“法律意思探究說,到底亦不免為一謬見。”[注]同前注,朱顯楨文。因為法律終究是一種人類的造物,所謂法律的意思不過是解釋法律者自己內心對法律理解的投射而已。
如果非要從文義之外尋找法律的解釋,既不能探求立法者意思,又不能假定法律有一定的客觀意思,那么解釋如何作“方法論上的盲目飛行”呢?
后來進入民法編纂委員會的胡長清對此的回答是:“夫法律,所以調和實際生活現象者也,解釋法律而不顧社會常識觀念,則去法律之本旨遠矣。”[注]同前注,胡長清文。朱顯楨在八年后重復了這一說法:“實際法律解釋家,不悉社會實際生活之情形,不能為法律解釋之基礎,而達法律最終之目的。”看來,讓法律適應社會生活這個核心的立場,并沒有因為成文法體系從舊律向“六法”的轉變而發生改變。朱顯楨進一步主張:“法律內容之規范的思想……從一定時代一定國民之思想上的要求,合理的判斷法文,可以得到普遍一致之結論。”[注]同前注,朱顯楨文。由此,法律解釋的前提就變成了去探究給定社會在思想上對法律提出的要求。于是,判例之所以成為創造法律規范的材料,是因為法官本身也是社會生活的觀察者。在社會面前,成文法規范的約束力顯得并不重要——這就觸及了民國時期法學上的一項重要議題,即法律社會化。
三、學說指導判例造法
讓法律解釋擺脫立法者的拘束而成為事實上的規范創制權行使到底有何意義呢?民國時期的法學家選擇了當時在歐美法學界頗流行的“法律社會化”理論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根據這種理論,法律一方面要適應社會發展,另一方面要推動社會發展。[注]參見朱明哲:《面對社會問題的自然法——論法律社會化中的自然法學說變遷》,《清華法學》2017年第6期。判例不斷彌合立法與社會之間的鴻溝,而決定社會有何發展、如何發展卻成了學說的任務。因此,反倒是學說在指導判例如何造法。如果把整個法律實踐作為一個社會場來觀察、把學者和法官看作這個社會場中的行動者,就會立刻發現兩個群體之間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競爭的關系。如果選擇把學說作為這個關系的中心,則不難看出實際上學說在證成判例造法的權力的同時,也規訓司法,并力圖鞏固自己在法律場中的地位。
(一)“法律社會化”的中國敘事
1.法律學說研究社會并引領社會
法律的解釋者如果“不悉社會實際生活之情形”,就“不能為社會實際生活建樹立法之意見”,這樣的法律人也就不是“真正善良之法律解釋家”。[注]同前注,朱顯楨文。與其探討立法者的意圖,還不如去研究社會的需要和對法律的訴求。這就是為什么要強調法學不能和其他對社會生活的研究相脫節的原因。“從來之法律學及法律之解釋,則全然只從法律方面觀察,而與其他之觀察,完全分離,毫不相干。……所以法律學必須與其他之社會學問,互相聯絡,以防止其孤立。如是則法律與實際生活,始能相互調和,而不發生隔離背棄之弊,法治之精神,始可以發揮盡致!”[注]同前注,朱顯楨文。如此一來,法律解釋者就成了社會實際生活的探索者。他的解釋是客觀的,因為社會本身是客觀的。然而,客觀的世界只能通過法學自我展現。法律適用者借助法學實現對客觀社會生活的認識,并把這種認識轉化為法律最終的意思。到頭來,司法機關創制新規范的權力最終要在法學的范圍內才能行使。司法機關以例造法的權力也實際上成了法學所限制的對象。如果說法學為判例賦予法律淵源的地位,并把司法中的法律解釋從成文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又立刻把司法置于自己的權威之下。因為判例為社會生活立法,學說則權威性地表達社會生活。
此種立場也得到蔡樞衡的認可:“成文法國家當作現象和形式的對象——法條雖然是成文;當作內容和本質的對象——社會卻是一本不成文的書。……正確理解這本書中有關事項的能力便是法學認識所需要的能力之最低度。”[注]蔡樞衡:《中國法學的病和藥》,《當代評論》1941年第23期。朱顯楨甚至認為法學的成果就是規范本身:“法之解釋,即法之認識,與法律學是絕對不能離開的。法律學之成果,即謂為一般的解釋論,精確的法律學上之說明,即謂為法規,亦非過當。”[注]同前注,朱顯楨文。這樣一來,法學反倒通過解釋社會,凌駕于社會之上,最終成為法律的真正來源。
既然法律學說有必要探究社會生活的實質,以特定社會中的客觀規范思想為法律解釋的標尺,決定何者為社會生活實質的就只能是法學(家)。由此可見,雖然法律解釋的制度安排和對各種制度安排的討論表現出強烈的權力面向(法律解釋的主體、程序、效力),但對法律解釋的理論探討又表現出了至少同樣強烈的科學或知識面向。正是經由后者,法學家正當化了他們解釋法律的活動。通過解釋法律創制規范的權力,不聲不響地從司法機關轉移到了法學家共同體手中。確實,也有批評理論界缺乏權威無法在法律實踐中發揮作用的聲音:“至于實務和理論之所以缺少合作,半因沒有這種需要,半因理論幼稚。實務不求理論幫忙,當然不會合作;理論沒有獲得支配實務的權威,當然沒有合作的表現。”[注]同前注,蔡樞衡文。然而,蔡樞衡此說雖然不失為通過尖銳的批判促使學說自我反省,卻未必可以看作對當時司法情況的準確反映。通盤考慮整個民國時期內判例說理時的依據,對西方的理論和實定法的知識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淵源,甚至比習慣還要重要。[注]參見王志強:《民國時期的司法與民間習慣——不同司法管轄權下民事訴訟的比較研究》,《比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然而,這種強調法律解釋之社會面向、強調解釋者之自由的主張,未必真的切合民國時期我國法律與社會的關系。主張法學通過觀察社會超越成文法更像是承襲自德奧自由法學的立場。
2.外來的“法律社會化”與本土的社會
饒有趣味的是,這種提倡研究社會現實的理論主張產生于和彼時中國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中。作為法律社會化運動一部分的自由法學于20世紀初興起以后,雖然從來沒在歐洲的法律實踐中成為主流,卻受到了許多東亞法學家的歡迎。石坂音四郎就認為:“近時德意志所謂自由法學勃興,可謂至革新之氣象矣。自由法學之所說,雖亦非盡可首肯者;然而指摘從來形式論理概念法學弊害之處,不可謂無傾聽之價值也。”[注]同前注,石坂音四郎文。于是,似乎外國法律與本土社會之間的矛盾,竟又要通過外來的理論來解決。須知自由法學不僅僅是一種客觀和技術性的解釋方法,其發展和繼受也很明顯地與20世紀初對法律社會層面的關注相連。刑法學家江鎮三對此早有省察:“吾人細推原由,蓋從前個人制度,過度發達,契約自由與所有權之絕對性,極端濫用,以致社會交接,全離仁愛之意念,唯利己之方策是務,借主雇主等有產階級,對于赤貧寒苦之物產階級,可以任意要求,所謂雙方意思之合致,事實上只為富者屈服貧者之結果。”[注]江鎮三:《法律與正義》,《法軌》創刊號(1933年7月)。
西歐所謂法律社會化,目的是校正工業化、城市化以后的弊病。在德、法、日等成文法國家,“法之解釋成為重大問題,固毫無足怪”,因為“成文法有使法固定停滯之傾向。一遇社會之事變情遷,不無與現實之法律現象桿格枘鑿之弊。恃以補救者厥為法之解釋”。[注]同前注,羅鼎文。這種因為成文法生效時間距離適用時間過長、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變革而產生的法律解釋需求其實屬于“后法典時代”。然而,民國時期的中國正處于新舊法制更替的交匯點,社會風尚保守而法律內容先進所造成的斷裂確實不少,社會發展導致法律不合時宜卻還不多見。中國的法律和政治仍在致力于把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同樣是法律與社會的不協調,在西歐表現為法典無法適應工業社會的生活,而在中國更像是外來的制度與本土之社會之間的矛盾。以致連法學家也感嘆“在現在的法律之下,往往人民以為是者,法律以為非;法律以為是者,人民以為非”,究其原因,無非“人民的是非觀念是中國的;而法律的是非觀念是外國的”。[注]阮毅成:《怎樣建設中國本位的法律》,《政治評論》1935年第156-157期合刊。于是,這里的“社會”不再是一個工業化后的城市社會,而是一個還沒跟上法典步伐的傳統社會。與其說落后的法典亟待自由解釋以跟上社會的步伐,倒不如說法學家希望借改頭換面后的“社會化”學說來緩和法律文本與傳統心態之間的落差。
近代法律史的中心問題之一是如何看待移植和自主之間的張力。筆者花相當筆墨討論了成文法上為判例之地位與效力留下的解釋空間,又明確提出從關于法律淵源的文本中應該得出起草者無意讓法官創制法律的結論。然而,司法實踐恰恰通過判例造法不斷創造規范,學說則不僅為這種造法行為辯護,更進一步主張按照西歐最新學說,法律適用者甚至應直接從社會中發現規范。這樣,司法活動如果不想淪為專斷,就必須倚重法學,因為法學家正是以最科學公允之方式觀察社會的一方。
至此,民國時期關于法律解釋的討論背后隱然浮現出《瑞士民法典》起草者胡貝爾(Eugen Huber)的微笑。學說讓司法獲得了規范的創制權,但這種創制權的行使必須遵循學界的共識。“著名的第1條”雖然沒有出現在法律文本上,卻成了對“行動中的法”最好的描述。
于是,在歐洲為調和社會進步與保守法律之矛盾而生的“法律社會化”命題,來到東亞卻成了調和保守社會與進步法律之矛盾的工具。堅持概念純潔性的人固然可以批評這種觀念傳播中的誤讀,筆者卻試圖通過這種傳播,理解民國時期的法律職業。筆者主張民國時期的法學家們高舉“法律社會化”旗幟乃是根據當時法律職業的情況作出的策略性選擇。為證明這一觀點,筆者擬引入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的“法律場”作為分析工具。
(二)民國時期法學家選擇“法律社會化”理論的原因
1.“法律場”的要素與結構
在1986年的作品《法律的力量:法律場的社會學基礎》中,布迪厄如此定義法律場:“法律場(champ juridique)是人們為了壟斷說出法律(即好的分配或秩序)的權利而競爭的場所。在競爭中相遇的行動者具有一種兼具社會和技術性質的權能,其中最關鍵的方面是他們可以相對自由地解釋一套把合法、正確的社會觀念神圣化的文本,這種能力為社會所承認。”[注]Pierre Bourdieu, “La force du droit. éléments pour une sociologie du champ juridique”, op. cit.無論題目中使用的“法律的力量”(la force du droit)還是解說時所使用的“說出法律”的用詞,都明確表明他要回應的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使用的著名比喻:“一個國家的法官僅僅是說出法律之語的嘴巴,他們是沒有生命的存在物,既不能降低法律的力量,也不能降低其嚴格程度。”孟德斯鳩的比喻完美地總結了民國時期關于法律解釋的爭論中所有的問題:誰有權以何種方式以法律的名義發言。然而,如果把法官看作無生命的造物,則大大誤解了法律實踐。每一個“社會場”(champ social)中都匯集了為爭奪與不同的地位相連的利益而進行的斗爭。法律場(champ juridique)也不例外。兩種不同的秩序使法律場區別于其他的社會場。其一,由規范和學說建立的象征性秩序,本身蘊含了發展的客觀可能卻無法完全獨自運作。其二,由行動者與體制之間客觀關系建立的秩序,行動者和機制時刻處于競爭中。[注]Cf. Ibid.孟德斯鳩所謂“說出法律之語的嘴巴”只重視了第一種秩序,卻沒有認識到行動者參與之后產生的第二種秩序。
誠然,規范本身就像是一個“正當性的源泉”,從象牙塔頂端的學說權威到最基層的法官(又或者警察),所有參與法律實踐的人都回溯到規范中尋求自己行動的正當性。對規范之存在和正當性的共同接受構成了法律場的“生存心態”(habitus),法律場不能在沒有這一生存心態的情況下存在。忽視第一種秩序的法律現實主義因此必然也誤解了法律實踐。[注]Cf. Ibid.在接受了規范的情況下,每一個法律場的參與者又都參與到對規范解釋之壟斷權的競爭中。雖然在實踐中不可能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夠真正壟斷規范,但每一個群體(作為社會學之研究對象)無疑都希望能夠讓自己的解釋更具有權威性。判例性質之爭的實質就是法律場內特殊利益之爭。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學說在競爭中都有各自的策略和工具。立法機關不但直接確定規范很大一部分的文本內容,也直接確定司法權行使的方式和范圍。司法機關既通過判決決定每個個案的利益分配,又通過法律確定的上下級關系統一法律在實踐中的意義。學說則借助法律本身在科學上的嚴格性,以構建融貫體系的名義獲得了對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和決定其他解釋之力量的權利。不過,每一種關于法律的話語都不是終局性的,每一種淵源都制衡和補充著另一種淵源。
在法律實踐(“法律場”)中,政治家、法官、法學家(“行動者”)采取不同的策略,從而最大化他們“象征性資本”的收益,在共同接受法律規范之存在和正當性(“生存心態”)的前提下,競爭著終局性地確定法律意義的壟斷權(“特殊利益”)。[注]括號中的是布迪厄所使用的術語。每一個行動者可以采取的策略取決于各個行動者實際上擁有的資源。易言之,究竟為何司法與法學的關系在民國時期呈現出如此樣態,究竟為何當時的法學家會接受自由法學這種特殊的立場,終究還要在立法、司法、法學三者的力量對比關系中尋找答案。全面的研究在如此小的篇幅內當然無法完成,但研究民國時期法學知識生產的土壤不妨成為一個突破口。
2.司法與政治之間的法學
最容易理解的顯然是社會化對法官地位的強化。在這一視角下回看法律社會化的理論選擇,就會發現其“詞”與其“物”的分立。在概念上,這種主張意味著“一種改良甚至帶有一些革命色彩的運動……反對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形式主義和實證主義,力求全面現代化法學,并特別主張法學與社會學之間的相互滲透”。[注]Albert Foulkes, “On the German Free Law School (Freirechtsschule)”, ARSP: 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 / Archives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1969, vol. 55, no°3, p. 367-417.然而,概念背后的現實是,法律的解釋者以法律和社會之間的中介面貌出現,在定義法律和決定法律的意義方面享有了更大的權力。其實,判例法在我國古已有之。畢竟“規則有限,情偽無窮……在現實型的法適用模式中,便出現了法有正條卻因為情罪重大而比附援引的現象”。[注]同前注,陳新宇書,第130頁。通過比附援引而成的判例,一旦經官方編纂認可,當然具有法律淵源的地位,就算未成“通行”,往往也是事實上的法律淵源。以例為法源,既沒有冒犯皇帝的絕對權威,又補充了律的不足。[注]參見前注,陳新宇書,第130頁。我國法典化的黎明之時,恰逢世界范圍內“法典化時代”的黃昏。此時的中國法學家以一種來自于西方的理論,在“西法東漸”的潮流中保留了中國古代法文化的多元主義特征。雖然這種結果很可能是法學知識生產中的一種“非意愿后果”,卻在客觀上避免了我國法律實踐陷入那種理論上堅持立法至上,實踐中司法活動卻處處突破法律文義的矛盾。這種矛盾在《法國民法典》生效后曾經嚴重阻礙了法國法學的發展。
要理解民國時期的法學知識,就得考察當時法律學說的性質。學說在當時是一種對政治生活的直接參與。[注]法學家的政治參與恰恰是此前歐美學術史所忽視的一個方面,最近才有一些成果問世。在這方面,我國的史學研究確實有可以貢獻于世界學術之處。Laurent Frajerman, “L’engagement des enseignants (1918-1968)”,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1 janvier 2008, no°117, p. 57-96; Nathalie Le Bou?dec, Entre théorique juridique et engagement politique: Gustav Radbruch, un juriste de gauche sous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Thèse de doctorat, Paris 4, 2007; Marc Milet, “Les publicistes fran?ais et la CED, controverse doctrinale et engagement civiqu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mai 2012, n° 149, no°1, p. 101-113.民國時期重要的法學家往往也同時是重要的政治活動家,王寵惠、史尚寬、謝冠生、吳經熊、王世杰、鄭毓秀和魏道明等人皆然。當時的法學家也一直認為法學需要服務于民族獨立、救亡圖存的政治事業。從清末民初領事裁判權廢撤,到20世紀30年代中華法系建設,法學上熱議的題目有不少就是當時政治發展中的重要課題。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學者把學說的任務看作“用立法和判例提供的初級材料建構雄偉的法律殿堂”,[注]Cf. Adhémar Esmein, “La jurisprudence et la doctrine”,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 1902, vol. 1, no°1, p. 5-19.或者把學者說成是“融貫法律體系之圣殿的守護者”。[注]Pierre Catala, “Discours de M. Pierre Catala”, in Remise des études offertes à Pierre Catala,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 2001, p.47.然而,在民國時期,法學的任務卻不是體系構建,而是以積極的方式推動民族現代化、參與國家的建設。雖然留法歸來任教于中央政治學校的阮毅成認為外來的法律是于天災人禍之外對人民的又一苦難,但以先進的歐洲法律助力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不但是很多法學家的心愿,[注]參見朱明哲:《論王伯琦對法國學說的揀選與闡述》,《清華法學》2015年第2期。恐怕也是政府本身的意圖。誠如蔡樞衡所言:“天下為公,親愛精誠等概念固有其應有的意義,不失為徹底摧毀農業社會組織之一對癥藥。”[注]同前注,蔡樞衡文。
因此,在民國時期的法律場中,法學的競爭優勢就取決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滿足現代化、解放等一系列任務。在這種情況下,一種獨立于政治生活的法學本來就不可能存在。與此同時,一種言說規范的語言模式也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生產和固化,即要求法律的解釋者適用三民主義、從具體時代的民族需要出發,推求革命人民心中主觀的法律情感,從而在解釋時采取“論理解釋”,創造實在的法律。在這種風潮之下,本來就在政治生活之中的法學家選擇法律社會化理論就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方面,他們通過適應這種得到官方提倡的話語模式,取得高度的象征性權力,另一方面,他們又以自己的理論闡釋為這種話語模式提供支持。
通過理解法律社會化理論在我國傳播的原因,人們還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法學本身。每一種法律學說不但有自己的歷史,更有一段全球史。法律社會化理論的思想淵源在德國可以追溯到基爾希曼(Julius von Kirchman)和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在法國則是夏爾蒙(Jules Charmont)的主張最為有力。日本法學家進一步把惹尼其實十分保守的理論摻雜其間。所以民國時期法學家接觸到的實際上是一個已經混合了多種影響與淵源的“法律社會化”和“判例造法”理論。然而,這種理論當時在歐洲雖然很有影響,卻并不是最主流的理論。至少在法國,立法至上的觀點和自由主義的民法觀仍占上風。有鑒于此,研究者最好將民國時期判例造法之爭中出現的論點視為法學家有意識選擇的結果。不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了“法律場”的存在及其結構,這些法學家確實在根據他們所競逐的特殊利益和所掌握的象征性資本進行選擇。那么,與其說把外國學說的傳入視為一種“殖民”,不如將其視為法學家為鞏固自己在法律場中地位而做出的主動選擇。法學家選擇這一貶低立法、強調進步的學說,令法學家們在司法、法學和立法之間的客觀結構中可以展示自己的作用。
四、結 論
行文至此,有必要談談從民國時期關于判例造法的討論中,可以獲得何種借鑒。首先,雖然我國今日法律體系中的規范已遠非20世紀初“六法全書”時代所能比,但其中使用的概念、借以思考的理念仍有不少傳承自當時。所以,回溯過去事件如何發生,對于理解今天“正在發生”的,是必要的。其次,民國時期最高司法機關既在個案中解釋法律又接受下級法院請求而抽象地統一法律解釋的雙重功能對人們理解當代世界各法律體系都有重要意義。比如,預先審理制度授權歐盟成員國最高法院在對歐盟法的解釋不確定時提請歐盟法院解釋。那么,似乎不應該認為司法僅僅把法律適用于個案,而應當承認其本身具有統一解釋乃至形成新規則的功能。再次,民國時期的歷史經驗顯示,不管是否有法典,司法機關通過判例造法在實踐中都無法避免。所以對今天的中國而言,無論判例指導制度多么不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實際上都借其形成新的規范。面對新的情勢,學說和判例都在各自創造著新的規范,而非“判例解決個案、學說整合成一整體”。正是因為它們是相互獨立的法律淵源,規范才一再碎片化,法典統一評價的功能也才一再受到限制。從這個角度說,“解法典化”等現象的種子早在法典化的時代已經種下。最后,就算承認了判例創制規范的功能,也不意味著學說要對司法亦步亦趨。只有正視其功能,學說對其展開的反思與批判才能更具有影響力。實際上,立法、司法、學說始終競爭著對法律的權威解釋。
回到本文的核心問題,其答案就是一個時期法律場的內部結構決定了一個法律體系中法學與司法的關系。通過考察民國時期司法與學說之關系,可以揭示組成法律場的要素。法律實踐的核心利益是創造規范并決定其意義。每個法律實踐者都以其自身的方式參與競爭。當代法學理論普遍承認的立法、習慣、判例和學說四種法律淵源對應的是四種不同的人群,即立法者、法律的使用者、法官和學者。他們用這些法律淵源競爭規范創造之權。如前所述,法典化的時代意味著所有的法律淵源都圍繞法典形成與發展。那種在法典化時代以前的法律多元實踐中存在的各種法律淵源之內容彼此明顯不同、相互競爭對抗的局面不會再出現了。然而,只要法律場仍然存在,那么不論法典如何規定,其他法律淵源創造新規范都是不可避免的情況。體系化的法典相對于一般單行立法而言往往更加穩定,這甚至意味著立法者在法典化的時代更難以壟斷規范的創造。學說與判例、法學與司法的關系取決于相應的人群在法律實踐中所享有的社會資本,他們反過來使用這種社會資本不斷鞏固、提高自己的地位。各種學說的引入與解釋、各種司法決定的立場和方法,都可以看作是學者與法官在法律場中選擇的策略,體現著他們對自己所處之實踐的認知。事實上,民國的法學家為學說和判例都爭取到了有限的獨立性。
筆者于本文中運用關于民國時期判例造法論爭的經驗性研究闡明了來自布迪厄反思社會學的一個理論性的主張。這種思路沒有回答諸如我國目前法律實踐中判例與學說各自地位之類的問題。相反,筆者提出了目前探討民法典制定時沒有提出的問題:我國目前的法律場構造如何。這個問題只能通過實證研究解決。僅就目前學界對案例指導制度既積極重視又大膽批評的討論而言,人們似乎又可以看到學說一方面為判例造法提供支持,一方面努力證明自己才應當是判例造法的指導者的民國舊事。當然,只有更全面的實證研究才能精確描繪當前法律場的構造,而這樣的研究將有利于人們破除法典崇拜,并為正確評估學說與判例的造法功能提供經驗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