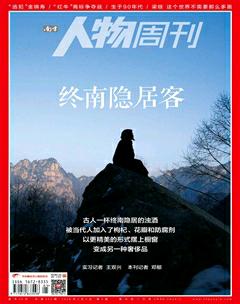家中的陌生人
王寶民
每個中國人的家庭中或許都有這樣一位“陌生人”:我們與其朝夕相處,但有時你可能會問自己:這個人到底是誰?有過什么故事或秘密?我真的了解他/她嗎?……一旦疑問開始,似乎就不能停下來。
臺灣導(dǎo)演黃惠偵家中便有這樣一位“陌生人”,她的母親。雖然在一起三十幾年,但除了桌上的飯菜,她們的生活可以說完全沒有交集。有一天,黃惠偵決定打破這種僵局,徹底了解她的母親,于是便產(chǎn)生了這部叫作《日常對話》的紀(jì)錄片。
這部紀(jì)錄片的內(nèi)容遠(yuǎn)非“日常”,它不僅涉及母親的同性戀者身份,且間雜以家暴、性侵等話題。但若暫時擱置這些易被過度關(guān)注的特殊元素,本片于現(xiàn)代中國人家庭關(guān)系的考察和描繪亦具有范本乃至原型意義。這種擱置或許能夠得到導(dǎo)演的默許,因她在片中對這些特殊元素若非一笑了之,至少也并未耿耿于懷;她從始至終未放棄追問、不能釋懷的,乃是我們每個人驀然回首自己的家庭時,或多或少都會遇到的問題:親密關(guān)系中的陌生感。血緣所帶來的關(guān)系如此脆弱,并不天生就親近,反而可能更加隔膜。
紀(jì)錄片中,媽媽表現(xiàn)為兩種狀態(tài):在外面跟女朋友們在一起時,如魚得水,有說有笑,生動而快樂;一回到家就立刻沉默起來,似乎和家人無話可說。這讓本片導(dǎo)演(女兒)感到非常受傷,認(rèn)為母親很討厭她,而母親也認(rèn)為女兒討厭她。對話進(jìn)行得非常艱難、尷尬,幾乎淪為“質(zhì)問”,讓人無從逃避,尤其是臨近片尾長達(dá)10分鐘的對話,令人異常痛苦。
這是弱者對弱者的質(zhì)問。那位始作俑者已經(jīng)不在了,只有她們?nèi)栽诨ハ鄠Α?/p>
對于“家中的陌生人”的追問、探尋和了解,是此類“私紀(jì)錄片”的永恒命題之一。在此意義上,我認(rèn)為本片對于中國觀眾的最大價值是:戳穿了層層面具,為哪怕最糟糕的家庭關(guān)系注入“理解”和“愛”。而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著將紀(jì)錄片的“真實(shí)”倫理貫徹到家庭關(guān)系領(lǐng)域。這本身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人們看慣了很多紀(jì)錄片導(dǎo)演樂于將鏡頭對準(zhǔn)外部世界,卻往往回避自家的私生活,尤其是家庭中的陰暗面,因?yàn)檫@太艱難、也太危險了。
另一方面,本片也并未呈現(xiàn)為有效的雙向“對話”。在咄咄逼人的攝影機(jī)注視下,是那個如坐針氈、時刻想逃離的母親。這暴露了紀(jì)錄片倫理與家庭倫理之間的沖突。攝影機(jī)擁有一種“權(quán)力”,它不僅表現(xiàn)于“凝視”和“追問”,同時也表現(xiàn)于“闡釋”。在女兒的攝影機(jī)面前,從前強(qiáng)勢的母親變成了弱者,被迫回答各種問題。
每個問題都基于“愛的匱乏”。這是一種有繼承性、遺傳性的癥候,導(dǎo)演的小女兒或許也繼承了下來,總是不時地要求“媽媽抱抱”。在經(jīng)過漫長的痛苦對話之后,導(dǎo)演似乎仍未滿足,在片尾,她讓小女兒用玩具攝影機(jī)再三追問母親:你愛不愛我?
“我愛你。”她們終于獲得了標(biāo)準(zhǔn)答案。那是這家人從前都不熟悉的一種語言,或者說,是她的母親身經(jīng)百戰(zhàn)、歷盡創(chuàng)傷之后的一個妥協(xié)性、禮儀性的回答,我們明顯看出其中的敷衍潦草,而女兒似乎也不再深入追究。
理性的觀眾或可質(zhì)疑,這種對“愛的索求”耽擱或妨礙了本片應(yīng)具有的更廣泛的人類學(xué)、社會學(xué)意義(或曰“私紀(jì)錄片”的公共性);但我們亦能理解,導(dǎo)演的不斷追問,其實(shí)并非僅僅為了真相,更多是為了“和解”,為了今后能夠讓自己以及身邊的人,像個正常的家庭一樣,相愛相親。余下的未解之謎仍很多,但只要她們心安于此,又有何妨?她們畢竟還能在一起度過余生。時間還很長呢!那就是她們自己的秘密生活了。我們只好祝福她們。
《家宴》(1998)
導(dǎo)演:托馬斯·溫特伯格
一場家庭聚會正在富紳海吉的豪宅中舉行,是為了慶祝他六十歲大壽而籌辦的。兒女們紛紛從外地趕來。不過原本該是融洽熱鬧的晚宴,卻籠罩著詭異的氣氛……本片為丹麥“Dogme95”運(yùn)動的開山之作,用DV攝影機(jī)手持拍攝,粗糙的畫質(zhì)揭開了家庭生活中不堪的本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