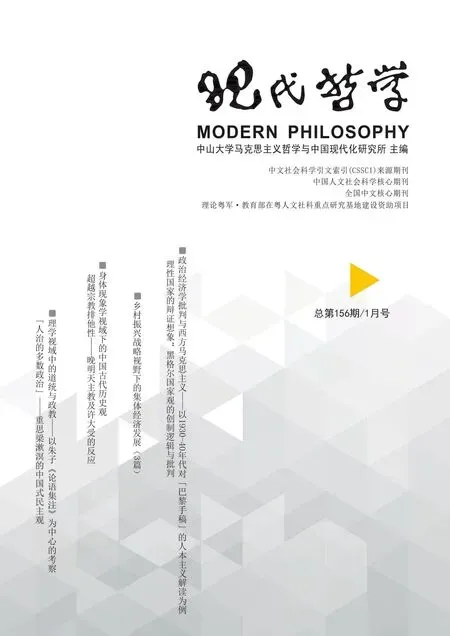最后的神的面目
朱清華
海德格爾后期關于最后的神和諸神的論述引起了廣泛興趣,一方面因其深奧難解,另一方面因其在海德格爾后期思想中占了極為重要的位置。研究者都試圖透過海德格爾艱深的描述來把握海德格爾所說的神是什么及其思想意義。海德格爾協會(Martin Heidegger Gesellschaft)2016年年會(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所討論的主題之一就是海德格爾與神學的關系,在會上Ingeborg Schüβler、Istvn M. Fehér、Günter P?ltner、Helmuth Vetter等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海德格爾的神。*其中Ingeborg Schüβler教授的報告《觀看、全能與暗示:海德格爾論上帝問題》論述了海德格爾的最后的神和上帝(作為存在者的最高根據)、基督教的創世神的對抗。(參見王宏健:《2016年海德格爾協會年會紀要》,首發于公眾號“大道不離萬有”。)在關于海德格爾的“神”的研究文獻中,有人強調海德格爾的神的非神學意義和神對此在的促成作用。例如,Figal強調《哲學論稿》和《存在與時間》的內容承接和聯系,提出最后的神是給出理解者,是此在和存在的時間-空間,通過神,此在在自由中成為自身*Günter Figal, “Forgetfulness of God: Concerning the Center of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in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C.E.Scott, S.M. Schoenbohm, D. Vallega-Neu & A.Vallega ed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06.;認為最后的神不會以任何個別的形式顯示自身,不會成為一個宗教信仰的中心。Crownfield也強調神在自我-決斷中的位置,神是超出自我決斷的贈予和要求。*David Crownfield, “The Last God”, in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pp.213-228.Polt認為海德格爾提出的諸神以及最后的神是“民族性的來源”。*[美]波爾特:《存在的急迫》,張志和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305頁。他們都淡化了最后的神和諸神的神學意義,而強調在提出眾神和最后的神之際,此在的成己就有了一個上限,或者說獲得了一個來自超越的力量的規定,即它的成己之路不再只靠自己的力量,還有一個在上的超越的力量可以訴求。孫周興的論述大概可以歸為此類。*孫周興:《后神學的神思——海德格爾〈哲學論稿〉中的上帝問題》,《世界哲學》2010年第3期,第44—54頁。有的學者則強調最后的神的神學特征,例如Seidel認為海德格爾的最后的神出自謝林“最后的神”,甚至是將謝林思想轉化的結果。*Seidel, “Heidegger’s Last God and the Schelling Connection”, in Laval Théologique et Philosophique 55, No.1, February 1999, pp.85-98.林子淳認同Seidel的觀點,認為海德格爾深受謝林神學影響,最后之神可能反映了海德格爾的基督論,所擔負的是“道成肉身”教義,即最后的神是存有的本現;但他也指出不能直接將二者等同,因為海德格爾最后的神的提出,是為了進入另一個開端服務。*林子淳:《“最后之神”即海德格爾的基督?》,《世界哲學》2015年第1期,第62—71頁。另外,Paola-Ludovica*Coriando, Paola-Ludovica, Der letzte Gott als Anfang: Zur ab-gründigen Zeit-R?umlichkeit des übergangs in Heideggers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Munich: Wilhelm Fink, 1998.、D. Vallega-Neu*D. Vallega-Neu,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Richard Rojcewicz*Richard Rojcewicz, The Gods and Technology-A Reading of Heidegg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2006.等都對海德格爾的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對海德格爾的“神”這個異常晦澀的概念應當如何理解?海德格爾的“神”是什么?神和人是一種什么關系?
一、最后的神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海德格爾所說的神因其難以正面描述,往往只能從否定方面被把握,所以他關于神的觀點常常被稱為“否定神學”*馬利翁(J.L.Marion)也將海德格爾放在狄奧尼索斯-埃克哈特大師神秘主義否定神學傳統中。關于否定神學,參見Flight of the God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Negative Theology, eds. Ilse N.Bulhof and Laurens ten Kat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0.。本文也首先從否定方面對海德格爾的神進行論述。海德格爾所說的最后的神顯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哲學論稿》對“最后的神”最先表明的,就是“最后的神完全不同于曾經的那些神,尤其是基督教的上帝”*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GA65),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403.,這就開門見山地把最后的神和基督教上帝區別開了。上帝已死,根本無力承擔海德格爾賦予神的任務。他在多處文本反復批評包含在形而上學史中的基督教的上帝。在他看來,基督教的“上帝之死”是必然結局,是形而上學史發展的結果。傳統的形而上學同時是存在論、神學、邏輯學*參見[德]海德格爾:《形而上學的存在-神-邏輯學機制》《同一與差異》,孫周興、陳小文、余明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Die Onto-theo-logische Verfassung der Metaphysik(1956/57)”,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t und Differenz,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6.,這三者是一體的。由于形而上學首先是存在論,它將存在作為奠基性的觀念,對存在者的存在的論述有兩個向度:一方面它是那最先的、最普遍的,另一方面它是最高的、最終的。從第一方面來說,存在就是邏輯學的最根本原則和論證的出發點;從第二方面來說,存在是形而上學上的最高存在者。上帝同時作為最高的和最終的存在者、根據以及最終因、自因,所以在形而上學歷史中,存在論、邏輯學與神學不相分離。但海德格爾認為,形而上學忽略了存在論的差異,所探討的主導問題是“什么是存在者”,而沒有思考存在自身。*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GA65), S.6, 12, etc.上帝被分解(Austrag)出來,成為存在論-神學-邏輯學的最終因的和最高根據,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根據,那祂自己也不免成為一個特別的存在者。這個貫穿形而上學史的上帝見證了形而上學的興衰,并隨著形而上學走向終結,而被宣稱“上帝死了”。 在海德格爾看來,上帝之死并非人們經常認為的那樣,是無神論以及虛無主義的開始,反倒是虛無主義的自我呈現。形而上學的本質就是虛無主義的,它既不思存在,也無諸神臨在。這種虛無主義一向被基督教的上帝所掩蓋,而上帝之死將這種虛無展示出來。海德格爾甚至提出,上帝不是剛剛才死了、死于現代,而是兩千年來神都已經不在場。虛無主義是歐洲的歷史基本運動,也是被歐洲所決定的世界歷史的基本運動,是西方民族命運的不為人所知的推動力。*[德]海德格爾:《尼采的話“上帝死了”》,《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232、234頁。以虛無主義為其本質的形而上學注定發生超感性世界的崩塌,包括上帝、道德法則、理性權威、文明、文化等的崩塌。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喪失,只是其中的一個結果。
近代以來,上帝和教會的權威被“理性”和“良知”代替,超感性的領域被“歷史進步”代替,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標被塵世幸福代替,似乎一種新的思想模式已取代了舊的神創論模式,但實際上這一切都沒有脫出舊有的世界構造和存在者的等級模式,只不過換了名稱而已。海德格爾指出這個舊的模式是在形而上學的開端處早就被柏拉圖所確立的泛希臘-猶太世界基本結構。*[德]海德格爾:《尼采的話“上帝死了”》,《林中路》,孫周興譯,第234頁。這個換湯不換藥的架構,雖然到了尼采才喊出“上帝死了”的哀鳴,實際從開始就已經離棄了諸神,離棄了存在。在尼采那里,“上帝”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而“上帝死了”是說那個超感性的、約束性的世界喪失了,柏拉圖以來形而上學的理念世界不再有效了。但是海德格爾認為,事實上,形而上學的“上帝”的位置沒有闕如,而是被“主體”所替代。形而上學的那種神學-存在論-邏輯學結構也沒有隨著上帝之死而喪失。主體性的本質規定是“表象著的主體保證其自身,并且始終也保證它所表象的東西本身”*[德]海德格爾:《尼采的話“上帝死了”》,《林中路》,孫周興譯,第257頁。,從而真理成了確定性,確定性具有可靠性的特征。這種可靠性靠數學觀念的清晰性、明確性來保證。因此,數學和計算成為真理的衡量標準。在以計算和機巧(Machenschaft)為特征的現代,真理不復是存在的真理。海德格爾斷言:還有幾百年機巧將會洗劫地球,使之荒蕪。*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65), S.408-409.
海德格爾認為,西方思想的崩塌是存在離棄的結果,其表現就是諸神的逃離,在現代這種從存在的連根拔起卻被“人的重現發現”所掩蓋*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65), S.118,119.。人作為主體是脫離上帝的控制而自我裁決的“自由人”,通過科技的“進步”,人的控制力變得強。但人自身卻是大眾化的、無根的,松松垮垮,精神貧困。人無能于思考,無能于真理。所謂“進步”只是存在的離棄的加深和增長。
二、人的本質和神性
諸神逃逸被海德格爾看作是存在離棄的標志,人也因此失去根基。問題是:為什么人必定需要神?在人的生存中,神有怎樣的位置?在海德格爾那里,存在的本現與人的本質的確立跟神的召喚密切關聯。他一再指出傳統對人的定義(即人是理性動物)是一個謬誤,原因之一是這個定義將人規定為某種實體,賦予人既定的本性。而他認為人除了生存外,沒有其他本質。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一切根據的根據,由此可以說人是無根據的(Abgrund)。*Heidegger, “Vom Wesen des Grundes” , in Wegmarke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76, S.174. [德]海德格爾:《論根據的本質》,《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207頁。不過,展露在此在面前的是命運帶給它的、它作為被拋的東西的那些可能性。這是有限的選擇可能性,而非薩特所說無限的可能性。不能將人歸為理性動物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從動物出發對人進行規定時,在范圍上已經畫地自限,將人跟動物劃歸一類,然后將人再區別出來,對人的研究也最終歸為生物學、人類學的范圍。而在他看來,雖然人和動物在肉體上最接近,但從存在上人更接近于神。*Martin Heidegger,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in Wegmarken, S.326.神一直和人的“本真狀態”或“人的本質”的奠基關聯在一起。神就在存在的真理的奠基中運作,作為召喚者,作為逝經(Vorbeigang)者。人和神的本現都來自存在自身,來自存在的真理,所以必須從人-神關系而非人-動物關系來規定人。
在海德格爾那里,人的本質同“家”和“家鄉”有難以割舍的聯系,一方面是此在本質的無家可歸狀態,另一方面又要返鄉和回家。《存在與時間》強調人本質上是無家可歸的。在家狀態(Zuhause-sein)只是常人在平均日常狀態的安然自信,沉淪于世界中如同在家一樣。畏將這種假象粉碎,此在失去熟悉的“家”,頓覺駭異驚恐,流離失所。人在畏中駭異于這種不在家(Un-zuhause)*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ue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0. S.188;[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217頁。,這是尋求本真存在的開端。此在更加源始的現象是無家可歸狀態(Unheimlichkeit),而非在家的平安寧靜狀態。在家狀態反而是無家可歸的一種變式。因而,在沉淪日常操勞的在家狀態中,總有無家可歸狀態在威脅著,它在最無關痛癢的處境中升起。此在在操勞中總是力圖逃避這個無家可歸狀態,逃進常人狀態中。而畏總是要打破它的寧靜,將帶它到自己面前。*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189;[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第218頁。在對無家可歸的強調中,海德格爾試圖說明人的本質和人的生存不受任何預定的實體決定。人是自由的,雖然這種自由令人驚怖,如同遭到流放。不過指出人本質的無家可歸狀態并非最終目標,海德格爾的目的是要為人找到真正的家,即人的立足之處。“只有那種存在者,它作為將來的(zukünftiges),也同等源始地是曾在的(gewesend),才能把繼承下來的可能性承傳給它自己之際接納本己的被拋狀態,為‘它的時代’而瞬間存在(augenblicklich sein für ‘seine Zeit’)。”*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385;[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第435—436年。此在的立足點就是其被拋其中的歷史(Geschichte),這里的歷史主要指涉民族歷史。此在通過對歷史之曾在的重演,在決心中傳承下、選擇出那些使得本真生存可能的可能性,也就是將自己交托給了自己,從而擁有他本己的命運。此在決斷之根基就來自這里。在這個本質立足點,人不再如同浮萍一樣處處是家而處處不是家,不再流轉于常人。
海德格爾在后期與前期一樣仍討論“無家可歸狀態”,但是從存在歷史角度來談的。自第一個開端之后,存在離棄日益深重,上帝之死更敞明了那種虛無。思想在形而上學之存在遺忘中掙扎,在機巧為本質的技術時代,已經面臨極大的危險和困境。在這個時代,諸神逃逸。處于存在離棄這種最大的困境(die Not)中,是最深重的無家可歸。在作為存在離棄的拒絕中,此-在(Da-sein)被迫回到自身,接受自己在存在歷史中的天命。因此,后期海德格爾除了揭示人的日益深重的無家可歸狀態,還強調“還鄉”,并且顯然更關注的問題是何處是人的“家鄉”、人如何“還鄉”。海德格爾說需要回到西方的天命去找到人的本質。“人的未來的天命就在于,人要找到存在的真理中去而且要走到找存在的真理的路上去。”*[德]海德格爾:《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海德格爾選集》,第384頁。所謂西方的天命,海德格爾指的是西方在存在歷史中現在所處的存在遺忘狀態和將來有可能的承擔起人類克服存在離棄,過渡到另外的開端的使命。這個使命尤其是荷爾德林的“同胞們”德國人的,“以便德國人從命定的歸屬于各民族的關系中與各民族一同變成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德]海德格爾:《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海德格爾選集》,第382頁。。人的天命便是在存在的真理中駐足,從存在歷史而言,人的駐足之處是存在的天命,回歸到存在的近處,就是回到家鄉。人真正的本質或者本真性,就是進入存在的真理,看護存在。除此之外人無本質,是一無所有的赤貧。*[德]海德格爾:《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海德格爾選集》,第385頁。
那么,人從何處獲得進入存在的真理的力量?易言之,人成其本質的尺度是什么?在機巧的時代,尺度敗壞為數學和數字的度量。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皆從數學獲得其存在性。一切對象皆從數字被表象。人自身作為統治者、支配者自身卻失去了尺度,唯有從尼采所依據的“動物性”或黑格爾所依據的“理性-意志”來規定和衡量。海德格爾認為,真正的尺度是詩人荷爾德林所把捉到的,乃是從神而來的尺度。“神本是人的尺度。”*[德]海德格爾:《人詩意地棲居》,《海德格爾選集》,第472頁。神能夠作為尺度,乃因神源自存在,出自居有(Ereignis)。神有其神圣性和神秘性。神作為尺度,意思是這個不可被認識者保持為不可被認識者,處于一種揭露活動中,讓被遮蔽者看到,但不是作為完全的、脫離了遮蔽的東西被看到,而是將其保護在遮蔽之中同時讓人看到。神在天空中,而人在大地上,同時在天空之下。在海德格爾看來,這不僅僅是人的地理位置,而且是人本質的維度——人需要從大地和天空同時獲得其存在尺度。作為在大地上的,人是有死者,人承擔起他的死亡;作為在天空下的,人從神獲得尺度。*[德]海德格爾:《人詩意地棲居》,《海德格爾選集》,第471頁。
神是那在親熟的東西中陌生的東西,也是詩人在作詩中所召喚的東西。*[德]海德格爾:《人詩意地棲居》,《海德格爾選集》,第476頁。詩人能夠從神獲取尺度,他的作詩活動就是從神“采取尺度”,詩人借神性度量自身。*[德]海德格爾:《人詩意地棲居》,《海德格爾選集》,第472頁。海德格爾所說的回到家鄉,承擔起被拋狀況,或承擔起存在離棄的困境,都是指人獲得本質,獲得其命運,為命運所把握,或者說被存在所派遣。只有能勝任這種困境的人才有命運,才能經驗到作為命運的存在。命運是半神的存有(das Seyn der Halbg?tter)。*Martin Heidegger, H?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GA39),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9. S.179.海德格爾所謂的只有詩人能夠“采取尺度/丈量尺寸”,就跟他說詩人是“半神”一樣。半神的內在特征是綻出地進入神和人的存有的中間,嵌回到家鄉大地,解放其中統治性的力量。所謂半神不是神,也不是完全的人,海德格爾稱之為超人的存有(Das übermenschliche Seyn),其本質是承擔起我們的被拋狀況,揭示出困境,并勝任這種困境。在這個承擔(Leiden)中,存在作為命運被敞開。*Martin Heidegger, H?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GA39), S.175.半神作為海德格爾的超人,正是那些以作詩、運思等方式打開澄明之境的人。在他看來,人需要先被存在拋進存在的真理,綻出地生存才有可能有最后的神和諸神進入澄明,但并不能保證他們會出現。唯有等待最后的神的召喚和拯救,才能擺脫存在遺忘狀態,回到家鄉。總之,神是人得以被派送存在的命運的中介,人藉由神而成為此-在,即存在的真理在此本現。
三、存在歷史和神的面目

神的形象既然是不可視見的神秘,其降臨就不會是跟人面面相覷的直視。海德格爾用逝經(Vorbeigang)來描述神的到場,提出逝經是諸神在場狀態的方式(das Vorbeigehen ist die Art der Anwesenheit der G?tter)*Martin Heidegger, H?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 (Winter semester 1934/35), S.111.;同時用諸神的逃離或到來(die Flucht oder die Ankunft der G?tter)這樣的說法;稱最后的神在暗示中本現(Wesung im Wink)*Martin Heidegger, Parmenides(GA54), S.12,409.,最后的神的“最偉大的接近”作為拒絕(Verweigerung)。這些說法的共同之處是,神的顯現不是現成的在場。波爾特(Polt)指出,“逝經”這種說法和尼采有關,即“查拉斯圖特拉逝經我這里”;但其更深來源是舊約《圣經》,即“神在其榮光中‘逝經’摩西,但摩西不能直接看神的面容,因為那意味著死亡”*[美]波爾特:《存在的急迫——論海德格爾的〈對哲學的獻文〉》,張志和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301頁。,同樣神伴著烈風、地震和火逝經了以利亞。波爾特正確地指出,上帝間接地展示自身,在人和神之間有某種接觸,但我們永遠無法表象或者考察他。海德格爾的神跟上帝一樣地逝經人,并不表明他的神是基督教的上帝,不過他提到在源始的猶太教中和耶穌的布道中的神是他所說的神的“曾在者”(das Gewesene)*Martin Heidegger, “Das Ding”, in Vortr?ge und Aufs?tze (GA7), ed. F.-W. von Herrman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0, S.185.。
海德格爾既用神(der Gott)也用諸神(die G?tter),還用最后的神(der letzte Gott)這樣的表達方式,在數量方面,既有單數也有復數。他提出神的數量并不是個問題,無論是單數的神還是復數的諸神,都不能做量化的理解。用單數的形式,神用以表述海德格爾所說的神性,所以他也用神圣者(das G?ttliche)、神性的(das G?tthafte)來稱他所說的神*在Parmenides(GA54)中多有這樣的用法。;而他用復數對應的是“基礎與去基礎的內在豐富性”*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11.。最后的神和諸神雖然在神性上沒有差別,但海德格爾按照存在歷史給了屬于他們的不同的歷史階段*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 (GA70), ed. F.-W. von Herrman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2005, S.65.。按照他的存在歷史,第一個開端及其作為形而上學的歷史已經到達終結,必將開啟另一個開端。現在所處的是過渡階段,即對形而上學的克服和向另外一個開端跳躍的階段。第一個開端處有希臘的諸神。伴隨著形而上學的歷史的開展并走向終結,諸神逃逸,隨之而來的是無神狀態(G?tterlosigkeit)。無神狀態并不值得人歡欣鼓舞,也不是人擺脫神權統治后獲得自由,而是人已經進入了最深重的存在離棄狀態,有待開啟存在歷史的另一個開端。在跳躍入另一個開端之前的過渡階段中,只有最后的神的召喚讓人出離存在遺忘的困境。海德格爾稱,最后的神是為了存有之本質的發生而來,祂開端性地本現作為開端的存有,而最后的神的召喚是“居有活動神秘的來襲和逃離”(Anfal und Ausbleib)*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06, 408.。由于最后的神產生自對真理的存有(Seyn der Wahrheit)的擁有,所以最后的神也是開端的神*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 (GA70), S.131.,祂喚起人向著另外一個開端。基督教因為拒絕了存在而拒絕了神,而海德格爾的最后的神丟棄了形而上學的造物主本質,祂卻因此更具神性。*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 (GA70), S.132.最后的神在過渡時期中是獨一無二的,具有唯一性,因為這是存有通過最后的神而有“獨一無二的切近”*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12.。而在另一個開端中,海德格爾又用諸神來表述神,“諸神被分配進神性中,人被分配進人性中”*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GA70), S.157.。在過渡階段,那作為神性的曾在者,無論是在希臘人那里的諸神還是在預言的猶太教、耶穌布道中的神,雖然已經不再(Nicht-mehr)在場,但是同時也是祂們的神性之“未被耗盡的本質的隱蔽的到來”的一種尚未(Noch-nicht)。*Martin Heidegger, “Das Ding”, in Vortr?ge und Aufs?tze (GA7), S.185.如果是這樣,那么對曾在的神的重演就是對未來的神的接近。
四、神和半神
海德格爾所說的神不是存有(das Seyn),不是某種存在者,也不是神化的人。*Vallega-Neu也強調這一點。參見[美]瓦萊加-諾伊:《海德格爾〈哲學獻文〉導論》,李強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1頁。神顯然不是任何存在者,即使是最高的存在者都不是,所以與基督教的上帝有質的差別。海德格爾的神也不是基督教上帝那樣的完滿的存在,不缺乏任何存在,相反,他的神需要存有,但是神有所需要、有所缺乏并不降低神的偉大。在海德格爾這里,存在比任何神都更具開端性(Das Sein ist anf?nglicher denn jeder Gott)*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GA70), S.64.。在神和存在的關系中,最后的神來自存在的居有(Ereignis),是居有“遲疑著的拒絕提升”,也就是一種拒絕(Verweigerung)。這種拒絕不是單純的不在場,而是在拒絕中已經有著居有發生,是一種最高的賜予的方式。在存在離棄中,存在顯示為拒予,而最后的神顯現的方式首先是拒絕顯現。這是神對人的最極端的遙遠。人認識到這個困境和這種遙遠,恰恰是由于聽到了神的召喚,所以這種遙遠同時是對神的獨特的切近。最遠和切近同時在一瞬間發生。在存在的拒予中,以暗示的方式,最后的神降臨。為此,人需要做到兩件事:一是經受住作為拒絕的存在的居有,二是讓存在者如其所是地顯現。*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11, S.412.由此,大地得到拯救,世界煥然一新。
神不但需要存在,也需要人,只有人的建基才把真理庇護進存在者中。神的歷史需要人來保存。說最后的神或諸神在存在和人之間溝通二者,或者說它是存在自身“道成肉身”*林子淳:《“最后之神”即海德格爾的基督?》,《世界哲學》2015年第1期,第62—71頁。,都有很大的解釋空間。但是基督和最后的神之間仍有本質區別。海德格爾的神所做的不是救贖,將人作為罪人、低下的存在物,讓人屈服于神才能得救。在他的神中,此在沒有被壓低,而是被提升到它的自由的奠基中,置身入存有之中。海德格爾明確說,諸神對于人“不是救贖,不是壓低人”*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13.,存在之居有發生在神和人的斗爭中。神和人之間的關系并非僅僅是聽從,而且還是斗爭。在天、地、神、人共同構成的游戲時空中,神、人、存在者整體才都各得其所地本真存在。
這個居有事件在決斷(Ent-scheidung)中發生。在《存在與時間》中,面臨虛無的惶恐畏懼,決斷打開了一個空間,從而完全擺脫常人狀態。在后期,決斷(Entscheidung)首先是屬于存在自身的運作。Ent-scheidung表示的是分離、分開,是存有的本質中心(Wesensmitte),即存在自身在最中心處就是分開、分離。在分開中,打開一個敞開域,這個敞開域就是澄明之境(Lichtung),也是居有活動(Er-eignung),是人對存在的歸屬,同時人成為存在的真理的奠基者。在存在的中點處打開一個游戲時空(Zeit-spiel-Raum)。通過分開,才有了人-神的分離和人對神的歸屬,人被神占有。在這個敞開域中,存在者整體被放入決斷。這種決斷從存在對人的派送而言屬于天命,而對人而言就是承受天命做出決斷。這種決斷或者朝向歷史,或者喪失歷史。海德格爾稱,所謂歷史即大地和世界的斗爭,這種斗爭的實施方式出于居有的召喚,其樣式是最后的神的召喚。這種決斷朝向歷史的方式,必須是對最后的神的歸屬樣式。神的暗示是“最短的、最陡峭的道路”*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96, S.408.。最后的神的暗示涉及諸神的“來臨和逃離的來襲和缺席”,也就是關于另一個開端的開啟。
Figal對最后的神和諸神的理解是深刻而有見地的,認為海德格爾最后的神不會以任何個別的形態顯示自身,也不會成為一個宗教信仰的中心,最后的神是那種讓人理解此在和存在的敞開的時間、時間-空間的東西,祂讓人經驗時間的統一,統一起這個敞開域。此在從對自由的把握而被奠基,它既非只相信自己的理論,也非僅僅依賴于一個在上的超越的能力。*Grünter Figal, “Forgetfulness of God:Concerning the Center of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pp. 207、208.Figal點明了神在人在此-在中奠基中的作用。在筆者看來,海德格爾的神的確有其神圣性。神不僅是促使人為存在所居有的一個力量,而且以其神秘和令人驚異的面目啟示人,這種神秘如同宙斯在天空發出的霹靂給人帶來敬畏*在《巴門尼德》中,海德格爾描述了宙斯發出的霹靂和真理女神的形象。。但這種神圣者又跟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不同,和“道成肉身”的耶穌也有本質區別。海德格爾說神給出尺度,而詩人“采取尺度”, 詩人如同“半神”一樣。同樣運思者、藝術家、政治領袖等也可以成為這樣的神和人之間的中介。*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65), S.302. Da-sein之“Da被經受,以各自的庇護真理的方式——思的,詩的,建筑的,領導的,犧牲的,受難的,歡呼的。”神通過諸如詩人、哲學家、政治家等給出尺度,他們承擔起了存在的天命,為此-在建基。在人的本質中,為存在所具有,被神所召喚,就是這種作為“半神”的“此-在”。這些少數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庇護了真理,由此成為歷史性的。同樣,“民族”也來自神的尺度。海德格爾強調,他所說的民族不是人類學上的某個族類,而是說他們都屬于存在自身。*Martin 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96.
結 語
海德格爾自早期就對神和神性的主題充滿興趣*陳治國曾對海德格爾早期的神學解構進行論述,朱松峰也對海德格爾早期思想與基督教的密切關系進行了論述。(陳治國:《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解構與神學的三重關系》,《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朱松峰:《早期海德格爾論原初基督教》,《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對神和神性的思考跟他不同時期思考的重點問題密切關聯著。在后期,海德格爾關于“最后的神”的論述同存在歷史以及此在的建基和人的安居密切相關。最后的神在存在離棄的困境中對人發出召喚,拒絕作為存在自身的本現的方式,是最后的神對人召喚的方式。最后的神是存在歷史從第一個開端到另一個開端的過渡中的神,就是那個能夠救渡處于極端困境中的我們的神。神還以諸神方式臨現。海德格爾說諸神是曾經的諸神的變形,應當指第一個開端處諸神的復活。他們是赫拉克利特在烤火爐旁共在的神,是人安居之神,也是在人“歸鄉”之后的“家鄉”的神,在此處,大地和天空、神和人在一個時間-空間的敞開之域中交相映射。在存在的真理之思中,在筑基中,神在。人對神是傾聽、不計算,為神所占有,被神所用*Martin Heidegger, “Von den G?ttern gebraucht”, in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GA65), S.87.,同時和神在斗爭。易言之,在海德格爾看來,“未來者”的生存必定與神同在。人的本質中有神性才得其所哉。
海德格爾的神不是有神論,也不是無神論,總之,不是神學上的神。他將神與人在存在的本現中以特別的方式結合起來。他對神的存在和神人關系的描述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