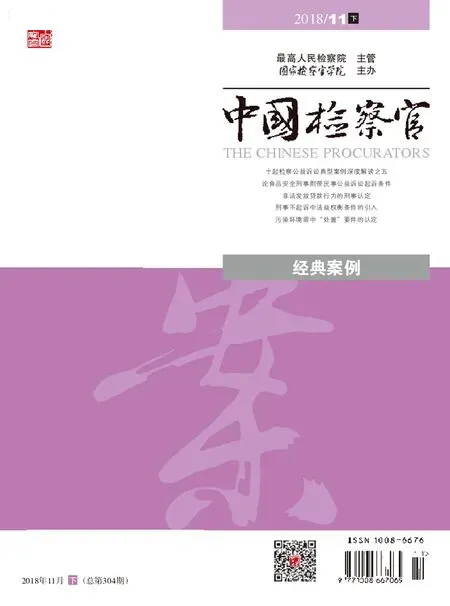累犯條款失效問題研究
文◎王 勝*
為了懲戒屢教不改的罪犯,世界各國成文刑法一般均對加重處罰累犯加以規定。我國《刑法》第65條、第66條也設置了一般累犯、特別累犯制度,同時第74條、第81條在刑罰執行上對累犯規定了不適用緩刑、不得假釋等限制措施。除了未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過失犯罪這二種情形外,累犯條款應當毫無例外地適用于“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所有罪犯。但近年來,累犯條款選擇性適用的問題愈發嚴重,重要原因在于隨著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司法機關為了解決行政與刑事處罰之間的銜接空缺問題,對刑法條文過度詮釋,出臺了不少將受過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作為定罪評價標準的司法解釋及相關規定,適用的罪名也呈不斷擴大態勢。盡管刑法理論界對是否將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作為定罪標準長期存在爭論,但實務界實際上已經按照“兩高”解釋來操作定罪事宜。伴隨而來的是,一旦將接受過刑事處罰作為定罪標準評價(或升刑格條件),對同時符合累犯成立條件的能否認定為累犯存在爭議。否定的觀點認為,將刑事前科列為定罪標準評價后,再次以累犯的量刑情節評價,違背了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而眾所周知的是,禁止對同一行為重復評價(俗稱一事不再理,以下簡稱禁止重復評價)是最基本的刑法原則,即罪前行為一般是不會成為本罪成立的依據。肯定的觀點認為,此種情形如果不認定累犯,則刑法總則的累犯條款在部分具體罪名中名存實亡。事實上,司法機關通過解釋的形式終止了立法機關所制定的刑法效力,使得累犯條款失去作用,從而導致部分罪名在某種意義上不再有累犯,嚴重侵犯了立法權。筆者將當下累犯條款適用所引起的爭論歸納總結為“累犯條款失效問題”,主張在反對簡單、機械套用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同時注重保護犯罪嫌疑人的相關權益。
一、問題的提出
累犯條款失效問題在非法行醫罪的認定中表現的最早也最為典型。2008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行醫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非法行醫解釋》)規定,“非法行醫被衛生行政部門行政處罰兩次以后,再次非法行醫的”,應認定為“情節嚴重”,以非法行醫罪定罪處罰。該規定出臺之初,便引起理論界的廣泛爭議,即行政處罰后再次作為刑法評價,是否違背了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反對者認為這顯然屬重復評價,“行政處罰是一種政府公權力對違法行為的評價,不能再次進行同樣是政府公權力的刑法性評價,該規定不存在正當性”。[1]較為流行并被司法實踐部門所接受的觀點認為,“行政法規與刑法屬于不同的法律部門,不同的法律對同一行為不同性質的評價,因此不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而且“我國刑法定性與定量結合的立法模式決定了刑法與其他法律對同一事實會重復做出評價,但是這個重復評價并未違反刑法中的禁止評價原則”。[2]最高法的司法解釋,實務部門當然要執行,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非法行醫剛被刑事處罰后再次 (第四次)非法行醫的,能否再次直接入罪?上海司法實踐中普遍認同直接入罪。但也有意見認為,對于曾因非法行醫被刑事處罰后再次非法行醫的,前面的刑事判決已經生效且執行,在后續刑罰的量刑中可以參照,但不能作為定罪的事實,應按照《非法行醫解釋》所規定的犯罪標準重新認定。嚴格來說,第四次非法行醫后直接入罪的,實際上對前二次行政處罰又進行了第二次評價,所謂的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在非法行醫罪認定中已蕩然無存。
給司法機關提出的最棘手問題是,對于曾因非法行醫被刑事處罰后再次非法行醫的,符合《刑法》第65條規定的能否認定累犯并從重處罰?從筆者檢索的全國非法行醫判決來看,各地做法不一,有直接認定為累犯,也有不再認定為累犯的。其中,細察上海青浦區人民法院的判決觀點,也有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例如,2015年該法院判決生效的紀某某非法行醫案中,紀某某于2014年因非法行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刑滿釋放后于2015年5月因再次非法行醫被抓獲,法院以其構成非法行醫罪且系累犯從重處罰,判處其有期徒刑9個月。而2016年該法院在王某非法行醫案、姚某某非法行醫案、薛某某非法行醫案判決中,則又糾正了2015年的觀點,對有期刑滿剛釋放再次非法行醫的都不再認定為累犯。毫無疑問的是,青浦區法院2016年判決的轉變更加符合禁止重復評價原則,但在行政處罰的二次評價上,仍然落入再評價的陷阱。
前述累犯條款適用問題并非局限于非法行醫罪,現今較為熱門的尋釁滋事、聚眾斗毆及容留賣淫等常見罪名上,司法部門也紛紛將前科劣跡作為刑法條款中“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具體內容。2013年“兩高”《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7項對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留出了一個“其他情節惡劣的情形”的兜底條款。2014年上海出臺《關于本市適用“兩高”尋釁滋事刑事案件司法解釋若干問題的工作意見》,對該兜底條款進行了詳盡規定,將“因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劫、搶奪、敲詐勒索、尋釁滋事、聚眾斗毆、妨害公務等違法犯罪曾受過刑事處罰,又實施隨意毆打他人行為”致一人以上輕微傷的,列為上述“其他情節惡劣的情形”。按照該意見,犯故意殺人罪等暴力犯罪的前科可以被作為尋釁滋事罪的定罪標準使用。如筆者辦理的葉某某尋釁滋事案中,2013年葉某某曾因故意傷害罪受過有期徒刑的刑事處罰,2017年又在公眾場所隨意毆打他人致輕微傷,檢察院以葉某某構成尋釁滋事罪且系累犯提起公訴,但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前科已評價為由,不再對葉某某認定為累犯,對此檢法分歧較大。聚眾斗毆罪也有類似規定,2013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 《關于辦理聚眾斗毆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見》將“因故意殺人、傷害、搶劫、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等暴力違法犯罪曾受過刑事處罰,又聚眾斗毆的”,直接作為聚眾斗毆罪定罪標準。
二、最高人民法院認定累犯的觀點
前科成為入罪標準后,慎用累犯條款似乎逐漸成為司法實踐共識,而此時最高人民法院卻在盜竊罪累犯認定中給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意見。歷史上,最高人民法院在盜竊罪認定中對盜竊前科評價、累犯如何認定等問題上始終態度含糊。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規定,盜竊數額達到“數額較大”或者“數額巨大”的起點,如果是累犯,就可以分別認定為“其他嚴重情節”或者“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而提高刑格。該規定在當時引起極大爭議,反對意見認為,“將刑事前科升刑格處罰后還要按照刑法總則累犯再次加重處罰,違背了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歸根究底,司法解釋的合法性在于其解釋內容是否在法律授權范圍之內,最高法院的上述解釋沒有正當性,應當予以廢除”。[3]對于量刑升格后是否能繼續適用累犯問題,最高法院彼時并未表態,而其近年對前科作為定罪條件后累犯適用問題的態度,讓情況更加錯綜復雜。
《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1項規定,曾因盜竊受過刑事處罰,盜竊公私財物的,“數額較大”標準可以按照定罪數額的百分之五十確定。盜竊前科已經被作為定罪標準所使用后,量刑情節上是否還可以以該前科為依據,認定其累犯?否定說認為此為重復評價,不應再認定犯罪嫌疑人是累犯。肯定說認為,應遵循法教義學和立法本意,認定其累犯情節。最高人民法院持肯定說,“本條是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對盜竊‘數額較大’明確的另一個具體認定標準,故對根據本條已構成盜竊罪的行為人,如同時符合累犯成立條件的,依法從重處罰,并不存在雙重從重問題”。[4]顯然,寥寥數語反映出最高法對定罪標準與量刑情節作了區分,認為兩者并不重復,而且要求依照刑法總則中累犯規定依法從重處罰。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場及觀點是否正確、合理,筆者將在后文進行評論。2017年青浦區檢察院辦理的張某某盜竊案中,就嚴格依照上述司法觀點,認為被告人張某某2017年6月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刑滿釋放后不久即實施盜竊,雖然金額未達(上海市)1千元的“數額較大”標準,但根據有盜竊前科人員數額減半的解釋,認定其已構成盜竊罪的同時,認定其已構成累犯,法院也判決認可。但實踐中也有不同意見,如江西省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蔡某某盜竊案判決中就不認同最高人民法院觀點,直接認為“盜竊前科作為定罪條件后再作為量刑情節,有違禁止重復評價原則,不能再認定為累犯”[5]。
最高人民法院觀點也影響了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的累犯認定。如,2013年上海出臺的 《關于本市辦理部分刑事犯罪案件標準的意見》明確,曾因偽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公文行為被刑事處罰或受過二次以上行政處罰,或者二年內因上述行為受過行政處罰,再次非法實施該行為的,均定罪處罰。2017年,青浦區檢察院在辦理李某偽造身份證件案中,認定李某于2016年因犯偽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017年再次偽造身份證二張被抓獲(上海市規定三張以上定罪處罰),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在盜竊罪中的觀點,認定李某曾因犯偽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被刑事處罰,本次又偽造身份證件,其行為已構成偽造身份證件罪,同時符合累犯條件,從重處罰。法院此后也采納了公訴機關意見,判決已生效。
三、禁止重復評價與累犯關系
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盜竊罪累犯認定問題上的立場是正確的,但解釋的理由是狹隘的。典型的重復評價,包括定罪上的重復評價和量刑上的重復評價。早就有學者指出,“刑法上的禁止重復評價,是指在定罪、量刑時,禁止對同一犯罪構成事實予以兩次或者兩次以上的重復評價”。[6]“重復評價是對犯罪構成事實的重復評價,雖然表面上,禁止重復評價多數會出現在量刑情節上,但必須明確的是,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既是量刑原則,更是定罪原則”。[7]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包含的內容有:“1.禁止將己經被刑法評價的不利定罪情節再次作為定罪情節進行刑法上的評價;2.禁止將己經被刑法評價的不利定罪情節作為量刑情節進行刑法上的評價;3.禁止將己經被刑法評價的不利量刑情節再次作為量刑情節進行刑法上的評價。第一種情形就是定罪上的禁止重復評價,第二和第三種情形就量刑上的禁止重復評價。”[8]綜上,最高人民法院將前科看作數額較大(或情節惡劣)的“另一種具體定罪標準,不涉及到量刑情節,不存在雙重從重”,因此不妨礙累犯條款適用的理由,在法理上無法站得住腳。嚴格來說,前科一旦作為定罪認定后,量刑上的任何評價均是再評價的一種形式。故而,最高人民法院既然已經將前科評價為入罪的標準,入罪后再行進行累犯的量刑考量,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重復評價。
前文所述的累犯適用問題上的矛盾沖突,歸結到一點,就是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能否使得累犯條款失效?筆者認為,累犯條款不能因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而失效,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累犯不僅僅是一種定罪,也是量刑情節,不能顧此失彼。在司法實踐中,對有前科的人員,為了強化懲戒屢教不改者的社會效果,無論是再犯或者累犯均應當從重處罰。再犯是酌定從重情節,累犯是法定從重情節,后者的加重幅度要明顯高于前者。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而言,累犯是一種特殊的量刑情節。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更是擴大特殊累犯的主體范圍,增加了對判處死緩的累犯限制適用減刑及累犯不得適用緩刑、不得適用假釋等特殊規定。累犯不僅是定罪、量刑情節,更肩負了從重打擊危害性極大的犯罪及指導刑罰如何執行的任務,僅因為累犯是定罪、量刑情節而不適用,系將累犯等同于再犯,與立法原意不符。
第二,累犯是《刑法》總則第65條、第66條所明確定義的法律概念,嚴格說屬于立法解釋的權限范圍。刑法理論學界始終認為,刑法分則中大量出現以“數額較大”“情節嚴重”或者“情節惡劣”作為定罪標準的認定,不應包括行為人犯前表現、犯后態度以及是否為前科、累犯,不能因司法機關作出具體罪名定罪標準的解釋違反了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就以刑法總則累犯條款的選擇性失效來糾正,否則就侵犯了立法權。
第三,累犯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再評價機制,不能再次機械套用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如在毒品再犯問題上,是否適用累犯就引起過極大爭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曾認為既然認定了毒品再犯,就不再適用累犯。但對累犯不適用引起很多不利的處罰后果,如喪失了緩刑、假釋等刑罰執行限制等等。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轉變態度,明確對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從重處罰。另外,作為定罪中的犯罪構成要素,顯然在量刑中不能完全排斥重復評價。所有以行政處罰或前科作為定罪標準的罪名,都存在認定過程中使用了已評價的前科劣跡情節,而后又為禁止重復評價原則主動回避的問題,此觀點前后矛盾,邏輯也不能自洽。
第四,禁止重復評價原則適用應當統一、規范。刑法理論界一般認為,現代刑法意義上的累犯,更多地強調犯罪人的人身特征,累犯是一種人身危險性較大的特殊犯罪類型。首先,將前科劣跡作為定罪標準,主要是將行為人再犯時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納入評價內容,并非再次評價前行為。其次,將前科作為定罪的因素,處罰的是現行行為,而非前科行為和累犯的前行為,不會造成二次處罰,也與重復評價無關。最后,如果僅僅因“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而導致累犯條款從常見罪名中徹底失效了,這也意味著此類案件不再有累犯,實屬荒謬至極。
四、結語
因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理論研究上的薄弱及受最高人民法院觀點的影響,司法實務中累犯條款選擇性失效問題愈發嚴重,極大影響了刑事司法的權威性、公平性。司法機關為了社會穩定的需要,隨意在司法解釋中運用法律擬制,把前科劣跡作為定罪標準,造成司法權的肆意擴張,不利于對犯罪人權益的保障,進而導致刑罰權的濫用。筆者認為,考慮到累犯制度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重復評價機制,刑法總則中所建立的累犯制度除了法律的特殊規定外,應當適用于所有罪名。司法機關通過解釋的形式將前科劣跡納入“數額較大”“情節嚴重”“情節惡劣”等定罪標準,實則對過去已經被刑事法律評價的行為再次進行刑事評價,侵犯了立法權,不具有合法性、正當性,應當逐步取消并禁止。
注釋:
[1]吳婉璐:《行政處罰事實作為非法行醫定罪條件的正當性研究》,載《鐵道警察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
[2]李高寧:《禁止重復評價在刑行交叉案件中的適用》,載《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3]胡乾輝、明新春:《盜竊犯罪累犯不宜加重處罰》,載《人民司法》2006 年 4 月(上)。
[4]胡云騰、周加海、周海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15期。
[5]肖福林:《前科作為定罪條件后不能再作為量刑情節》,載《人民司法》2015年第2期。
[6]于志剛:《刑法總則的擴張解釋》,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頁。
[7]周光權:《論量刑上的禁止不利評價原則》,載《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1期。
[8]譚軼城:《論刑法評價中的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華東政法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