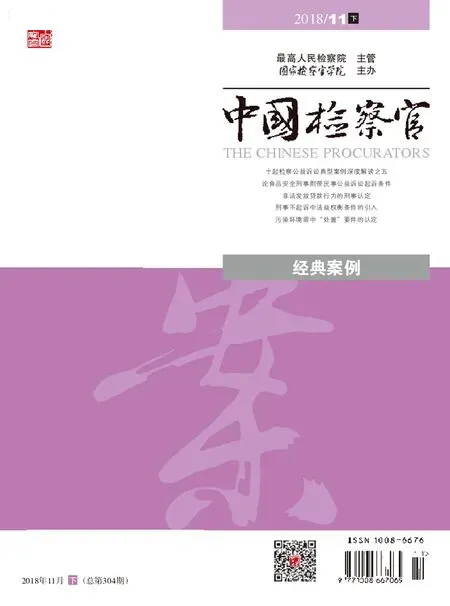存疑性侵案件質證中如何排除合理懷疑
文◎唐新宇
隨著庭審中“幽靈抗辯”的多發,公訴人在質證過程中必須充分運用靈活方法排除一切合理懷疑,使得審判者查明真相,旁聽者聽得清、看得懂,做到案結事了,避免辯護人“死磕”法庭及當事人常年上訪等。當辯方在提出“幽靈抗辯”,否認犯罪事實,質疑證據真實性的時候,多個相互印證的證據所產生的證明案件事實的說服力,遠遠大于“幽靈抗辯”對判定案件事實的干擾力。因而證據間相互印證原則是司法工作數十年傳統智慧的結晶,也是目前最為行之有效的質證方法。但是,證據相互印證原則也存在一些較明顯的弊端。相互印證對口供依賴較多,甚至實行“口供本位主義”,以被告人的口供為中心進行印證分析。很多“一對一”隱秘性犯罪,比如受賄、販賣毒品、強奸等案件的被告人都不供認犯罪事實,而且其他證實犯罪的證據數量也偏少。相互印證往往要求案件擁有較多數量的證據,這種特點在性侵案件中尤為突出。如果過分強調相互印證,有可能在庭審質證中無法說服審判方,使審判方以無法相互印證為由作出認定犯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判斷。
一、加強排除合理懷疑在庭審質證中的應用
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從此,“排除合理懷疑”被正式寫入我國刑事訴訟法。“‘證據確實、充分’具有較強的客觀性,但司法實踐中,這一標準是否達到,還是要通過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的主觀判斷,以達到主客觀相統一。只有對案件已經不存在合理的懷疑,形成內心確信,才能認定案件‘證據確實、充分’。這里使用‘排除合理懷疑’這一提法,并不是修改了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而是從主觀方面的角度進一步明確了‘證據確實、充分’的含義,便于辦案人員把握”。[1]由此可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排除合理懷疑”就是為了彌補“證據切實、充分”標準的不足,使得公訴人在庭審中面對“幽靈抗辯”時,得以在法庭質證過程中說服主審法官及人民陪審員,使其相信現有證據已經達到或者超過認定犯罪事實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二、把社會經驗法則作為排除合理懷疑的重要準則
社會法學認為,在具體司法實踐中要改變概念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觀念,將眼光更多地投向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更多的考量社會因素。一些“一對一”隱蔽型犯罪案件,較為普遍的情況是證據數量不多,符合相互印證原則所要求的證明程度的情形較少,因而社會經驗法則在辦理“一對一”隱秘型案件中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比如性侵案件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各執一詞,有時因被害人力量不足及缺乏經驗等原因,現場遺留物證極少,被告人身體沒有抓痕等客觀證據,此時其他證據的證明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公訴人往往要從為數不多的證人證言、物證、鑒定意見等證據來提煉犯罪事實,當庭舉證質證。這要求公訴人不應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必須要有眾多的口供相互印證才算大功告成,而應該按照一個正常理智的人所具有的理性和良知來審視判斷證據的證明力。
社會經驗法則首先適合用于“一對一”證據證明力的判斷。“證明力評價與認定需要遵循認識的規律,遵守經驗法則和邏輯法則,受到合理的心證制約。”[2]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各執一詞的時候,采用哪一方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認定法律事實,社會經驗法則就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某成年人多次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50多歲的犯罪嫌疑人前五次供述自己不認識被害人,未和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第六次民警告知其DNA鑒定結果后開始供述被害人每次均自愿和自己發生性關系,自己撫摸被害人的時候被害人笑瞇瞇的,發生性關系時被害人未反抗,事后也未報警。而年僅15周歲的被害人陳述內容是首次被性侵時犯罪嫌疑人按住自己雙手,結束后自己下身出血,被威脅不許說出去,否則就找自己家人。被害人妹妹證實后來被害人一直在躲避犯罪嫌疑人。該案雖然是一對一證據,但是從證明力比較上來看,犯罪嫌疑人供述明顯低于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前五次不供述,面對DNA鑒定意見的時候被迫供述,逃避心理明顯。考慮到雙方年齡的巨大差異,事先也無感情基礎及金錢基礎,犯罪嫌疑人供述發生性關系的時候“被害人笑瞇瞇”的,明顯不符合客觀實際。相反,被害人作為年僅15周歲的未成年人,其陳述首次發生性關系時出血等細節屬于非親身經歷不可能完整描述的內容,案發后被恐嚇而不敢立即報警的陳述更加符合農村留守女孩的常理。其后為防止再次被性侵害而躲避犯罪嫌疑人的陳述與年僅13周歲妹妹的證言相印證。而犯罪嫌疑人辯解被害人自愿發生性關系無任何證據印證。
具體辦案中,公訴人對案件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把握有兩個重要原理:一個是“基本原理”,包括并不限于法律基本原理;另一個是“社會生活經驗”,亦即平常所謂的社會“常理、常情、常識”。以性侵案為例,性侵案件往往涉及復雜的人際關系、豐富的社會知識和多元化的心理狀態,更應當結合具體案情分析其中蘊涵的社會因素,這需要辦案人員本身具有較為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和社會知識,敏銳判斷案件中違背社會生活常規常理的問題,從而得出有益于查清犯罪事實的結論,并結合其他證據作出總體判斷。有的性侵案中,被告人當庭辯解自己在公共場所聽陌生人說過被害人精神正常或者被害人年滿14周歲,自己和被害人發生性關系只是為了談戀愛。這需要通過詢問、觀察被害人,向被害人鄰居及案發地點附近證人了解被害人案發前的言行舉止有何特殊之處等,運用社會知識在庭審質證中讓審判者判斷被告人在和被害人發生性行為時是否知道其為精神病患者或者年滿14周歲。有的性侵案件中,被告人當庭辯解自己沒有恐嚇被害人,被害人系自愿和自己發生性關系,但是被害人案發時來了月經,這在庭審質證中可以說服審判者相信被告人違反被害人意志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有的被告人辯解自己某年某月曾經得罪過某個很有勢力的人(只有綽號,姓名不詳),被害人報案系受人指示誣陷自己。但是通過社會調查,被害人平時作風正派,和被告人素昧平生,庭審質證中可以說服法官及人民陪審員排除被害人虛假報案和誣告陷害的可能。對于判斷被害人是否半推半就,被告人是否是求奸行為等影響定罪的關鍵事實,都需要公訴人具備一定的社會經驗和社會常識,從而在庭審質證中排除合理懷疑,讓審判方形成內心確信。如筆者在2014年起訴的某強奸案,被告人當庭辯稱案發時自己是經過陌生人撮合的嫖娼行為,但是物證證實的被害人衣服等損壞部位和被害人陳述的強奸情況吻合;鑒定意見證實的被害人、被害人頸部、肘部的身體損傷特征與程度和被害人陳述的情節相符,被告人朱某對此則無合理解釋,在庭審質證階段保持沉默。主審法官通過庭審質證后形成內心確信,判定強奸事實成立。
運用社會經驗法則,還可以在庭審質證中解釋證據間存在的合理差異。所謂合理差異,就是因為各個人的感知、表述、記憶以及其他因素有差異,導致證據間細枝末節問題并不吻合或者陳述內容稍有出入。比如證人甲證實看到作案現場實施犯罪的被告人身高1.65米,證人乙證明看到同一案件作案現場實施犯罪的被告人身高為1.70米,被告人實際身高是1.68米,那么甲乙的證言均可采信。因為根據生活經驗判斷,證人目測被告人身高不可能精確到厘米。
三、靈活運用社會經驗法則開展舉證質證
以庭審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使得一切犯罪調查必須在庭審中進行,給控辯雙方在庭審質證中有了充分的自由發揮空間。對“幽靈抗辯”,公訴人在質證中可以積極進攻,主動訊問,充分披露“幽靈抗辯”的矛盾之處。具體訊問方式可以靈活多樣,可以和舉證、質證有機結合,可穿插(使得辯方“幽靈抗辯”不能自圓其說)、可重復 (使得辯方回答同一性質的問題前后矛盾)、可埋伏(使得審判方認為辯方提出的“幽靈辯解”超出常理,實際生活中不可能出現),甚至可以在質證階段對“幽靈抗辯”的辯護觀點予以堵截(堅定不移地指出其撒謊)。庭審是最好的釋法說理的場所,公訴人在質證階段如果以社會經驗法則為依托,舉證、質證方法靈活有效,不僅有利于審判方在庭審中查明起訴書認定的事實證據,而且能夠讓被告人、辯護人及旁聽群眾聽得清、看得懂,從而保證庭審結束后案結事了,避免出現辯護人“死磕”法庭及當事人上訪等后遺癥。
筆者在2014年起訴的朱某某強奸案,朱某某審查起訴階段已經翻供,開庭時繼續否認犯罪,并且辯解自己在偵查階段的有罪供述系刑訊逼供所迫。公訴人出示一份偵查人員在看守所訊問被告人的配有視頻光盤的有罪供述筆錄時,被告人朱某某及其辯護律師辯解雖然視頻光盤中被告人神情自然地自主供述犯罪事實,但是在此次訊問初期被告人遭到偵查人員的言語威脅,被告人被逼迫向偵查人員承諾作有罪供述后偵查人員才開啟錄像機開始錄像。辯護律師要求公訴人調取此次訊問的看守所完整的監控視頻以查清真相。因為2014年筆者所在市的看守所監控錄像15天后存儲空間已滿,監控數據會自動覆蓋舊數據,公訴人出示的有訊問視頻的筆錄中實際訊問時間距離開庭時間已經過去2個多月。控辯審三方都知道讓公訴人調取看守所當時的訊問室監控視頻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
庭審質證時筆者依托社會經驗法則,通過訊問、舉證、質證的有機組合,使得合議庭當庭查清真相。首先筆者訊問被告人,要求被告人詳細供述偵查人員開啟錄像機前如何言語威脅、誘供的過程,被告人予以詳細解答。然后公訴人訊問被告人,此次偵查人員訊問一共持續多長時間?被告人回答大概兩個多小時。此時筆者舉證并質證,訊問錄像光盤顯示訊問時間持續30分鐘,本次訊問筆錄中反映時間跨度為35分鐘(有訊問人員及被告人簽字),提押證反映提押被告人及押回被告人時間跨度為42分鐘(有訊問人員、看守所人員簽字及偵查機關、看守所蓋章)。去除訊問前開啟錄像機器及押解被告人來回的時間,偵查人員并無實施言語威脅、誘供的時間可能。筆者當庭堵截,指出被告人庭審中提出的“幽靈抗辯”系撒謊。此時辯護律師繼續辯解訊問筆錄時間、提押證時間被公訴方篡改。筆者再次出示審查起訴階段訊問被告人筆錄 (含聽取被告人意見內容)及聽取辯護人意見的書面材料(系辯護律師當初提供,有辯護律師本人簽字及簽注日期),并提出質證意見,指出當庭舉證、質證的書證及被告人供述系原始證據,已經在案件提起公訴之時隨案移送法院。因為在之前的審查起訴階段,被告人及辯護律師從未向公訴人提出此類辯解,所以公訴人不可能提前預知辯方具體的“幽靈抗辯”意見,從而提前有針對性的篡改證據。最終,合議庭的審判員及人民陪審員采納筆者的質證意見,判決被告人朱某某強奸犯罪事實成立。
當公訴人應用社會經驗法則,靈活機動地進行舉證、質證時,作為辯方,當然可以予以反駁并提供證據,但是,試圖僅僅通過提出“幽靈抗辯”逃避法律制裁顯然不可能。如果辯方在庭審中提出“幽靈辯護”質證失敗后,在法庭上“死磕”或者保持沉默,更容易使審判方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內心確信,從而作出有罪判決。
注釋:
[1]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頁。
[2]李明:《證據證明力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