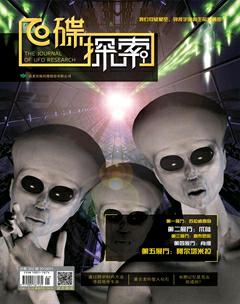外星生命可能是怎樣的
張唯誠
識別地球之外的生命并不那么容易,如果那個地方的生命組成不是我們熟悉的材料就會更加困難。在1967年的科幻電視劇《星際迷航》中,柯克船長和他的船員調查了嘉納斯六號星上的神秘謀殺者。那是一個名叫“奧爾塔”的巖石怪物,被界定為有生命的外星生物,與地球上的碳基生物很不相同。
確立生命的標準
在地球之外尋找生命的科學家被稱為天體生物學家。對他們來說,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給生命確立一個基本的定義。這樣,當人們遇到外星生物時,他們就能夠毫不猶豫地向世人宣布,“它們是生物體”。
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克里斯多夫·阿達米就是這樣一位界定生命定義的科學家。阿達米也有他的硅基生物,他親眼看著它演化和發展,但這個生物不是真實的,而是一個計算機模擬的東西。阿達米說:“識別生命有時很容易。如果你發現有什么東西在你身邊晃來晃去,你就能很容易地判斷它是不是生命。”但另一種可能是,人類遇到的第一批外星生命并不是“小綠人”,而是擁有某種顏色或者根本就沒有顏色的微生物。
這樣看來,科學家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他們要怎樣識別外星生物。如果那些生物是我們不熟悉的,那就真的很困難了。于是人們提出了一些區分生物與非生物的基本標準。許多人堅持認為,任何生命,包括外星生命,都必然具備某些共有的特性,例如活躍的新陳代謝、繁殖和進化等。另一些人則主張,生命必須擁有足夠大的細胞來容納由蛋白質制造的核糖體。
然而,這些定義有可能過于嚴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卡羅爾·克萊蘭德說,為生命制定一些限定的條款有可能限制科學家的視野,從而使他們忽視宇宙中生命的多樣性。例如病毒。有科學家認為它們不應該被當作生命,因為病毒是依賴宿主細胞進行繁殖的,但阿達米認為,病毒是生命應該是“確定無疑的”。阿達米說:“病毒不攜帶它們生存所需的所有東西,但我們也是這樣。”他認為,病毒能將遺傳信息從這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強調說,生命是一種能自我復制的信息。
克萊蘭德認為,進化不應該成為識別生命的標準,因為人們可能永遠也不會有足夠的時間來判斷某個個體是否在進化。除此之外,即使是對細胞的大小進行限制也有可能把一些微生物排除在生命之外。美國佛羅里達州阿拉楚阿應用分子進化基金會的天體生物學家史蒂芬·本納說,一個因為太小而不包含核糖體的細胞是有可能以另一種方式運作的。他推測,這種細胞有可能使用被稱為RNA的遺傳物質進行生化反應,而不是依靠蛋白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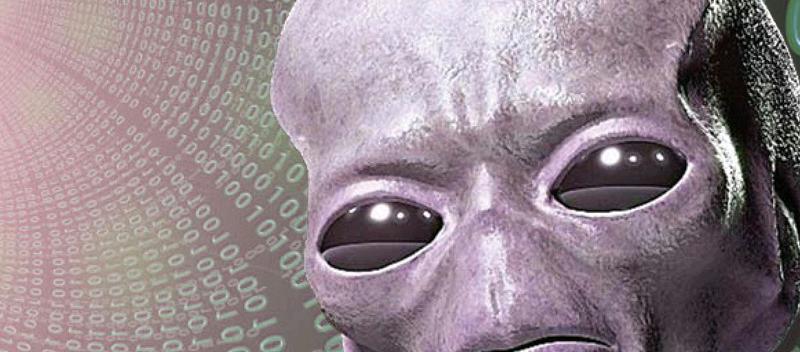
這樣看來,對生命來說,至少細胞是必要的,因為它們得將一個有機體與另一個有機體分隔開來。但阿達米說,黏土層也可以做到這一點。克萊蘭德甚至認為,生命可以作為化學反應的一部分而存在,這種化學反應根本不需要任何分隔。這種觀點雖然只是猜想,但如果外星生命真的出現,它就有可能成為對認識非同尋常的生命形式大有裨益的想法。
尋找“生物標記”
近年來,人們在太陽系外發現了1000多顆行星。隨著這些行星的發現,找到外星生命的可能性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了。然而,即使是最強大的望遠鏡也無法看清遙遠的生命,尤其是當它們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顯露真形的時候。如果科學家能夠直接觸摸遙遠的星球,找到這種微小生命的機會就會大很多。這意味著要發現外星生命,目前最現實的途徑還是在太陽系內尋找。羅伯特· 海森是華盛頓卡內基科學研究所的一位礦物科學家,他認為,要在太陽系內尋找生命,我們需要一個可以在外星球上分析化學物質的探測器。現在,這樣的探測器正在火星上采集樣本,“卡西尼”號也在寒冷的土衛二上探測了間歇泉。也許,這些機器人探索者會在某一天傳回生命的跡象,但那可能只是很細微的跡象,科學家稱之為“生物標記”。
行星地質學家凱西·托馬斯·科普塔曾是美國航空航天局約翰遜航天中心一個研究小組的成員,當時這個研究小組由凱普塔已故的同事大衛·麥凱領導。1996年,這個研究小組聲稱,他們在一塊火星隕石中看到了疑似生物標記的東西。這塊隕石名為ALH84001,是1984年在南極洲的艾倫山冰原(Allan Hills ice field)上找到的。他們發現,那嵌在隕石中的碳酸鹽小球看起來有點像地球上的微生物。科普塔還發現了微小的磁鐵礦晶體與小球的重疊。這些晶體看起來和地球上的某些細菌制造的晶體很相似。他們最后得出結論說,這塊隕石是一件火星生物的化石。
然而,其他科學家并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批評人士說,那些小球和晶體也有可能通過其他過程形成,并非一定是生命的結果。火星生物化石的觀點沒有得到科學界的認同。
但是,尋找外星生命并不一定非要放眼遙遠的星球,我們在地球上就可以做同樣的事情。克萊蘭德提到了一種名為“沙漠清漆”(desert varnish)的東西。它們是一些巖石向陽面在極端干燥的氣候下產生的暗斑。一些科學家認為,某些細菌或真菌可能是這些暗斑的始作俑者。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一些微生物可以從這些巖石中吸取能量,并用這些能量制造堅硬的外殼。這種生物將鐵和錳“粘”在黏土和硅酸鹽的顆粒上,從而產生了“清漆”。奇怪的是,一些科學家試圖在實驗室里使用真菌和細菌重現這種“清漆”,但他們都失敗了。
在野生環境中,這種“清漆”用了幾千年才最終形成。有人認為,如果微生物在此過程中創造了某種東西,這樣的速度就太慢了。但克萊蘭德反問道:“我們怎么確定它就太慢呢?我們慣于假設地球上的生命是以某種速度生長和繁衍的,但有些不活躍的生物可能會生長得非常緩慢。”
為了找到生命并正確地進行分類,科學家將目標轉移到一些非同尋常的事物上。海森就做著這樣的工作,他利用礦物方面的信息尋找生命。在自然界里,礦物的分布并不均勻。他說,地球上有4933種公認的礦物, 而他們已經對4831種礦物的位置進行了確認,其中22%只存在于一個地區,接近12%的礦物分布在兩個地區。

這種偏斜的分布是生命造成的,生命利用當地的資源,把它們變成了新的礦物。以海森礦為例(是的,這個礦物是以海森的名字命名的),這種基于磷酸鹽的礦物就只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莫諾湖(Mono Lake)被發現。生活在那里的微生物是它們僅有的來源。海森的團隊推測,其他物種可能也創造了類似的罕見礦物。
這就是說,在其他行星或衛星上發現類似的礦物分布可能也表明生命存在于那里,或者曾經存在過。鑒于此,海森已經向美國航空航天局提交了一項關于火星探測器如何利用礦物線索識別生命跡象的建議。
對遙遠外星生命的猜想
火星曾經是濕潤的,它現在還可能有少量的液態水,這表明它曾經有可能承載過生命。本納甚至認為,正是火星把生命帶到了地球。當然,這個想法能否站得住腳,還要看人們是否能在火星上找到生命。不過本納似乎并不擔心,他說:“如果人們在火星上找不到生命,我反而會感到驚訝。”另一位天體生物學家也對在火星上找到生命充滿信心,他就是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德克·舒爾茨·馬庫奇。他相信,現在的太空任務已能很容易地把宇航員送上火星,這樣,人們就能證明此前的一些猜想了。馬庫奇開玩笑說:“如果有人用顯微鏡看到了微生物,看到它就在那里搖擺和舞動,那人們就不得不相信事實了。”
但在更加遙遠和陌生的地方發現生命就可能非常困難了。目前,這樣的地方主要是指木星和土星的衛星。科學家已經把目標鎖定在木衛二和土衛二上,普遍認為在它們冰冷的外殼之下都有一個液態的海洋,而液態水正是人們認為的、支持生命化學反應的必要條件。
但馬庫奇指出,在構建可承載生命的復雜分子方面,水是一種糟糕的溶劑。他認為,外星生命更有可能在土星最大的衛星——土衛六上被找到,那些生命很有可能存在于土衛六碳氫湖深處的熱點地區。他說:“在目前,大自然究竟擅長用什么方法制造生命,我們并不清楚。”
但科學家知道,在土衛六上,最大的挑戰是極寒。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化學工程師波萊特·克蘭西介紹說,這顆衛星極其寒冷,它上面的甲烷是一種黏稠的、幾乎凍結的液體,水則同石頭一般堅硬。因此他認為,具有地球化學性質的生物體在土衛六上不會有機會存在,因為在那樣的環境下,地球生物體的細胞膜已經無法正常工作了。
克蘭西及其同事模擬了土衛六上的環境后發現,某些短尾分子會自發地形成穩定的氣泡,而那種氣泡就具有類似細胞膜的功能。有科學家推測,土衛六上的生命有可能存在于一種含氮的結構中。由于缺乏陽光和熱量,土衛六上的化學反應可能非常緩慢,生命體的壽命非常長,甚至長達數百萬年,它們很可能每千年才繁殖一次,甚至呼吸一次!
克蘭西預測,既然有這么多可能,在太陽系的有些行星和衛星上找到生命就是有可能的了。不少研究人員樂觀地認為,外星生命是可以找到的。將來,天體生物學家很有可能與它們面對面,并說出它們是什么。
延伸閱讀
2017年年底,美國航空航天局傳出消息說,他們計劃展開一連串的星際任務,尋找太陽系外的生命蹤跡。
據悉,美國航空航天局計劃于2069年,也就是人類首次登月100周年時,發射一艘機器人宇宙飛船,探索鄰近的半人馬座α星系。
半人馬座α星系位于南天的半人馬座,是一個三合星系統,也是距離太陽最近的恒星系統,因此又被稱為比鄰星。在天文學家眼中,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半人馬座α星系的類地小行星可以支持外星生命的生存。
不過,要抵達半人馬座α星系,宇宙飛船的速度必須達到光速的10%,即每秒3000萬米。然而,即便我們的技術跨過了這道門檻,這趟旅程仍需耗費44年,意味著這艘宇宙飛船要到2113年才能抵達半人馬座α星系。
當然,美國航空航天局也在探討不同的探測方式,包括由激光、核反應或正反物質碰撞驅動的微小探測器。理論上,這些探測器的速度可達1/4 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