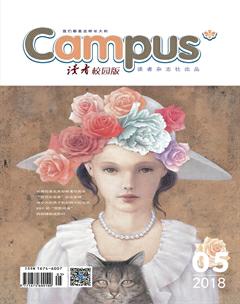有你一封信,來自文森特
劉睿
梵高生前不曾闊綽,卻是郵局的大客戶。除了在電影中穿針引線的那最后一封信,他還有900多封書信存世,它們大多寄給弟弟提奧,也寄給了永恒的未來。
星空沒有謎
做粉絲有不同的境界,有人天天去機場求合影,也有人用7年的時間為至愛的偶像拍攝了一部“世間最美的電影”。
2017年歲末,電影《至愛梵高·星空之謎》樹立了藝術界粉絲的新高度。
導演多洛塔·科別拉從15歲起,就是梵高的鐵桿粉絲,梵高的畫作與信件曾幫助求學時期的她對抗抑郁癥的折磨,她立志要以梵高的作品為素材,拍攝一部梵高的傳記電影。她“眾籌”了15個國家的125位畫師,手工繪制了6.5萬幀油畫,繪畫加制作,用了足足7年時間。
當速度與激情已成為電影工業的主流,7年的制作周期堪稱漫長,而拍攝一部傳記的想法在其間轉變為講述梵高一生中最后的一段時光。
故事由那個早已被世人熟識的藍色旋渦開始,繼而畫卷展開,藍色的夜空與黃色的星斗在寂靜中暗戰,無邊的焦慮與不安籠罩在村莊上空,也流動到了畫面之外,而旋渦中心的人,就是這幅畫的作者—文森特·梵高。
故事很簡單。1890年盛夏,籍籍無名的年輕畫家梵高在寄居的法國小鎮奧維爾離奇身亡,這在當時的藝術界并沒有掀起波瀾。是的,這座位于巴黎以北32千米外的小鎮,因為那明朗的天空、花木稀疏的鄉村街道還有仿佛和時空一樣無垠的金色麥田而成為梵高最后的至愛,但他的到來打破了它固有的寧靜。
直到梵高去世1年后,他所激起的回響仍未平息。阿爾勒的郵差、與梵高私交甚篤的魯蘭老爹,從梵高的前房東手中得到一封信,是梵高生前想要寄給弟弟提奧卻沒有寄出的信。由于無法郵寄,他委托兒子阿爾芒完成這個任務,把梵高的最后一封信送到收信人提奧那里。但是提奧已經去世,為尋找提奧遺孀的地址,阿爾芒來到梵高最后居住的奧維爾小鎮。他和鎮上與梵高接觸過的居民聊天,試圖還原梵高生前最后6個星期的生活。
故事又撲朔迷離起來。阿爾芒不曾想到,一封無法寄出的信成了“尋找梵高”的線索,關于他,鎮上每個看似漠然的人都有話要說。
顏料商唐吉老爹認為,梵高是一位天分很高的畫家,完全不可能自殺。
加歇醫生的女管家認為,梵高是個邋里邋遢的瘋子,一無是處。
旅館老板的女兒卻坦言,梵高中槍后,曾經急于醫治,完全不像自殺者所為。
加歇醫生、農民、船夫,每一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提供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于是這座原本簡單到乏味的小鎮上竟然上演了一場關于梵高的“羅生門”。阿爾芒的身份漸漸從郵差變成了偵探,卻無法從漫天飛舞的信息碎片中抓住一個真相,因為所有的故事都只是口說無憑,沒有一個人能提供確鑿的證據。
在此過程中,阿爾芒對梵高的看法也在改變。他原本認為梵高不但一生碌碌無為,同時也是家人的累贅,后來漸漸開始了解其人其畫,甚至為了梵高陷入紛爭,最終也同樣面臨被逐出小鎮的結局。
與那些影影綽綽的推測與猜想相比,梵高的作品是明確無疑的存在。電影中所有的人物確實都出自梵高生前的畫作,但這部電影并不只是“畫”出來的。他們先找出了與梵高畫中人物“撞臉”的真人演員,演員在綠幕前拍攝了12天,之后轉換成CG動畫,然后再融入梵高畫筆下奧維爾的場景一幀一幀進行描繪。
這樣一個極其麻煩的拍攝過程,串聯起了梵高畫筆下的村莊與人物,讓他們都不可思議地“動”了起來,為電影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創作可能,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視覺享受。
這份辛勞,是對梵高生前勤奮創作最好的致敬:
他從未受過科班訓練,27歲才開始涉足畫壇,直到37歲去世,短短10年間,卻留下了864幅油畫、1037張素描、150幅水彩畫,雖然生前只有1幅賣出。
他猝然離去,沒有留下只言片語,但他畫中的人物與景象,卻足夠讓后人串聯起一部扣人心弦的電影。麥田、烏鴉、星空、平原、街道與咖啡館、少女和醫生……他為自己所有的見與聞、孤獨與歡暢,都留下了最真實的憑據。
文森特的信
電影以奧維爾小鎮為藍本,以梵高的“星空之謎”為線索,表現了西方社會中難以跨越的階層鴻溝。
刻板的女管家與沖動魯莽的梵高注定“水火不容”,平民聚集的小旅館被她稱為“老鼠洞”;而在旅館老板女兒的眼中,住在花園別墅里的人也未必有多么高尚,不過是故作姿態。梵高將富家子弟雷內視為朋友,而后者只將他當作戲弄的對象。
但比階層更難跨越的,是天才與凡人的距離。聽從父命拿到行醫執照的加歇醫生享有成功的物質和社會生活,但在苦苦追求的繪畫領域,他又成了十足的失意者,尤其在梵高光芒的映襯下。如果愿意,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還有可能通過努力去改善,而藝術世界里這一層若隱若現的隔膜似乎永遠也無法消除。梵高離世后,加歇醫生用自己的后半生去臨摹梵高的所有畫作,一次次地去感知那種他所可望而不可即的才華,個中滋味,該有多酸楚。
于是當銀幕上的故事曲終人散時,我們才發現,它真正想要破解的謎題是:一如文森特·梵高的藝術天才,怎樣才能在復雜多變的世界里過好一生?
加歇醫生的女兒瑪格麗特對阿爾芒說:“為什么你總是關心他怎么死,卻不關心他怎么活?”
一語道破天機。
“夜空布滿了星星,調色板上藍灰交映。”電影在一曲《文森特》中結束,這首紐約男孩唐·麥克萊恩于1970年寫給孤獨的大男孩梵高的民謠,以梵高的代表作《星空》為起點,吟唱了他的生前身后所有的絢爛與憂傷,聲音清澈,娓娓道來,雖然遠隔萬水千山,卻仿佛明朗少年就在身邊彈唱,他即興演繹著一個老朋友的故事,年華似水,流淌在質樸的旋律中,曾經的歡喜傷悲,一如塵封的信箱被打開,一切清晰如昨。
那個少年的眼睛好像梵高的一樣,總是看見世界明亮,萬物可親。
他也看見畫家在其間,喜歡花,喜歡草,喜歡阿爾勒的路和橋、奧維爾的教堂,甚至瘋人院的院子,關心農事,感受它們的美好。
他的歌聲最終將人帶往梵高那張藍色的自畫像,畫中人難得地穿著齊整,頭發梳齊,卻因而顯得更怪異,表情反倒比那些割耳后或頭發憤怒的自畫像里更不安—像是小孩努力想跟老師證明自己是個“好小孩”又不知老師有沒有看見、有沒有收效,然后想開了,啊,這個世界對于他來說總是那么難懂。
梵高的畫在有生之年僅賣出1幅,而唐·麥克萊恩的音樂專輯在首次出版時無人問津。有趣的是,梵高的《星空》現藏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內,每天開館與結束時,藝術館都會播放唐·麥克萊恩的《文森特》。
所以該館的每一天,都在這樣一句感慨中結束:“這個世界不適合你這么美的人。”這或許是在一遍遍地提示:天才的命運不該如此。而電影《至愛梵高·星空之謎》以梵高生前的書信落款“至愛你的文森特”結束,讓人心中五味雜陳—一個如此熱愛生命的人,卻不曾被生活善待,難道藝術的天賦便意味著人生的孤獨?
梵高生前不曾闊綽,卻是郵局的大客戶。除了在電影中穿針引線的那最后一封信,他還有900多封書信存世,它們大多寄給弟弟提奧,也寄給了永恒的未來。
文森特的信,你可曾收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