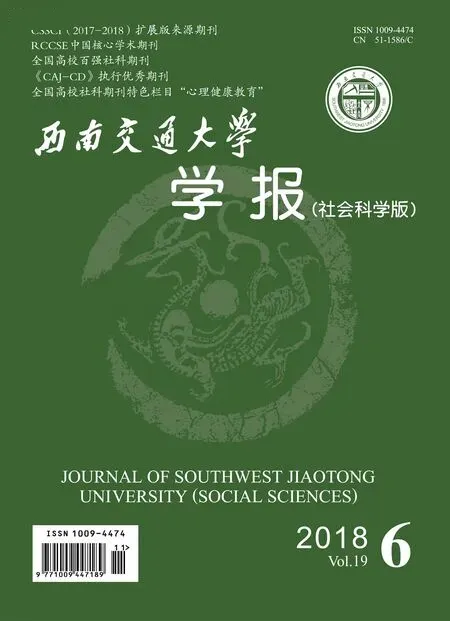論《尤利西斯》漢譯主體間性的倫理規范
(1.淮陰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 江蘇 淮安 223001; 2.常州大學 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研究所, 江蘇 常州 213164)
國內目前對《尤利西斯》譯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漢譯的語言技巧及表現。有學者著重探討《尤利西斯》中意識流語言變異現象,如詞匯變異、語法變異、語義變異和語域變異等以及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將這些語言變異現象再現。有的學者則通過比較分析多個譯本,以功能翻譯和語料庫翻譯為理論基礎探討譯者語言處理的差異,并聚焦于《尤利西斯》漢譯的“陌生化”或“前景化”語言或結構和敘述模式再現的研究。(2)從語言學角度研究《尤利西斯》的漢譯。不少學者借助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分析譯者如何實現譯作與原作的語碼轉換。(3)譯者主體性研究。此類研究側重于研究蕭乾、文潔若譯本的創造性叛逆,圍繞突破原文藩籬,以目標語讀者閱讀期待為中心,分析如何實現語義連貫、形遠意達、注釋之便、翻譯選擇和翻譯思想等“叛逆”現象。(4)對《尤利西斯》兩個漢譯本的評價。有學者從總體上考察蕭乾、文潔若譯本和金隄譯本的得失,尋找導致巨大差異的原因,重點圍繞兩譯本的譯者、譯風、注釋等進行比較研究。(5)從文化視角研究《尤利西斯》的漢譯。此類研究主要以勒菲弗爾的操縱論為理論基礎,圍繞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對《尤利西斯》進行文化解讀。
翻譯活動是主體與主體、主體與客體、客體與客體之間多元互動的過程,即“間性”互動過程;而翻譯倫理學研究則是圍繞文本間性、文化間性與主體間性三維層面的道德規范和倫理價值進行理論體系的研究。筆者認為只有“譯者中心”、“原文中心”和“譯文中心”形成“共生共處”,才能使“原文—譯者—譯文”三元生態關系得到均衡和諧發展〔1〕,這是間性倫理規范的重要原則。翻譯過程是具有典型的間性特質的活動,包括文本間性、文化間性和主體間性等,其中主體間性是間性活動中最為活躍、最為顯性的行為,因此討論主體間的翻譯倫理具有很好的理論意義,而《尤利西斯》漢譯本主體行為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一、翻譯主體間性的相關概念
主體間性是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英文是“intersubjectivity”,主要指主體之間某種源自不同心靈的共同特征而形成互動與交流的現象。從本質上來說,主體間性就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主體間直接的互動與影響,是人的主體性通過相互承認、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而實現在主體間的延伸。主體間性概念的提出消解了一元中心主體論,實現了主體多元平衡、共生的多元性。傳統的語際闡釋一直是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主要特征是強調一個“中心”,忽視其他“中心”,割裂了作者、文本、闡釋者(包括譯者、讀者等)和贊助人等之間的內在聯系。孫瑜博士認為,主體間性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涉及到人際關系和價值觀的共性問題〔2〕。哈貝馬斯的交際理論把間性理論推到一個高度,認為主體間性是主體間的互動、互融和互相理解的交際關系,能實現不同主體之間的共識與統一。主體間性的哲學倫理思想就是要倡導主體之間的相互承認與彼此尊重,要進行和諧、平等、理性的交流與互動。
翻譯活動是主體間性發揮的重要表現形式,因為翻譯活動本質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如果翻譯沒有多元主體的參與,譯者也沒有存在的意義。因此,翻譯得以完成離不開譯者的主體性的實現。同樣,譯者作為主體地位的核心,還要和他周圍的各種“他者”要素產生交集、關聯和互動,因此翻譯主體間性必然是翻譯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屬于現代哲學,特別是當代哲學的理論研究范疇,也被稱為“交互主體性”、“主體際性”和“共主體性”。根據《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詞典》,“主體間的東西主要與純粹主體性的東西相對照,它意味著某種源自不同心靈之共同特征而非對象自身本質的客觀性。心靈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隱含著不同心靈或主體之間的互動作用和傳播溝通,這便是它們的主體間性。”〔3〕這是一種從認知上對主體間性狹義的闡釋和理解。從廣義上看,主體間性應是“人作為主體在對象化的活動方式中與他者的相關性和關聯性”〔4〕。由于人的本質屬性是多維、異質性的,因此主體間性也必然具有多維性和異質性,具體表現形態是主體與他者之間的關聯性和互動性或為心靈上的,或為物質上的。主體間性的相同性和異質性必然導致主體間會產生親和力和排他力。翻譯活動本質上是間性活動,其中主體間性活動是最為活躍的能動關系。許鈞教授認為:“翻譯活動,特別是文學翻譯活動中所涉及的作者、譯者與讀者三個主體,不是孤立的主體,而是以對方存在為前提的一種自在的共體”〔5〕。他借助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闡釋學認為作者、譯者和讀者構成一個開放的共體,翻譯結果會受到這一共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最佳的結果就是和諧共生。陳大亮對翻譯目的論進行了反思,認為目的論的重點是“放在譯前的跨文化人際交往上,重視對發起人、譯者、委托人、譯文使用者、譯文接收者等目的語中的行動參與者和環境條件等翻譯外部因素的分析”〔6〕,雖然他沒有明確提出這些跨文化人際交往中的各類人是翻譯主體,但他們也是翻譯活動中主體間性的共體。劉衛東根據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指出,翻譯主體在翻譯活動中要以“某種形式承認和遵循某些規范”,因為在翻譯活動中主體間性不是以單一直線的方式展開的,而是以復雜的多維方式呈現的,具有群體交互特征〔7〕。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翻譯的主體間性是指以譯者為共體核心的主體和其他主體,包括贊助人、作者、讀者、文本主體等之間產生的關聯性和互動性,他們之間具有同質性和異質性,通過各自的視域形成某種默契或在異質中尋求某種妥協,構建一種“間性主體”。翻譯主體將遵循什么樣的主體間性倫理規范?譯者是繼續作為原作的“奴仆”還是對原作肆意“宰割”?贊助人系統是否要根據自己的需要,對譯者施加壓力,讓譯者朝著自己期待的視域發展?讀者是否為了自己的審美需求或閱讀期待對譯作的呈現態勢施加影響?這些是翻譯主體間性倫理規范應該思考的主要問題。
二、譯者與作者的主體間性
翻譯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原著的闡釋,需要譯者和原著作者相互“對話”才能實現。譯著其實是原著的一種“復調”,充滿著原著作者和譯者的雙重聲音〔8〕。譯者對原作者和原著的推崇,就會加大譯者和原作者之間的某種共鳴,譯者在翻譯時則更會對原著充滿敬畏,會最大程度地忠實原文。反之,譯者與原作者之間缺乏共鳴,譯者就會對譯作采取“宰割”的態度,會根據自己對原著的理解肆意翻譯,甚至會扭曲原作的意思,這時譯者的創造性、叛逆性就表現得特別強烈。傳統的譯學倫理觀認為原作者處于主宰地位,譯者必須盡可能靠近原作者,在充分揣摩原作者的意圖后忠實地再現原作,譯者儼然成為原作者和原作的“奴仆”。現代的翻譯倫理觀則把原作者和譯者“隱身”到后臺,文本成為翻譯的主體,強調翻譯語言的“對等”、“等效”或“等值”,譯者由“奴仆”變為“幕后者”,即俗稱的“譯者隱形”。后現代解構主義思潮的翻譯倫理觀強調譯者的主宰地位,認為譯者可以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闡釋力,原作者的意圖被邊緣化,文本成為譯者操縱的對象,譯者變成了“操縱者”和“改寫者”。不難看出,上面的三種譯者與原作者主體間性的翻譯倫理都是一元的,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呈現,主體間性的交流缺乏平等和相互認同。
事實上,許多譯者在翻譯時很少有機會和原作者進行交流,即便有機會交流,有時候對一些文本的理解也未必能達成一致。當然,若有機會和原作者交流,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省去不少困惑。例如,1921年12月7日,拉爾博為《尤利西斯》的出版準備了一場報告會,在準備過程中他建議西爾維婭·比奇和艾德里安娜·莫尼埃把《尤利西斯》的部分段落譯成法文在報告會上朗讀,于是她們請雅克·伯努瓦把《珀涅羅珀》翻譯成法文。伯努瓦為了準確翻譯《珀涅羅珀》,就懇請喬伊斯把《尤利西斯》的提綱給他,并且和喬伊斯當面探討了一些翻譯難點。如第十八章結尾處的“我愿意”很難譯成法語,按法語的習慣,女人在這里說的是je veux bien,語氣比je veux弱,所以他在最后添上了一個“oui”。當喬伊斯發現雅克·伯努瓦添了字,很為驚訝,因為原文沒有那個字。伯努瓦解釋說添加了該詞后語氣會更好一些,他們為這個問題討論了好幾個小時。事實上,更多時候,譯者和原作者沒有機會面對面交流,因此翻譯時就需要譯者擁有獨立的理解力和闡釋力,翻譯活動的順利進行需要譯者和原作者的相互認同、承認,雖然很多情況下,更多的是譯者對原作者的認同。《尤利西斯》的譯者金隄和蕭乾、文潔若夫婦都具有類似的對原作者的認同過程。金隄于1945年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后,留校任助教,期間曾讀過《尤利西斯》一次,后來受命翻譯《尤利西斯》,再后來被它的語言和藝術性所吸引,最后畢生從事喬伊斯和《尤利西斯》的翻譯研究。蕭乾早在1939年就對“喬伊斯及其作品比較感興趣,特別對《尤利西斯》簡直是頂禮膜拜”;文潔若年幼在日本時,擔任外交官的父親拿著日文版的《尤利西斯》對她說:“要是你刻苦用功,將來就能把這本奇書譯出來,在這個奇書的中譯本上印上自己的名字”〔9〕。三位譯者都對喬伊斯和《尤利西斯》同樣地膜拜,并共同選擇了喬伊斯和他的“天書”來翻譯和介紹。喬伊斯雖然沒有機會一睹其作品的中文譯本,但是歷史和機緣選擇了這三位中文譯者,相信他一定會對他們成為自己作品的譯者而欣喜若狂。譯者對原作者的認同是翻譯活動的基本前提之一(行政命令的翻譯活動例外),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翻譯活動中原作者和譯者雙方應該是相互獨立、平等的間性主體,他們的交流必須是在相互認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的。原作者并不具備對原作的唯一解釋權,譯者在原作的基礎上也同樣具有他自己的解釋權。因此,翻譯就是把他者的語境解釋融合到本我的語境解釋中,譯者只有很好地領會原作者的意圖,才能實現間性主體的融合和平等交流。
三、譯者與贊助人系統的主體間性
翻譯活動不是孤立的行為,它與外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因素密不可分,雖然這些因素的影響有時是直接的,但更多是通過贊助人間接地在意識形態、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對譯者施加影響。筆者認為贊助人是一個由多維要素組成的,互為影響、互為能動的互動系統。譯者翻譯活動離不開贊助人系統的支持和幫助。贊助人系統為譯者提供必要的生活津貼和工作場所,同時對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楊武能先生曾對自己受益于贊助人感受頗深,他認為《世界文學》的李文俊先生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綠原先生在非常情況下破格編發他這個小人物的書稿,對他比較順利地走上文學翻譯之路至關重要〔10〕。如果沒有出版人的魄力、視野和甘為他人奉獻的精神,也不會有一部部優秀的世界文學作品在中國獲得新的生命,也不會出現一大批風光無限的譯者活躍在中國的譯壇。雖然在特定時期,有的譯者完全聽命于贊助人系統的安排,如選材、翻譯方式、出版無法署名等,但是總體來說,贊助人對翻譯的具體翻譯活動影響是有限的,他們側重于對選材、目的、出版和服務對象有較為明確的要求,因此譯者有充分的翻譯自由度。譯者在接受贊助人委托時,就要履行服務承諾,但是翻譯的結果是多因素的產物,譯者只按照贊助人的要求去翻譯是不夠的。從倫理學的角度考量,如果客戶的翻譯要求違背了翻譯的基本倫理,譯者是可以提出異議甚至拒絕服務的。《尤利西斯》這部天書在中國的譯介離不開贊助人的努力。金隄先生是在《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主編袁可嘉的不斷勸說下才開始翻譯《尤利西斯》的,后來《世界文學》、百花文藝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都對他的翻譯工作予以積極支持,金隄先生直至去世前一直從事《尤利西斯》文本研究和翻譯研究。和金隄先生類似,蕭乾先生、文潔若先生翻譯《尤利西斯》是在譯林出版社主編李景端多次登門拜訪勸說后才開始翻譯的。譯者和以委托方為代表的贊助人系統積極互動,形成了譯者和贊助人的間性主體關系。例如《世界文學》主編李文俊專程到天津和金隄先生商議《尤利西斯》選譯章節和發表的計劃。人民出版社在得知金隄先生選譯《尤利西斯》部分章節后,“主動派出副總編秦順新和金隄先生商談出版《尤利西斯》全譯本事宜,并提出因為該書特別困難,可以多給時間,三至五年交稿”〔11〕。贊助人不是具體的某類人,而是一個群體。筆者認為,贊助人系統“可能是一個個具體的實體,也可能是抽象的單位,可能是可分的,也可能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系統性和關聯性。”“可以是具體的實體團體,如宗教集團、政黨,特別是執政黨、政府、出版機構、大眾傳媒、團體組織、民間機構、學校;還可以是實體個體,如出版商、叢書的主編、使節、家人、朋友等;也可以是抽象的形態如政治環境、方針政策、詩學觀、精神支持、輿論導向等。”〔12〕一部優秀的譯作離不開贊助人系統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交流、互動,理想的譯者與贊助人的間性倫理關系是各主體間能夠相互能動、相互尊重和相互承認,在溝通和理解中達成共識,最終獲得理想的譯品,從而實現贊助人與譯者的雙贏局面。
四、譯者與譯作讀者的主體間性
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最好體驗是直接閱讀原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讀者都擁有閱讀原著的外語能力和理解能力,因此翻譯在很多時候承擔了延續原著在異域生存和再生的任務。譯者和讀者發生間性主體關系是因為譯本這個紐帶,譯者是原文本的闡釋者和創作者,而讀者是譯作的闡釋主體。很少有譯作讀者會去比對譯作與原作,因此他們更希望通過譯作感受到和原作讀者同樣的閱讀體驗。這需要譯者充分地傳達原作的意圖,實現譯作讀者的閱讀期待,同樣讀者也需要對譯者充分信任和理解。譯者通過引導讀者閱讀譯本,促進讀者對譯本的接受與批評,而讀者通過閱讀,能對譯者做出一定的評價,促進譯者繼續修訂完善譯本,這種間性關系是在懷疑與信任中構建的。傳統的譯學倫理認為譯者與譯作讀者是主客體關系,譯者是動作的施動者,而譯作讀者和原作一樣是被動者。雖然譯者是主體,但是處于“一仆二主”的境遇,譯者處于“仆”的地位,要伺候好原作和譯作的讀者。“伺候”好原作,就是要求譯者能夠充分領會并傳遞原作的意圖;伺候好譯作讀者就是要獲得譯作讀者對作品的滿意和認同。解構主義翻譯倫理認為譯者是原本和譯作讀者的主導者,可以肆意操縱和改寫原作,譯作讀者是譯者的被動接受者。事實上,好的譯作也需要讀者的反饋和批評,才能不斷修正不足,從而譯出理想佳作。《尤利西斯》譯本一問世就引起了學者和廣大讀者的關注。馮亦代在比較金譯和蕭、文譯第一章后,就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見:“但是把兩個譯本仔細地讀了第一章首十頁,就有36處可以推敲商榷的地方。”〔12〕金隄先生對此也曾撰文進行了解釋,譯者和讀者的互動就這樣發生了。劉軍平對比了兩個譯本的目標語的可讀性、注釋后得出結論:“兩家在一些細微末節處都存在一些疏漏,相比之下人民版出現這樣的情況較多一些。”〔13〕王振平先生對金隄譯作逐字逐句通讀一遍后,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王友貴先生也把他過去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反饋給了金隄,這些學者從比較高的層面為金隄提出了建設性的修改意見。“通過和同行讀者討論具體譯法和等效原則等,他不斷受到啟發,促進了他對譯作的不斷修訂完善。”〔12〕金隄先生在去世前完成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尤利西斯》譯作的修訂工作,但是這部天書的修訂是無止境的,太多的謎團也留給后世讀者去想象。崔少元教授也指出,金譯和蕭、文譯翻譯中出現了一些誤解和夸大信息,在比較兩種譯本的得失之后,他指出了譯文中的許多錯誤,如“wretched bed”,蕭、文翻譯為“簡陋”,忽視了女主人的內心情感變化;“fourworded speeeh”則被翻譯成“浪語”,顯然都是不貼切的〔14〕。蕭乾先生去世后,文潔若先生一直根據學者和讀者的反饋意見對譯文進行修訂完善。在譯林版最新修訂版的序中,文先生明確指出,“本書全譯本出版后,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一些熱心的朋友(尤其是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馮建明先生)還就某些譯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并提供了補充的人物表。”文先生把原來繁瑣的文字修改得更加簡潔,盡量保持意識流特色,同時仍堅持力求易懂的原則。負責出版《喬伊斯全集》的責任編輯孟保青曾對記者說:“文化界普遍認為蕭乾、文潔若合譯的譯本偏重文學性,有些譯文未必準確;金隄作為學者追求嚴謹、還原作品原貌,但同時可能欠缺生動。”〔15〕該評價雖然籠統,但是基本上準確地評價了兩個版本的譯作。兩個譯本的譯者在有生之年都能和讀者很好地互動,傾聽讀者的建議,并不斷對譯作進行修正,他們的行為很好地詮釋了譯者與讀者主體間性的互動,即讀者對他們充滿了信賴,因為他們都用自己的譯作為讀者提供了意識流巔峰之作的大餐。他們力圖對原作者的意圖真實的、正確的傳遞,同時也深信現代讀者的理解和闡釋能力,能和他們進行良好的互動,盡量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這就是譯者與讀者之間形成的良好的“契約”關系,即譯者有自己明確的翻譯策略、詩學和定位,做到翻譯的每一個字都是對讀者的一種誓言,實現譯者與讀者之間視野融合一致,真正做到譯者和讀者之間的平等對話、共識共存、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簡言之,對于像《尤利西斯》這樣的“天書”,譯者一方面要通過各種形式,如序言、譯后記、研討會、讀者見面會等形式介紹原著,構建讀者閱讀期待,降低讀者對這部語言形式、敘事藝術多變,內容博大精深的巨著的閱讀困難,又要避免過度闡釋,剝奪讀者自己的探索與專研空間,這樣才能給讀者足夠的自由性和主體性,形成原著與讀者先見視野的融合,真正讓譯者和讀者之間實現主體平等、相互認同、相互尊重的倫理規范。
五、結語
翻譯是復雜的活動,譯者如何在翻譯活動中平衡好內外要素之間的關系,這將直接影響著譯作的質量。我們在對傳統翻譯倫理思想和現代翻譯倫理思想“去粕存精”的同時,需要進一步構建更為平衡與和諧的翻譯間性倫理規范。主體間性作為間性理論研究的領域之一,是現代哲學和人文科學的前沿。伽達默爾認為解釋活動是主體間的對話和“視界融合”,哈貝馬斯也認為孤立的個體是交互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活動本質上就是原作者、譯者、贊助人和讀者共同參與的活動,因此譯作是一種“共生”的結果。這些主體中不存在主次關系,而是平等互助、相互尊重、相互認同的共同主體。翻譯共同主體間性關系主要表現為:(1)譯者與原著作者的主體間性反映了譯者在選材、作者選擇等方面和原著作者具有某種心靈契合性;(2)譯者與贊助人系統以及譯著讀者的間性關系反映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到翻譯外部生態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通常情況下多是積極的,對文學作品在異域譯介起著推動作用和改善譯著水平的作用。主體間性理論破除了翻譯中的二元對立命題,打破了兩極封閉的系統,實現了翻譯行為的多元化。因此,翻譯活動不再是文本層面的語言轉換,還涉及社會因素、譯者個人背景、贊助人系統和讀者期待等諸多要素。翻譯主體間性倫理規范的構建需要主體關系中的各參與主體既要保持相對獨立又要相互關聯、相互認同和相互制約,要平等對話、彼此理解與尊重,才能實現共識共存,也才能翻譯出理想的“譯作范本”。理想的“范本”就要求譯者在翻譯原文時既充分考慮作者的意圖,并盡可能地準確傳遞原文的內涵,同時又要能兼顧譯作讀者的閱讀期待〔16〕。因此,譯者應該是這個主體間性系統中的主動者,他要主動地和其他間性主體協商、溝通,并運用自身具有的雙語能力,使原作在譯語文化中得到生命延續或者新生,實現把“理想范本”作為世界文學交流的介質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