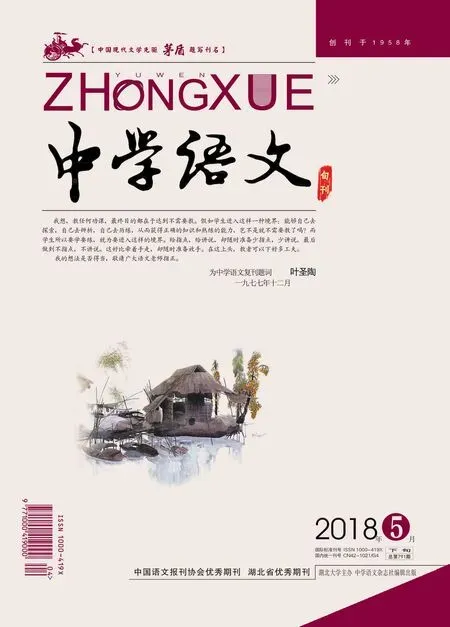找準最適合的教學切入點
徐德兵
當下語文課堂依舊沉悶,主要是由于教師抓得太緊,管得太多,基本還是自己在講,讓學生一味地接受,導致學生學習被動,無法激發內在的學習動力。那么如何改變語文課堂這一現狀,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呢?筆者認為教師要找準提問的切入點。提問的切入點形式多樣,關鍵在于找準最適合的切入點,和學生一同研討,在研討中激發思維,傳授知識,糾正偏差,最后歸納總結達成共識,定能事半功倍。下面筆者結合自身的教學經歷來談談切入點的設計。
一、以教師對文本的獨特發現為切入點
在備《高祖本紀》時,筆者發現文章開頭對劉邦身世的介紹極為簡單:“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僅用了26字。大概就是介紹高祖是哪里人,姓什么,字什么,父親是誰,母親是誰。不僅如此,甚至他的父母連正式姓名都沒有,有的僅僅是口語化的稱謂。這不是很奇怪嗎?而司馬遷在介紹項羽時卻是這樣寫道“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除了交代籍貫姓名之外,還重點介紹了他的家族。但是卻沒寫他父母。相比之下項羽的身世顯然比劉邦華貴多了。基于這樣的發現,教師可以在課堂上提出這樣的問題:你覺得劉邦的身世怎樣?你是怎么看出來的?作者這樣寫有何用意?其實司馬遷就是用極為簡單的文字、極為普通的介紹來告訴讀者劉邦出身于平民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創造了非凡的功業。看接下來的敘述“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段文字雖帶有傳奇色彩,令人難以置信,卻告訴讀者劉邦有天子之命。可以說司馬遷一上來就抓住了劉邦的人物特點。
以教師的發現作為問題探討的切入點是很有價值的,這不僅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引導學生深入文本,而且可以培養學生質疑探究的習慣。當然發現本身也可以引起教師探究文本的興趣。又如筆者在讀韋應物的詩《寄李儋元錫》:
去年花里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
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
當讀到“春愁黯黯獨成眠”時,筆者覺得應該寫成“春愁黯黯難成眠”才對。按常理說因為滿懷愁緒,從而難眠。教師可從這里切入與學生一起探討。當學生帶著問題進入文本,就不難發現詩歌的標題“寄李儋元錫”,也就是說這首詩是寫給友人的,再從結尾“西樓望月幾回圓”對友人的盼望來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用“獨”而不用“難”了。理解“點”不是目的,通過“點”,讀通、讀懂文章才是真正目的。
二、以文本中議論抒情的語句為切入點
小說一般少有議論抒情性質的文字,但作者寫到動情處,情不能自已時,也會出現。《項鏈》是一個典型。作者在感慨瑪蒂爾德命運時這樣寫道:“倘若當時沒有失掉那件首飾,她現在會走到什么樣的境界?誰知道?誰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變化無常啊。無論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點點小事。”從這里我們可以讀出作者對瑪蒂爾德的態度,可以讀出作者創作項鏈的初衷。教師可以提出下列問題:1.說說作者對瑪蒂爾德的態度,并從文中其它地方尋找依據。2.“小事”在文中是指什么?“人生的無常”在文中有怎樣解釋?把這些問題弄明白了,學生對文章的內容就把握了,對作者思想感情也就能準確理解。實際上作者對瑪蒂爾德的不幸命運是極為同情的,作者是想告訴大家人生往往是變化無常的,而并非像有些參考書說的那樣批判愛慕虛榮,提醒人們要安分守己。
再看《史記·李將軍列傳》。筆者認為司馬遷把最高的評價給了李廣。為什么這樣說呢?“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夸李廣“身正”,說他象桃李一樣受到人們愛戴。一個地方,兩次引用,兩次贊美,語氣多有贊嘆,足見司馬遷對李廣用情之深。那么在文中是怎么體現李廣“身正”的?為什么把李廣比作桃李呢?司馬遷自己又是怎樣的人呢?等等。教學中以議論抒情語句為切入點,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研讀文本,調動已有知識,甚至去查閱資料,深度加入到師生互動交流中來。
三、以文本中行文前后矛盾處為切入點
文本矛盾處,是疑點。如果不加探究,恐怕很難深切領會作者思想感情和寫作意圖。既然是疑點,就有普遍性,大多數學生都有想弄明白的心理期待。所以以矛盾處為切入點,進行探究,定能激發學生思維,激活課堂氣氛。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就有這樣的矛盾處。文章開頭反復說“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后來卻說“實在無話可說”,最后又說“說不出話”。這是為什么?讓學生依據文本進行探討。“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是為了悼念逝者,喚醒民眾,牢記血案,同時也是為了回擊反動文人,揭示他們兇殘的面目、險惡的用心;“實在無話可說”是表達自己對反動派兇殘、無恥行徑的憤怒;“說不出話”是表達自己悲痛欲絕的情感。這樣以“說”與“不說”作為切入點,引導學生梳理內容,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就能深入文本,貼近作者的心靈。
文本矛盾處是理解作者寫作用意的突破口。蕭紅《春意掛上了樹梢》,從題目來看充滿暖意,但內容讀來苦澀、凄涼。前后矛盾。為什么?春天確實來到了人間,上層的人們沐浴在春光的快樂中,而底層的人們連生計都無法維持,春天雖然來了,他們依然在痛苦中掙扎,無法感受到春天的溫暖。作者有意選擇春天這樣一個特定情境,引導人們關注底層,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關注貧富的差距,社會的不公,以求變革。只有抓住矛盾點,深入探討,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寫作用意。有的教師僅僅告訴學生這是反襯,以樂景襯哀情,如果僅此而已,學生只是接受了概念,無法真正領會作者,形成自己獨特的認識與體驗,收獲就不會不大。
四、以學生錯誤理解作為問題的切入點
一般教師對學生的誤解甚為討厭。殊不知這恰恰是教學的契機。某市高三期末調研考試卷中,論述類文本有這樣一道題目“請簡要概括西方哲學家對人生意義的不同觀點”。答案所涉及的文字如下“人生的意義是什么,這個問題一直使西方哲學家備受困惑。他們從目的論出發,認為包括蚊子乃至傷寒菌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是為這個自負的人類的利益而存在的。今生今世自有百般磨難,因而自傲的人類始終無法事事如意。于是目的論又轉向來生來世,把今生的世俗生活看作為來世所進行的準備。另外有一些人,像尼采那樣知難而上,否認人生‘必須’有什么意義,認為人類的進步不過是一種循環,一種野蠻人的舞蹈,而不是去市場采購,所以沒有什么特殊的含義。然而問題還是沒能解決,它就像海浪一樣不斷沖擊著堤岸:‘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許多學生的答案都分成了三點:1.萬事萬物都是為這個自負的人類的利益而存在的;2.把今生的世俗生活看作為來世所進行的準備;3.否認人生“必須”有什么意義。其實第一點并非在陳述人生的意義,而是在描述西方哲學家對萬事萬物的看法(態度)。那么這些文字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這時教師可以讓學生進行探討。只有通過探討,學生才能明白這是西方哲學家對人生的意義的認識過程,才能加深對這段文字的理解,從而積累閱讀的經驗。
總之,教師在實際教學中,真能找準教學的切入點,那么就能實現從教師講授灌輸轉變為師生共同研討,教師就能在研討中給予學生引導、幫助、啟發,這樣方能體現學生主體、教師主導的精神,真正提高課堂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