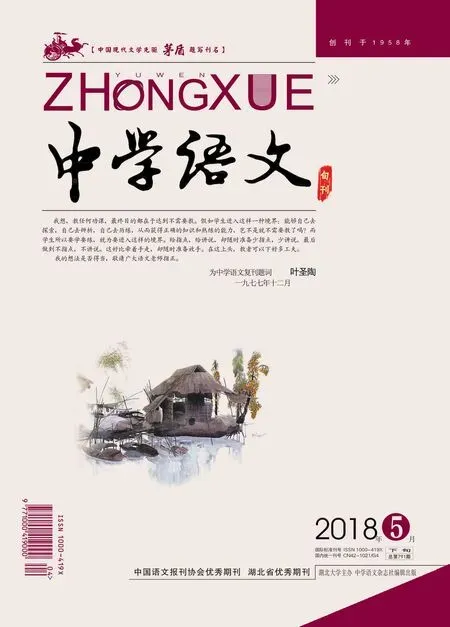串讀《〈史記〉選讀》的教學案例與反思
顧小蘭
《〈史記〉選讀》在高中語文教學中的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它是中國傳統文史材料中的典范,有著重要的傳承意義;另一方面它全部是文言文本,學生學起來相對吃力,要解決許多字詞句義等工具性問題,要理解其中的人文性也不容易。筆者的思考是:可以本著“組塊”的思路,選用串讀的方式,來讓學生完成對同一主題的文本意義的構建。本文就以蘇教版高中語文選修教材《〈史記〉選讀》中的“《史記》的理想人格”這一主題為例,談談筆者重構教學的思路、實踐與反思。
一、尋找文本主線:串讀重構的基本思路
《〈史記〉選讀》中的“《史記》的理想人格”這一主題有三篇文本:《孔子世家》《管仲列傳》《屈原列傳》。這三篇文本歸于同一個主題,在教材編寫者那里肯定是有緣由的,但對于教師的教學而言,這種主題能否為學生所明察,則是教師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筆者在重構教學中,嘗試讓學生自主去尋找文本主線,為串讀奠定基礎。
在實際教學中,解決了基本的工具性問題,即保證學生在閱讀的時候能夠較為順暢地閱讀后,文本主線的尋找就開始了。
有學生說:我讀《孔子世家》一文,感覺孔子在心目中不再是一個高不可攀、只能仰視的人,“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貧且賤”說明孔子的出身甚至不如我們同學中的絕大多數人,但英雄不問出身;其后“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本是問“政”,孔子卻答“人”及“人與人的關系”,這體現了孔子的大智慧,他認為“政”本就是“人及人與人的關系”……
有學生說:我讀《管仲列傳》,也看到管仲雖然出身貧寒,但卻“賢”,待鮑叔不計前數嫌而將其推薦給公子小白,其最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文中管仲自知自己的缺點,且知鮑叔對自己的寬容,從而得出那句流傳至今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有學生說:我讀《屈原列傳》,看到的則是一個“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的一介書生滿懷救國之志卻不得施展,最后抑郁投江的故事。通過比較這一文與其它兩篇文章發現,本文沒有介紹屈原年輕時的貧苦,但我猜想他這樣經不起挫折,可能與年輕時沒有管仲、孔子那樣的挫折有關,所以做不到百折不撓。
最后一個學生的觀點引發了學生的熱烈反響,同時筆者意識到,文本解讀的線索產生了。這個線索就是三則文本中的主人公思想抱負與個人經歷之間的關系,而其與“理想人格”又恰恰是相關的。
二、基于主線閱讀:串讀重構的高效教學
于是筆者跟學生明確:對三則文本進行串讀,看孔子、管仲與屈原三個人的理想抱負有何異同?在理想抱負得到實現或未得到實現之后,他們三人的表現又是如何?為什么又會有不同的表現呢?
這樣的問題激發了學生研讀文本的熱情,讓學生在無形當中將三個人物聯系在一起進行關注,三則看似不通的文本忽然之間似乎就有了聯系,于是課堂上出現了這樣的情形:
有學生說:我覺得屈原和管仲更具可比性,他們都是輔佐一方諸侯,都想成一番經天緯地的事業。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出號令”“應諸侯”,但其成功的前提是“王任之”,待到“王怒而疏”之后,只能“疾王聽之不聰”;而管仲則不同,其“任政相齊”,以其卓越的管理才能而“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遂成霸業。兩個人相同的抱負而結果截然不同,這可能與屈原太過“小氣”有關,因為他應該知道上官大夫的習性,對于這種人因上官大夫見憲令“而欲奪之”卻“不與”,自然是得罪人的舉動,若洞察其性,以一假憲令使之奪,然后再以真憲令駁斥于王前,或許就不這么被動了……
在這樣的教學實踐中,文本之間的串讀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串讀所依之主線也決定了學生的思維更多的是圍繞文中的主人公而展開的:先研讀人,再研讀事,再研讀史并從史的角度去認識人與事,此時學生對文本所形成的印象,就成為一個大的組塊,這促進了學生對文本的記憶,也促進了學生對《史記》的理解,課堂教學效益的提升自然蘊含其中。
三、反思《史記》教學:串讀教學的價值思考
《史記》本是大部頭巨著,擇其要而形成《〈史記〉選讀》一本薄薄的冊子,需要的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一“點”突破一個“面”,形成一個“體”,也就是說需要教師就其中的文本解讀,讓學生形成對“史”,對“文”的認識。而文本常常是孤立的,需要教師將同一主題的文本“串”起來,以讓學生在互文解讀中形成認知,這就是串讀的意義所在。
其實,“串讀”的意義不僅在于“讀”,更在于“串”,因為有效的“串”需要教師認真研究文本之間的聯系,預設可能的聯系點,然后在教學中有意引導。故而串讀其實是需要串問、串講作為輔助的,在此教學情境中,課堂是立體的,學生對文本的理解也是有機的。
誠然,高中語文選修教材的教學面臨著諸多挑戰,尤其是教學效益的提升,需要廣大語文教師想方設法去實踐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