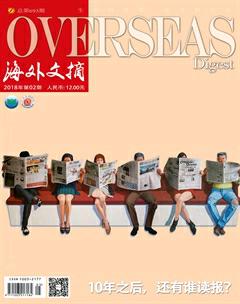讓·多麥頌:你好,歡樂
菲利普·迪費
從圣法爾戈城堡到七星文庫,多麥頌先生的一生都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下。
2015年4月,七星文庫出版了4部讓·多麥頌的作品,而這一年距離多麥頌先生進入法蘭西學院已有42年。這兩項成就足以讓他名垂史冊。
路易斯·斐迪南·塞利納主持電視節目,采訪歌手路易斯·鮑威爾時,重復道:“人類真是太沉悶了。他們呆板而遲鈍。”讓·多麥頌卻與常人不同,他輕盈自在。
輕浮,卻不令人厭煩。如今,一些文學評論家故意把他塑造成圓滑世故的形象。但那都不是真實的他。他不世故,也不無病呻吟。長時間應對世人的偏見似乎成了一場修行。50多年來,偏見和詆毀如影隨形。
而他,卻輕盈如一葉羽毛。
法國作家們選擇了他的4部作品編入七星文庫文集,法蘭西學院院士馬可·福馬羅利在文集的序言中寫道:“即使他沒有人們說的那樣輕盈,但他仍然有奇跡般的力量和樂觀的心態,給生活減負,驅散生命中的陰霾。”正如作家王爾德所說:“深刻的內涵往往就在事物的表面。”
回望他的青年時代。先是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生活,那里啤酒女郎的胸部比電影《茜茜公主》的女主人公還要挺拔;接著到了羅馬尼亞有“小巴黎”之稱的布加勒斯特,那里因莫朗夫婦而聞名;后來,他又到了巴西,喬治·貝爾納諾斯(反對西班牙內戰天主教暴行的斗士)的流放之地。整個青年時代,讓·多麥頌的個性都隨他的父親——外交官安德烈——“寬容開明、樸實隨性、共和主義”。父親的影響和多國游歷的經歷沒有讓他樹立遠大的事業目標,也許正是因為經歷多了,所以他決定順其自然,“什么都不做”。
博紅顏一笑
巴黎是多麥頌先生人生的起點,他的父母居住在巴克大街97號,距克萊蒙·東奈酒店只有幾步路的距離。當年,革命戰士夏多布里昂就是在這里聽到了法國七月革命的號角,而瞑目而去。戰士們在這里摧毀了國王的雕像,舉起代表“窮苦人民”的三色旗。
讓·多麥頌在動蕩的青春中,仍抱有日耳曼人的火熱之心。透過房間的窗戶,他看到了宗教教會里的游魂和騎兵軍官的寡婦走向廉價商場,聽見了圣敘爾皮克和圣克洛蒂爾德的鐘聲,他決定什么都不做。20歲,當同齡人都在嚴肅地思考著人生選擇時,他決定什么都不做。這不是戲言。還有什么比哲學更有意思嗎?為了考進高等師范院校,他進入了文科預科班學習。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是觀點的匯聚之地,涌流著各種思想,讓·多麥頌在這里擁抱了哲學。
夏天,在7號國道上,他開著意大利敞篷汽車,駛向陽光照耀的地方,迎向光明的未來。那時,他內心深處仍然不渴望有所作為。在巴黎,戴高樂政府的財政部長,他父親的朋友雅克·魯艾弗把他這個剛畢業的學生引薦到政府工作,做一名干事。這個職位雖不起眼,卻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以后可能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探索更廣闊的世界。人種學家、人類學家、生物學家等各種專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施展才華。讓·多麥頌也在這里找到了他的使命和位置。羅杰·卡約邀請他擔任《第歐根尼》雜志的編輯助理,這本雜志探討文學和哲學,是一門跨學科類的期刊。寫作了3個多月后,他決定留在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那他又是怎么進入文學領域的呢?“年輕的時候,我從未想過以后要從事寫作。我覺得索福克勒斯、福樓拜、普魯斯特的作品已然無法超越。您知道我為什么開始寫我人生中的第一本書嗎?只是為了博紅顏一笑!”1956年,他寫作了第一部作品《愛情是幸福的》。
10年后,他涂上發膠,梳了背頭,緊張不安地帶著手稿來到加斯頓·加利瑪出版社。他在七星文庫文集的序言中寫道:“我想要取悅我心愛的姑娘,她那么尊貴,她從沒注意過我。她用紅色和黑色交織的網,守在山洞口,等著她的獵物。而我害羞又倔強,拿著那些為她怦然心動時寫的手稿,不知所措,最后吞下了這些手稿。我真是太傻了。15天以來,我一直等著加利瑪出版社的回音。”但是,加斯頓沒有回復他。于是,他打算把手稿給勒奈·朱利亞納看,試試運氣。勒奈的出版社在學院路30號,就在對他的作品不理不睬的加利瑪出版社對面。機遇來了,一個周日的早上7點,電話響了,出版社選中了他的作品《再見,謝謝》。這部作品更像是他的自傳,沒有矯揉造作,比一般的文學作品更加紀實。
“我不想再寫小說了。我希望寫一些新形式的作品,開創文學的宇宙。已經有很多前輩寫作過優秀的小說作品了,比如夏多布里昂、普魯斯特、喬伊斯、韋爾斯還有博格斯等。”
蓄勢待發,他的夢想成為了現實。
1971年末,一篇692頁的作品像一小塊石子一樣落入了法國文學的長河中。發表這部作品的作家不是某個從索邦大學逃學成才的作家,而是著名的“非知名”作家,他穿著天藍色的襯衫,有一雙天藍色的眼睛,那年他46歲。
書名是《帝國的榮耀》。歷史學家和作家雅克·勒高夫在《新觀察家》雜志中評價道:“一部先鋒式的著作,人文科學類的第一本小說。”
《帝國的榮耀》擺脫了前幾部作品的風格,用他自己的風格講述了歷史,同時又以世界歷史作為靈感來源。雅科琳·皮婭提耶在《世界報》上贊嘆道:“世界歷史事件在這部作品中再現,書中的歷史仿佛具有當代性,不禁令人贊嘆佩服。”雅科琳出生在北部廣袤的森林,是波菲利人的后裔。青年時期在一位哲學家的陪伴下,過著到處游蕩的日子,接著,他統治了一個部落帝國,并率軍打擊來犯者,征服了一方。最終,他功成身退,并在平靜的日子中走向生命的終點。
第一句話就為整部作品奠定了基調:“帝國從未見識過和平。”就像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寫作的交響曲的起音,又如電影《野蠻人柯南》的氣氛。“寓嚴肅的史實于戲謔的調侃中。”馬可·福馬羅利在七星文庫文集的序言中寫道。“我躺在床上,邊寫邊看我已經寫過的內容,我回憶起了在教科文組織的時光,西方文學作品中的片段,還有日本電影中的橋段。”讓·多麥頌曾經這樣描述他的寫作經歷。
榮譽光環
這部作品幾個星期后拿下了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很快,又獲得了銷量上的成功,突破了10萬印刷量。這次,讓·多麥頌受邀加入加利瑪出版社的評委會——這次加利瑪出版社的電話可算是沒壞。1973年10月18日,他被法蘭西學院任命為第12屆主席,而此前這一席位屬于于勒·羅曼。1974年2月,在雙向選擇的前提下,《費加羅報》的主要股東,他的岳父貝甘,請他到《費加羅報》編輯部上班。
銷量成功、學院榮譽、《費加羅報》社長……讓·多麥頌榮譽加身。不過,給他帶來榮譽的《帝國的榮耀》剛剛出版,他就開始寫新書了。
1974年春天,加利瑪出版社為他出版了《上帝的喜悅》,這部書有點像法國勃艮第版的《亂世佳人》。3年后,《上帝的喜悅》被改編并搬上電視熒幕,有上萬法國觀眾收看。作品講述了一個歷史悠久的法國家庭的故事,模仿《亂世佳人》的風格,卻又增添了一些新意——引入了現代元素——戰爭、社會和技術變革、習俗的變遷、現代藝術和觀點等等。《上帝的喜悅》就像“法國貴族家庭的肖像畫”,作家好友弗朗索瓦·努里西耶評價道。“《帝國的榮耀》和《上帝的喜悅》這兩部作品給我帶來了榮譽,把我引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多么幸運!法蘭西學院院士、《費加羅報》社長……榮譽涌向我。大家祝賀我,從老婦人到年輕的小伙子,都請我在我的書的扉頁上簽名。多么幸福!我在鮮花的海洋中前行,那是我兒時的美夢。”讓·多麥頌感嘆道。
1974年,小說《三劍客》出版的第20年,故事的主人公似乎已經有些過時,而讓·多麥頌卻沒過時。
我們可以在哪里找到讓·多麥頌的作品?與同時期的作家相比,讓·多麥頌的作品幾乎無處不在,在書店、加利瑪出版社的書架上、酒店的房間里、拉豐出版社里,在他的密友馬勒西·歐贊那和他女兒愛洛依絲的手中,在電視上、劇院舞臺上、電影院的熒幕上,在歷屆總統的書柜里……
當然,還有《費加羅報》的專欄里,昨日的報紙上他撰文評論盧旺達的種族屠殺,今日的報紙上,他哀嘆著東方基督徒的命運。
千面人生
脫口秀上,他永遠系著海軍藍色針織領結,在科西嘉海岸上則穿著粉色的短褲,光著腳。歷屆總統都與他有著不錯的私交,從蓬皮杜到季斯卡,再到交情或許沒有那么親密的密特朗。波拿巴和他的繼任者波旁王朝不喜歡夏多布里昂。而讓·多麥頌把夏多布里昂奉為他的精神導師。
他說:“如果我非常幸福,如果一切都很完美,我不會去寫作。我寫作是因為有些事情不盡如人意。到底是哪些事情,我也說不清楚。我在追逐未知的事物,追尋渺然的天際,我努力去夠到那里,但那個目標又不斷地隱去。”作家佩索亞也寫道:“生活永遠不能滿足我們……而這就是人生。”
《抱怨的讓,大笑的讓》是30年前的《費加羅》雜志專欄文章的題目,不少讀者都看過,文章評論了讓和他的作品《上帝的喜悅》。老朋友馬勒西·歐贊那回憶稱,幾乎沒見過讓·多麥頌有過壞脾氣:“從未存在于我的記憶中,幾乎沒有這樣的時刻。”
2014年6月,得知自己已患癌癥的讓·多麥頌在瑞士廣播電視臺上發言稱:“我只有20%的把握能重獲新生,我相信上帝,因為每天一睜眼,我就又迎來了生命中的一天。”
2016年初,他在加利瑪出版社出版了新書,那不是他的最后一本書,但是書里的話,可以當作他的墓志銘。讓·多麥頌,這個永遠熱愛生活的人告訴我們:“我想說,無論如何,我這一生是美麗的。”
[譯自法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