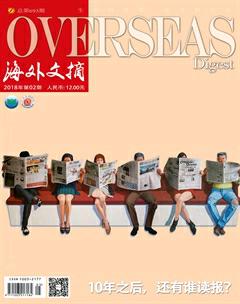集體生活電影的迷思
克里斯多夫·伽利耶爾
從《無巧不成婚》到《天上再見》,宣揚善意和“和平共處”的電影激增,它們是我們在焦慮的日常生活中的慰藉。讓我們共同解讀。
從某個時刻起,法國電影銀幕上開始浮動利他主義的芬芳。電影里充滿了寬容、友誼、家庭、愛情之類的價值觀。提及這類電影,我們會立刻想到埃里克·托萊達諾和奧利維埃·納卡什聯合執照的《觸不可及》。《無巧不成婚》也是這二位的作品,它從幕后策劃的角度講述了一個關于婚禮的歡樂故事,一經上映,票房登頂。這兩位導演已經成為宣揚善意電影的擁護者。他們的作品也被歸為大熱的“治愈系電影”,與令人焦慮的日常現實形成鮮明對照,保證能帶給觀眾心靈上的享受。此刻我們可以說,在一部電影里,一切皆有可能發生。比如法布里斯·厄布埃的《共處》里塑造出的烏托邦,或者可以叫做“唱片制作人是怎么編排出了一個由猶太教教士,伊斯蘭教教長和天主教教士之間的故事”;又比如卡琳娜·塔迪厄導演、弗朗索瓦·達密安主演的《打消我的懷疑》,有著錯綜復雜的親子和戀愛關系;當然,還有剛剛上映的《天上再見》。這部電影由阿爾貝·杜邦泰爾導演,改編自皮埃爾·勒梅特榮獲2013年龔古爾文學獎的暢銷書,講述了兩個一戰老兵策劃一起巧妙詐騙的傳奇故事。我們發現,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必然來源于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和在時代中承受痛苦的人物。震撼的故事才是精彩的故事,這已經成為電影創作的趨勢。
就好像幸福,或者至少是消除偏見的情感主題,已經控制了法國電影市場。誰曾想在《9月懷胎》里飾演一個最傲慢的暴徒的阿爾貝·杜邦泰爾,反過來執導了這樣一部宣揚善意的電影呢?“我無意中成為了一個擁護社會團結的人,”這位編劇兼導演放緩了語氣,“如果觀眾從中看到善意就更好了,但實際上,這部電影是從一本抨擊時政的書中得到的靈感。”真滑稽,這表明了藝術家們對善意這一概念持有著懷疑。但是得說,這個詞確實是被濫用了……人們原本褒揚那些宣揚手足之情和寬容價值觀的電影,但是質疑也漸漸滋生。電影創作者們不再知道他們的電影是否取得了成功,或者也許他們一直在煽情的泥沼里打滾。“如果不能宣揚樂觀主義或表達和平相處的愿望,他們就會發瘋,”法布里斯·厄布埃解釋道,“但是現在,平和首先是一種服務于消費社會的力量,‘和平共處也已成為市場營銷的前提。有一天,我買了一包紙尿褲,外包裝上印著一個黑人寶寶、一個白人寶寶和一個亞洲人寶寶。由此可以歸納出:即使我們在紙尿褲里排便,我們也是在倡導種族間的和平共處。”這一切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我們也有權利厭倦這種人道主義的欺騙性宣傳,因為它多半由純粹的商業目的驅使。
但也不都是這樣。誠然,先不談喜劇片是否搞笑,或是悲劇片是否傳達了一種對社會現實的無力感,傳播寬恕、善良的喜劇片的數量總比引人反思、使人肅穆的悲劇片多。但這不足以構成質疑喜劇創作者是否真誠的理由,他們的創作靈感恰恰反映了一個共同愿望:逃離現實,或者將現實理想化,因此產出的作品都大同小異。“世界上存在的暴力和生活的艱辛,使人道主義文藝作品成為一種撫慰心靈的永恒需要,”精神病醫生克里斯多夫·安德烈分析道,他是一系列探討幸福和積極思維的書的作者(類似的書有奧迪爾·雅各布的《和我們一起思考》),“在社會富裕、前景大好的過去,我們反而無休止地批評社會,并且向人們披露那些好像從他們日常生活消失了的不幸和苦難。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今日已不同往昔。”
下面我即將談到的內容也可以證明以上觀點。我們也注意到,和上個世紀不同的是,電影不再以悲劇收尾。少有例外,甚至悲劇也會有大團圓式結局。更妙的是:電影里幾乎沒有惡人了!從《歡迎來北方》到《無巧不成婚》,以及《貝利葉一家》,反面人物是缺位的,或者即使有一些不當的觀點(比如《岳父岳母真難當》里的克里斯蒂昂·克拉維耶),也會及時糾偏,最終走上一條由常識和道德組成的狹窄道路。本雅明·百樂古爾(伊朗·古德曼·德·埃德蒙德的聯合制作人)透露,一部獲得現象級成功的“治愈系”戲劇將在2018年被改編成電影,“惡人,即使有,也不再具有惡意。他只是象征著事物的秩序以及時代環境、社會的宿命性。‘惡的消失意味著現今理想主義對犬儒主義的勝利。”
創作者們難道生活在夢幻世界里?當然不是。他們只是在努力地樂觀看待生活,同時平息自己的憤怒。杜邦泰爾導演的《天上再見》里,羅倫·拉菲帝塑造出了一個真正的壞蛋,但是導演承認他已經構思了一個主要人物,由納威爾·佩雷茲·畢斯卡亞特扮演,主人公有著“無瑕的良知,是個篤實的人道主義者,極盡熱情和真誠”。“我現在比拍攝《伯尼》的時候大了20歲,”他說,“老去,就是要學會享受細微的變化。 但我一點不否認年輕時創作的 ‘惡!”在今天的電影中,幾乎所有人都是美好的,所有人都是友好的。這也是投資人和發行商會犯的過錯,因為他們一直擔心電影的選角、主題和可能惱人的評價。“特別是在喜劇片里!”法布里斯·厄布埃明確指出,“很多人問過我,是否確定會在電影里保留這樣或那樣的刺耳的笑話……我的回答是:除非這種既無禮又冷酷的幽默從世界上消失,而那時我的電影也就不復存在。”“要迎合所有人,就不該得罪其中任何一人,”一位匿名的制作人憂心忡忡地回答道,“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減少適時的幽默,事實上,人們看電影就是為了體會一種更好的生活,而且娛樂大眾是必需的。”除了出于回應大眾娛樂需求的考慮,如果剔除諷刺,就會失去原本傳達的內容,也會否定大眾對爆米花電影的嗜好。最好的例子就是《觸不可及》。“當我們寫出‘沒有胳膊,就拿不到巧克力這句電影臺詞時,針對的是身體某一部分不能活動的殘疾人,然而我們并非出于惡意,相反,這句話是友好的,”埃里克·托萊達諾解釋道,“這是個不錯的段子,雖然不符合政治正確原則,但在電影里,這句話只是為了緩和氣氛,使人物全面審視自己。”希望觀眾懂得創作者的良苦用心。
但是,使原始的善意文明起來是一件公認的傻事,達到的結果會是“法國的喜劇片多少都帶有諷刺意味”,就像德國《每日鏡報》記者丹妮拉·桑瓦爾德2016年8月認為的那樣。同樣我們可以舉出例子,比如《回娘家》論證了一個“干癟的公理”,又比如克洛維斯·科爾尼亞克的《非誠勿擾》,是一部“幼稚的”電影。當然,這些電影沒有《無巧不成婚》和《天上再見》影響力大,但是同樣吸引了不少觀眾,票房喜人。“如果你本身偏向對情緒的把握,就會立刻對這類電影有成見,” 斯蒂凡尼·塞勒維耶(《貝利葉一家》以及將要上映的《第二顆星星》的發行人、制作人)指出,“新浪潮運動的余波給了創作者負擔感,他們抵觸這類劇本,一方面害怕別人認為自己淺薄愚蠢,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總的來說媒體對待這類電影非常苛刻。” “雞蛋里挑骨頭的都是那些住地講究、不愁生計的知識分子們,”克里斯多夫安德烈觀察到,“對于那些為生計終日奔波的人來說,開心才是重要的。在電影院中體會幸福不是一種忘卻煩惱的辦法,而是當從放映廳出來時,能夠直面煩惱。” 這類電影因此擁有了公共效用,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益處。“當我們能目睹到消極電影的回潮時,”克里斯多夫·安德烈補充道,“這就意味著我們來到了黃金時代。” 我們心懷善意,期待這一時代的到來。
[譯自法國《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