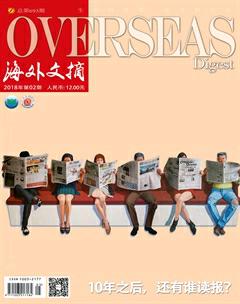手寫的魅力
文森特·費爾南德斯
現(xiàn)代社會中,鍵盤和屏幕已經(jīng)快要取代傳統(tǒng)的筆和紙,成為文字的主要載體,那么手寫字在未來該何去何從?
2014年末,芬蘭教育部宣布要正式放棄使用了幾個世紀的書寫系統(tǒng),于2016年全面取消寫字課,采用包括發(fā)短信和打字技巧在內的新式教學內容,“拋棄墨水,擁抱鍵盤”,正式進入數(shù)字時代。
這項規(guī)定一出,立刻在西方社會引起了大規(guī)模的激烈討論。為此,芬蘭教育官員還專門就這則消息做出了解釋:芬蘭并不是不再開設寫字課,只是將寫字課從必修課改為了選修課,同時還增設了一門打字課也作為選修課,讓學生可以自主選擇更感興趣的課程。不過,他也強調:“能夠流暢地打字,是很重要的‘國民能力,因為打字與日常生活的相關性更強。”
打字vs手寫
為此,社會各界關于“在電腦打字逐漸威脅到手寫地位的今天,學校還是否應將寫字課列為必修課?”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歐洲多國媒體表示,對芬蘭此舉并不贊同。英國BBC稱:“對小學生而言,開始使用鋼筆書寫是一種重要的儀式。”盡管有一些德國學校也在考慮取消寫字課,但德國教育協(xié)會主席仍表示:“取消寫字課在教育學上是完全錯誤的做法。”法國心理學家也指出,讓學生抄寫課文對提高閱讀能力有重要幫助,尤其是對于小學三年級以前的孩子。
不過,也有多家美國媒體表示支持芬蘭教育部這項大膽的決定,并表示:“良好的打字能力在就業(yè)市場上比寫字更有用,芬蘭的決定是向前邁出了一步。”
美國學者安妮·特魯貝克也在《紐約時報》上發(fā)表了題為《書法的歷史與不確定的未來》的文章,她在其中指出,在當前社會,已經(jīng)越來越少會出現(xiàn)非要用手寫不可的情況了,對于現(xiàn)在的小學生來說,未來這種情況會更少。雖然,她也承認,手寫對于人類發(fā)展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她相信,人們之所以不愿意放棄手寫,更多的是出于情感上的需求,而不是實際上的需要。因為過去人們發(fā)明草書和連筆字,就是為了提高書寫速度,而現(xiàn)在,明明打字比寫字更快,那人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選擇這種更快、更高效的書寫方式呢?
安妮·特魯貝克還用她兒子的情況舉了個例子,她的兒子曾經(jīng)因為大寫字母“G”寫得不夠漂亮,而被老師要求罰寫了整整一頁的“G”。這種現(xiàn)象的背后,體現(xiàn)了社會上對于手寫字的傳統(tǒng)偏見——“如果一個人的字寫得不好,就說明這個人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那些書寫得規(guī)范工整的試卷才更容易拿高分。正是因為這種偏見,才導致很多學校過度重視寫字課,總是讓孩子一頁頁機械地抄寫字母,卻忽視了對他們其他方面的培養(yǎng)。
但是,這則消息之所以能造成這么大的社會反響,是不是因為在人們心中,對于手寫字沒落還有著很深的憂慮?人們是否也在擔心,未來的孩子可能完全不認識紙和筆,唯一會書寫的只有自己的名字?透過這則消息,人們看到了對手寫字未來的擔憂。
文字的歷史
盡管有人認為,用鍵盤和屏幕取代紙和筆,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背叛。不過,歷史人文學家表示:文化的傳承和文字載體的形式并無太大關系。從文字出現(xiàn)至今,文字的載體已經(jīng)變更了無數(shù)次,從最早的墻壁和石子,到后來的羊皮紙和蘆管筆,直至150多年前出現(xiàn)的打字機,文字的載體總是順應著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斷變化,但這并不會影響到人類文明的傳承。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5000多年前蘇美爾人發(fā)明的楔形文字。考古學家在神廟出土的泥板上,發(fā)現(xiàn)了諸多類似牛頭、谷穗、魚和日用器具的符號,因為在當時,城邦之神被認為是城邦土地的所有者,各村落都將農產品送到神廟來支付費用,于是就產生了對記錄應付費用和已付費用的需求,而這些刻著牛頭和谷穗圖案的泥板,就是村落交給神廟多少頭牛和多少糧食的記錄。盡管蘇美爾人記錄這些只是為了滿足當時經(jīng)濟和管理的需要,但這種楔形文字也代表了文字的真正開端。
從文士到抄寫員
在早期的社會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寫字和認字的,即使是王公貴族,也沒有把寫字看作是一項必備技能,于是,一種以專門和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應運而生。在古埃及,有個專門的職業(yè)叫作文士,他們具有讀寫能力,既要記錄收獲時生產了多少食物,軍隊中有多少士兵,每年為眾神獻上了多少貢品,又要記錄法老和貴族們制定的法律,以及他們的生平事跡。文士的工作都是終身制的,在古埃及的社會地位僅次于法老、大祭司和貴族,在士兵、工匠、農民和奴隸之上。
早先文士用蘆管筆來寫字,這種筆用起來又慢又費勁,到了后來,古埃及出現(xiàn)了用紙莎草制作的紙張、羽毛筆、羊皮紙和墨水,到了公元2世紀,中國發(fā)明了造紙術,這項改變世界的技術在公元8世紀傳到了阿拉伯,又經(jīng)阿拉伯傳到了北美和歐洲,直到1150年,西班牙人開辦了歐洲第一家造紙廠。紙、筆和墨水等書寫工具的不斷改進,為書寫的普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法國語言學家喬治·尚在他的書《文字與書寫》中介紹,在中世紀的歐洲,還是有很多人只識字,但不會寫字。在當時,文字的傳播仍需要依靠手抄,而能寫得一手好字,又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象征。所以,當人們需要寫信的時候,就會上街去找專門的抄寫員,用口述的方式讓抄寫員替自己寫下一封字跡漂亮的信。那時侯,抄寫員是一份體面的工作,就像古埃及的文士一樣,只有受過良好教育又精于書法的人才能勝任。但隨著造紙業(yè)和印刷業(yè)的興起,整個抄寫行業(yè)的風光不再,大批的抄寫員失去了生計,這些憤怒的抄寫員還曾試圖去工廠搗毀印刷機,但社會技術革新的趨勢到底還是無法逆轉的。
打字機和文學寫作
抄寫員失業(yè)了,同樣依靠寫字謀生的作家卻并未受到影響。在打字機出現(xiàn)之前,作家們都是用筆和紙寫作的,但在寫到文思泉涌的時候,他們手中的筆往往就跟不上腦海中遣詞造句的速度了,打字機的出現(xiàn)改善了這種狀況。1874年,美國雷明頓蘭德公司推出了市面上第一批打字機——“雷明頓一代”打字機,它是當時最新、最高科技的打字設備,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就是這款打字機的第一批用戶,他的《湯姆·索亞歷險記》也是第一部在打字機上打出來的小說。
不過,不是所有作家都接受用打字機寫作。美國作家卡波特就認為,寫作還是應該采用傳統(tǒng)的手寫方式進行,寫作者只有一邊寫一邊不停地涂改,才能捕捉到在腦海中一閃而過的想法。他表示,用筆寫作才是最優(yōu)雅的寫作方式,如果用打字機“機械書寫”,寫出的東西只會顯得粗俗且無禮。
直到電腦已經(jīng)廣泛普及,文字處理軟件也已十分成熟的今天,還是有很多作家仍在堅持用筆寫作。比如,美國最著名的科幻小說家艾薩克·阿西莫夫,他一生寫了近500本書,尤其擅長在書中描繪各種天馬行空的未來高科技,但在寫作方式上,他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筆完成的。
除了這些仍在堅持用紙筆寫作的作家,也有很多作家欣然選擇了用打字機和電腦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這其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就是一位資深的打字機愛好者。他在采訪中提到:“我和電動打字機結下了不解之緣,不使用打字機我簡直無法寫作。”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獨》就是在打字機上完成的,歷時兩年,但在他坐到打字機前創(chuàng)作之前,光是構思這部作品就用了整整16年。所以,馬爾克斯表示,用打字機寫作并不會妨礙創(chuàng)作靈感,相反,打字能比手寫更快地記錄下創(chuàng)作者的思想。
手寫的益處
手寫的擁護者們也承認,打字確實要比手寫快得多,但是“快”就一定等同于“好”嗎?西班牙記者瑪麗·卡門認為,正是因為寫字的速度要比打字慢,人們在手寫一篇文章時才會字斟句酌,一句話要在腦子里反復提煉多次才會被寫下來,所以,手寫出來的文章會比打出來的語句更精煉,內容更有深度。
再回到“寫字課還是否應該列為必修課”這個問題,如果僅僅是因為打字比寫字的速度更快,就要用打字課來代替寫字課的話,那人類早就發(fā)明了算盤、計算器和計算機,為什么學校還要開設數(shù)學課呢?這些計算工具明明就比人算得更快、更精確,為什么孩子們還要學算術呢?道理很簡單,因為算術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經(jīng)常用得上的,人不能太過依賴于這些工具。
西班牙神經(jīng)學專家卡洛斯·德赫洛表示,隨著生活中用到手寫的頻率越來越低,人們手寫的技能會逐漸退化,大腦也會開始萎縮。因為只有在書寫時,大腦與閱讀有關的區(qū)域才會被激活,打字就沒有這種效果了。尤其是對于孩子來說,學著用筆寫字不僅能充分鍛煉大腦,加快他們的閱讀速度,還能讓他們更容易記住文章中的信息。不能為了追求方便和快捷,就用打字課取代了孩子們原本的寫字課,這對孩子的成長發(fā)育沒有好處。
手寫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好處之外,還能讓人放松,舒緩神經(jīng)。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曾說過,讓他感到最舒服的事情,就是拿著筆漫無目的地在稿紙上涂涂寫寫。這就像東方文化中的書法一樣,是一種在書寫的過程中獲得的愉悅感,東方人認為,練習書法能夠讓人的心情平靜下來,修身養(yǎng)性,提升專注力。在這個快節(jié)奏的社會中,我們的眼睛、思緒總是在各種網(wǎng)頁之間穿梭,注意力不斷地被分散,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更應該提起筆寫寫字,讓躁動的心安定下來。
隨著時代發(fā)展的趨勢,也許會有越來越多的學校不再把寫字課列為必修課,也許手寫字在未來用到的機會越來越少,但這不妨礙手寫成為一門藝術。而那些代替了紙筆的鍵盤和屏幕,在未來說不定又會被哪些更先進的發(fā)明所取代呢!
[譯自西班牙《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