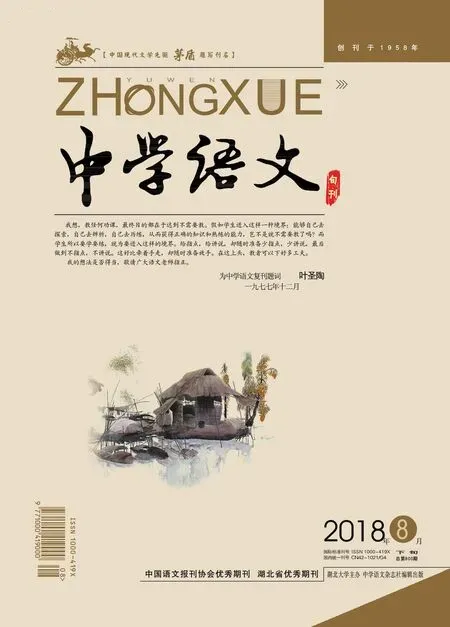諷喻癡迷今人醉 愛恨交織《長恨歌》
——《長恨歌》主題探究
李美紅
《長恨歌》是一篇長篇敘事詩,所詠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但這篇作品的主題究竟是什么,卻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爭論的問題。古人的評論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這首詩的主題是諷喻,“譏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另一種則認為它只是在寫李、楊的愛情,“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而今人在這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中又產生了雙重主題說,即認為該詩既有對明皇的諷刺批判,又有對李、楊愛情的同情歌頌。目前常見的《長恨歌》選注本不是采用愛情說,就是采用雙重說。到底是哪一種正確呢?在教授《長恨歌》時,我與學生一起進行了研究探討,我們認為《長恨歌》的主題應是諷喻,即借古諷今,諷前皇之“惑”以誡后皇。
一、品讀文本說主題
1.立足全篇看主題
《長恨歌》開篇,便直言不諱,“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一個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躍然紙上。而這也正是導致李楊感情悲劇及禍國殃民的根源。詩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畫出唐明皇得楊貴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又如,詩中描寫楊家權勢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從側面寫出唐明皇對楊貴妃的寵幸之至。全詩借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悲劇故事,暴露統治階級荒淫無恥,諷刺李隆基貪色誤國,以致引起安史之亂,告誡最高統治者應引以為戒。至于詩歌的后半部分對李、楊悵恨綿綿愛情的描繪,也不是對他們表示同情,更不是歌頌,而是通過描繪李隆基晚年的狼狽景象,曲折隱諱地諷刺他荒淫誤國而終于苦果自嘗。
這首詩敘述的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李、楊早年的逸樂和后來的長恨,都是這個故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且,這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早先的逸樂是導致后來貴妃喪生、彼此長恨的原因,而長恨則是李、楊荒淫誤國、終于殃及自身的必然結果。作為悲劇中的兩個主人公,李隆基與楊玉環具有特殊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的荒淫逸樂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發生,是這一悲劇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安史之亂的發生使他們死生異處,相見無期,因而,他們又是這一悲劇的承受者。評價《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必須注意這一點,因為它是我們理解作者對這一悲劇的感情傾向和是非評價的一個必要前提。因此,突出或忽視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將損害故事的完整性,割斷前后情節的內在邏輯聯系,其評價也就難以符合作品實際和作者的原意。
通過以上分析,《長恨歌》應該是以諷勸君王 “不惑”,勸后人引以為鑒為主要目的的。
2.對矛盾焦點(詩歌后半部分)的理解
從“臨邛道士鴻都客”到“在地愿為連理枝”四十四句,對李、楊纏綿愛情描寫的理解,也是歷代學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為,此部分與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創作至此時被李、楊的愛情故事所感,而轉變了詩的主題嗎?這也正是雙重主題說的觀點。然而,如果對白居易的創作特點進行一下研究,就可以發現雙重主題說是站不住腳的。
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新樂府》中,曾談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創作新樂府時的一個區別:“關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較,又有可得而論者,而元氏諸篇所詠,似有繁復與龐雜之病,而白氏每篇則各具事旨,不雜亦不復也。《白氏長慶集》云:‘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寅恪案:‘一吟悲一事’雖為樂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則,實則《新樂府》五十篇亦無一篇不然。……每篇唯詠一事,持一旨,而不雜以他事,此之謂不染。此篇所詠之時,所持之旨,又不復雜入他篇,此之謂不復。”
可見,白居易在創作上,主題有單一性和單純性的特點,因此《長恨歌》也不應是雙重主題的。那么我們應該怎么理解詩中關于李、楊愛情的動人描寫呢?
其次白居易對唐明皇的基本評價:“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此段文字,白居易將唐明皇與唐代公認的模范皇帝唐太宗相提并論,可以說對唐明皇的評價高得可謂至矣盡矣了。但,就在《才識兼備明于體用策一道》中還有下面一段話:
“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這一大段話,全是批判唐明皇當政時期的天寶政局的。
由此可見,白居易對唐明皇的看法客觀公正,肯定前期,而批判后期。對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詩作中有所反映,即在詩歌后半部分中把唐明皇描寫成一個“惑”于色而亂國的悲劇性君王,實際上也有為唐明皇略作開脫之意,但批評還是主要的。
再者,從寫作動機分析。從白居易的身世及當時的政治環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為,一個封建君王要能夠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樣,關鍵在于“不惑”。因為“不惑”是任用賢人的條件和前提。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后半生為鑒。白居易正是通過塑造這樣一個令人同情的、悲劇性的君王來警示今王引以為戒。因此,詩中有些問題就容易理解了,如寫楊貴妃是“養在深閨人未識”,而避唐明皇搶兒媳的史實不談,將他們的愛情描寫得純真;或后來,寫唐明皇至國破妃亡之時仍不悟,還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愛情悲劇,把一個何等癡情的君皇展現在讀者面前。然而正因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癡情”和“重色”才導致了國家的傾亡。
如此看來,詩作表面上的矛盾實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二、從詩教傳統看主題
1.溫柔敦厚、委婉含蓄的詩教傳統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有著悠久的“詩教”傳統。所謂“詩教”,本指《詩經》“溫柔敦厚”的教化作用,后來也泛指詩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是“詩教”的最早也是最積極的倡導人和身體力行者。“溫柔敦厚”是孔子的詩教對人的政治道德和思想修養的基本要求。在政治上,統治者要行仁政,被統治者要守禮制而不犯上,怨刺而不作亂,思想感情的表達要含蓄委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論詩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其代表封建意識形態的詩教,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甚至至今仍影響著國民的性格。在漢代,《毛詩大序》就是繼承了孔子“思無邪”和“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說。它還要求諷諫要“發乎情,止乎禮義”,把孔子“溫柔敦厚”的詩教具體化。在此基礎上,《毛詩小序》把各篇詩定出美和刺,形成了《詩經》的“美刺說”。及至唐時,文人強調詩文與政道的合一,提出“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反映現實”與“譏刺”相結合,堅持傳統的“下以風刺上”,發揮孔子“詩可以怨”之精神,即是保持傳統不變,強調詩歌對社會的功用,重視委婉的美刺與諷喻。
2.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白居易堅持委婉諷喻之道,甚至直切袒露的譏刺。大致從青年時代開始,一直到四十三歲貶官江州司馬之際,白居易對封建君王抱著較大希望,有極高的參政熱情,屢次上書,指陳時政,倡言蠲租稅、絕進奉、放宮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諍。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秦中吟》《新樂府》等大量諷諭詩,促進新樂府運動,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自覺地以詩歌作為 “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鋒芒所向,權豪貴近為之色變。
白居易是中唐新樂府運動的主要代表,繼杜甫之后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理論上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唐玄宗李隆基與貴妃楊玉環之間的愛情悲劇,因與安史之亂密切聯系,有著嚴肅的政治色彩,它往往成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關注的對象;而其情事始末之獨特、生動、曲折,又極富于傳奇色彩,故而受到歷代詩人文士的矚目。由此,出現了以此為題材的大量的文學作品,而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恨歌》更是其中翹楚,當然激流勇進,銳意改革,極盡諷喻之能事。張倫的話說得好:“白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楊妃之始末,雖史傳亦無以加焉。蓋指其覆華,托為聲詩以諷時君,而垂來世”。詩中白居易借“漢皇”來說事,雖諷勸卻又委婉含蓄,美飾掩蓋了許多事實,溫柔敦厚地諷喻后主后人。所以,后一部分給人以傷感同情的錯覺,但是諷喻才是最終目的。可見,《長恨歌》的主題是諷喻,應歸為諷喻詩才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