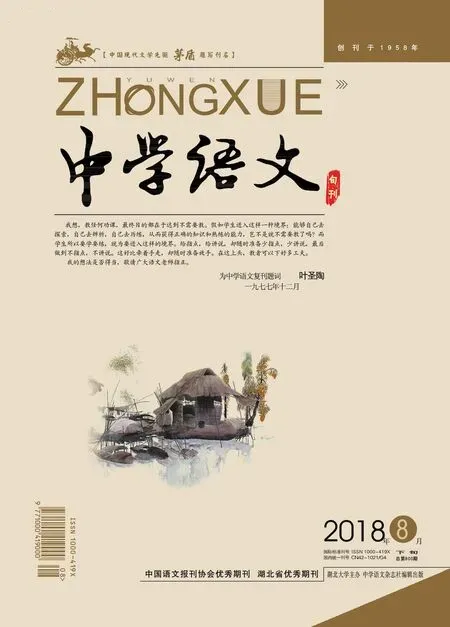一蓑風雨 兀自風流
——淺談蘇軾的黃州精神
張 琳
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星空中,蘇軾如同一顆璀璨的明珠,無論經歷多少滄海桑田,依然閃爍著奪目的光芒。蘇軾集散文家、詩人、詞人、書畫家、學者、美食家等于一身。歷經諸多磨難,他依舊瀟灑豁達,自有一股豪俠之風,令人蕩氣回腸。他身上散發的無窮魅力,至今讓人敬仰贊嘆。
一、從云端跌到低谷
1.一舉成名天下知
宋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同父親蘇洵同時參加科舉考試,其才華深受主考官歐陽修和梅堯臣的嘆賞,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青年才俊,滿腹經綸,一腔抱負,卻在遭遇新法與保守派的斗爭時,跌下云端,開始被貶謫的坎坷一生。“烏臺詩案”更使他受到沉重的打擊。
2.寂寞沙洲冷
貶謫黃州是蘇軾仕途的重大轉折點。黃州是荒僻之地,蘇軾初到黃州的生活也十分艱難。在《答秦太虛書》中,他寫道: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寒食雨二首》中描繪大雨之中:小屋如漁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送沈逵赴廣南》寫謫居生活: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里。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饑寒疑死矣!從這些文句中,我們不難看出蘇軾初到黃州的失意、憤恨、悲傷,思想處于低谷。
二、一蓑煙雨任平生
讓我們敬重的是蘇軾并沒有被生活打倒。在黃州,蘇軾開啟了自己生命的轉型。
1.曠達樂觀的稟性
《游沙湖》中寫道蘇軾的生活困境“往相田”,他被貶黃州,沒有絲毫的經濟來源,然而生活的窘迫沒有讓他陷入絕境,他召集全家自己動手蓋了雪堂;他退下文人的長衫,穿上農夫的短裝,開荒種田。當時甚至有人嘲笑他如此落魄,還這么高調,他卻樂觀地稱自己為東坡居士,從此“東坡居士”響徹了中國文學史上近千年!
他一身才華,滿腹經路,一腔報國熱情,卻遭人嫉恨打擊,淪落于窮鄉僻壤之中,英雄無用武之地。同李白相比,他少了幾分桀驁不馴,多了幾分隱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幾分痛心疾首,多了幾分豁達樂觀。這正是蘇軾異于他人,超凡脫俗的稟性。
2.元氣淋漓的赤子心
蘇軾的性格真率,不善于做表面功夫,有話也藏不住,用他自己的話說:“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蘇軾待人不分高低貴賤,不分男女老幼。《游沙湖》中寫到蘇軾遭遇貶官,又得病,這對誰來說都是一件令人心情郁悶的事。可蘇軾卻發現痛苦生活中也有積極的一面。于是,他和耳聾的村醫龐安常結友,興致勃勃一起同游清泉寺。“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可謂“老夫聊發少年狂”,既是自勉,表達老當益壯,不墜青云之志,他仍渴望成就一番功業的樂觀進取的精神。蘇軾熱愛生活,樂觀向上,處處能體會到生活的甘美,發現美好的事物。這曲生命常青的頌歌,更表達了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人生哲理。
3.熱愛生活的進取心
蘇軾雖然仕途坎坷,歷經患難,貶所黃州亦為荒僻之地,苦悶凄悲的心情不難理解,但他并沒有消沉頹廢,而是能夠通變達觀,熱愛生活,甘苦自適。
陶淵明和蘇軾在仕途中同樣嘗遍酸甜苦辣,政治抱負得不到施展,又不愿隨波流,“卻躬耕”便是他們“了了”之后的選擇。淵明是自愿的,蘇軾卻為環境所迫。此時他已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地道的田間老農,親身參加體力勞動,還為自己能擁有寧靜平和的生活而欣慰。
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善于調節自己,善于使自己瀟灑起來的一個真實的自己,這就是真實的蘇軾。蘇軾共在黃州生活了四年零四個月。他開始思考和探索許多問題。其結果是他的政治態度、生活態度,以及藝術創作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他開始更多關注個體人生的底蘊和價值,其作品也常常直接抒寫對自然、社會和人生命運的思考和感悟。回想自己的人生歷程,蘇軾深深地感到一種空漠、無聊、孤寂與憂郁。然而,種種閱歷,以及在黃州的生計、游歷、與儒釋道思想的接觸,蘇軾也表現了熱愛生活、積極進取,與超然淡泊、曠達豪放的一面。
4.一腔赤熱的報國心
建功立業是每個熱血男兒的追求,蘇軾也不例外,盡管多次被貶謫,可為國為民之心從未停止。《密州出獵》中“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西北望,射天狼”,聊發少年狂氣,渴望報效朝廷。被貶到杭州,他治理水患,疏浚西湖,修筑蘇堤。《赤壁賦》中描寫曹操“一世之雄也”也流露他“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現實處境的無奈落寞。
然而,身為“罪臣”的蘇東坡,在貶謫之地不忘“仁義為本”“匡世濟時”。他上書鄂州太守朱壽昌,希望官府能制止黃州溺嬰的風俗。為此,他組織救護,募集錢物,自己還捐款十千,使黃州民風為之一變。他還從切身感受出發,推己及人,表達對百姓的深切同情。作于元豐四年《浣溪沙》五首:“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表達了詩人“視民如視其身”的仁厚情懷。
從中年至晚年,蘇軾先后分別被貶黃州、惠州、儋州,在其生存狀況極其艱難、無權無錢的境況下,他還力所能及地為當地老百姓謀福祉,他堅定的惠民之志,過人的惠民之術值得我們敬仰和推崇,并惠澤千年后世,為歷代為官者提供了借鑒和思維的空間,是值得挖掘的精神財富。
東坡的魅力,絕不僅僅在其詩作,而在于他歷經磨礪卻日益純凈、天真爛漫的大情懷。黃州、惠州、儋州,是從蘇軾到蘇東坡的精神轉向,記載著他從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記載著他從失意而至詩意的精神躍升,記載著他從走向大境界的踽踽背影。蘇軾在被貶的路上,從黃州時期的擺脫功利態度,到惠州時期的身世永相忘,再到儋州時期的“寄我無窮境”,一路走來,一路頓悟,成就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