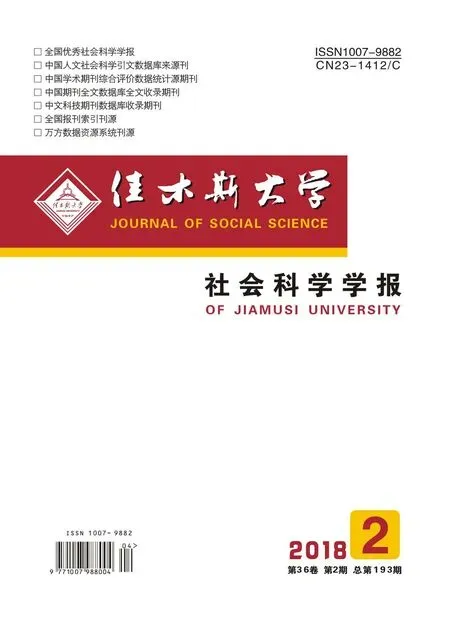文化夾縫中生存之艱難*
——《群山回唱》中阿富汗移民的身份重構
余意夢婷
(桂林旅游學院 外國語學院, 廣西 桂林 541001)
2013年5月出版的小說《群山回唱》是當代世界文壇知名的美國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又一力作,因為這部作品,2014年胡塞尼還獲得了約翰·斯坦貝克文學獎。《群山回唱》展現的是一群阿富汗移民在文化夾縫中艱難生活的境遇。由于討論到少數族裔與邊緣性群體的生存問題,這部作品備受國際文藝界的關注。本文之目的就是通過對阿富汗移民身份追尋過程的分析,找出其解除身份焦慮,再次身份重構的方法,以期為以后少數族裔和邊緣性群體解決身份歸屬問題提供借鑒。
一、阿富汗移民的生存困境
《群山回唱》講述的是一群阿富汗平民由于戰爭與饑餓不得不逃亡他國,在異鄉艱難求生的故事。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在文化夾縫中痛苦掙扎的阿富汗移民形象,比如妮拉、帕麗、小帕麗、阿卜杜拉、伊德里斯、鐵木爾等,而其中又以妮拉和帕麗最為典型。
妮拉是《群山回唱》中最悲催的人。她雖然出生在貴族家庭,但由于血統不夠純正,所以族人總是以怪異的眼光看她。十歲以前,妮拉父親忙于工作,對她疏于照顧,所以她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與法國人母親生活在一起,接受的是母親給予她的法式教育。十歲之后父母離婚,妮拉由于失去母愛而感到極度焦慮,為了安撫妮拉,父親請來家庭教師給她傳授阿富汗文化,這兩種文化交織在一起,讓她感到極度混亂和無所適從。妮拉希望婚姻能改變一切,但婚后丈夫對她的不尊重與漠視讓她對生活感到絕望,于是她背叛婚姻,遠逃外國。在異國她一直沒有找到體面的工作,只能靠寫作和開小店謀生。但她的詩歌卻得不到宗主國主流社會的認同,不久小店又倒閉了,就連男友也背叛了她,她窮困潦倒,心靈空虛,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帕麗是《群山回唱》中對自己身份最感到迷惘的人。她是妮拉的養女,一開始她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隨母親移民國外后,帕麗在那里念書,上名牌大學,然后留在大學里做老師。系里只有兩名女性教師,她是其中之一,又是學校最年輕的教授,可以說她是事業有成的知識女性。而且她結婚后的生活也很富足,并有個愛她的丈夫和三個聰明的孩子,但她并沒有感到真正的快樂:首先她懷疑自己的出生,想了解自己的過去,但母親卻絕口不提;她從小在宗主國長大,又是高級知識分子,她以為自己早已完全融入了那里的主流文化,但是與同事和朋友的接觸,以及一次雞尾酒會上與別人的對話,讓她意識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并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同,于是她萬分迷茫和無所適從。
二、文化夾縫中的身份焦慮
在異國他鄉生活的阿富汗移民被文化身份問題引發的焦慮壓得透不過氣來,他們在文化夾縫中不斷努力掙扎、艱難求生。
(一)跨界生存的掙扎
作為游走在兩種文化邊緣的混血兒,妮拉的一生都在痛苦中度過。法國的思想與阿富汗的文化一直交織于她,并影響著她,使她對自己文化身份的認識十分模糊與混亂,她有時甚至不知道自己屬于哪一邊。查爾斯·泰勒曾在《承認的政治》一文中指出“一個人的認同,部分是由他人的承認引起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者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認,就會對個人認同造成影響”[1]208。于是為了追尋自己的文化身份,妮拉必須要得到父親與族人的認同,于是她開始用叛逆的行為來引起大家的關注。
在妮拉的民族里,女性是不可以著暴露服裝的,但她卻故意背道而馳:她“穿一條短袖的橘紅色裙子,短至膝蓋。她光裸著兩腿,雙腳也赤露在外”,甚至還“點燃一支香煙,不緊不慢地吸著”[2]79。妮拉希望改變自己的外表,用出格外露的穿著和不合禮教的舉止來獲取族人的認同,但她卻以失敗告終,被族人視為粗俗放蕩的女人。嘗試失敗后,妮拉又希望婚姻能拯救自已,但是不平等、不自由的婚姻更讓她喘不過氣來,她想改變卻遭到了丈夫的漠視,于是她決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開私人派對,抽煙喝酒,甚至通過亂搞男女關系來報復婚姻,由此她被族人視作傷風敗俗的代表。妮拉采用反抗禮教的方式來尋求身份認同,但她再次失敗。戰爭爆發后,妮拉逃到了國外。在那里妮拉本想開創全新的生活,但事實卻給她以沉重的打擊:她找不到體面的工作,只能開家小店并以寫作為生。她的詩歌一直得不到主流社會的認可,只是在臨死前一年才收到一家雜志的專訪。她的書店因經營不善而倒閉,最后連男友也離她而去,于是窮困潦倒的她只能酗酒消愁。雖然她熱愛生活,勇敢戀愛,但是生活卻一次次傷害了她,她“不顧一切地沖向幸福卻兩手空空”[2]226。
妮拉作為阿富汗裔移民,自然擁有雙重文化身份。所謂“文化身份”有兩層含義,它既指“某個個人或群體據以確認自己在一個社會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確的、具有顯著特征的依據或尺度”,又可指“某個人或群體試圖追尋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的過程”[3]283。妮拉在宗主國,顯然屬于少數族裔和邊緣性群體,雖然她代表的是少數文化,但她仍希望被宗主國的多數文化所接受、所認可,她遇到種種困境,雖然奮勇掙扎,但最終事與愿違,這種身份認同感的缺失,讓她感到極度的焦慮。
(二)身份迷失的痛苦
阿富汗移民中也有通過自身努力在宗主國獲得成功并過著富足生活的人,他們本以為自己已完全融入了宗主國的主流文化中,但仍然無法驅散身份異質帶給他們的焦慮感。功成名就的大學女教授帕麗就是這其中的一員。
帕麗六歲時就隨養母移居國外,她對祖國的記憶早已模糊,但她卻又一直對自己的身世與民族身份感到好奇,她想從母親那里探知一切,但卻知之甚少。長大后,她為人豁達、處世成熟,深得同事們的喜愛,而且也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她完全生活在幸福中。她以為自己早已完全融入宗主國的主流文化,但實際上她的文化身份并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作為少數族裔移民,她將一直具有這種雜交的文化身份,她依然會被主流社會視為“他者”,這種強烈的民族排異感讓帕麗感到焦慮。但是按照賽義德的看法,這種“他者”地位是可以改變的:“自我或‘他者’的身份絕對不是一件靜物,而是一個包括歷史、社會、知識和政治諸方面,在所有社會由個人和機構參與競爭的不斷往復的過程”[4]21。既然可以轉變,所以“他者”們一直在力圖改變它。帕麗想通過找回自己身為阿富汗人的民族之根,來緩解這種“他者”的窘迫感,但她對阿富汗語言和民族文化一竅不通,于是她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對自己的一切都感到迷茫。
帕麗永遠無法改變她少數族裔的身份,無論她在宗主國是多么的事業有成、多么的生活富足,但她在身份認同上仍然是倍感焦慮。她迫切希望能完全融入宗主國的生活與文化,并被完全接受,但是她在追尋這個夢想的時候,才恍然發現自己仍然是這個文化世界中的“他者”,仍然被視為邊緣性群體中的一員。于是這種雜交身份,讓她始終存在疑慮,如何尋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將成為帕麗永遠也擺脫不了的夢魘。
三、雜交文化下的身份重構
在追尋文化身份的過程中,阿富汗移民們一直都是飄在旅途中的“游客”,很難找到“終點站”。但是他們從不灰心,仍然堅持不懈地進行著這個身份追尋之旅。
(一)民族身份的回歸
在漫長的身份追尋過程中,帕麗終于明白,要最終確定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首先就應找回自己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之根。
帕麗尋回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第一步就是學習波斯語。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只有把載有文化的語言學會了,才有可能理解和掌握這種文化。帕麗很小就離開祖國來到異鄉,她能說一口流利的外國語言,但卻對自己的民族語言一竅不通,這體現了她民族身份的缺失。為了了解自己的民族,填補這種身份缺失,帕麗開始學習波斯語。個體存在感的缺失也是帕麗丟失民族文化身份的又一個原因。帕麗很小就與養母一起離開阿富汗,離開了自己真正的親人,在養母那里她感受不到自我的個體存在,當大學同事奚落她時,她也對自己的個體存在產生了質疑。所以她急需找回自己的民族之根,只有找回了民族之根才有可能重新自我定位。正如薩義德所說:“我覺得回歸的真正意義在于讓回歸者回到自身,也就是說回到歷史,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么,為什么發生,我們究竟是誰。我們是來自那片土地的一個民族,我們也許不在那兒生活,但我們的根在那兒,我們的歷史不容忽視”[5]8。
霍米·巴巴曾說過,移民文化是一種“遷徙文化,只有在文化差異下找到協商的空間,移民的文化身份才有改寫的可能”[6]39。帕麗原以為自己早已完全融入宗主國主流文化。但是當同事奚落她時,她才猛然發覺自己只是宗主國主流文化中的“他者”和“異類”,才清晰地體會到原有民族文化身份對自己的重要性。于是為了尋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帕麗踏上了艱難的尋根之旅。在這個旅途中帕麗的文化身份是動態變化的,她一直都在改寫自己的身份狀態:她先是承認自己的雜交身份,然后是尋回民族身份,接著是不斷調整和改寫,最后她在自己的民族身份和現實身份中尋找到了平衡點,重新建構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身份,在帕麗的不斷努力下,她真的成功了。
(二)雜交身份的重構
阿富汗移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種種與文化身份相關的問題,只有通過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構才能解決。《群山回唱》中的鐵木爾就是重構雜交身份的典型代表。
鐵木爾是為逃避戰爭而全家離開阿富汗的,最后他終于在美國定居下來。在加利福尼亞生活的他不像其他阿富汗移民一樣還用原來的阿富汗名,他改用了英文名。自從改名之后他的生意變得非常紅火,所以他認為是英文名的使用改變了他的命運,給他帶來了福氣。在加利福尼亞,鐵木爾真正融入了美國人的生活,他像美國人一樣為人處世,甚至還模仿美國人的生意作風,到處投機倒把、四處游說,網絡生意,逐漸他在美國獲得了成功,過上了受人尊敬的生活。但是,鐵木爾從不忘本,始終銘記自己是阿富汗人,他常常和手機里阿富汗群中的朋友聊天和聚會。發財回到阿富汗后,當鐵木爾看到小羅斯因為貧窮而做不了手術時,他能伸出援助之手,為羅斯準備手術經費。他生活在美國,并融入美國的文化中,但是他不忘記自己的民族之根,始終記得自己的民族之魂。
鐵木爾是成功的阿富汗移民。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首先承認而不是否認自己所遭遇的文化迷茫,在文化困境中,他能清醒地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異族文化身份之間的差異性與可交融性,他能快速地重新認識自己的雜交文化身份,并能立足于宗主國,重建新的、屬于自己特有的文化身份。
四、結語
《群山回唱》聚焦于阿富汗移民身份問題的重構,引起了國際文藝界對世界少數族裔移民生存境況的思考。通過對阿富汗移民身份追尋過程的分析,我們找到了少數族移民解除身份焦慮的方法:清醒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異族文化身份之間的差異性與可交融性,欣然接受自己的雜交文化身份,并立足于宗主國,重構自己特有的文化身份。希望這一身份認同方法的提供能為以后少數族裔和邊緣性群體移民現實中遇到的文化身份困境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1]趙稀方.后殖民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卡勒德·胡塞尼. 群山回唱[M]. 慷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4]愛德華·薩義德.東方不是東方——瀕于消亡的東方主義時代[J]. 唐建清,張建民,譯.天涯,1997(4).
[5]王逢振.愛德華·薩義德訪談錄[DB/OL].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 2001.
[6]張淼.跨界生存中的文化身份追尋之旅[D].齊齊哈爾大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