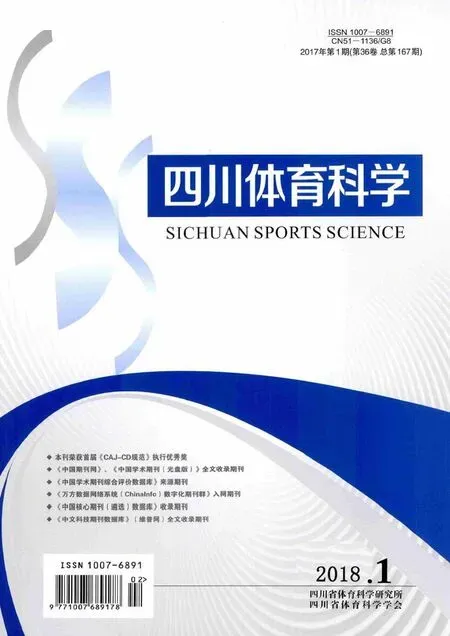世界優秀吊環運動員成套動作編排特征研究
馮德森,余文祿,趙元吉
?
世界優秀吊環運動員成套動作編排特征研究
馮德森1,余文祿2,趙元吉1
1.成都體育學院,四川 成都,610041;2.成都大學體育學院,四川 成都,610106。
運用文獻資料法、錄像觀察法、比較分析法和數理統計等方法,梳理里約奧運周期的3次世界錦標賽和里約奧運會吊環單項決賽前8名運動員的32套動作進行研究,旨在對其動作組別、難度價值和編排特征進行統計和分析,結合2013年和2017年男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探析世界優秀吊環運動員成套動作編排的規律。研究得出:(1)動作組別的變化使動作選擇趨于豐富,屈伸上類動作的選擇更加趨于明確;“后擺上成靜止”類動作深受運動員喜愛;“力量動作和靜止動作”使用頻率最高;(2)下法動作較為單一,E組以上難度的下法還需多加創新和挖掘。成套動作的難度和完成要充分平衡,“以技術難度打天下”的理念要向以“力量、難度和藝術三者的完美結合”轉變;(3)新規則的評分要求更加細化,動作組別由5變4,難度價值有升有降,動作選擇愈加豐富,成套動作的編排將會越來越多樣化、個性化、合理化、藝術化以及高難度化;(4)在東京奧運周期內,吊環項目的成套動作D分也將會出現5%左右的降幅。
競賽與訓練;優秀運動員;吊環;成套動作;編排;特征
體操是一項以難和美共存的體育項目,“吊環王”陳一冰曾在國際賽場上獲得28枚金牌。而后起之秀的劉洋、尤浩、鄧書弟、林超攀也成為這個項目的焦點,在里約周期中嶄露頭角[6]。里約奧運會后國際體操聯合會發布了2017-2020年男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標志著2020年東京奧運會備戰沖鋒號的響起。但在里約奧運會上中國隊在吊環項目上的低迷表現實在讓人嘆息,與北京奧運會、倫敦奧運會相比。中國體操隊走下了不敗的神壇[3]。根據運動訓練學理論,競技成績由自身表現、對手的表現和裁判評定結果3方面決定。由于體操屬于難美性項目,其競賽成績由裁判打分決定。因此,一出現失利都歸結于裁判因素。但是,自2013年引入參考裁判后,每一位運動員的評分都會更加的公平、公正。忽略了對手和自身競賽能力,而糾結于裁判因素顯然不是明智之舉。如何看待“里約之殤”,如何“再續輝煌”,是研究的主要目的[8]。以里約周期內的體操比賽為研究對象,以2013、2017年男子競技體操規則為依據,從動作選擇、成套編排、難度價值、規則變化等幾個方面對吊環項目進行分析,總結經驗、找出差距,期望能為中國隊備戰東京奧運會提供參考。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依據國際體操聯合會(FIG)2013、2017年頒布的國際體操評分規則,以里約奧運周期的第44、45、46屆世界體操錦標賽和第31屆里約奧運會(共計4次世界大賽)吊環單項決賽前32名運動員作為研究對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獻調查 通過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檢索吊環項目發展趨勢及成套動作編排等相關文獻;登錄中國體操網、國際體聯、美國體操在線官方網站收集4次世界大賽相關統計數據和信息。
1.2.2 錄像觀察 通過觀看第44、45、46屆世界體操錦標賽和31屆奧運會吊環單項決賽電視直播和錄像資料,對32套吊環單項決賽成套動作組別和內容等進行觀察、記錄和解析。
1.2.3 數理統計 運用Excel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對4次世界大賽吊環決賽32套成套動作編排的動作類型選擇、難度動作選用、動作編排形式等因素進行統計分析。
1.2.4 邏輯分析 通過文獻的二次研究、錄像解析、官網數據的核實以及數理統計等方法,為相關闡釋提供邏輯前和分析依據,在此基礎上,嘗試對世界優秀吊環運動員成套動作的編排特點、成套動作編排的發展趨勢等進行歸納和總結[12]。
2 結果與分析
2.1 成套動作分析
“動作結構就是動作的各個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和相互關系。”[1]成套動作結構是指運動員按照規則,根據自身身體素質和特點將各單個難度動作進行科學、高效的搭配和排列[7]。“吊環成套動作由擺動、力量和靜止動作組成。這些動作和連接是通過懸垂、經過或成支撐,經過或成手倒立來完成的,以直臂完成動作為主。”[2]從表1來看,里約周期內的4屆比賽成套動作結構比較趨于一致,主要難度涉及B、C、D、E、F組難度的動作共計324個。其中B組難度動作4個,占1.23%;C組61個,占18.83%;D組142個,占43.83%;E組72個,占22.22%;F組45個,占13.89%。由此可以看出,D組、E組動作是運動成套動作結構中主要的難度動作。而C組、F組比例較小,特別是F組動作在成套動作結構中是運動員競技實力高低的直接表現。據統計,成套動作結構比較緊湊的有5名運動員,他們動作結構相對集中。就獲得過前3名的運動員成套動作看,中國、俄羅斯、希臘、美國、巴西實力較強。特別是中國隊表現尤為突出,4屆比賽均有運動員進入決賽,并獲得了4塊獎牌,成套動作結構也比較精煉,難度主要集中在D組、E組、F組等動作上,充分反映出中國在吊環項目上的實力。同時,美國、巴西、希臘、俄羅斯、法國等運動員實力也比較接近,是有力的獎牌爭奪點。

表1 4次大賽吊環單項決賽運動員成套動作結構統計一覽
從動作難度價值來看,B組難度基本穩定,常用于過渡和調整動作;C組難度先升后降;D組動作是成套動作的支撐,E、F組動作是成套動作的亮點,在奧運會時明顯增加,這樣難度的選擇與運動員競技水平的發揮和比賽要求完全一致。從44-46屆世錦賽到31屆奧運會來看,C組動作的選擇波動幅度較大,D組動作的選擇呈“V”字形變化趨勢,E組動作在奧運會前夕達到了最高點,而F組動作基本呈曲線上升趨勢。每一屆奧運會結束后都是一個新老交替的過程,所以運動員在動作選擇上難度較低,以鍛煉新人為目的。而奧運會前夕的世錦賽一般是奧運會入場券的爭奪,運動員為了保證進入奧運會,一般不會選擇難度較大的難度動作,以穩定發揮為主。奧運會比賽是運動員的最高榮譽,為了能夠獲得獎牌,都會將自己的D分盡量提高,已獲得較高的起評分,提高自己獲得獎牌的實力。

圖1 4屆比賽吊環單項決賽運動員動作難度選擇變化趨勢圖
2.2 難度動作使用情況分析
由于2017-2020版新規則發布以來尚未舉辦過世界大賽,故本文以里約周期4次大賽動作為研究依據。參考2013-2016年男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和2017-2020年男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進行分析。為了便于分析,文中對動作組別分類仍然采用2013版規則分類進行數據統計。2013版規則將吊環項目動作分為了5個組別:第1組別(屈伸上和擺動動作),第2組別(擺動至手倒立動作),第3組別(擺動至力量靜止動作),第4組別(力量動作和靜止動作),第5組別(下法動作)。據表2,4次世界大賽力量動作和靜止動作使用比例頻率較高,達到了38.2%;其次是擺動至靜止動作,占21.4%;第三是擺動至手倒立動作,占15.8%;最后是屈伸上和擺動動作,占14.6%。
2017版新規則將吊環動作組劃分為:(1)屈伸上和擺動動作及擺動經倒立或成倒立(2s);(2)力量動作和靜止動作(2s);(3)擺動至力量靜止動作(2s);(4)下法等4個組別。原有的第2動作組即擺動成倒立(2s),并入第1動作組內;原有的第4動作組即力量動作各靜止動作(2s)移至第2動作組;而原來屬于第1動作組的屈伸上/前擺上成直角支撐動作,則移至第3動作組。同時,以前的組別難度加分也將會由2.5分下降到2.0分[2][4]。

表2 4次大賽各組別動作使用情況一覽
注:文中僅統計了C組及其以上難度的動作。
2.2.1 屈伸上和擺動動作使用情況 2013版規則上共有34個動作屈伸上和擺動動作。主要涉及“李寧、古佐基、宏馬、雅瑪瓦基、喬納森以及屈伸上和支撐擺動等類型動作”。據表3,該組別動作在大賽中使用的主要有5個,分別為“古佐基(2)、奧尼爾(3)、雅瑪瓦基(12)、喬納森(30)”4個類別動作[2][4],使用率分別占該組別動作的4.3%、6.4%、25.5%、63.8%。其中,向前空翻動作比向后翻動作使用頻率更高。從動作完成角度考慮,向前空翻動作更容易發力,配合懸垂后擺動作,更加有利于運動員較高質量的完成。特別是喬納森,雅馬瓦基這兩個動作成為每一位運動員的首選動作,也是周期的潮流動作。像蘭伯特斯(荷蘭)、劉洋(中國)、阿布梁齊(俄羅斯)、杜拉奇(英國)、伊格納蒂耶夫(俄羅斯)等將這兩個動作同時編排在一套動作中。吊環動作的完成主要靠運動員上肢力量來完成,因此在編排成套動作時,從體力角度都不愿選擇高難動作。一些“A”“B”組別的動作所使用的頻率也較高,僅在成套動作中以過渡或調整使用,如“向前慢轉肩、前轉肩、本間、大回環”等。至2017版規則將擺動經或至倒立動作劃入第I組別后,整個屈伸上和擺動動作并擺動經或至倒立動作涉及33個,有部分動作被劃入到擺動至力量靜止動作如“前擺上成直角支撐”等。這也使得每一個動作組的動作更加趨于一致,運動員選擇動作也更加明確。

表3 4次大賽屈伸上和擺動動作使用情況一覽
2.2.2 擺動至手倒立動作使用情況 擺動至手倒立動作屬于擺動至靜止類動作,吊環又是所有器械項目中唯一沒有固定的。規則規定在成套動作中,靜止動作要直臂完成,必須直接到位,不應有姿勢和位置的調整;環繩不能有交叉;環繩不能有過多的擺動等。由于吊環的擺動半徑較大,最后的動作又是倒立狀態的靜止,因此難度較大[10]。2013版規則在“擺動至手倒立類”動作組別中僅有6個動作,其中B組2個,C組3個,D組1個。這樣以來運動員在成套動作編排時可供選擇動作有限,如表4所示,4次大賽中“后擺成手倒立”使用總計39次,占76.5%;“前擺上成手倒立”使用共計12次,占23.5%;就45、46最近兩屆世錦賽來看,“后擺成手倒立”的頻率增加明顯,僅個別運動員沒有編排此難度動作。2017版周期將“屈伸上和擺動動作”和“擺動經倒立或成倒立(2s)”合為第Ⅰ類動作,無疑將擴大了運動員的動作選擇面。而在動作編排上,“擺動成手倒立動作(2s)必須在被認可的最好10個動作中。”2013年規則,此類型動作僅僅是滿足組別要求,為了0.5的加分。而在2017年規則改為編排上的要求,如沒有完成該動作,D裁判組將扣中錯0.3分,這些新的規定,使運動員更能夠結合自身實際進行不同風格的成套編排,在新周期內這個類別的動作可能會更加集中。

表4 4次大賽擺動至手倒立動作使用情況一覽
2.2.3 擺動至靜止動作使用情況 就“擺動至靜止動作”難度動作價值觀察,主要分為3個類型動作,(1)懸垂擺動類,如:“前擺上成靜止,后擺上成靜止”;(2)(向前/向后)屈伸上成靜止,如:“屈伸上成水平十字、屈伸上成前水平十字、莫利納里”等;(3)支撐擺動成靜止,如:“直臂后翻上成水平”[2][4]。表5所示,“懸垂擺動動作”中“后擺上成靜止”類動作共有4個。4次大賽中占到整個動作組的半壁江山,占76.7%。第2類和第3類動作幾乎無人問津[9]。在新規則中,限制了該組別動作最多能夠連續使用3個,如果再做這類組別動作,中間必須完成一個至少是B組難度的擺動動作(屈伸上/向后屈伸上除外),同時,該B組難度動作必須是計算在10個有效動作中,這樣才能獲得D裁判的認可。這樣的限制會使運動員更多的去選擇其他組別的難度動作,以此來使成套動作的編排多樣化。

表5 4次大賽擺動至靜止動作使用情況一覽
2.2.4 力量動作和靜止動作使用情況 “力量動作和靜止動作”是吊環所有動作組別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難度組別(據表1、6),4次大賽分別占全部動作的36.6%、40%、37.5%、38.75%。其中“阿扎良十字、水平十字落下成十字”是該難度組別中排名第一,分別有20人次、28人次,占該組別動作總數的16.3%、22.8%。另外,巴蘭丁(1、2)、直臂直體后滾慢翻成水平支撐、直臂直體后滾慢翻成水平十字支撐、從背水平壓上從水平十字支撐等以不同支撐動作結束的動作都是該組別的熱點動作。從難度價值看,整個組別難度為“24D43E28F”,E、F組高難動作是運動員的主力動作,也是運動競技能力水平的表現。在完成該組別動作時,運動員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控制能力,從擺動動作開始到靜止動作結束,或者直接由力量動作完成,要求相對比較高,環上的輕微晃動都會被扣分。而且對于水平十字和水平支撐動作來講,要求身體必須在一個平面上。從動力性動作開始到靜力性動作結束,在水平類動作上難度較高,很容易出現失誤,而以前水平為結束動作幾乎無人使用。因此,運動員在選擇這一類動作時一般完成后擺上成十字(水平十字)、以純力量的慢拉上成十字等類型動作是主流選擇。

表6 4次大賽力量動作和靜止動作使用情況一覽
2.2.5 下法動作使用情況 在下法動作的選擇,國際體操評分規則規定,所有單項下法動作組別符合D組或D組以上難度的下法才完全滿足獲得0.5的加分。[5]就4次大賽下法動作看,里約周期32位運動員所使用的下法動作只有三個,分別為:直體后空翻兩周轉體360°下(D組)、占下法動作總比例的65.6%;直體后空翻兩周轉體720°下(F組)、占下法動作總比例的28.1%;團身后空翻轉體720°(E組)、占下法動作總比例的6.3%。而直體后空翻兩周轉體360°下(D組)被大多數運動員所使用。在2017版國際體操新規則中,已經有了更多F組和更高一級的動作選擇。從賽事和項目發展的角度來看,下法的多樣性、新穎性、個性化能夠給整套動作編排帶來不一樣的效果,必將成為吊環發展的重點和任務,而落地的穩定性是運動員制勝的關鍵之一。[2][4]
2.3 成套動作成績分析
體操規則規定:“D”分的內容是10個難度動作的價值之和,包括最好的難度價值動作加上下法,計算動作組別價值。“E”分從10分開始,以0.1分為單位進行扣分。在44屆吊環世錦賽最高難度為6.9分,最低6.7分,難度分的平均分值6.825分;45屆吊環世錦賽最高難度為7.0分,最低6.6分,難度分的平均值6.8分;46屆吊環世錦賽最高難度分為7.0分,最低分為6.6分,難度分的平均值為6.8分;第31屆奧運會最高難度分為7.0,最低難度分為6.6。第44、45、46屆世錦賽和第31屆奧運會吊環單項決賽“D”分最大差值分別為0.2、0.4、0.4和0.4;“E”分的最大差值分別為1.334、0.433、0.4和0.867。

表8 44、45、46屆世錦賽和31屆奧運會吊環決賽32名運動員成績統計一覽表
從表8統計顯示,運動員在追求難度的同時不得不考慮“E”分在成套動作分值的作用,就第46屆吊環冠軍佩爾羅尼亞斯(希臘)來講,他的“D”分為6.8分,而他的“E”分高達9.0分,因為他在獲得第46屆世錦賽冠軍之前,參加了不少國際大賽,先后獲得歐錦賽和歐洲運動會兩枚金牌。并在“科特布斯”和“多哈”世界杯與巴西名將同場對決,最終收獲銀牌。佩爾羅尼亞斯的金牌主要就是依靠完美的“E”分戰勝了擁有“D”分為6.9和7.0分的全部運動員。從而獲得了希臘歷史上第一枚世界錦標賽體操金牌。在2015年賽季中,2013金牌和2014銀牌獲得者扎內蒂(巴西)也是底氣十足,為了準備2016里約奧運可謂飽經滄桑,六次比賽獲得五枚金牌,其中最好成績是在巴西舉行的世界杯獲得金牌成績,“D分”為6.8,“E分”為9.1。這一成績均超過了三屆世錦賽的所有成績。2016東道主的扎內蒂對“D分”“E分”的準確把控,再次證明“E分的決定性作用”。
中國隊在第45屆世界體操錦標賽劉洋和尤浩分別獲得金牌和銅牌,其中劉洋“教科書”般動作獲得裁判和業內人士的一致贊譽。雖然尤浩的“D分”都要高于劉洋,但其“E”分出現失誤,特別在結束動作的穩定性上稍差一些,導致與金牌無緣。在2016里約奧運賽場上,尤浩的“D分”依舊是唯一一位最高的運動員,落地時的不穩定就充分顯示出“E分”在成套動作完成中的重要性[11]。難度的發展是在高質量動作完成的基礎上才能夠體現出價值,“D分”越高無形之中也增加了運動員失誤的幾率。鼓勵運動員結合自身綜合素質不斷創新,編排出具有個人特色的成套動作,并充分衡量難度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將是東京奧運周期需要密切關注和探討的關鍵問題。
2017年新規則的實施,動作的編排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組別數量的改變,難度動作的合并(“懸垂前擺上與李寧前擺上進行合并”涉及4個動作、“李寧及李寧 2 進行合并”涉及3個動作),動作難度價值的升級與降級(如:“李寧2成十字支撐或直角十字支撐(2s)”由D組降為C組;“李寧2成銳角十字支撐(2s)”由E組將為D組;“從懸垂直臂垂直拉上成倒十字支撐(2s)”由E組升級為F組;“后團三周下”由F組升級為G組),E組裁判扣分的特殊要求(如:“沒有擺動成手倒立動作”和“2 次以上古佐基或 2 次以上李寧動作:的扣分由E裁改為D裁扣分。“環繩過多的擺蕩”由一個動作扣0.1變為每個動作扣0.1分。而2013年規則的“姿勢錯誤”改為“編排錯誤”進行扣分)對運動員的成套動作完成有重大的影響。而且由于體操發展理念的錯位“以技術難度打天下”的效果會大打折扣。加上動作組別的加分從最高 2.5 下降至 2.0,以及各種新的編排限制,預計 D 分會略下降5%-15%不等[3]。
3 結 論
(1)從44、45、46屆世界體操錦標賽和第31屆奧運會吊環單項決賽32名運動員成套動作結構特征來看,后擺前空翻類動作(雅馬瓦基、喬納森)是運動員使用頻率最高的兩個動作;“擺動至手倒立類”中“后擺成手倒立”使用總計39次,占76.47%;“前擺上成手倒立”占23.53%;“擺動至力量靜止類動作”中后擺上成靜止類動作占據了整個第Ⅲ組別的半壁江山;“力量動作和靜止動作”是吊環成套動作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動作;“后直兩周360°下”是運動員下法動作的主打,E組以上難度下法是運動員的追求。隨著2017版新規則的逐步理解,東京奧運周期的成套動作將會呈現個性化、簡約化、多樣化和高難度等趨勢。
(2)E分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動作之間的銜接、選擇和落地穩定性成為取勝的關鍵。“以技術打天下”的項目發展理念將以“力量、難度和藝術”三者完美結合的理念轉變是吊環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處理好成套動作難度與藝術之間的關系,依然是東京奧運周期需要密切關注。
(3)為適應新周期的規則變化,吊環成套動作的編排都有著清晰的結構特征,為遵循規則的方向性,動作類型多樣化,充分展示出運動員的能力特點、技術風格和競技水平,根據運動員自身條件和特征將是吊環成套動作編排參考和借鑒的長期道路。
(4)2017年新規則中,動作組別的合并及變化,E、D組裁判扣分項目的細化對吊環項目的要求越來越高[12]。預計在東京奧運周期中吊環項目的成套動作編排會愈加符合運動員的個性特征,D分難度價值也將會出現5%-15%之間的降幅。
[1] 肖國梁.體操動作結構之我見[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95:29~31.
[2] 國際體操聯合會.2017-2020年男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S].2017:76.
[3] 袁家強.2017男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簡析[DB/CD]. http://gymnastics.sport.org.cn/cga/inland_gymnastics/505663/.html,2016-07-04.
[4] 國際體操聯合會.2013-2016年男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S].2013.
[5] 徐益雄,胡 磊,熊文齊,等.新周期男子單杠成套動作的“D”分價值與編排特征研究[J].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11,27(3):68~73.
[6] 張涵勁,馬海濤.我國青少年男子體操運動員成套動作價值與編排研究——基于南昌城運會與新加坡青奧會[J].中國體育科技,2012,48(6):48~56.
[7] 趙元吉,常德慶.第43屆世界體操錦標賽男子雙杠成套動作編排特征研究[J].中國體育科技,2012,48(6):41~47.
[8] 李思民,于 濤.第38屆世界體操錦標賽男子吊環成套動作編排特點與趨勢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6,21(4):299~302.
[9] 肖 春.第43屆世錦賽男子自由操成套動作編排特征研究[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12,4(7):74~77.
[10] 黃 旭.優秀體操運動員雙杠成套動作編排模式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8,31(9):1202~1206.
[11] 鄭湘平,袁衛華.世界優秀體操運動員單杠成套動作編排特征研究[J].中國體育科技,2012,48(6):41~47.
[12] 趙元吉.世界優秀男子自由體操運動員成套動作編排模式研究[J].中國體育科技,2015,51(5):16~21.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lete set of Action Choreographies of the World's Elite Rings Athletes
FENG Desen1, YU Wenlu2, ZHAO Yuanji1
1.Chengdu Sport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2.P.E. College of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video observ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32 sets of movements of the three Olympic championships of the Rio Olympic Games and the top 8 athletes of the Rio Olympic Gam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ules of the action group, the difficulty value and the arrang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s the rule of the elite athletic gymnastics scoring rules in 2013 and 2017. The study shows that: (1) the change of the action group makes the choice of action rich, the choice of the type of action is more clear; "after the put on the static" class action by the athletes love; "force action and static action "The use of the highest frequency; (2) the next action is more single, E group above the difficulty of the law also need more innovation and mining. The difficulty of the set of action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ed to fully balance the "technical difficulty to conquer the world" concept to "strength, difficulty and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artists";(3) the new rules of the score requirements more detailed; (4) in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period, the number of sets of action will b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personalized, rationalized, artistic and highly difficult; (4) in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 Rings project sets of action D points will also be about 5% decline.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Excellent athletes; Rings; Complete sets of movements; Arrangement; Characteristic
G832.6
A
1007―6891(2018)01―0042―06
10.13932/j.cnki.sctykx.2018.01.11
2017-10-25
2017-11-02
成都體育學院科研項目(課題編號:17YJ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