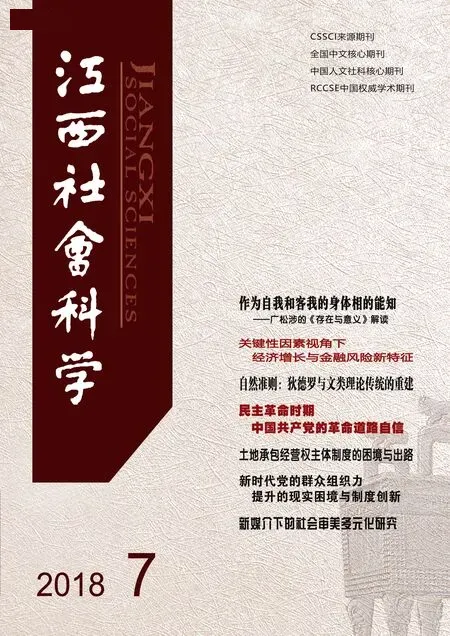南宋江湖文人的游邊文學
■程海倫
隨著宋金、宋元之間戰事的發展,游邊逐漸成為一時風氣。江湖文人①不憚險遠,紛紛前往江淮、荊湖、四川地區,并匯聚于升、揚、潤、鄂等邊地要郡。江湖文人的游邊文學即在這種地域文化與時代背景下展開,是江湖文人在游邊的歷程中創作的與邊地相關的文學作品。本文將在全面考察南宋中后期江湖文人游邊經歷的基礎上,分別從時間指向(回望六朝)和空間指向(北望中原)兩方面具體論述江湖文人的游邊文學,以期更全面地認識江湖文人的生活狀態與文學寫作,并進一步探討江湖文人的游邊文學在唐宋邊地文學發展中的位置。
一、江湖文人游邊行實考述
南宋時期,邊塞地區主要指兩淮、荊襄、四川三邊。這其中又有極邊與次邊之分,據《宋會要》記載,楚州、盱眙軍、滁州、濠州、安豐軍、光州、隨州、郢州、光化軍、均州、信陽軍、金州、洋州、鳳州、西和州、成州、階州等沿邊州軍屬于極邊,其余沿江諸州軍則為次邊。[1](P4436)總體來看,江湖文人游邊的地域主要分布在江淮地區與荊襄地區,尤以江淮地區為多,而至四川者則較少。江湖文人游邊一般是進入位于邊地的幕府。據筆者統計,約有18位江湖文人曾任職或行謁于宣撫司、制置司、安撫司等具有軍事性質的邊幕。除此之外,以其他原因赴邊地的江湖文人亦有30位之多。按游邊時間的不同,南宋中后期江湖文人游邊情況可分為前后兩期。
第一,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至寧宗開禧北伐(1206)之前。這段時期是江湖文人游邊的準備期,人數不多,代表人物有劉過、姜夔、周文璞等。此期游邊風氣尚未盛行主要是由于隆興和議簽訂之后,邊地多為太平場景,留給江湖文人一展抱負的空間并不是很大。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此期疆場比較平靜,故而江湖文人能遠行至極邊州軍。如劉過曾漫游京湖、兩淮諸地,足跡遍及盱眙、襄陽等邊城。
第二,寧宗開禧北伐(1206)至宋亡(1279)。寧宗開禧北伐之后,宋金戰事再度開啟,邊地壓力陡增。嘉定和議后,金朝為補償對抗蒙古的損失頻頻南侵,淮襄地區戰事不斷。而隨著南宋端平入洛的失敗,金朝雖亡,與蒙古的戰事亦拉開序幕。此期疆場多事,為江湖文人創造了更多的機會。劉克莊在《跋楊公節論語講義》中寫道:“當赤白囊交馳、戎馬滿郊之際,蓋辨士說客、奇才劍俠奮發功名之秋。”[2](P4508)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江湖文人游邊的風氣逐漸興盛。此期江湖文人游邊的地點主要集中在當時的幾大戰區,除了四川因為比較偏遠較少為江湖文人所涉足外,京湖與江淮地區成為主要的目的地。由于戰事緊張,襄陽、盱眙等極邊之地已少見江湖文人的行跡,沿江的次邊之地則多見江湖文人駐足。這一時期,送人游邊詩也在江湖文人的筆下大量出現,如周弼的《送人游邊》《送人之漢上》《送人之京口》《送人之荊門》諸作即是其例。在這些詩中,不見為國立功的豪情壯志,而是彌漫著亂世的悲音。征途的遙遠、邊地的殘破,都為游邊文人的前途蒙上一層陰影。這種悲涼的情調,顯示著國事蜩螗之下士人們渴望為國立功卻常感前路渺茫的心理。
江湖文人游邊的目的,固然有謀求生計的考慮,而實現“談兵”②理想更是促使其身臨邊塞險地的精神動力。南宋中后期埋首場屋、困于選調的文官生涯對于士人逐漸喪失吸引力,不少江湖文人選擇投筆從戎的游邊生活。如游邊文人的早期代表劉過在《盱眙行》一詩中比較了“起草黃金閨”“侍宴白玉墀”“生死困毛錐”這幾種人生道路之后,指出“何不夜投將軍飛,勸上征伐鞭四夷”。[3](P2)在其之后,理宗朝的盛世忠有《胡葦航寄古劍》詩:
有人尺錦長安來,遠寄寶匣手自開。紅云紫氣燦虛室,鋏中青蛇鱗生苔。誠攜掌握一揮動,瞬息天地興風雷。少年志氣老益壯,惟愿圣詔下九垓。廐中我有汗血馬,與汝直北清氛埃。丈夫當為國雪恥,笑指經生真不才。[4](第59冊,P36827)
詩題中的胡葦航即胡仲弓,也是本文所討論的游邊文人中的一員。在此詩中,盛世忠敏銳地捕捉到“古劍”一物所蘊含的深意,并指出丈夫應該為國雪恥,肅清邊患,而非如經生般皓首場屋。由上舉二詩可以看出,許多江湖文人對于科舉頗有微詞,甚至放棄士大夫傳統的仕進榮身之路。這種人生道路的轉向,出于南宋選官制度的制約,也受到時局的影響。學界關于南宋中后期士人中舉之不易、仕途之緩滯已多有研究,本文不擬贅述。對于不少仍具有強烈政治責任感的江湖文人來說,游邊成為一種更為可行的政治參與方式。宋代文臣將兵本是祖宗家法,文武兼備的普通士人也不在少數。在南宋國勢傾危的時局下,“談兵”更成為許多江湖文人的政治理想。而南宋日益緊迫的邊事在使游邊具有潛在危險性的同時,也為其賦予一種豪壯的色彩,這恰與江湖文人本身具有的“俠氣”相吻合,因此對江湖文人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邊地經歷到底為江湖文人實現談兵的理想創造了多少可能?這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實際問題。對于進入邊地軍幕的江湖文人來說,參與軍事謀議,甚至親臨戰陣都是很有可能的。如劉克莊嘉定十二年(1219)在江淮制置使李玨幕時曾“與同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帥,虜旗幟隔江,明滅可數”[2](P5203)。又如方岳端平二年(1235)在趙葵幕為淮東安撫司干官時平定高郵軍亂,被趙葵譽為“儒者知兵,吾巨山也”[5](P673)。而對于未進入幕府擔任正式官職的江湖文人來說,多數只能如戴復古“軍前獻籌策,第一守光山”[6](P63)那樣針對戰事獻上自己的建言。總的來看,江湖文人參與軍事決策與行動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在軍幕之中,江湖文人往往無法處理文與武之間的平衡。方岳在《次韻范侍郎寄趙校正》中云“朱轓挾武將,白眼輕儒生”[5](P477),劉克莊在《祭余子壽尚書文》中回憶李玨幕的經歷時亦云:“早客閫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闔四五。流涕諸侯,根立勢舉。眾指而笑,兩生不武。”[2](P5491)都指出文士身份的尷尬。除此之外,彌漫朝堂內外的萎靡士風更是造成江湖文人壯志難酬的深層原因。如黃大壽的《公安》即是一首典型的“談兵”之作。黃大壽曾游歷荊湖地區,因此對于邊地的地理形勢有切實的感受。在此詩中,黃大壽強調了公安一帶的戰略地位,指出朝廷應該“善衛保其吭”“更能用吾長”,以對抗外敵。然而全詩以“休兵不敢論,凄咽含余情”[4](第57冊,P36092)作結,將南宋朝廷文恬武嬉的景象一筆畫出,而詩人的壯志難酬,也成為意料之中卻又無可奈何之事。這種失落心態在江湖文人的筆下并不罕見,由于政治理想與現實處境之間的極大反差,江湖文人游邊的結果往往是不遇而歸,這也為其游邊文學染上一層黯淡的底色。
二、江湖文人游邊文學中的歷史反思
江湖文人在游邊的過程中創作了大量詠史懷古題材的作品。以建康幕府為例,此地文風之盛即與登覽懷古活動的舉行分不開。劉克莊曾惋惜地說:“頃游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業又有六朝陳跡,詩料滿目,而余方為書檄所困,留一年閱十月,得詩僅有二十余首。”[2](P4180)所謂“詩料滿目”,正是指建康地區的歷史遺跡,為文人提供了大量的寫作素材。金陵幕士多作詠史懷古詩,這些作品除了對于歷史興亡的感嘆,更多地體現了江湖文人強烈的歷史反思意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曾極的《金陵百詠》。《金陵百詠》的題寫對象是建康附近地區的歷史遺跡,其主旨并非泛泛地抒發黍離麥秀之悲,而是在“距南渡尚未遠”的時代表達一種“仆悲馬懷之嘆”,即對于國事的關切與感懷。試舉數首為例進行說明:
冰玉摩尼如鵠卵,大千世界倒懸中。何人提向江頭照,照見神州一半空。[4](第50冊《水精大珠》,P31516)
青山四合繞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于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4](第50冊《新亭》,P31506)第一首題詠水精大珠,為本朝事。據《方輿勝覽》記載,水精大珠為“真廟所賜,照物皆倒,又物影沉在下,上段無影”[7](P257)。曾極借前朝所賜之水精大珠寫出南宋朝廷只剩半壁江山的現實,語含微諷。第二首所詠之新亭是南宋詩人筆下常常出現的事典,本意是東晉時王導認為周侯諸人只知楚囚對泣,而無恢復之志。南宋詩人在使用這個典故往往又更進一層,意圖說明南渡君臣不但比不上王導,連周侯那樣的對泣之人都沒有了。曾極此詩化用陸游之意,更進一步指出“江左于今成樂土”的茍安之狀,表達了對于朝政的不滿。四庫館臣認為曾極的《金陵百詠》“大抵皆以南渡君臣畫江自守,無志中原而作,其寓意頗為深遠”[8](P1381),正點出這組懷古詩的主旨。
在前代歷史中,由于六朝與南宋偏安一隅的處境極為相似,因此南宋出現大量研究六朝歷史的地理類、史評類著作,如張敦頤的《六朝事跡編類》、李舜臣的《江東十鑒》、李燾的《六朝通鑒博議》等。這些著作大都是“專為南宋立言者”[9](卷八八,P753),有著鮮明的現實指向。在這種時代風潮的影響下,江湖文人對于六朝歷史也給予較多的關注,方岳即著有《重修南北史》一書,惜已不存。而在江湖文人的詩詞創作中,更鮮明地體現了“十年懷古恨,多在六朝中”[4](第63冊釋斯植《金陵道中》,P39313)的特點。借古諷今,通過吟詠六朝舊事,表達對于國事的見解,是其中常見的主旨。試以陳造與方岳感慨佛貍舊事的兩首詩為例進行具體說明。南宋詩人登臨瓜步,常常會憶及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之事。陳造的《魏帝廟》[4](第45冊,P27978)即從拓跋燾陳兵瓜步寫起,指出祭祀魏帝乃“事讎”之行,并不會得到庇佑,由此發出“云何此山椒,遺像儼高殿”的詰問。陳造認為,與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拓跋燾相比,南宋抗金的義士趙立、薛慶、魏勝更應該被立廟紀念,這不但能夠使“頑懦”之人振奮,亦可避免“后嗣忘敵怨”的悲劇重演。陳造此詩寫于開禧北伐之前,其用意當是借批判為拓跋燾立廟之事,提醒南宋朝廷不可安于對金之和議而忘記恢復舊日河山。方岳的《登瓜步山》亦是借拓跋燾之事發出感嘆:當年拓跋燾并未渡江,如今蒙元卻不會滿足于此,而瓜步正是其入侵江南的第一站。因此南宋朝廷應該吸取前朝的教訓,不可僅僅倚恃長江之險,便以為可以高枕無憂。[5](P358)這兩首詩皆以議論為主,然詞旨含蓄、感慨深沉,無生澀枯槁之弊。方岳在《深雪偶談》中評論晚唐與宋人懷古詩時認為:“本朝諸公喜為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于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后為勝。”[10](第9冊,P8886)可知其趨向所在。
江湖文人的詠史懷古諸作是在游邊的實際經歷中所寫,因此也將邊地的見聞融入這些詩作,增添濃重的亂世情調,懷古實為傷今。如吳惟信的《鳳凰臺懷古》云:“憑高北望舊神州,江繞秦淮萬古流。塞草寒沙埋戰血,更無林葉共傷秋。”[4](第59冊,P37083)唐宋詩人詠懷鳳凰臺的作品可謂數不勝數,而吳惟信的這首絕句卻顯得十分獨特。此詩寫登鳳凰臺北望,只見邊塞戰場的秋景一派凄涼蕭颯。題為“懷古”,卻只用“江繞秦淮萬古流”一句輕點懷古之意,全篇用意實在感懷現實,對犧牲在邊地的戰士深致哀悼。又如陳允平的《多景樓》:
懷古心情獨倚樓,荻花楓葉滿江秋。地雄吳楚東南會,水接荊揚上下流。鐵甕百年春雨夢,銅駝萬里夕陽愁。西風歷歷吹征雁,又帶邊聲過石頭。[4](第67冊,P42010)
此詩吟詠登臨多景樓所見之景,頸聯的“鐵甕”指的是三國時孫權所建的堅城,然而亦逃脫不了銅駝荊棘的命運,仿佛春雨一夢,盡化烏有。尾聯的“邊聲”將懷古的思緒拉回現實世界,提醒著詩人此地現已接近戰場,國事日非,前朝覆亡的悲劇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重演。可以看出,這些詠史懷古詩并非套路化的感慨興亡之作,而是受到現實政治因素的強烈影響,隱現出對于時局的焦慮與不安之感,充滿傷悼的氣氛。而這種傷悼的氣氛在南宋后期江湖文人的作品中表現得愈發強烈。柴望是一位由宋入元的江湖文人,其《石頭城和王寧翁韻》詩云:
懷鄉吊古易傷心,絕頂危亭共客臨。朝市曾經兵火后,山川轉覺樹云深。百年歌舞空臺沼,六代豪華漫陸沉。惟有亂鴉歸去晚,夕陽無限暮城陰。[4](第64冊,P39908)
此詩吊古傷今,情調悲涼,置于晚唐人集中,幾不能辨。可見在南宋后期江湖文人的詠史懷古詩中,抒情一體似乎又占了上風,反思的意識逐漸被濃烈的感傷情緒所淹沒。晚唐詠史懷古詩中的末世情調于此重演,昭示著王朝落幕時刻的到來。
三、江湖文人的北望情懷及其文學書寫
北望,是江湖文人游邊文學中重要的空間指向,北望的對象則是南宋丟失的領土——中原地區。北望情懷從南渡伊始即在宋人的作品出現,如陸游即有以北望為題之詩③。由于江湖文人游邊的地點主要集中在江淮與荊襄地區,而又以游淮為普遍,因此其北望的對象即以中原地區為主。游邊的經歷為江湖文人提供了接近邊境線的機會,使其對于中原有了更為真切的感受。正如朱繼芳的《淮客》詩所云:“長淮萬里秋風客,獨上高樓望秋色。說與南人未必聽,神州只在闌干北。”[4](第62冊,P39075)如此近距離面對神州故土的體驗是長期居住在南方的士人無法擁有的。地理距離的縮短帶給江湖文人的是心理上的極大沖擊,戴復古的名作《頻酌淮河水》即描述了這種情感體驗:
有客游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風吹綠波,郁郁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6](P24)
行至濠州,中原已不僅是在望中,而是只有一水之隔。酌取淮河之水,中原之氣也似乎可觸可感。淮水中的“英雄淚”,既是北地英雄的無盡憾恨,也蘊含著作者對于茍安時局的悲憤。“頻酌淮河水”對于南宋文士來說是罕有的機會,戴復古游邊的特殊經歷,使其獲得超越時人的沉痛感悟。
由游邊經歷出發,北望情懷在江湖文人筆下得到集中和深刻的呈現。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局日漸傾危,江湖文人北望情懷中的感情取向也在發生轉變。劉仙倫的《題張仲隆快目樓壁》是江湖文人表達北望情懷的早期作品:
天上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閶闔,不管欄干犯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入貂裘。面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盡頭。[11](卷六,P24)
此詩作于孝宗淳熙十一(1184)、十二年間,宋金之間處于隆興和議簽訂之后的休兵階段。劉仙倫在同期所作的詩中寫道:“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12](卷六,P24)可見其對于南宋未來的判斷還是頗為樂觀的,因此借著題寫快目樓之機,表達恢復舊疆之愿,全詩情懷振奮、豪氣健舉。不過這種樂觀進取的心態在江湖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多見,當收復故土的希望在南宋中后期的政治局勢下變得日漸渺茫之時,北望的行為與內在動機之間便產生矛盾,江湖文人由渴望極目中原而逐漸產生不忍望、不敢望的情緒。如劉克莊《冶城》詩云“神州只在闌干北,度度來時怕上樓”[2](P49),張蘊《維揚即事》詩云“愁來莫上城頭望,西北浮云接太陽”[4](第63冊,P39380),方岳《水調歌頭·九日多景樓用吳侍郎韻》詞云“莫倚闌干北,天際是神州”[5](P604)等,都以相似的語氣表達了矛盾的心態,可見這種情緒在江湖文人間極具普遍性。在這些作品中,又以戴復古的兩首絕句最為出色:
橫岡下瞰大江流,浮遠堂前萬里愁。最苦無山遮望眼,淮南極目盡神州。[6](《江陰浮遠堂》,P240)
北望茫茫渺渺間,鳥飛不盡又飛還。難禁滿目中原淚,莫上都梁第一山。[6](《盱眙北望》,P241)
這兩首絕句都作于戴復古游淮期間,詩意的表達十分曲折。尤其是第一首詩,首二句寫出浮遠堂所處的地勢,起調甚壯,然而這登高極目之地帶給人的卻是“萬里愁”。為了避開萬里之愁,詩人不但不忍北望,更希望有山能遮擋住遠望的視線。至此為止,詩人皆未明言憂愁的起因,直到末句,作為回答:只因淮南之北盡是神州故土。此詩將沉痛之感以宛曲之筆寫出,較之劉克莊、張蘊等人的作品更為耐人尋味。從劉仙倫的“面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盡頭”到戴復古的“最苦無山遮望眼,淮南極目盡神州”,可以看出江湖文人北望詩詞中表達的情緒從欲圖恢復的豪情壯志逐漸轉向恢復無望的痛苦哀傷,北望的姿態雖一,但其中包含的情感內蘊卻是極為復雜的。
表達北望情懷的作品多出現在登覽之作中。江湖文人的邊地登覽有一些特定的地點,在江湖文人的游邊詩詞中,僅以“多景樓”為題的就有趙汝鐩、高翥、吳惟信、陳允平、張蘊、王琮、柴望、劉過等人所作十多首,數量十分可觀④。多景樓位于鎮江北固山甘露寺內,乾道年間有題記云:“登者以為盡得江山之勝,蓋東瞰海門,西望浮玉,江流縈帶,海潮騰迅,而惟揚城堞浮圖陳于幾席之外,斷山零落出沒于煙云杳靄之間。至天清日明,一目萬里,神州赤縣,未歸輿地,使人慨然有恢復意。”[12](卷十二《宮室》,P278)多景樓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登者可以將神州故土盡收眼底,一覽無余。地理空間的相近與政治空間的阻隔之間形成極大的反差,昭示著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所謂“使人慨然有恢復意”,正是由此而生。在南宋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多景樓被賦予特殊的歷史文化意義,逐漸成為江湖文人抒發“北望”情懷的最佳地點。如劉過的《題潤州多景樓》:
金山焦山相對起,挹盡東流大江水。一樓坐斷水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游,木葉漸脫人間秋。煙塵茫茫路渺渺,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才名今蓋世,當時未遇庸人爾。琴書落魄豫章城,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然,時人未省為謫仙。一朝放浪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行將遍,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下無人獨登覽。樓高思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汝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3](P6)
此詩作于開禧元年(1205)⑤,首四句描寫多景樓的形勝之勢,點出其地“收拾淮南數千里”,為下文北望中原做了鋪墊。“西風”句以下記敘游蹤,“煙塵茫茫路渺渺,神京不見雙淚流”二句抒發由北望舊都而產生的中原阻隔、恢復無望的悲憤,情緒的表達十分強烈。接下來詩人引王勃、李白作比,感嘆自己也遭逢不偶,四海浪游,如何能與前人一般名垂千古。最后以“樓高思遠愁緒多”統攝全篇,沉郁悲涼。從此詩也可以看出,與滕王閣和鳳凰臺這類古跡不同,多景樓的意義是在南宋時才被發現的,而經典作品的產生亦從此時開始,劉過此詩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值得注意的是,多景樓的修成在北宋時期,本身并不具有長期的歷史積淀,但多景樓所在的鎮江地區卻具有豐富的歷史內蘊,祖逖擊楫中流、劉裕北伐中原等六朝舊事均可引起江湖文人的興感,這就極大增添了多景樓的文化意義。如張蘊的《多景樓》詩:
假日此登臨,凄涼北望心。戍烽孤障杳,塔影一江深。黠虜投鞭想,將軍誓檝吟。所嗟人事異,天險古猶今。[3](第63冊,P39380)
此詩首聯點明“北望”之情,“凄涼”二字則為全詩定下情感基調。頷聯敘登臨所見,“戍烽”“孤障”,繪出邊塞實景,表明此地靠近前線。頸聯轉入對于苻堅、祖逖故事的敘寫,尾聯承接此意,抒發英雄難覓的嗟嘆。江湖文人游邊文學中回望六朝的時間指向與北望中原的空間指向于此交匯,而多景樓的特殊意義也得到完全地展現:歷史與現實的感懷超越欣賞風景的需要正如柴望《多景樓》詩所云:“昔日最多風景處,今人偏動黍離愁”,這種黍離之愁即由于“關河北望”而產生。[3](第64冊,P39908)
四、結 語
在宋代的邊地文學中,學界關注的對象主要是北宋的使遼詩及南宋的使金詩⑥,有關兩宋使北詩的寫作特色及其相較于唐代邊塞詩的變化,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討論。然而,對于江湖文人的游邊文學,學界尚較少論及。與唐代、北宋及同時期官僚士大夫的邊地書寫相比,江湖文人的游邊文學在作者身份、題材表現、情感取向等方面都有其獨特之處。
其一,江湖文人在身份上屬于中下層士人,與同時期官僚士大夫的使北之作相比,其游邊文學常常將家國之思與身世之感相結合,對國事既有理性的思考,也包含著不平與悲憤的強烈情緒,反映出這一社會群體感時憂世卻又報國無門的復雜心態。
其二,江湖士人能夠親至邊地,尤其在宋末戰事頻仍的背景下,正常的交聘已成歷史,江湖文人的邊地經歷無疑更為難得。這使其邊地書寫具有強烈的真實感,在表現的廣度與思考的深度上,都具有邊塞詩所無法比擬的價值。
其三,江湖文人的邊地寫作有著較長的時間跨度,隨著南宋中后期政治局勢的發展,江湖士人恢復中原的壯志逐漸被對國家前途的無力感所取代,其游邊文學中的情感色彩近于晚唐邊塞詩的蕭瑟悲涼,而憂患意識與危機感更為強烈,顯示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總體來看,江湖文人的游邊活動涉及的地理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并創造了數量眾多的詩詞作品。其游邊文學在繼承前代寫作經驗的基礎上亦形成自己的特色,對我們全面認識宋代的邊地文學有重要的意義。
注釋:
①本文所討論的江湖文人包括江湖詩人與江湖詞人,分別采用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附錄一“江湖詩派成員考”和郭峰《南宋江湖詞派研究》(巴蜀書社2004年版)第一章第二節“江湖詞派的界定”中的界定。本文之所以將江湖詩人與江湖詞人統名之為江湖文人進行研究,主要是基于將其視作一個共同的社會群體而非文學流派。江湖文人群體具有階層與文化兩方面的特點:一是身份并非顯達,二是擅長文學寫作。
②江湖文人作品中常出現“談兵”一語,如“幕下相從若弟兄,當年曾悔誤談兵”(《劉克莊集箋校》卷四,第257頁),“本無謀略強談兵,每愧臨邊病未能”(周弼《秋日馬上》,《全宋詩》第37770頁)等。
③參看黃奕珍《論陸游南鄭詩作中的空間書寫》(《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
④據李德輝《多景樓與兩宋文學》(《文學遺產》2010年第2期)統計,《全宋詩》和《全宋詞》中所收題詠多景樓之作約四十三人、五十五首。
⑤岳珂《桯史》卷二:“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饒幕庾吏,因識焉……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略)。”
⑥如王水照《論北宋使遼詩的兩個問題》(《山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張高評《南宋使金詩與邊塞詩之轉折》(《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傳志《論南宋使金文人的創作》(《文學遺產》2003年第5期)、諸葛憶兵《論北宋使遼詩》(《暨南學報》2006年第3期)、曾維剛《南宋中興時期士風新變與使北詩歌題材的開拓》(《文學遺產》2017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