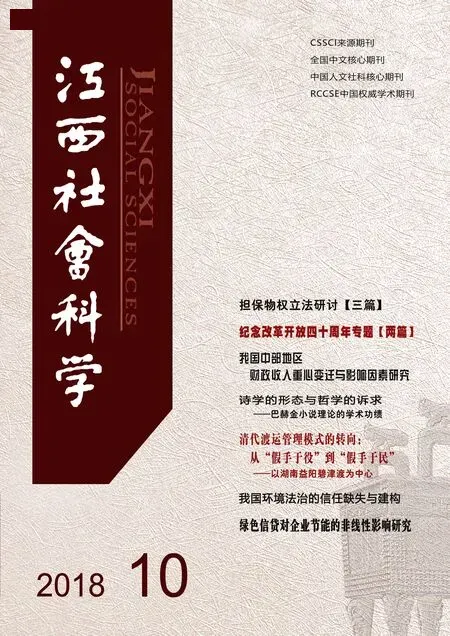讓與擔保的成文化與立法模式選擇
《民法總則》通過之后,民法典各分編的編纂成為目前民法學界討論的重心。在物權(quán)編擔保物權(quán)分編中,是否規(guī)定讓與擔保實為重大立法疑難問題。2002年全國人大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中擔保物權(quán)編規(guī)定了“讓與擔保權(quán)”一章,但2007年通過的《物權(quán)法》最終并未規(guī)定讓與擔保制度。立法的缺位,并未影響到實踐中讓與擔保方式被金融實務(wù)所廣泛采用。
讓與擔保糾紛產(chǎn)生之初,法院判決多以“契約內(nèi)容違反流質(zhì)禁止規(guī)定、違反物權(quán)法定原則而認定其無效”①或以“其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②而否認其合同效力。新近的判決中開始承認讓與擔保的優(yōu)先受償性(物權(quán)性)③,認為:“讓與擔保制度是一種須移轉(zhuǎn)標的物上權(quán)利歸屬的非典型的物的擔保制度,債權(quán)人以擁有擔保物的所有權(quán)來擔保自己的債權(quán),該擔保形式雖未為法律所規(guī)定,但亦未禁止”。或認為:“讓與擔保作為一種物的擔保制度,擔保標的物通常為設(shè)定人所直接占有,不發(fā)生物的留置效力問題,僅存在優(yōu)先受償問題。讓與擔保權(quán)人取得擔保物的財產(chǎn)權(quán),有排除第三人的優(yōu)先效力,讓與擔保權(quán)人在債務(wù)人不履行債務(wù)時,可以以擔保物獲得優(yōu)先受償。”④抑或認為:“讓與擔保合同系當事人之間關(guān)于轉(zhuǎn)移標的物所有權(quán)以設(shè)定擔保的真實意思表示,此外當事人還通過登記備案的方法對所有權(quán)的變動予以了必要公示,同時債務(wù)人實質(zhì)上控制所有權(quán),滿足了債務(wù)人對擔保標的物利用的實際需求,符合不動產(chǎn)讓與擔保的要件,所以,當債務(wù)不能按時履行時,擔保權(quán)人可以在擔保范圍內(nèi)對擔保財產(chǎn)折價和拍賣、變賣所得的價款享有優(yōu)先受償權(quán)。”⑤更有法院指出:“應從讓與擔保的內(nèi)外部關(guān)系來判定讓與擔保的效力。從外部關(guān)系來看,擔保標的物已完成物權(quán)轉(zhuǎn)移,從內(nèi)部關(guān)系來看,讓與擔保當事人之間仍為信托關(guān)系,所有權(quán)并未實現(xiàn)移轉(zhuǎn)。”⑥
通過裁判案例的整理發(fā)現(xiàn),在司法審判層面,各地法院已然呈現(xiàn)出對讓與擔保法律效力相異的解讀。讓與擔保的成文化問題,存在兩個層次的理解:一則是否應在立法上對讓與擔保做出規(guī)定,即必要性的探討;二則可否將讓與擔保作為一種擔保物權(quán)規(guī)定于物權(quán)法編之中,即立法模式的探討。[1]如何對待讓與擔保制度,是否承認其物權(quán)效力,在中國民法典物權(quán)編的編纂過程中不可回避,本文擬就此一陳管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讓與擔保立法必要性
關(guān)于讓與擔保立法必要性之爭,也即于第一層次意義上的成文化,反對者多從讓與擔保可被當前制度所容納出發(fā)予以論證,而此類制度不外乎“所有權(quán)保留、融資租賃、動產(chǎn)抵押”三者。因而,該問題又可簡化為,讓與擔保與此三種制度是否有同時存在的必要,亦即在現(xiàn)有民法體系下,可否在不引入讓與擔保制度的前提下,對以轉(zhuǎn)移標的權(quán)利的擔保方式進行合理規(guī)制。
(一)讓與擔保與所有權(quán)保留、融資租賃
我國《合同法》在有名合同中對所有權(quán)保留和融資租賃予以規(guī)定,這一模式在《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中得以延續(xù)。兩者均以債權(quán)人保留所有權(quán)的方式擔保價金或租金的清償,在經(jīng)濟功能上確系以所有權(quán)作為擔保,與讓與擔保在表象上貌似一致,但仍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不可同日而語。
以所有權(quán)保留為例,所有權(quán)的移轉(zhuǎn)是買賣合同中出賣人的主要義務(wù),也是買賣合同的締約目的,而保留所有權(quán)則意味著這一義務(wù)并未切實履行,以此來為買受人履行給付價金義務(wù)予以擔保。此與以擔保人自身權(quán)利的轉(zhuǎn)移供作擔保的讓與擔保方式,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從物的擔保形態(tài)看,所有權(quán)保留、融資租賃并不可與讓與擔保一起歸為“轉(zhuǎn)移作為標的權(quán)利自身而為擔保”的權(quán)利轉(zhuǎn)移型擔保。[2](P6)從廣義上講,讓與擔保可被定義為“當事人經(jīng)由轉(zhuǎn)讓供作擔保之財產(chǎn),以達成信用授受之目的的擔保制度”[3](P646),也即權(quán)利移轉(zhuǎn)型擔保。但在所有權(quán)保留和融資租賃中,標的物一直為出賣人和出租人所有,原則上并無移轉(zhuǎn)權(quán)利之環(huán)節(jié),不可為廣義的讓與擔保所囊括。換言之,所有權(quán)保留與融資租賃并非為了擔保而設(shè)立買賣合同,相反,其是為擔保(買賣或租賃)合同的履行而為授信的行為。由此可見,《合同法》或《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同編的一系列規(guī)定不能容納讓與擔保制度。
(二)讓與擔保與動產(chǎn)抵押
讓與擔保與動產(chǎn)抵押均為非移轉(zhuǎn)占有型擔保,兩者之間的功能差別更難厘清。我國學界就讓與擔保與動產(chǎn)抵押制度之取舍形成了以下觀點:其一,我國已有動產(chǎn)抵押制度,實無規(guī)定讓與擔保之必要。首觀德國,讓與擔保實為彌補無動產(chǎn)抵押制度之缺陷而設(shè)。[4][5]再觀雙制度并存之日本,除四部特別動產(chǎn)抵押法所規(guī)定的動產(chǎn)可以設(shè)定動產(chǎn)抵押外,其他動產(chǎn)只能采用讓與擔保的形式設(shè)定占有改定式的擔保,使得動產(chǎn)抵押無法完全取代讓與擔保,從而為兩制度之并行留下了空間。[6](P220)我國《物權(quán)法》已經(jīng)明定動產(chǎn)抵押制度,且動產(chǎn)抵押物的范圍已泛化為所有“法律、行政法規(guī)未禁止抵押的財產(chǎn)”,“單從形式上講,讓與擔保因抵押權(quán)概念的泛化已被擠壓出局”;“僅從內(nèi)容上看,原有的讓與擔保制度已經(jīng)被抵押權(quán)概念整體收編,內(nèi)涵于抵押權(quán)制度之中”。[7](P7)[8]其二,動產(chǎn)抵押制度以英美法為藍本突破了傳統(tǒng)大陸法系擔保物權(quán)體系,引發(fā)了物權(quán)公示效力的不統(tǒng)一,應以讓與擔保取代之,使抵押權(quán)回歸不動產(chǎn)物權(quán)的范疇,促使不動產(chǎn)物權(quán)與動產(chǎn)物權(quán)公示方法的準確適用。[4]其三,動產(chǎn)抵押與讓與擔保各有所長,并不具有替代性,可予并存。讓與擔保標的物不以動產(chǎn)或不動產(chǎn)所有權(quán)為限,凡“具有讓與性之財產(chǎn)權(quán)或其他未定型化之財產(chǎn)權(quán)均得為讓與擔保”[9](P5),其標的物的范圍廣于動產(chǎn)抵押。基于物權(quán)客體特定原則,動產(chǎn)抵押僅能就各個獨立物分別設(shè)定,但讓與擔保可以針對集合財產(chǎn)、一定期間內(nèi)多數(shù)流動之債權(quán)整體設(shè)定擔保,符合工商資本流動迅速之需求。[9](P6)讓與擔保還可節(jié)省擔保權(quán)的實行費用,并避免標的物在拍賣程序中因變價過低而造成的損失。[2](P542)
讓與擔保與動產(chǎn)抵押可否并存,與其在一國民法規(guī)范中可否相互替代有關(guān)。我國現(xiàn)行民法體系中,讓與擔保與動產(chǎn)抵押仍具差別,此中最重要的差別乃是“讓與擔保實現(xiàn)方式之便捷”,且也正是因為這一特性,足以使得讓與擔保與動產(chǎn)抵押進行區(qū)分,而具成文化的必要。筆者雖支持這一結(jié)論,但對上述支持理由仍存有不同見解。
首先,就“讓與擔保設(shè)定標的更廣泛”[10]這一論斷,不論讓與擔保采何種法律構(gòu)造,均不能成立。如若讓與擔保采取了擔保權(quán)構(gòu)造,其對標的物的要求,必然受到擔保物權(quán)體系化的限制,因而與動產(chǎn)抵押在標的物方面無以區(qū)分;而若采所有權(quán)構(gòu)造,從舉重以明輕的法理出發(fā),法律上規(guī)定可以轉(zhuǎn)讓的財產(chǎn),必可設(shè)立擔保,因而不存在轉(zhuǎn)讓的標的物范圍較之動產(chǎn)抵押更廣的道理。但就集合財產(chǎn)而言,因動產(chǎn)浮動抵押對標的物的范圍采取嚴格限制態(tài)度,且不承認不動產(chǎn)與動產(chǎn)共同組成的集合財產(chǎn)作為擔保財產(chǎn),讓與擔保確實更具優(yōu)勢。此外,從增加擔保形式以供當事人選擇而促進貿(mào)易融資的角度看,也應支持雙制度的并立,“切不可應立法者一時不放心,而阻斷人們利用財產(chǎn)的一種新的方式的誕生”[11]。
其次,體系背反也不能成為“否定動產(chǎn)抵押,代之以讓與擔保”的理由。讓與擔保的設(shè)立通常不移轉(zhuǎn)標的物的占有,而動產(chǎn)以轉(zhuǎn)移占有為公示生效要件,與動產(chǎn)抵押一樣,讓與擔保也與債權(quán)形式主義物權(quán)變動模式相悖。在同樣采取登記對抗這一債權(quán)意思主義模式之下,讓與擔保也對傳統(tǒng)物權(quán)的登記公示效力、登記簿之公信力產(chǎn)生沖擊。在功能主義的立場下,厘清動產(chǎn)抵押與讓與擔保的實質(zhì)差別,基于融資交易市場對二者的現(xiàn)實需求,在立法已予承認動產(chǎn)抵押的基礎(chǔ)上,對讓與擔保也予規(guī)定,實為最佳選擇。[12]解決這一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建立起完善且配套的動產(chǎn)擔保登記制度,而不應簡單地以體系背反為由否認被金融實踐廣泛采納的融資擔保方式。
最后,讓與擔保實現(xiàn)程序簡便,不僅可使擔保物取得最大的清算價值,更符合現(xiàn)代交易迅捷的要求,使其與動產(chǎn)抵押產(chǎn)生了實質(zhì)區(qū)分。動產(chǎn)抵押權(quán)可得實現(xiàn)之時,雖然法律上規(guī)定動產(chǎn)抵押權(quán)人可以與抵押人協(xié)議以抵押財產(chǎn)折價或以拍賣、變賣所得價款優(yōu)先受償,但這一私的實行方式此際已經(jīng)難以達成,抵押權(quán)人只能尋求公的實行方式以為救濟,訴訟程序冗長、訴訟成本較高,直接影響標的物的變現(xiàn)價值。而在讓與擔保之下,債權(quán)人依事先的協(xié)議直接取得該財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并在清算后,對債務(wù)不獲清償?shù)牟糠钟枰詢?yōu)先受償。這樣的事前約定將會大大減少后續(xù)履行的爭議和成本,更能切實保障擔保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這也是讓與擔保區(qū)別于動產(chǎn)抵押的主要特征。
總的來看,從制度的設(shè)計目的以及法律關(guān)系的基礎(chǔ)構(gòu)造上來看,讓與擔保完全有其獨立存在之必要,并不可被當前民事法律中相關(guān)的制度所涵蓋。也即,從我國當下民商事法律規(guī)范出發(fā),因為缺乏相應配套的制度規(guī)范,讓與擔保至今仍無法通過對現(xiàn)行法的解釋使其徹底被所有權(quán)保留、融資租賃和動產(chǎn)抵押等制度所包含。
二、讓與擔保理論阻卻辨析
承認讓與擔保具有成文化意義的前提下,以何種方式予以成文化,仍存爭議。德國、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qū),都經(jīng)歷了讓與擔保權(quán)是否有效的變遷過程,且均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違背禁止流質(zhì)規(guī)定”“違反禁止使用占有改定”“違反物權(quán)法定”等視角展開討論。[2](P543)[3](P648)[9](P7)我國裁判實踐中否定讓與擔保的效力也是基于這些理由,典型案件說理如下。
(一)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論
我國裁判實踐中,有法院認為,讓與擔保債務(wù)人形式上將標的物所有權(quán)移轉(zhuǎn)于債權(quán)人,而實質(zhì)上并無移轉(zhuǎn)標的物所有權(quán)之意思表示,故屬于雙方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應為無效。⑦我國臺灣地區(qū)在讓與擔保的發(fā)展歷程中也曾被該問題困擾,但實務(wù)發(fā)展已經(jīng)漸趨統(tǒng)一:讓與擔保當事人以真意進行信托讓與行為,屬有效的法律行為。[13]新近,《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24條指出:“當事人以簽訂買賣合同作為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還款,出借人請求履行買賣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民間借貸法律關(guān)系審理。”這一規(guī)定將讓與擔保認定為一種擔保合同,而非買賣法律關(guān)系,實則已經(jīng)否定了虛偽意思表示的論點。
(二)流質(zhì)禁止規(guī)避論
我國實定法上禁止流質(zhì)契約,即在擔保物權(quán)可得實現(xiàn)之前,擔保權(quán)人與擔保人不得約定,在債務(wù)屆期未獲清償時擔保物歸擔保權(quán)人所有。其立法目的在于保護債務(wù)人,以防止債權(quán)人獲得成果擔保債權(quán)額的不當利益。[14](P1199)對這一形式化、僵化的規(guī)定,學界早已指出其弊端,并認為應納入強制清算程序予以緩和流質(zhì)禁止之規(guī)范。[15]但就讓與擔保是否違反流質(zhì)契約禁止的規(guī)定,即使同一個法院,司法態(tài)度也不一樣。例如,(2015)黑高商終字第74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當事人出售房屋的做法實際上是將擔保財產(chǎn)直接歸于擔保權(quán)人所有,以消滅雙方的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此種做法排除了擔保物權(quán)實現(xiàn)時對擔保財產(chǎn)的清算程序,存在因市場變化而產(chǎn)生實質(zhì)不公的可能性,違反了禁止流質(zhì)契約的法律原則,應為無效。而在(2014)黑高商終字第37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又認為:讓與擔保合同應為有效合同,但必須對擔保物進行清算,明顯采納了禁止流質(zhì)條款的緩和理論,認可其在清算程序過后的優(yōu)先受償效力。總而言之,在賦予讓與擔保強制清算程序作為對債務(wù)人的保障后,流質(zhì)契約之禁止便不再是反駁讓與擔保有效性并將其成文化的阻礙。
(三)占有改定之違反論
我國實定法上以交付作為動產(chǎn)質(zhì)權(quán)的生效要件,同時禁止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設(shè)定動產(chǎn)質(zhì)權(quán)。讓與擔保人在轉(zhuǎn)讓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之后,仍然占有標的物,以占有改定作為公示方法,違反了該強行規(guī)定。有學者對此提出質(zhì)疑,認為:動產(chǎn)質(zhì)權(quán)與讓與擔保作用不同,動產(chǎn)質(zhì)權(quán)的擔保作用在于其留置效力,故禁止以占有改定方法為之;但讓與擔保的擔保作用在于取得標的物的受償權(quán),并非留置作用,自無禁止占有改定的必要。[16]筆者認為,該問題之核心在于如何解決對權(quán)利狀態(tài)的公示,防止第三人遭受不利益,使得第三人易于知悉讓與擔保之存在,從而維護交易安全。因而,在確定了讓與擔保的法律構(gòu)造并解決了公示問題之后,該問題自當不攻而破。
(四)物權(quán)法定主義違反論
以違背物權(quán)法定主義而判定讓與擔保無效的理由,可以見諸各法院的判決之中,典型的表述如:“我國法律不承認讓與擔保,且該約定包含流質(zhì)條款,違反了物權(quán)法定的原則,應當認定無效。”⑧物權(quán)法定主義違反論認為,讓與擔保是物權(quán)法中未規(guī)定的新的擔保物權(quán),是對物權(quán)法定主義的違反,因而無效。[3](P649)
從解釋論出發(fā),有學者對此提出反駁,認為:讓與擔保的法律構(gòu)造有兩種,一為所有權(quán)構(gòu)造,讓與擔保其本質(zhì)為當事人信托行為之債的關(guān)系,外加擔保標的物權(quán)利移轉(zhuǎn)的物權(quán)關(guān)系,并非創(chuàng)設(shè)法律所未規(guī)定的新型擔保物權(quán),自不違反物權(quán)法定主義;二為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讓與擔保根據(jù)所有權(quán)的外部變動,達到債權(quán)擔保的目的,此種方式已經(jīng)演變?yōu)榱晳T法上的一種擔保物權(quán),習慣法本屬民法法源之一,也不違反物權(quán)法定原則。[9](P8)筆者認為,我國《民法總則》第10條已明定習慣法的法源地位,將習慣法納入物權(quán)法定的“法”之中,即可緩和物權(quán)法定,消除其既有缺陷。⑨
在立法論上看,物權(quán)法定中的種類法定不允許當事人在法定物權(quán)種類之外合意創(chuàng)設(shè)其他種類的物權(quán)。將讓與擔保制度納入物權(quán)體系,使得讓與擔保作為擔保物權(quán)體系中的一種法定類型,或不納入物權(quán)編而只是將其成文化,承認其所有權(quán)構(gòu)造,物權(quán)法定主義違反論的理由將不復存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物權(quán)法應當盡可能地將一些新的經(jīng)實踐證明成熟的擔保方式納入我國的物權(quán)法當中。”[17]
總而言之,上述無效之理由皆不足以從本質(zhì)上成為讓與擔保的立法障卻。相反,讓與擔保是否有效與其法律構(gòu)造息息相關(guān),其爭辯之實質(zhì)應為讓與擔保立法模式的選擇。
三、讓與擔保立法模式選擇
讓與擔保是 “大陸法系德日等國家沿襲羅馬法上的信托行為理論并吸納日耳曼法上的信托成分,經(jīng)由判例學說之百年勵煉而逐漸發(fā)展起來的一種非典型物之擔保制度”[18](P2),所有權(quán)移轉(zhuǎn)外加信托行為的組合構(gòu)成了其最初的合法性基礎(chǔ)。而后,日本法在經(jīng)歷了所有權(quán)構(gòu)成之后,以《國稅征收法》的公布為契機,轉(zhuǎn)而注重讓與擔保之實質(zhì)目的及社會作用,完成了由所有權(quán)構(gòu)成向擔保物權(quán)構(gòu)成的立法模式轉(zhuǎn)變。[7](P13)“以權(quán)利轉(zhuǎn)移為方式的擔保”作為一個獨立的制度在法律中被予承認,實現(xiàn)了“因買賣而轉(zhuǎn)移”向“因擔保而轉(zhuǎn)移”的變革。[2](P540)
在傳統(tǒng)所有權(quán)構(gòu)成模式下,讓與擔保權(quán)人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quán),只是在行使所有權(quán)時受其內(nèi)部信托行為之限制。若讓與擔保權(quán)人違反內(nèi)部信托行為而對標的物進行了處分,該行為對外有效,[19](P81)讓與擔保人僅對債權(quán)人享有返還合同項下標的物的債權(quán)請求權(quán),而喪失返還標的物之物權(quán)請求權(quán)。換而言之,讓與擔保協(xié)議在當事人雙方之間僅具債權(quán)效力,對第三人并無對抗效力。
在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之下,讓與擔保權(quán)人并非直接取得標的物之所有權(quán)而是取得讓與擔保權(quán),實質(zhì)是對擔保物的優(yōu)先受償權(quán),待債權(quán)屆期未獲清償時,以轉(zhuǎn)移所有權(quán)的方式,對標的物折價清算后優(yōu)先受償。亦即其外形上雖呈現(xiàn)擔保物所有權(quán)轉(zhuǎn)移的特點,但實質(zhì)是讓與擔保權(quán)的設(shè)定。[20](P183)在完成公示后,讓與擔保權(quán)人的處分權(quán)受到物權(quán)類型的限制,第三人無法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quán)。
上述兩種法律構(gòu)造均有其合理性,但筆者更為支持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理論,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所有權(quán)構(gòu)造無法解決動產(chǎn)所有權(quán)公示登記問題,更無法解決所有權(quán)受限的公示問題,對當事人的權(quán)利保護均屬不利。動產(chǎn)大多沒有所有權(quán)登記簿,其公示方式多以移轉(zhuǎn)占有為限,在讓與擔保人繼續(xù)占有標的物的情形下,第三人完全可基于表象上的占有而善意取得標的物,從而使得讓與擔保權(quán)人失去擔保之意義。在讓與擔保權(quán)人違約變賣標的物之時,讓與擔保人清償債務(wù)后返還標的物的利益也難得保障。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即使采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如何平衡保護債務(wù)人利益的問題仍然存在,債務(wù)人在以所有權(quán)提供擔保后,同樣面臨著難以有效制約不誠實的債權(quán)人不當剝奪標的物的危險。[5]筆者認為,在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之下,當事人之間采限制物權(quán)化的形式設(shè)立擔保物權(quán),并輔以強制清算義務(wù),以消除當事人之間的暴利行為,保障讓與擔保當事人在內(nèi)部關(guān)系中的權(quán)益平衡;同時,可借助動產(chǎn)擔保登記簿,輔以登記對抗之公示效力,可滿足對雙方當事人在外部關(guān)系中權(quán)利平衡保護的要求。較之所有權(quán)構(gòu)造,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更為周全。
其次,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不存在危及傳統(tǒng)物權(quán)概念體系的風險。多數(shù)反對讓與擔保成文化的學者多以其背離傳統(tǒng)物權(quán)體系為論證理由[21],認為“讓與擔保并非質(zhì)權(quán)或抵押權(quán)等的定限物權(quán),而是通過‘所有權(quán)功能’作為權(quán)利移轉(zhuǎn)型擔保,即所有權(quán)擔保而得以承認。自羅馬法以來,民法、物權(quán)法一直以‘所有權(quán)——定限物權(quán)’的兩級構(gòu)造作為骨干,若作為所有權(quán)擔保的讓與擔保被承認,則會造成兩級格局的崩潰”[19](P81);“在擔保物權(quán)均采‘限制物權(quán)’的情況下,插入一個‘完全所有權(quán)’制度的讓與擔保制度,就破壞了物權(quán)法體系的完整性,與物權(quán)的所有基本原則:公示性、種類強制、特殊性、抽象性相矛盾,也使得該擔保制度與其他擔保物權(quán)制度在邏輯上難以協(xié)調(diào)”[22]。上述理由均圍繞“讓與擔保以所有權(quán)移轉(zhuǎn)作為擔保的方式與傳統(tǒng)擔保物權(quán)以限制所有權(quán)處分權(quán)能作為擔保的方式相矛盾,且所有權(quán)移轉(zhuǎn)后讓與擔保權(quán)人并未取得完整的所有權(quán),從而與物權(quán)體系中完全所有權(quán)的概念相背離”予以展開。筆者認為,在立法論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設(shè)一個讓與擔保權(quán)確實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在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之下,讓與擔保人讓與的只是一個擔保權(quán),其在表象上雖已轉(zhuǎn)移所有權(quán),但讓與擔保權(quán)人只能對讓與擔保人的所有權(quán)之處分權(quán)能進行限制,取得該標的的優(yōu)先受償權(quán),亦即只有在債務(wù)得不到履行時,才當然移轉(zhuǎn)所有權(quán)對債務(wù)予以優(yōu)先受償。因而,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之下的讓與擔保權(quán),從本質(zhì)上就不存在所有權(quán)概念的體系違背現(xiàn)象。
再次,就讓與擔保制度的沿革可以看出,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說符合學理發(fā)展趨勢,也與擔保物權(quán)價值權(quán)屬性相契合。除了日本以外,讓與擔保在我國臺灣地區(qū)也呈現(xiàn)出擔保物權(quán)化的趨勢。我國臺灣地區(qū)對于讓與擔保之立場起初沿襲德國通說見解而采納所有權(quán)構(gòu)成理論,亦即其以移轉(zhuǎn)標的物之所有權(quán),實現(xiàn)擔保為目的。[3](P646)但由于讓與擔保移轉(zhuǎn)所有權(quán)僅為其外觀,實則并非真正地轉(zhuǎn)移標的物的完全所有權(quán),因而有學者指出:“無必要將其作為所有權(quán)人之權(quán)利來對待,而應當將其限制物權(quán)化,以完成其法律構(gòu)成,亦即直接將其確定為擔保物權(quán)制度之一種。”[3](P651)也有學者基于“民法已許習慣法形成新物權(quán)”的視角,認為讓與擔保可視為“習慣法形成之物權(quán)”,也即,可改采擔保物權(quán)法律構(gòu)造,“類推適用抵押權(quán)規(guī)定”,承認其“從屬性、不可分性與物上代位性”。[9](P9)因所有權(quán)構(gòu)造對當事人保護的不利,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之學理均呈現(xiàn)向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轉(zhuǎn)變之勢。此外,普通法系國家更有學者提倡功能主義立法,認為只要具有擔保功能的交易,均應適用擔保交易規(guī)則。[23]從擔保物權(quán)的特性看,擔保物權(quán)屬于定限物權(quán),即于他人之物或權(quán)利設(shè)定的物權(quán),以確保債務(wù)的清償為目的,因其以支配擔保物的交換價值為內(nèi)容,又稱為價值權(quán)。[24](P366)讓與擔保也旨在確保債務(wù)之清償,也以標的物的交換價值為內(nèi)容,符合價值權(quán)屬性。其權(quán)利移轉(zhuǎn)的表象只是為了起擔保作用,且在擔保物權(quán)構(gòu)成說之下,這一表象作用更為明顯,真正做到了僅起優(yōu)先受償之價值權(quán)功能。
最后,流質(zhì)契約的緩和并不構(gòu)成否定讓與擔保成文化的充分理由。其一,我國現(xiàn)行立法并未對流質(zhì)契約之禁止采取緩和的態(tài)度,中國民法典的編纂最終也不一定采取這一態(tài)度。規(guī)定讓與擔保權(quán),變相對流質(zhì)契約予以緩和,也不失為一種立法選擇。其二,流質(zhì)契約即使得到立法的緩和,也只是對擔保物權(quán)實現(xiàn)方式做出的改變,與先前設(shè)定何種擔保并無相關(guān)。解禁只是簡化了實行程序,在完成清算后,使擔保權(quán)人獲得對標的物移轉(zhuǎn)所有權(quán)登記的請求權(quán),而并未于擔保合同訂立之初就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quán)。在《物權(quán)法》放開第191條“未經(jīng)抵押權(quán)人同意不得轉(zhuǎn)讓抵押物”的規(guī)定后,因擔保權(quán)人與擔保人之間對擔保權(quán)實現(xiàn)方式的約定并不對外公示,交易第三人無從得知,便加大了流質(zhì)契約目的落空、擔保權(quán)人需要公力救濟才能實現(xiàn)擔保物權(quán)的可能性。但是讓與擔保,即使采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擔保權(quán)人于設(shè)立之初也已于外觀形式上取得了標的物的所有權(quán),只是須待實行條件成就后才當然獲得標的物的所有權(quán),其外觀特征易為第三人觀得,且在擔保物權(quán)存續(xù)期間,其轉(zhuǎn)讓也須經(jīng)形式意義上的所有權(quán)人(讓與擔保權(quán)人)同意才得實現(xiàn),更易保護讓與擔保權(quán)人,使其實現(xiàn)擔保物權(quán)更為便捷。其三,讓與擔保極具靈活性,可以彌補立法者有限的預見能力,很多不能歸入抵押或質(zhì)押的新型擔保類型,可為讓與擔保所涵蓋,集合財產(chǎn)的擔保即為著例。因而即使承認流質(zhì)或流抵契約,讓與擔保也并不能被其所取代。其四,當某種融資擔保方式成為交易慣例,構(gòu)成習慣法之時,法律便應對此種新型擔保方式予以認可,不至于出現(xiàn)本文開篇所稱“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如此,選擇讓與擔保成文化,較之流質(zhì)契約的緩和,也更具優(yōu)勢。
總的來看,在現(xiàn)今民法典編纂之際,為發(fā)揮讓與擔保最優(yōu)之法律效果,在證成其成文化必要性與合法性之后,當采擔保物權(quán)法律構(gòu)造對讓與擔保予以規(guī)范。國內(nèi)也有學者認為:“完善中國法中既有的各種動產(chǎn)抵押權(quán),或許是更好的選擇。”[25]在擔保物權(quán)構(gòu)造說之下,讓與擔保權(quán)在民法典中應規(guī)定于擔保物權(quán)編,其具體的法條可表述為:“債務(wù)人或第三人為擔保債務(wù)的履行,將擔保財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移轉(zhuǎn)予擔保權(quán)人的,該擔保權(quán)人僅對擔保物享有讓與擔保權(quán),債務(wù)得以清償之后,擔保權(quán)人應當將該財產(chǎn)返還債務(wù)人或者第三人,債務(wù)未獲清償?shù)模瑐鶛?quán)人有權(quán)直接取得該財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并經(jīng)清算程序之后,在債務(wù)不獲清償?shù)姆秶鷥?nèi)優(yōu)先受償。”此外,為保證讓與擔保規(guī)則的公平適用,民法典中還應對其公示方法和效力、強制清算程序等予以詳細規(guī)定。
注釋:
①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qū)來賓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來民一初字第6號民事判決書、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2011)桂民一終字第18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10號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35號民事判決書等,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判決因契約內(nèi)容違反流質(zhì)禁止規(guī)定,否定了該部分合同的效力。
②參見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淮中商終字第00104號民事判決書。
③除了下文詳述的三個案件外,還有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051號民事裁定書、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蘇商終字第0205號民事判決書、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黑高商終字第37號民事判決書、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佛中法民一終字第2826號民事判決書等一系列民事判決對讓與擔保的優(yōu)先受償效力予以了肯定。
④參見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閩民終字第360號民事判決書。
⑤參見湖南省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邵中民二初字第84號民事判決書。
⑥參見江蘇省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泰中商初字第00045號民事判決書。
⑦參見張秀文與陳林生保證合同糾紛案,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淮中商終字第00104號民事判決書。
⑧參見江蘇省鹽城市鹽都區(qū)人民法院(2014)都大民初字第0308號民事判決書。
⑨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蘇商終字第0205號民事判決書中,一審法院認為,涉案合同是債權(quán)人為保障其收回全部借款和實現(xiàn)購房目的而設(shè)定的一種非典型擔保方式,符合讓與擔保的法律特征。雖然目前我國法律尚未明確規(guī)定讓與擔保制度,但當事人約定的讓與擔保條款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亦不違反物權(quán)法定主義立法意旨,且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具有促進交易、對抗風險、融通資金等價值與功能,應當認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