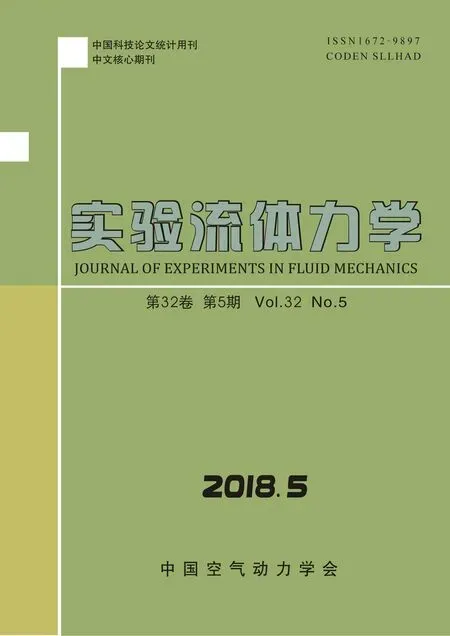隔離段橫向噴流作用下激波串運動特性研究
李一鳴, 李祝飛,*, 楊基明, 吳穎川
(1.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近代力學系, 合肥 230027; 2.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超高速空氣動力研究所 高超聲速沖壓發動機技術重點實驗室, 四川 綿陽 621000)
0 引 言
隔離段作為超燃沖壓發動機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其作用是承受燃燒室反壓及隔離進氣道和燃燒室,通過激波與邊界層相互作用產生的激波串結構,匹配進氣道與燃燒室工作條件,從而實現發動機較寬的工作范圍[1]。大量關于激波串準穩態結構的研究[2-5]表明:反壓、壁溫[6]、截面形狀[7-8]等因素,通過改變激波串的形態和長度,繼而直接影響隔離段設計。然而,隨著迎角[9]和反壓[10-12]的變化,激波串在隔離段內的運動本質上是一個動態過程。此外,因上游進氣道對氣流的壓縮作用,在隔離段內事先形成的反射激波(背景波系[13-15])也會影響激波串的運動過程。
鑒于進氣道/隔離段流動的復雜性,為獲得激波串運動規律,自由射流風洞實驗是其中重要一環。由于直接使用燃燒產生反壓[16-17]開展進氣道/隔離段實驗的難度較大、成本較高,一般采用節流擋板、堵錐等機械結構[18-19]調節流道出口面積,或噴射高壓氣流[20]產生流動壅塞,迫使隔離段內產生激波串。常規風洞實驗時間較長,這些措施容易施展;而激波風洞實驗時間很短,進行激波串運動特性研究不僅富有挑戰性,而且對在高焓脈沖風洞中開展大尺度進氣道/隔離段模型實驗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李祝飛等使用預先設置楔形堵塊的方式[21-22],在激波風洞中開展了進氣道激波振蕩研究。然而,這種預先“硬”堵塞流道的被動控制方法,不僅在激波風洞中難以調節和卸除反壓,而且在實驗初期產生的激波串前移現象與激波風洞及進氣道的流場建立過程相耦合,并不具有普適性。因此,需要發展一種適用于激波風洞的、待進氣道流場穩定后再產生反壓的實驗方法。
本文在不改變流道出口幾何面積的前提下,采用隔離段壁面橫向噴流產生的“軟”堵塞,主動控制隔離段的反壓變化,以期更加接近燃燒形成的反壓的影響,研究激波串在噴流形成的反壓作用下的運動特性。
1 實驗模型及實驗方法
實驗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KDJB330激波風洞中開展。風洞采用的型面噴管出口直徑330mm,試驗段長1.8m,截面直徑約0.7m。來流名義馬赫數為6,總溫875K,總壓1.52MPa。使用氮氣驅動空氣,采用平衡接觸面運行方式。
使用的二元進氣道模型與文獻[21-22]類似,如圖1所示,模型寬54mm,唇口捕獲面高15.3mm,第一級壓縮面長126mm,壓縮角9°,第二級壓縮面長120mm,再進行5°壓縮,等直隔離段長134mm,高10mm。隔離段下壁面布置2排直徑3.6mm的橫向噴流孔,分別距離隔離段出口40和50mm,每排7個噴流孔,孔心間距7mm。為了加快氣流在隔離段內的蓄積過程,在隔離段出口預先安裝高度1.5mm的楔形堵塊。模型側板安裝玻璃觀察窗,以便對流場進行紋影觀測。唇罩壁面(上壁面)沿中心線布置5個壓阻式壓力傳感器NS-2(Shanghai TM-sensor Co., Ltd.),量程300kPa,滿量程精度0.2%,按流向編號CH1~CH5,其中CH4位于第一排噴流孔附近,用于監測隔離段反壓。紋影采用PHANTOM V611高速攝影機進行拍攝,拍攝速率20 000幀/s,曝光時間2μs。
噴流系統如圖2所示。由于激波風洞的實驗時間短,需要快速響應的噴流裝置,經過探索和篩選,采用動作時間約為3ms的電磁閥(MAC-34C系列,通徑1.8mm)作為噴流控制器,氣源由800±20kPa的儲氣罐提供。風洞運行時,通過激波管內的運動激波觸發數字延時器DG645(Stanford Research Systems),產生多路方波信號,分別觸發高速紋影系統和壓力采集系統,同時利用DG645的延時功能,控制噴流電磁閥打開和關閉。
2 結果與討論
噴流時序控制路徑為:事先關閉噴流,待進氣道/隔離段流場建立后打開噴流,直至激波串被推出進氣道后,再關閉噴流。根據進氣道/隔離段流動現象的不同,實驗過程可大致分為流場建立、激波串前移、喘振和再起動4個階段。
圖3給出了模型上壁面CH1~CH5的壓力信號(采用來流靜壓p∞進行無量綱化)。在t=20ms時刻,測量系統被觸發;t=41ms左右,風洞實驗氣流開始流入進氣道,進氣道/隔離段流場逐漸建立;t=44ms左右,噴流進入隔離段,隔離段反壓升高,激波串開始形成,并向上游運動;t=57ms左右,進氣道不起動,并出現喘振現象;隨著噴流關閉,反壓降低,t=71ms左右,進氣道進入再起動階段。
2.1 進氣道流場建立階段
由于事先關閉噴流,在流場建立階段,進氣道能夠正常起動。從圖3的壓力信號和圖4的紋影照片可以看出,t=43ms之后,流場和沿程壓力均較為平穩,進氣道處于穩定的起動狀態。考慮到實驗的壓力測點有限,為獲得沿程壓力分布規律,前期采用三維數值模擬計算了該進氣道(無堵塊)通流狀態下的流場[23]。對稱面的數值紋影和壁面壓強分布如圖5所示,均與實驗符合較好。這也表明:為了在后續實驗中加快氣流積累而在隔離段出口預設堵塊,雖然產生了激波7(圖4),但并未對其上游流動產生明顯影響。
在進氣道起動狀態的流場中(圖4),唇口激波1與進氣道肩點附近邊界層作用,使得下壁面出現流動分離,產生較弱的分離激波2和較強的再附激波3,此外,肩點和分離區外緣還產生了膨脹波。激波和膨脹波在隔離段上下壁面間多次反射,導致壁面壓強出現峰谷值交替(圖5)。對于上壁面(唇口側),激波3入射在CH2附近,產生分離激波4和反射激波5,并在激波3入射點下游附近出現壓強峰值點。與之類似,激波5入射在下壁面,產生反射激波6,并在激波5入射點下游也出現壓強峰值點。
進氣道的起動流場構成了后續激波串前移時的背景流場,而隔離段噴口上游的多道反射激波,構成了非對稱的背景激波。鑒于后續激波串前沿激波上游的流場仍然與背景流場類似,根據Li等[10]的研究,由背景激波引起的壓力分布,可以定性預測出:在背景激波壓強峰值點和入射點之間會出現激波串的急劇前移現象。然而,由于實際流動的復雜性,這一現象仍然需要實驗檢驗。
2.2 激波串前移階段
橫向噴流開啟后,在t=44ms左右噴流進入隔離段,反壓隨之逐漸升高,激波串開始形成并向上游運動。為了從整體上分析和把握激波串前移階段,從t=40~58ms的紋影照片序列中,提取距離隔離段上壁面1mm和距離下壁面3.5mm處(圖4中Line1和Line2所示位置)的灰度值制作x-t圖,如圖6所示。x-t圖中的橫坐標是沿流向位置,縱坐標是時間,色階是紋影照片的灰度。圖6直觀反映出激波串前移階段的激波運動軌跡。
如圖7所示,t=44ms紋影照片中噴口處出現的激波表明,噴流逐漸進入隔離段。隨著氣流在隔離段下游不斷地積累,上壁面CH5的壓強明顯升高(圖3)。t=46ms左右,噴流已經穩定,隔離段內出現激波串,可以清晰地看到激波串的前沿由于流動分離而形成的分離激波8,后續分析中以該前沿激波的運動代表激波串的運動。此時,前沿激波8呈X形結構“騎”在噴流上,該激波結構的上半支位于CH4上游,下半支也入射在CH4附近,使得CH4的壓力信號產生階躍(圖3)。這一過程,在x-t圖中表現為噴流逐漸增強(圖6(b)),出現激波串及前沿激波8(圖6(a))。
激波串前移過程中,其前沿激波上下兩個分支的強度和形狀會發生變化,在背景激波的入射點附近尤為明顯。如圖8(a)所示,在t=46.2~46.4ms,前沿激波8的下半支快速前移,跨過背景激波5在下壁面的入射點,從紋影和x-t圖(圖6(b))可知,前沿激波8運動速度約為61m/s(實驗室坐標系)。在激波串的前移方向上,背景激波5在下壁面的入射點處,本身就存在較強的逆壓梯度,雖然背景流場中沒有出現流動分離區,但是當反壓前傳至該區域時,其流動分離的趨勢惡化,繼而前沿激波8的下半支表現為急劇前移。隨后,前沿激波8進入背景流場的順壓梯度區(圖5),下壁面抵抗流動分離的能力增強,因而前移速度明顯降低,在t=47.0~47.2ms,其平均速度約為12m/s。此時,由于前沿激波8上游背景流場的下壁面壓強低于上壁面(圖5),更有利于激波串前移,導致前沿激波的下半支始終靠前并占主導。
如圖8(b)所示,在t=47.2ms時,前沿激波8運動到背景激波3在上壁面的入射點下游。由于背景流場本身已經存在較強的逆壓梯度(圖5),并產生了較小的流動分離區,當反壓前傳至該區域時,上壁面的流動分離加劇,導致前沿激波8的上半支急劇前移。如t=47.3ms紋影所示,前沿激波8的上半支迅速跨過背景激波3在上壁面的入射點,并與背景激波4合并。前沿激波的上半支占主導,而下半支仍處于背景流場的順壓梯度區(圖5),變化較小。
在t=47.3~48ms時,前沿激波緩慢前移,在此過程中,其上半支處于背景流場的順壓梯度區(圖5),其下半支雖然處于背景流場的逆壓梯度區,但該逆壓梯度平緩(圖5),使得其下半支增強緩慢。如圖8(c)中t=48ms紋影所示,前沿激波的下半支與背景激波3合并。隨著反壓的前傳,在t=48.3ms左右,激波串在下壁面的分離區與背景波系中唇口激波1誘導的分離區融合,使得肩點處的分離區顯著增大,背景波系中原有的分離激波2也明顯增強;同時,分離激波2在上壁面的反射激波也明顯增強。由于肩點處的分離區融合,后續分析中將分離激波2看作是激波串的前沿激波。
背景波系通過在隔離段內產生的壓強變化,特別是壁面邊界層內壓強分布規律的變化,影響激波串前移過程。借助通流狀態下數值模擬得到的背景流場(圖5),獲得了背景激波以及逆壓梯度區分布示意圖,如圖9中紫紅色區域所示。對圖8激波串前移過程的分析表明:在背景激波入射點附近,壁面壓強事先存在較強的逆壓梯度,使前沿激波相應一側的分支增強并快速前移。隔離段內前沿激波快速前移的區域,與圖9背景流場中近壁面處的逆壓梯度區大致相符。
如圖10所示,激波串的前沿激波跨過肩點后,并沒有迅速前移產生溢流,而是在t=49~56ms左右,分離激波2和其產生的反射激波9在肩點附近出現振蕩,從圖6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種振蕩形成的Z字形軌跡。這種振蕩與Tan等[13]觀測到的由于側向溢流而出現的進氣道“小喘”不同,本文進氣道模型被側壁限制(圖2),此時沒有發生溢流,但仍然存在分離激波振蕩。其原因主要是:對逆流前移的分離激波2而言,內收縮段的流道面積大于隔離段,可以容納更大的流動分離區,因此,有利于緩解下游的反壓。如圖10所示,當分離激波2向上游移動時(t=49.2ms),其強度增大,反射激波9波后的壓力隨之升高,同時,靠近上壁面的超聲速通道也擴大,使得抗反壓能力增強,CH1下游的激波串回撤;繼而肩部的逆壓梯度下降,分離區縮小,分離激波2又退回下游(t=49.4ms);此時,喉道處的超聲速通道減小,抗反壓能力下降,下游的激波串再次前移,通過增大肩部分離區又推動分離激波2向上游移動(t=49.7ms),如此往復振蕩。然而,這一振蕩過程只能短暫維持,隨著噴流不斷積累,反壓繼續升高,在t=52ms之后,激波串又持續向上游移動。從圖6可知,前沿激波整體向上游移動的同時仍然存在振蕩。
2.3 喘振及再起動階段
隨著噴流的持續進行,隔離段內氣流進一步積累,反壓不斷增加(圖3中的CH4)。如圖11所示,在t=57ms時,分離激波2運動到唇口附近,與唇口激波1之間產生馬赫反射。隨后進氣道發生溢流并出現喘振現象,分離激波在唇口外前后振蕩。進氣道不起動后,雖然隔離段壓強的平均值有所下降,但喘振造成的峰值壓強仍然較高(圖3)。
在進氣道不起動后,關閉控制噴流的電磁閥,噴流管路中殘余氣體產生的噴流強度大幅減弱,使得反壓降低,進氣道進入再起動階段。如圖12所示,在t=71.5ms時,分離激波2退回到內收縮段,并與唇口激波1發生馬赫反射,然后,分離泡逐漸被吞入隔離段。在t=73.1ms時,分離激波入射在CH1附近,但沒有出現明顯的振蕩。隨著肩部分離區的縮小,t=75ms時,隔離段前部的流場以及CH1和CH2的壓力已經穩定(圖3)。由于隔離段積累的高壓氣體的排出過程較為緩慢,在試驗時間的末期,CH3下游流動未能達到與噴流開啟前(圖4中t=43ms)完全相同的狀態,但是進氣道已經起動。實際上,通過縮短噴流持續時間的手段很容易消除這種現象。這也表明,該進氣道具有自起動能力。
3 結 論
(1) 隔離段橫向噴流模擬反壓的方式,不改變流道出口幾何面積,通過合理設計噴流時序,能夠在激波風洞有限的實驗時間內控制隔離段出口反壓,為在脈沖風洞中開展激波串運動規律、進氣道起動性能和抗反壓能力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途徑。
(2) 隨著噴流在流道內積累,隔離段出口壓強升高,產生向上游運動的激波串,激波串前沿激波的運動規律受進氣道/隔離段內的背景激波影響,特別是在背景激波的入射點附近,背景流場自身存在較強的逆壓梯度,使得與入射點同側的前沿激波分支增強,并出現快速前移。
(3) 噴流產生的反壓將激波串的前沿激波推出至進氣道肩點附近時,進氣道的內收縮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容納流動分離區、緩解下游反壓的作用,出現短暫的激波振蕩現象,但是待反壓進一步增大后,進氣道出現不起動溢流。
鑒于激波串運動過程的復雜性,在激波串前移速度的量化比較以及噴流產生的反壓規律方面,還有待進一步開展細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