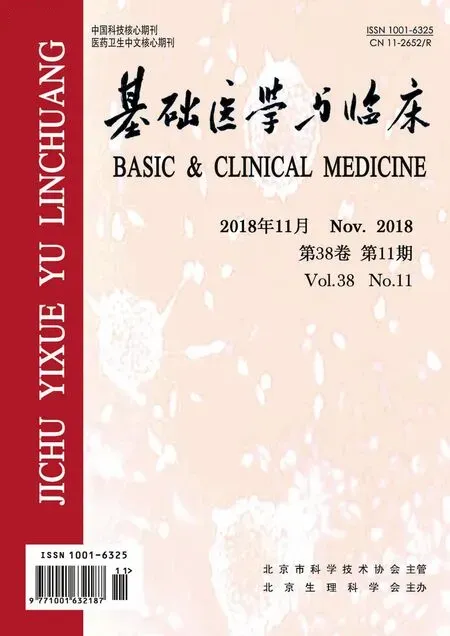CD26在T細胞及相關免疫性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朱 怡,楊曉清,張玉泉*
(1.南通大學 醫學院, 江蘇 南通 226001;2.南通大學附屬醫院 婦產科, 江蘇 南通 226001)
CD26又稱二肽酶Ⅳ(dipeptidyl peptidase Ⅳ, DPPⅣ),是在大鼠腎臟上皮細胞內發現的一種高度糖基化的Ⅱ型跨膜糖蛋白,廣泛分布于嚙齒類動物和人類細胞表面,參與細胞黏附、遷移和凋亡等生理過程[1]。作為T細胞表面的活化抗原及共刺激分子,CD26參與T細胞成熟與活化的全過程,并在人體諸多相關免疫性疾病中發揮重要作用[2]。本文將對CD26在T細胞中的表達與作用及其在相關免疫性疾病中的最新研究進展進行概述。
1 CD26在T細胞中的表達及功能
CD26表達于多種免疫細胞表面,尤其作為T淋巴細胞表面的標志物及共刺激分子,CD26參與T細胞成熟與活化的全過程,包括T細胞成熟和遷移,T細胞刺激與共刺激,T細胞亞群的組成及功能發揮等。在T細胞發育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1.1 CD26在T細胞中的表達
CD26是T細胞表面的活化抗原,在有絲分裂原或同種抗原刺激活化T細胞后,其表達量顯著上調,并參與CD4+CD45RO+的記憶性T細胞(memory T cell, Tm)亞群的組成,是一個合適的T細胞活化標志物。流感特異性CD8+T細胞表面高表達CD26,而慢性病毒感染特異性CD8+T細胞表面幾乎無CD26表達。CD26的表達量與CD8+T細胞的“記憶性”即再次響應抗原的能力呈正相關[3]。同時,CD26是一些T細胞亞群的篩選標志物。例如,在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 Treg)中,CD26表達量較低,為其陰性選擇標志物[2];在效應性T細胞(effector T cell, Teff)中[4],有近98%的Th17細胞高表達CD26。
1.2 CD26在T細胞成熟與活化中的作用
1.2.1 CD26參與T細胞成熟:胸腺中大量成熟的T細胞表面表達CD26,骨髓起源的T細胞也在胸腺中發育成熟。無論是嚙齒類動物還是人類,CD26都被視為胸腺成熟的標志。同時,CD26也是淋巴細胞遷移出胸腺所需的介質因子,其表達量在淋巴細胞凋亡時下調,成熟時上調。但不同于人類的是,小鼠體內CD26可能不參與T細胞的活化[5]。此外,CD26可作為非整合蛋白受體,結合纖連蛋白和膠原,從而介導胸腺發育過程中重要的細胞間黏附:首先,祖細胞進入胸腺,經過陽性選擇和陰性選擇,隨后,CD4+或CD8+T細胞從皮質運輸到髓質,最后發育為成熟T細胞,遷移出胸腺,進入外周免疫器官。在遷移過程中,CD26還參與滅活和降解大量生物活性肽、趨化因子以及一些新細胞克隆,但其自身酶活力的調節具有個體化差異[6]。
1.2.2 CD26參與T細胞刺激與共刺激:對轉染CD26的Jurkat細胞聯合使用抗CD26和抗CD3單抗時,Jurkat細胞表面的CD26和CD3發生交聯,致使胞內Ca2+濃度上調,IL- 2分泌。說明,CD26是T細胞活化所需的協同刺激信號來源[3]。既往研究,就CD26的催化區域是否對誘導T細胞的共刺激有重要作用存在爭議。而目前發現,嵌入T細胞脂筏內的CD26能直接通過其二聚體胞質尾結合CARMA1的PDZ區域,介導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 NF-κB)觸發CD4+T細胞的增殖、激活和分化。此外,抗原提呈細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APCs)表面的小窩蛋白1(caveolin- 1)是CD26的功能性配體,T細胞脂筏內的CD26可通過caveolin- 1直接與APCs相互作用,促使Tollip和白介素- 1受體相關激酶1(interleukin- 1 receptor-associated kinase- 1, IRAK- 1)從caveolin- 1表面解離,從而磷酸化IRAK- 1,介導共刺激分子CD86表達上調,并結合其T細胞表面的配體CD28,協同TCR-pMHCⅡ及各種黏附分子形成的免疫突觸,共同激活NF-κB,誘導CD26+T細胞分泌IL- 2,最終活化抗原特異性T細胞[7]。在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hronic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cGVHD)的小鼠模型中證實,caveolin-1-Ig Fc共軛體能阻斷CD26介導的共刺激作用而影響CD4+T細胞釋放IL- 26,從而減輕免疫反應[8]。盡管關于CD26在介導CD8+T細胞共刺激中作用的研究甚少,但也有發現,CD26可通過顆粒酶B (granzyme B)、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以及干擾素γ(interferon-γ, IFN-γ)介導人類CD8+T細胞活化,發揮其細胞毒性作用;且CD26介導的CD8+T細胞的共刺激作用強于CD28介導的CD8+T細胞的共刺激作用[9]。
1.2.3 CD26參與T細胞亞群的功能發揮:抑制人外周血T淋巴細胞中CD26的酶活力,可通過影響相關細胞因子的分泌水平,來調節T細胞亞群的增殖分化能力。研究發現[10],應用CD26抑制劑Sitaglptin作用于健康人外周血單核細胞,能導致IL- 6、IFN-γ、IL- 17分泌以及CD4+IL- 4+T細胞生成減少,從而抑制Th1,Th2以及Th17細胞的增殖分化能力;同時,能誘導轉換生長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分泌增加,從而促進Treg細胞的生成和分化。CD26+的Th細胞也有增強B細胞合成抗體,激活細胞毒性T細胞(cytotoxic T cell, CTL)的能力。CD26介導的共刺激信號可使CD4+T細胞向1型調節性T細胞表型(Tr1)分化,并分泌大量趨化因子IL- 10,從而限制T細胞的過度活化[11]。
2 CD26在相關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
由于CD26在T細胞中分布廣泛,參與各種T細胞相關的免疫調節過程,故多種相關免疫性疾病的病理進展和疾病嚴重程度都與CD26的免疫調節作用密切相關。主要包括精神神經內分泌障礙性疾病[12]、代謝性疾病[13]、自身免疫性疾病[14- 16]、炎性感染性疾病[17- 20]及腫瘤[21- 23]。本文重點闡述CD26在后3種相關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其中分別以類風濕性關節炎、支氣管哮喘及皮膚T細胞淋巴瘤研究較多。
2.1 CD26在類風濕性關節炎中的作用
類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種以漸進性關節軟骨破壞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炎性反應性疾病。CD26在RA患者外周血T淋巴細胞中高表達,同時,caveolin- 1也在關節滑膜血管及類風濕細胞中高表達;兩者相互作用增強了CD26-caveolin- 1介導的共刺激作用,上調單核細胞表面的CD86,最終活化大量抗原特異性T細胞,引起免疫性炎性反應[14]。最初發現Th細胞不同亞群中,CD26的表達水平反映RA的不同疾病狀態。與健康人相比,約有50%的RA患者CD4+CD45RO+CD26-細胞的比例大幅下降;而高表達CD26的Th1細胞數量變化與治療方法相關[15]。另有研究對RA患者及健康人血清中抗CD26抗體(immunoglobulin, Ig)的不同型別進行了檢測,發現RA患者體內每個同種型別抗CD26 Igs都較正常人增加約兩倍以上(與可溶性CD26的清除率無關),其滴度與疾病活動參數高度相關。因此,檢測抗CD26 Igs顯示出極高的診斷價值(82%的敏感性和96%的特異性)[16]。同時,RA患者血液中CD26酶活力下降,未被降解的基質衍生因子1α(stromal-derived factor-1α, SDF- 1α)介導炎性細胞進入滑膜,引起關節破壞[14]。CD26通過介導抗原特異性T細胞的活化,及其自身酶活力的下降,促使炎性細胞和炎性因子聚集,引起RA患者的免疫性炎性反應。故而,CD26在T細胞不同亞群中的表達量及血清中抗CD26 Igs的水平對于RA的診斷有潛在臨床價值。
2.2 CD26在支氣管哮喘中的作用
支氣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是由多種細胞及其組分參與的氣道慢性炎性性疾病。CD26是哮喘IL- 13通路激活的標志物。在IL- 13的強促炎作用下,患者氣道上皮、血液以及T細胞中CD26的表達量均上調[17]。氣道炎性反應模型實驗也證明,大鼠肺實質暴露于過敏原后,CD26的活力增加,蛋白增多,表明CD26在肺上皮細胞中的表達與哮喘發病機制密切相關[18]。CD4+T細胞在適應性免疫反應、急慢性哮喘及其他過敏或過敏性疾病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CD4+T細胞主要分為4類,即Th1、Th2、Th17和Treg細胞。目前認為,CD26+Th細胞亞群在哮喘免疫調節中的作用愈發重要。尤其在哮喘轉為慢性或耐藥時,CD26+Th1細胞被確認為呼吸道促炎細胞[19]。在嚴重急性發作的哮喘患者的黏膜活檢中發現,CD26+的Th17細胞介導趨化因子參與嗜酸粒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的募集;而Treg細胞(FoxP3+,CD26-)在控制Th2細胞的過度分化和延緩哮喘病程中發揮相關作用;Treg細胞通過調節可溶性因子、膜相關性因子以及哮喘抑制基因發揮免疫抑制作用;且CD4+T細胞各亞群的表達量高低及表達平衡會影響哮喘的免疫表型及嚴重程度[20]。可見,CD26通過調節CD4+T細胞活化及其亞群間的表達平衡,影響支氣管哮喘患者的疾病進展及表型變化。進一步探討CD26在哮喘中的作用機制,可能對哮喘的防治研究,以及新藥物開發有重要價值。
2.3 CD26在皮膚T細胞淋巴瘤中的作用
皮膚T細胞淋巴瘤(cutaneous T-cell lymphoma, CTCL)屬于結外非何杰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 NHL)中的一種,是原發于皮膚的由T淋巴細胞惡性克隆性增生引起的疾病。蕈樣霉菌病和塞澤里綜合征屬于侵襲性CTCL,其5年存活率分別為25%和40%。外周血中CD26-CD4+T細胞的高比例被認為是CTCL患者的診斷標志[21]。通過PCR及高通量測序分析CTCL患者外周血單核細胞表面的TCR發現,最初惡性T細胞克隆來自于CD26-T細胞,在疾病進展中,T 細胞表面再次出現CD26的表達提示預后不良[22]。而采用多變量流式細胞術分析,曾得出與此矛盾的結論。研究者認為,血液循環中出現CD26+T細胞是CTCL患者預后良好的標志[23]。CD26+T細胞病例的出現,表明CD26參與了CTCL患者初始T細胞惡性克隆,但其參與作用的確切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3 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CD26在T細胞中表達廣泛,并參與T細胞的免疫調節功能,使其成為多種相關免疫性疾病的生物標志物和潛在治療靶點。隨著近年來對于免疫靶向治療研究的興起及多種CD26抑制劑的上市,CD26在人體T細胞成熟活化及其作用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得到關注。CD26抑制劑雖已應用于臨床糖尿病治療,但研究者尚未對長期抑制CD26是否影響T細胞的免疫調節過程進行深入探究,如T細胞的成熟活化,T細胞亞群的體內平衡等;同時,CD26在多種實體腫瘤中的促癌作用已被證實,但探討的致癌機制多基于其酶活性和膜結合蛋白的功能展開,關于其致癌作用是否與T細胞的免疫調節功能相關亦研究甚少。因而,進一步探索CD26在T細胞及相關免疫性疾病,包括腫瘤中的作用機制,不僅可為更多臨床免疫性疾病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論依據及治療方向,也可為CD26相關藥物的多領域應用及長期使用的免疫安全性提供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