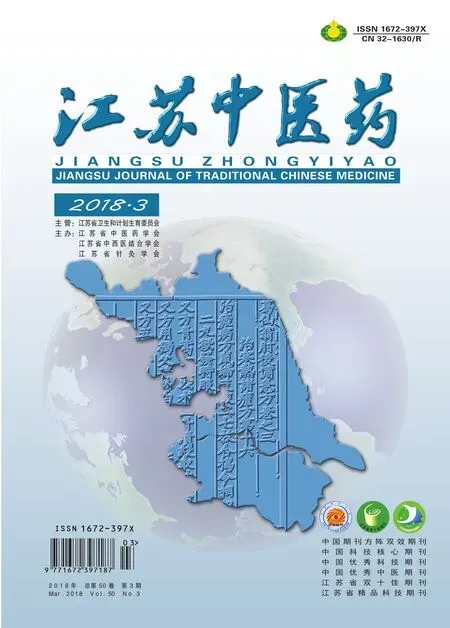孫偉正治療內(nèi)傷發(fā)熱驗(yàn)案3則
雍彥禮 孫 鳳
(黑龍江中醫(yī)藥大學(xué),黑龍江哈爾濱150040)指導(dǎo):孫偉正
內(nèi)傷發(fā)熱是由于臟腑功能失調(diào),氣血陰陽(yáng)虧虛而引起的以發(fā)熱為主要表現(xiàn)的一種病癥,以低熱為主,有時(shí)高熱或自覺(jué)發(fā)熱而體溫并不升高。一般起病較緩,病程較長(zhǎng)[1]。內(nèi)傷發(fā)熱的治療以辨證論治為基礎(chǔ),辨證候之虛實(shí),但內(nèi)傷發(fā)熱屬虛者居多,臨證時(shí)可針對(duì)病情補(bǔ)益氣血陰陽(yáng),以促進(jìn)臟腑功能及陰陽(yáng)平衡的恢復(fù),切不可一見(jiàn)發(fā)熱,便用發(fā)散解表及苦寒瀉火之劑,以致耗氣傷陰或傷敗脾胃。
孫偉正教授為全國(guó)老中醫(yī)藥專家學(xué)術(shù)經(jīng)驗(yàn)繼承指導(dǎo)老師,黑龍江省名中醫(yī),中醫(yī)理論淵博,臨床經(jīng)驗(yàn)豐富,臨床過(guò)程中辨證治療內(nèi)傷發(fā)熱療效顯著。現(xiàn)將其治療內(nèi)傷發(fā)熱驗(yàn)案3則介紹如下。
1 血虛發(fā)熱案
徐某,女,62歲。2013年7月5日初診。
反復(fù)發(fā)熱4月余。癥見(jiàn):低熱,面色無(wú)華,唇甲色淡,乏力,活動(dòng)后心悸氣短,頭暈,關(guān)節(jié)疼痛,失眠多夢(mèng),飲食和二便尚可,舌質(zhì)淡、苔白,脈細(xì)弱。中醫(yī)診斷:內(nèi)傷發(fā)熱。辨證:血虛發(fā)熱。治法:養(yǎng)血益氣,佐清虛熱。方用歸脾湯加減。處方:
黃芪50g,黨參15g,白術(shù)15g,當(dāng)歸15g,茯苓15g,遠(yuǎn)志15g,酸棗仁15g,龍眼肉15g,木香5g,炙甘草10g,阿膠15g,雞血藤20g,白薇15g,地骨皮15g,銀柴胡15g。
7劑。常法煎服。囑患者注意生活調(diào)護(hù),以防外邪乘虛而入。
7月12 日二診:患者發(fā)熱,最高體溫為37.8℃,乏力、心悸氣短、失眠多夢(mèng)癥狀略有好轉(zhuǎn),飲食和二便尚可,舌質(zhì)淡、苔白,脈細(xì)弱。繼服上方7劑。
7月19日三診:患者低熱,乏力、心悸氣短、失眠多夢(mèng)癥狀緩解,飲食和二便可,舌質(zhì)淡、苔白,脈細(xì)。上方去白薇、地骨皮和銀柴胡。7劑。水煎服。
7月26 日四診:患者無(wú)發(fā)熱,無(wú)明顯乏力和心悸氣短,睡眠、飲食和二便可,舌質(zhì)淡、苔薄,脈細(xì)。患者停服湯劑,予歸脾丸,每日3次口服。囑其每半月來(lái)診,監(jiān)測(cè)血常規(guī)。
按:孫偉正教授認(rèn)為導(dǎo)致內(nèi)傷發(fā)熱的病因有虛實(shí)之分,實(shí)者有氣滯、血瘀和濕郁之別;虛者有氣虛、血虛、陰虛和陽(yáng)虛之分;也有因虛致實(shí)及邪實(shí)傷正者,其臨床表現(xiàn)既有正虛,又有邪實(shí),而為正虛邪實(shí)、虛實(shí)夾雜的證候,亦屬常見(jiàn)。其病機(jī)為臟腑功能失調(diào),氣血陰陽(yáng)虧虛,其病位在五臟,可因病機(jī)不同,分別伴有氣滯、血瘀、濕郁或氣虛、血虛、陰虛、陽(yáng)虛的表現(xiàn)。
本案為內(nèi)傷發(fā)熱之血虛發(fā)熱,血虛發(fā)熱為內(nèi)傷發(fā)熱中常見(jiàn)的一個(gè)證型。血虛發(fā)熱出自李東垣《內(nèi)外傷辨惑論》:“血虛發(fā)熱,證像白虎,惟脈不長(zhǎng)實(shí)為辨耳,誤服白虎湯必死。此病得之饑?yán)谝邸!卑l(fā)熱是癥狀,血虛是內(nèi)在機(jī)制,主要病機(jī)為營(yíng)血虧虛,陰血衰則陽(yáng)氣偏勝(血本屬陰),則見(jiàn)發(fā)熱。
該患者為老年女性,病程日久,長(zhǎng)期飲食失調(diào),偏食,素食,且食量小,脾虛失于運(yùn)化,氣血化生無(wú)源,臟腑功能失調(diào),日久導(dǎo)致血虛,營(yíng)血虧虛,陰虛不足,陽(yáng)氣偏盛,故見(jiàn)發(fā)熱。血虛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失養(yǎng),則見(jiàn)面色無(wú)華,乏力,心悸氣短,頭暈和關(guān)節(jié)疼痛;心血不足,心失所養(yǎng),心神不安,故見(jiàn)失眠多夢(mèng);舌質(zhì)淡、苔白,脈細(xì)弱均為血虛不足之象。
《證治匯補(bǔ)·發(fā)熱》指出:“血虛發(fā)熱,一切吐衄便血,產(chǎn)后崩漏,血虛不能配陽(yáng),陽(yáng)亢發(fā)熱者,治宜養(yǎng)血。”故用歸脾湯以補(bǔ)氣養(yǎng)血,佐清虛熱,使血足陽(yáng)平,則虛熱自退。方中黃芪、黨參、白術(shù)補(bǔ)氣健脾;當(dāng)歸、龍眼肉養(yǎng)血補(bǔ)心;阿膠、雞血藤補(bǔ)血和血;茯苓、遠(yuǎn)志、酸棗仁養(yǎng)心安神;木香理氣醒脾,與補(bǔ)氣養(yǎng)血藥配伍,使之補(bǔ)不礙胃,補(bǔ)而不滯;白薇、地骨皮和銀柴胡清退虛熱;甘草益氣補(bǔ)中,調(diào)和諸藥。諸藥共奏補(bǔ)氣養(yǎng)血,清退虛熱之效。患者初診時(shí)在歸脾湯加減的基礎(chǔ)上合用清退虛熱的白薇、地骨皮和銀柴胡,熱退之后則繼續(xù)應(yīng)用歸脾湯以調(diào)理脾胃,促進(jìn)血液的化生,并在隨訪時(shí)囑患者堅(jiān)持服用歸脾丸以鞏固療效,經(jīng)過(guò)適當(dāng)?shù)恼{(diào)理,疾病痊愈。
另在內(nèi)傷發(fā)熱的過(guò)程中要注意,由于病機(jī)的變化,證候間可以相互轉(zhuǎn)化或兼夾出現(xiàn)。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血虛日久發(fā)熱必兼氣虛,而轉(zhuǎn)化為氣血兩虛之發(fā)熱,則應(yīng)氣血并治。
2 氣虛發(fā)熱案
牛某,女,45歲。2014年5月15日初診。
間斷性發(fā)熱、乏力、頭暈1年余,加重5天。癥見(jiàn):語(yǔ)聲低微,面色潮紅,乏力,頭暈,心悸氣短,活動(dòng)后加重,形體消瘦,納差,寐差,大便秘結(jié),小便正常,舌質(zhì)淡、苔薄,脈細(xì)弱。中醫(yī)診斷:內(nèi)傷發(fā)熱。辨證:氣虛發(fā)熱。治法:益氣健脾,甘溫除熱。方用補(bǔ)中益氣湯加減。處方:
黃芪50g,黨參15g,白術(shù)15g,甘草15g,陳皮15g,當(dāng)歸15g,茯苓15g,砂仁(后下)15g,酸棗仁15g,夜交藤15g,柴胡10g,升麻10g,防風(fēng)5g。7劑。常法煎服。囑患者防外感。
5月22 日二診:患者體溫略有下降,最高時(shí)為37.6℃,乏力頭暈、心悸氣短等癥減輕,大便秘結(jié),小便正常,舌質(zhì)淡、苔薄,脈細(xì)弱。原方減酸棗仁、夜交藤,水煎服。
5月29 日三診:患者無(wú)明顯發(fā)熱,乏力頭暈、心悸氣短癥狀緩解,睡眠、飲食和二便可,舌質(zhì)淡、苔薄,脈細(xì)弱。效不更方,繼服上方7劑,水煎服。
6月4 日四診:患者無(wú)發(fā)熱,余癥大減。停服湯藥,予補(bǔ)中益氣丸,每日3次口服,連續(xù)服用1個(gè)月。患者治療后發(fā)熱、乏力、心悸氣短等癥狀消失,半年內(nèi)未復(fù)發(fā)。
按:孫教授指出調(diào)理陰陽(yáng),補(bǔ)虛瀉實(shí)是本病的基本治療原則。虛證者,補(bǔ)氣血陰陽(yáng)的不足以消其虛火;實(shí)證者,宜視肝郁、濕阻及瘀血之異,分別行氣、化濕、活血,祛除病邪以清其實(shí)熱;虛實(shí)夾雜者,則需分清主次,兼而顧之。
本案氣虛發(fā)熱為內(nèi)傷發(fā)熱中較為常見(jiàn)的一個(gè)證型。孫教授指出氣虛發(fā)熱的主要病機(jī)為氣虛、虛火內(nèi)生兼合脾胃氣機(jī)升降失常,治療上只有兼顧補(bǔ)氣和調(diào)暢中焦氣機(jī)才能達(dá)到治療效果。
患者間斷性發(fā)熱1年余,實(shí)驗(yàn)室檢查未見(jiàn)明顯異常,雖多次應(yīng)用抗生素,但效不顯,反復(fù)發(fā)作。患者以發(fā)熱為主證,勞累后加重,伴有乏力頭暈、心悸氣短等氣虛不足之癥,且平素易于感冒,綜合四診辨證為氣虛發(fā)熱。患者平素氣虛體質(zhì),易感外邪,失于調(diào)理,病程日久,脾胃氣衰漸重,中氣下陷,陰火內(nèi)生故發(fā)熱;勞則耗氣,故發(fā)熱在勞累后加重;脾虛失于健運(yùn),氣血化生不足,五臟六腑失養(yǎng),故見(jiàn)乏力頭暈,心悸氣短;氣虛衛(wèi)表不固,則易于感冒;氣虛推動(dòng)無(wú)力,故見(jiàn)大便秘結(jié);舌質(zhì)淡、苔薄,脈細(xì)弱,均為氣虛不足之證。治療投以具有甘溫除熱和調(diào)暢氣機(jī)作用的補(bǔ)中益氣湯,即在補(bǔ)氣藥基礎(chǔ)上,加用具有升提中氣、調(diào)暢氣機(jī)作用的升麻、柴胡,則脾胃升清降濁功能正常,氣機(jī)通暢,虛熱自退,并隨癥加減,療效顯著。方中黃芪、防風(fēng)補(bǔ)中益氣、升陽(yáng)固表;黨參、甘草、白術(shù)、砂仁、茯苓健脾補(bǔ)氣;當(dāng)歸養(yǎng)血活血,與黨參、黃芪配伍能補(bǔ)氣和營(yíng);升麻可引胃氣上騰復(fù)其本位,柴胡可引少陽(yáng)之氣上升,二者既可升舉清陽(yáng),又能透泄熱邪;陳皮理氣和胃,使諸藥補(bǔ)而不滯;砂仁行氣溫中,北方人用量可大;酸棗仁、夜交藤養(yǎng)心安神。諸藥合用,共奏健脾胃、升清陽(yáng)、補(bǔ)元?dú)狻⒊裏嶂πА?/p>
甘溫除熱法是李東垣在《脾胃論》中明確提出來(lái)的,并創(chuàng)立補(bǔ)中益氣湯治療。方中黃芪、人參、白術(shù)補(bǔ)氣健脾,當(dāng)歸養(yǎng)血和血,陳皮理氣和胃、補(bǔ)而不滯,升麻、柴胡升清舉陷,甘草調(diào)藥和中。孫教授指出在臨證過(guò)程中慎用發(fā)散及苦寒瀉熱的藥物,因發(fā)散易耗氣傷津,苦寒則易損傷中陽(yáng),亦可化燥傷陰,均可致病情加重。對(duì)于內(nèi)傷發(fā)熱的患者,實(shí)證可適當(dāng)清熱,虛證可選用清虛熱之品。內(nèi)傷發(fā)熱雖有虛實(shí)之分,但以虛證居多,臨床上切不可一見(jiàn)發(fā)熱即用辛散解表或苦寒攻下,以免耗液傷津,或苦寒傷及脾胃,或化燥傷陰。
對(duì)于氣虛發(fā)熱者應(yīng)注意證候間的相互轉(zhuǎn)化及兼夾。氣虛及陰,陰虛及氣,日久可見(jiàn)氣陰兩虛之證;氣虛及陽(yáng),陽(yáng)氣衰弱,日久可轉(zhuǎn)化為陽(yáng)虛發(fā)熱;陰陽(yáng)互根互用,陰損及陽(yáng),陽(yáng)損及陰,則可轉(zhuǎn)化為陰陽(yáng)兩虛之重證。盡管氣虛發(fā)熱可以出現(xiàn)多種兼證,但本質(zhì)是由氣虛所導(dǎo)致的,因此在治療過(guò)程中仍以補(bǔ)中益氣湯為主要方藥,以期恢復(fù)脾胃的升清降濁之功,使之氣機(jī)通暢,并辨證配伍其他方藥,達(dá)到標(biāo)本兼治的目的。
3 瘀血發(fā)熱案
王某,女,44歲。2014年10月20日初診。
間斷性發(fā)熱2月余。癥見(jiàn):面色晦暗,形體適中,語(yǔ)聲正常,低熱,乏力,口渴不欲飲,時(shí)有小腹部疼痛,納差,月經(jīng)先期,量多,睡眠和二便尚可,舌質(zhì)紫暗、苔白,脈細(xì)澀。中醫(yī)診斷:內(nèi)傷發(fā)熱。辨證:瘀血發(fā)熱。治法:活血化瘀、涼血清熱、益氣養(yǎng)血。方用血府逐瘀湯加減。處方:
當(dāng)歸20g,生地15g,熟地15g,雞血藤20g,川芎15g,赤芍15g,桃仁10g,紅花10g,柴胡15g,枳殼15g,桔梗15g,牛膝15g,甘草15g,黃芪20g,黨參15g,茯苓15g,白術(shù)15g,白薇15g,丹皮15g,梔子15g。7劑。常法煎服。囑患者須注意調(diào)節(jié)情志并保暖避風(fēng),防止感受外邪。
10月27日二診:患者無(wú)發(fā)熱,小腹疼痛癥狀好轉(zhuǎn),仍覺(jué)乏力、納差,口干渴癥狀稍輕,舌質(zhì)紫暗、苔白,脈細(xì)澀。繼服上方7劑,水煎服。
11月3日三診:患者無(wú)發(fā)熱,無(wú)小腹疼痛和口渴,乏力、納差癥狀緩解,飲食和二便可,舌質(zhì)暗、苔白,脈細(xì)。上方去白薇、丹皮、梔子,7劑,水煎服。
11月10日四診:患者諸癥消失,舌質(zhì)淡、苔薄,脈細(xì)。患者停服湯劑,予血府逐瘀膠囊,每日2次口服,連服2周。患者治療后無(wú)發(fā)熱,面色紅潤(rùn),口渴、乏力、納差等癥狀消失,月經(jīng)恢復(fù)正常。
按:本案為內(nèi)傷發(fā)熱之瘀血發(fā)熱。孫教授認(rèn)為導(dǎo)致瘀血發(fā)熱的病機(jī)主要有兩個(gè)方面:一方面,瘀血阻滯日久,郁而化熱。其次,瘀血內(nèi)存,新血不生,導(dǎo)致血虛生熱。但臨床上瘀血發(fā)熱的主要病機(jī)是以郁而化熱為主,部分兼有血虛之熱。瘀血發(fā)熱辨證要點(diǎn)為發(fā)熱、以夜間發(fā)熱為主,伴瘀血相關(guān)之癥。唐容川《血證論·卷六·發(fā)熱》說(shuō):“瘀血發(fā)熱,瘀血在肌肉,則翕翕發(fā)熱,證象白虎,口渴心煩,肢體刺痛,瘀血在腑,則血室主之,證見(jiàn)日哺潮熱,晝?nèi)彰髁耍簞t譫語(yǔ)。”
患者月經(jīng)先期、量多,病程日久導(dǎo)致氣血兩虛,血液運(yùn)行不暢,血脈瘀阻,壅遏不通,故見(jiàn)發(fā)熱;瘀血阻滯,不通則痛,則小腹疼痛;瘀血內(nèi)停,新血不生,臟腑失于濡養(yǎng),故面色晦暗、乏力;瘀血阻滯,津液運(yùn)行不暢,故口渴不欲飲;舌質(zhì)紫暗、脈細(xì)澀均為瘀血內(nèi)停表現(xiàn)。瘀血發(fā)熱的治療以活血化瘀、涼血清熱為法,不可妄投苦寒,以免傷正。《金匱翼》謂:“瘀血發(fā)熱者,其脈澀,其人但欲漱水而不欲咽,兩腳必厥冷,小腹必結(jié)急,是不可以寒治,不可以辛散,但通其血,則發(fā)熱自止。”故孫教授選用血府逐瘀湯(當(dāng)歸、生地、川芎、赤芍、桃仁、紅花、柴胡、枳殼、桔梗、牛膝、甘草)加白薇、丹皮、梔子、黃芪、熟地黃、雞血藤、黨參、茯苓、白術(shù)。血府逐瘀湯為桃紅四物湯與四逆散的合方,其中桃紅四物湯活血養(yǎng)血,四逆散行氣活血;桔梗開(kāi)肺氣,引藥上行;枳殼行氣,使氣血上下通調(diào),而疏通于全身;川牛膝通利血脈;白薇、牡丹皮、梔子清熱涼血,且具走而不守之性,無(wú)寒涼凝滯之嫌;雞血藤、熟地黃養(yǎng)血和血;黃芪、黨參、茯苓、白術(shù)補(bǔ)氣生血;甘草調(diào)藥和中。諸藥配合,使血活氣行,則瘀化熱消,諸證自愈。
另外,氣機(jī)阻滯日久,以致血液運(yùn)行不暢,也可見(jiàn)瘀血的表現(xiàn)。虛實(shí)夾雜也常多見(jiàn),如陰虛夾血瘀,氣虛夾血瘀等。證候的相互轉(zhuǎn)化及兼夾,這是疾病纏綿日久不愈的一個(gè)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在臨證過(guò)程中要辨明證候的轉(zhuǎn)化及兼夾,以標(biāo)本兼治,并應(yīng)同時(shí)進(jìn)行辨證治療,防止病情變化。
[1] 張伯禮,薛博瑜.中醫(yī)內(nèi)科學(xué)[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