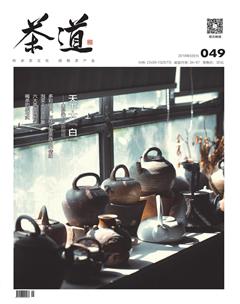霍山黃茶 金雞山間瑞草魁
陳勇光



霍山地氣所鐘,故有“仙草”霍山石斛,產于他山者藥效輸矣。而霍山茶亦得仙草之名,《霍山縣志》載:“茶稱瑞草魁,霍茶又為諸茗魁矣”。
一直向往霍山仙境,直到近年才有空前往尋訪霍山的茶。可惜之前喝到的霍山黃茶,幾乎都是綠茶的樣子,很難找得到悶黃到位的茶葉,很多人以為霍山黃芽只是綠茶呢。
霍山隸屬于安徽六安,位于大別山腹部,傳說這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霍山茶的歷史也已久矣。據壽州、霍山地方志記載,早在西漢年間,當地便已開始茶樹種植。唐朝中期,霍山成為產茶重地,李肇在《唐國史補》中有言:“風俗貴茶,茶之名品亦眾……壽州有霍山黃芽。”在那時候,霍山黃芽就已成貢品。那時的黃茶就因其黃色芽葉而得名。直到明朝,黃茶的制茶技藝才漸趨成熟。當時霍山“小茶攤黃,大茶堆燜”,應該是“悶堆渥黃”的黃茶工藝了。據《霍山縣志》記載:明初規定年貢20斤。正德十年貢寧王府芽茶1200斤、細茶6000斤……購芽茶1斤需銀1兩,尤恐不得。
新中國成立后,各地黃茶改制成紅茶出口。直到1972年,霍山黃芽才率先恢復生產。大別山廣闊蒼莽,橫跨鄂豫皖三省。山脈所在的六安、霍山、金寨、岳西、潛山、舒城等諸縣市皆有好茶。自豫南至皖西,號稱“茶葉走廊”。
為尋霍山黃芽,特意選擇了谷雨期間的4月22日到來。霍山之境尤為高大曠遠,海拔1774米的大別山主峰白馬尖就位于該縣境內。霍山生態優異,源于竹根的剮水,泡茶滋味清甘細潤。因為有好水,也釀就了這里的好酒,還有生態基礎很好的高山茶。
聯系了山中手工制黃茶的劉俠女士,因為性格爽直,人們都稱他“大俠”。從霍山縣的城關沿東淠河順佛子嶺水庫溯流而上,海拔上升,我于中午到達佛子嶺,大俠的茶坊就在那兒。這是山后一排的小屋,屋后有大片竹林,有兩個大焙籠。焙籠上的茶葉透出陣陣的花蜜甜香。
前來尋茶的合肥茶友已經在大俠家呆了幾天時間了,在各地的茶季,癡迷于茶的茶友往往要到原產地尋訪。大俠的黃茶制作從清明后開始,茶季的最初幾天,她使用佛子嶺山后的野茶來制作些黃茶。到了谷雨前后,就用大化坪金雞塢的珍貴鮮葉制作最好的黃芽了。
大俠的霍山黃芽在初烘后進行慢慢悶黃,屬于干悶,所以她的悶黃程序可以不急不慢,完全根據茶葉狀態與火候來調整,悶黃所用的時間超過了其他地區黃茶的數倍,有時長達數天甚至十余天。她覺得這樣的制作工藝會使茶味更加醇厚。有時候她也會采用濕悶的方式,也就是茶葉殺青后趁著還有水分直接堆悶。她的每一堆茶葉她都會用字條寫上制作的時間與程序。這一堆正在焙火的茶,是昨天天晴時在烏米尖才采的茶青,今天中午殺青,第一次焙火,干悶,茶葉條索自然舒展,如蘭花狀,白毫顯現。后期還要一次烘干與悶堆、揀剔與復火,估計還需要一星期才能完工。
午后,大俠帶我們進山,她要到山里收青葉并炒茶。出發前,她給我們的杯子里悶了些前幾天才用佛子嶺野茶制好的霍山黃芽,栗香中還有微微的蜜香,滋味清甘醇厚鮮美,和這片大山的氣息相融。
面包車的動力適合在山里奔跑,車后斗還可以藏下很多鮮葉或準備帶回烘干的毛茶。山太大,太遠,大俠的理想要在山里做一個初制所。我與她沿途探討,談起茶有太多體會。每到茶季,她一天休息不到四五個小時,談到制茶的工藝細節對黃茶的重要影響,她如數家珍。
霍山黃芽的茶樹多為霍山金雞種,以大化坪鄉的金雞塢、金山頭,上和街的金竹坪,姚家畈的烏米尖的“三金一烏”品質為優。其芽葉生育力較強,為灌木型,大葉類,晚生種屬性,所產茶葉品質上佳。
據大俠介紹,霍山的黃茶,從清明左右至谷雨間,采一芽一葉或一芽二葉初展制作的稱霍山黃芽。谷雨后至5月初,采一芽二三葉,稍長新葉,制蘭花茶(綠茶),黃茶就叫黃小茶,味道更為醇厚有力。5月后鮮葉長到一芽三四葉,新梢長度約從指尖到手腕處,可制黃大茶。黃大茶經高溫殺青,悶堆發酵,老火焙出五谷鍋巴香。干悶的霍山黃茶有栗香蜜味。而濕悶的黃茶黃湯茶葉的特征更為明顯,有玉米燉馬蹄水的感受。
車子在山間轉繞,一小時多,終于到達位于大別山主峰白馬尖相遙望的金雞山,這里的茶季顯得更為熱鬧。很多人在這里會收購茶青鮮葉,這是有名的產地,制出來的黃茶滋味厚醇,價格亦比其他地區為高。
霍山黃芽的采摘期約一個月,這時候已經是一芽一二葉初展的茶青了。山里的茶青會根據海拔、地域、植被狀態等而有不同的價格。大俠在金雞塢做些手工黃茶,已經第6個年頭。借用的農家的場地并不大,位于頂樓,但用起來正好合適。有專門炒茶的鐵鍋,大俠喜歡使用炭火炒、炭火烘,燒透的青杠木炭,火力夠足,大俠說這樣的火更適合掌控炒青的溫度,茶葉也更香一些,至少不會有煙火氣。
留在農家的幾筐茶葉正在萎凋,要在傍晚時分進鍋炒青,炒后初烘完帶下山,再進行后期的烘悶。霍山黃茶的工藝重在悶黃(攤放),能真正做得好的少之又少。其中的霍山黃芽經由殺青(也叫生鍋炒茶、熟鍋做形)、毛火(初烘)、攤放、足火、灘放、揀剔、復火等數道工序精制完成。
殺青階段就決定黃茶的品質。安徽霍山黃芽的手工炒制分為生鍋熟鍋兩個階段,兩口鍋相鄰,一口生鍋,一口熟鍋,黑褐的鐵鍋已顯得油亮。大別山脈的六安瓜片和信陽毛尖,都有類似的炒法。
生鍋高溫殺青,投入約三四兩的鮮葉,生鍋數分鐘炒完后用茶帚快速掃到相鄰的熟鍋,在火溫略低的熟鍋中再進行理條整形。茶葉與熱鍋相交,翻炒悶抖間沙沙作響,氣氛專注而緊張。炒后的茶直接上烘籠烘焙,黑夜里,竹烘籠下透著紅色的炭火的光,慢慢地蘭花香就隱約顯現了。
大化坪,海拔七八百米處的茶農家,茶園多在屋前舍后,下午六點鐘的時候,陽光仍舊燦爛,茶園中新發的芽葉郁郁蔥蔥,充滿了生命的力量。在竹林掩映處,是紅色屋頂的小屋,再遠處的大山,和晚霞中的排山倒海般的層層云彩。
晚霞繼續濃烈,緋紅與占據了藍天,遠山的黛藍,山坳里近處的茶園深綠,一株株分散種植,芽葉層層密密,想是早期的茶園,才有這樣的種植方式。大化坪金雞塢,以鐵籠圍起的“金雞神茶”母樹,從地上部生長出的枝條繁多,茶樹并不高,約一米多,芽葉的持嫩性甚好。
天氣漸漸冷了下來,天色正晚。此間土質肥沃、晝夜溫差大,所產霍山黃芽品質自然不差。
我曾在霍山的金雞塢采了一點點松杉下拋荒的茶,茶樹在松軟的土壤上自然生長,健康的土壤讓芽葉充滿了生命的力量,這不到一兩的鮮葉,大俠幫忙炒過。我離開霍山,就一路悶著走了。茶葉帶著濕度,白天用透氣的棉布茶巾悶,晚上就用小電爐憑感覺小烘一下,最后亦用炭火烘干,至今珍藏,每次飲來,在栗香蜜味里,猶覺余韻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