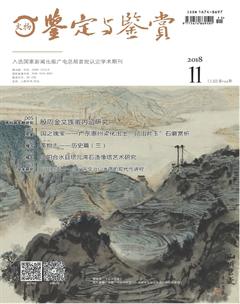淺談施瑯的歷史功績
陳進東



摘 要:施瑯,福建晉江衙口鎮人。17歲投入鄭芝龍軍中,任千夫長,后歸入鄭成功麾下,屢立奇功,為鄭成功開創金門、廈門抗清基地做出了卓越貢獻。歸附滿清后,他積極整飭海防,發展海上防御力量,并率軍平定臺灣,使我國寶島臺灣納入祖國的版圖。戰后,力諫康熙皇帝留住臺灣,使臺灣成為祖國神圣不可分割的領土。施瑯和鄭成功這兩位叱咤一時的英雄,盡管因性格和各種原因而反目,但二人順應歷史潮流,客觀上為祖國統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不能不說是功莫大焉。
關鍵詞:施瑯;鄭成功;臺灣;“績光銅柱”坊
1 獻計取廈門
施瑯,明天啟元年(1621)出生在福建省晉江縣衙口村的一戶沒落的富戶家中。父親施大宣生有三子:長子施肇科,早年夭亡;次子施瑯;三子施顯。施瑯與弟施顯感情甚篤。施瑯幼入鄉里私塾就讀,兼習“戰陣擊刺諸技”和兵法。據《涵芬樓古今文鈔》所載:“稍長,識度湛厚,膂力絕人。見明季所在多竊發,遂學萬人敵,精研五花陣法。以居濱海,尤善于水師,海洋中風云氣候,講之甚悉。”
崇禎十年(1637),17歲的施瑯加入到了鄭芝龍的軍中,任千夫長。施瑯在自己的《決計進剿疏》中也談到:“然臣生長濱海,總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履歷。”元雜劇《龐涓夜走馬陵道》中有這樣一句話:“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學有所成的施瑯自然想憑著自身的本領博一個好的前程。
施瑯所處的那個年代正是大明王朝江河日下、內憂外患的動蕩歲月。身處這樣的一個時代,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幸的。或許對于施瑯來說,這是歷史賦予他的機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煤山自縊,承繼明朝的南京弘光政權擢升施瑯為副總兵。施德馨在《襄壯公傳》寫道:“崇禎甲申,明祚覆于闖賊。旋值興朝鼎革,弘光建號江之南。以公將略素著,由參戎晉副總兵。”盡管弘光政權僅僅維持了一年時間,但在接下來的明隆武政權中施瑯又被擢升為左先鋒。雖然大明王朝的局面是一天不如一天,可此時的施瑯似乎前程越來越光明。然而并不是事事都能盡遂人愿,明隆武二年(1646),鄭芝龍降清了。作為鄭芝龍的部屬,施瑯第一次成為了清軍的一員,這是施瑯一次被動地降清,但很快他又歸入到了鄭成功的麾下。1648年4月,清廣東提督李成棟叛歸南明,施瑯隨之又回到了明軍的陣營,鄭成功對其極其重視。據《福建列傳》卷三二記載:“鄭成功托故明賜姓棲海上,以瑯為左先鋒,相得甚,軍儲、卒伍及機密大事悉與謀。”鄭成功委任施瑯為左先鋒,此時二人相處甚為融洽,軍中的大小事宜,包括糧食倉儲、士兵訓練等,鄭成功均與其商議,這是一份非常難得的信任。清代早期名相李光地也說過,“鄭國姓用施瑯如手足”。
1650年,施瑯向鄭成功進獻了一計——襲取廈門。這一計的成功使長期以游擊戰、運動戰為主的鄭成功最終擁有一塊穩定的抗清后方基地,同時也使清王朝統一中國的歷史進程延后了二十余年。
此時,盤踞在廈門的鄭聯、鄭彩所部戰船、兵力數量均數倍于鄭成功。據《臺灣外記》記載:“施瑯進言:‘聯乃酒色狂徒,無謀之輩,藩主可領四只巨艦,揚帆回事,寄泊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其余者陸續假為商船,或寄泊島美、浯嶼,或寄大擔、白石頭,或從鼓浪嶼轉入崎尾,或直入寄碇廈門港水仙宮前。藩主登岸拜謁,悉從謙恭,然后相機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施瑯具有很高的戰略眼光和戰術素養。而這一計帶來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鄭聯的人頭落地、鄭氏各派勢力的繳械,鄭成功的抗清大業從此擁有了一塊穩定的基地。這其中施瑯所做出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
然而,施瑯和鄭成功有著極其相似的性格缺陷——沖動、暴躁。且施瑯還有些恃才傲物,作為上下級,這些似乎都注定二人的和諧關系難保持太久。古往今來不乏這類事例,如魏延之于諸葛亮、楊修之于曹操。很遺憾,二人終究還是重復了古人的悲劇。
1651年初,鄭成功率部進抵廣東南澳,施瑯因反對鄭成功為補充軍需在粵東地區實施劫掠,力勸鄭成功南下而引起鄭成功的極度不悅。鄭成功下令解除施瑯左先鋒之職,命其將印信和所部兵將交副將蘇茂統轄,令施瑯同部將陳塤、鄭文星返回廈門,自此二人之間開始生了嫌隙。接下來所發生的事件似乎又使兩人惡化的關系山重水復、柳暗花明。三月初一,清泉州總兵馬得功率部攻破廈門,鄭軍留守將領鄭芝莞、阮引等不戰而逃。恰逢遭貶返廈的施瑯抵達廈門,聞訊率陳塤、鄭文星等六十人從廈門港迅速登岸,進擊馬得功,馬得功所部大敗。據《巴哈納等題為輕貪啟釁廈門等地失陷事本》記載,馬得功稱“即發船七十只,兵六百名,臣至廈門”。此時,馬得功所率領的兵馬約為六百名,施瑯僅率六十余名親兵即擊潰馬得功所部六百余人,以一當十,足見施瑯和所部的英勇善戰,以及施瑯卓越的治軍能力。此戰的勝利保住了廈門,保住了搖搖欲墜的南明王朝在東南的最后一塊抗清基地,也才有了鄭成功后來浩浩蕩蕩的北伐,以及鄭成功東征臺灣收復寶島的偉大壯舉。
2 力主平臺
接下來的曾德事件使施瑯與鄭成功終成仇讎。施瑯親兵曾德因犯法逃到鄭成功營中,被鄭成功拔為親隨。施瑯徑入鄭成功營中將曾德捉回,鄭成功急令勿殺,施瑯卻堅持將曾德斬首,再加上此前的一系列事件最終導致了施瑯投向了清王朝的大旗下。1651年5月20日,鄭成功下令拘捕施瑯、施顯和其家屬,施瑯在舊將蘇茂等人的幫助下逃到安平(今福建安海)族叔施福處。施瑯父親施大宣、弟施顯被斬首示眾,懷著殺父弒弟的仇恨,施瑯二次降清。這使鄭成功在軍事上又多了一個深諳水戰的強勁對手,為后來鄭軍將領大規模降清開了先例,同時也為日后鄭氏集團的覆亡埋下了伏筆。
降清的最初幾年,施瑯并未得到清廷的足夠重視,只是隨著清軍前往西南征討李定國等南明勢力。1656年8月,昔日同僚海澄公黃梧向世子濟度、浙閩總督李率泰舉薦施瑯,濟度與李率泰合疏上奏保舉施瑯。清廷起用施瑯為同安副將,進而擢升為同安總兵。隨后,施瑯將自己的名字由此前的“施郎”改為了“施瑯”。江日昇在《臺灣外記》中寫道:“梧薦施瑯水務精熟,韜略兼優。若欲平海,當用此人。”“郎遂改名瑯,貝勒與率泰合疏保題施瑯為同安副將,尋而擢為總兵。”從這時候起,施瑯走到了和鄭氏集團作戰的最前線。
公元1661年3月,鄭成功率兩萬五千余名士兵從金門料羅灣出發,完成他一生中最偉大的功業——從荷蘭侵略者手中收復被強占三十八年之久的我國寶島臺灣。經過九個多月的激戰,同年十二月,荷蘭殖民者宣告投降,臺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次年五月,鄭成功病逝于臺灣。其子鄭經繼位,就在這一年的七月,清軍擬在福建水師設提督一名、總兵兩名。在大學士蘇納海的推薦下,清廷任命施瑯為福建水師首任提督,駐扎海澄。同樣是在七月,清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泰遣都司王維明、李振華同總兵林忠一起前往廈門招撫鄭經。鄭經給出的答復是依照朝鮮例,不剃發、不登岸,稱臣納貢而已。姑且不論鄭經的答復是出于何種戰略考量,這個和議如果成功,今天的中華恐怕就再無寶島臺灣了。
施瑯上任福建水師提督后,大力發展水師力量。據施德馨《襄壯公傳》記載:“康熙元年壬寅,著提督福建水師,自茲秉鉞專閫,而公始大展驥足矣。”《靖海匯紀》記載:“康熙壬寅元年,圣祖仁皇帝御宇,特設水師提督,擢祖,移駐海澄與賊對壘而軍。每出奇制勝,鄭氏不敢登岸窺竊者數年。東南民人,賴安生業。祖自茲統轄全閩。乃改造樓櫓、旗幟、炮火、器械。著五花、三疊、八卦、十連環諸六十四陣,以訓練士卒,源出于八門、六花,世傳為法則。”
清康熙三年(1664),施瑯率水師向臺灣挺進,開始他的第一次平臺征程。《清圣祖實錄·卷一二》記載:“康熙三年七月十八日(丁未),敕福建提督水師總兵官施瑯等曰:‘海寇雖已蕩平,逆賊鄭錦尚竄臺灣。率以爾施瑯素諳海務,矢志立功,特命爾為靖海將軍,以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師左都督楊富為副,以左都督林順、何義等為佐,統領水師,前往征剿。”然而閩南一帶夏季多臺風,在那個還沒有氣象預報的時代,臺風觀測只能憑借經驗,所以多了許多不可預知性。十一月,施瑯水師進發臺灣,行至臺灣海峽,臺風襲來,水師被迫返航,徐圖再進。施瑯的第一次平臺行動被迫中止。次年四月,施瑯再度率師東征,可是天公依舊不作美。十七日,船隊進入澎湖,狂風暴雨,大霧漫海,舟師幾乎被狂風吹散,施瑯被迫再度返回廈門。史籍中對施瑯舟師遇臺風襲擊多有記載。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二》載:“康熙四年四月,靖海將軍施瑯等出洋,未至澎湖溝,颶風大作,各船飄散,不能相顧,皆引還。”施瑯《擬克期復征疏》中提到:“十七日午時,臣等駛入澎湖口,驟遇狂風大作,暴雨傾注,波濤洶涌,白霧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師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擊,人仰船傾,悲號之聲,猶如水中發出,情勢十分危急。”兩次征臺都宣告失敗。
兩次征臺的失敗使清廷開始對施瑯的能力和以剿為主的平臺方略產生了質疑。《清圣祖實錄·卷一八》記載:“康熙五年正月二十六日(丁未),福建總督李率泰遺疏言:‘閩海余氛,遠竄臺灣。奉旨撤兵,與民休息,洵為至計。”由此可見,清王朝開始考慮放棄對臺灣鄭氏集團的武力征剿,轉而以撫為主的平臺新方略。
康熙六年(1667)八月,清廷派遣總兵孔元章等往臺灣招撫鄭氏集團。十月,鄭氏集團給出的答復依舊是不剃發、不登岸,依照朝鮮例,儼然欲將臺灣游離于祖國版圖之外。鄭經在《鄭經復孔元章書》中談到:“況今東寧(臺灣)遠在海外,非屬版圖之中,東連日本,南蹴呂宋,人民輻輳,商賈流通。王侯之貴,非吾所自有,萬世之基已立于不拔。”另外,鄭經在給他的舅父董班舍《鄭經復董班舍書》一文中也談到:“今日東寧,版圖之外另辟乾坤,幅員數千里,糧食數十年,四夷效順,百貨流通,生聚教訓,足以自強。又何慕于藩封?何羨于中土哉?倘清朝以海濱為虞,蒼生為念,能以外國之禮見待,互市通好,則甥亦不憚聽從。”此時,鄭氏集團的分裂之心昭然若揭。
近年來,有許多專家和學者對鄭成功的是非功過重新進行了客觀的評價。筆者以為,鄭成功前期的抗清活動并不是其人生的閃光點,最多就是封建王朝更迭過程中的征服與反征服的戰爭,其前提是基于樸素的家國觀念。鄭成功一生中的頂峰則是收復寶島臺灣。盡管先進的科學理論體系在那個時代還遠未形成,支撐他的理念還是樸素的、原始的,但其收復臺灣的壯舉客觀上使寶島臺灣仍舊和大陸形成一個整體,依然還在祖國母親的懷抱。通過戰斗從西方列強手中收復這么大片的領土,縱觀明、清五百四十三年的歷史,沒有幾人能夠做到。鄭成功可謂是明史第一人,其功至偉,光耀萬世。時間僅僅過了數年,作為臺灣鄭氏集團繼任者的鄭經,就妄圖使臺灣游離于祖國大陸之外,妄圖分裂中華,不管他出于何種考量,注定必將失敗。
這時候的滿清王朝卻已經將平臺的大政方針完全轉向了以招撫為主,清廷認為臺灣孤懸海外、地勢險要,只能招撫而不可進剿。緊接著,清廷撤銷福建水師,原水師提督施瑯留在京城,改任內大臣,投誠的原鄭氏官兵被分插到各省進行開荒種田。
康熙八年(1669)六月,清廷再派興化知府慕天顏同季佺等人赴臺招撫鄭經,然而得到的答復依然是“照朝鮮例”。同年九月,康熙皇帝下詔身在福建的明珠、蔡毓榮等:“遵制剃發歸順,高爵厚祿,朕不惜封賞。即臺灣之地,亦從彼意,允其居住。”“至于比朝鮮不薙發、愿進貢投誠之說,不變允從。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若因居住臺灣,不行剃發,則歸順悃誠,以何為據?”從康熙皇帝的詔書中可以看出,康熙皇帝依然希望通過和平招撫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并對鄭經的分裂行徑明確表示了反對。明珠等再次派員入臺招撫,得到的答復還是依照朝鮮例,招撫再次失敗。
康熙十年(1671),福建水師復設,共設官兵一萬名,戰船二百艘,分屬海澄鎮和興化鎮統轄。形勢似乎開始向施瑯主張的武力收復臺灣的想法發展。可是,接下來的三藩之亂使施瑯收復臺灣的夢想被迫再度擱置。康熙二十年(1681),施瑯終于等到了再度施展抱負的機會。這一年的七月,在李光地的舉薦下,施瑯復任福建水師提督。十月,施瑯抵達廈門,大力整備,打造戰船、軍械,積極準備平臺。此時,臺灣鄭氏集團卻仍在做分裂的美夢。據《清圣祖實錄·卷一〇九》記載:“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福建總督姚啟圣疏言:海賊劉國軒遣的偽官黃學賚書至,請照琉球、高麗等外國例,稱臣進貢,不薙發登岸,應否所請,請旨定奪。上曰:臺灣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如果悔罪,剃發歸誠。該督、撫等遴選賢能官前往招撫。或賊聞知大兵進剿,計圖緩兵亦未可料,其審察確實。倘機有可乘,可令提督即遵前旨進兵。至是,姚啟圣奏:遣福州副將黃朝用往諭,劉國軒等仍如前言,上乃趣施瑯進兵。”六月十四日,施瑯率師從東山出發,東征臺灣。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澎湖一戰,擊潰鄭軍水師主力,劉國軒逃回臺灣。七月,鄭克塽等向施瑯投降,施瑯完成了他近一生的抱負。也許有人詬病施瑯平臺的出發點是為了報弒父殺弟之仇,可歷史終究是注重客觀事實。事實就是寶島臺灣終于回到祖國統一的大家庭里。施瑯和鄭成功一樣,終將是明末清初史冊上最閃亮的一筆。
3 力保臺灣
臺灣收復了,但在當時科學技術、地理知識和官員認識的局限性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清廷內部開始出現一種聲音,那就是放棄臺灣,認為臺灣地少人稀、荒涼貧瘠,留下只會加重政府負擔。作為平臺的第一功臣,施瑯力主清廷保留臺灣。他在那篇著名的《恭陳臺灣棄留疏》中談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并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文章充分陳述了臺灣的富饒、放棄臺灣將給臺灣和臺灣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同時,建議清政府在臺灣駐軍,設置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總共有兵一萬名駐防臺灣澎湖。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決定派兵鎮守臺灣。盡管近代臺灣經歷了許許多多的風雨,但它始終是祖國神圣不可分割的領土。這其中,施瑯可謂是功莫大焉。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瑯病逝于廈門福建水師提督任上,終年76歲。
今天,在廈門同安頂溪頭村漳泉古驛道邊還屹立著一座“績光銅柱”坊,系康熙五十六年(1717)福建巡撫等地方官員為紀念施瑯的歷史功績而修建的。它也是目前廈門地區保存最大、最完好的清代石牌坊。牌坊通高9米,明間寬3.6米,次間寬1.23米。上檐刻有“雙龍搶珠”“太公釣魚”浮雕。牌坊正面刻有“績光銅柱”,背面鐫刻有“思永峴碑”字樣。
參考文獻
[1]吳曾祺.涵芬樓古今文鈔[M].北京:商務印書館,[1912].
[2]江日昇.臺灣外志[M].濟南:齊魯書社,2004.
[3]日講起居注官.清圣祖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2012.
[4]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5]彭孫貽.靖海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