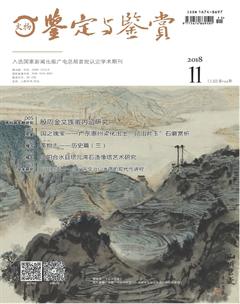慶陽合水縣塔兒灣石造像塔藝術研究
李涇婷



摘 要:塔兒灣石造像塔是隴東宋金時期重要的佛教文化遺址,作者通過對合水縣塔兒灣石造像實地調(diào)查和資料的整理與比較,從藝術學角度對塔兒灣石造像塔人文背景、藝術形制、造像內(nèi)容、造型特點、藝術價值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與探討。塔兒灣石造像塔所呈現(xiàn)出的鮮明的藝術特征,證明它是隴東宋金佛教藝術傳承的重要部分,對中原佛教文化交融流變,乃至對整個隴東地區(qū)佛教藝術的系統(tǒng)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關鍵詞:合水縣;塔兒灣石造像塔;人文背景;藝術形制;造像內(nèi)容;藝術特點;學術價值
1 地理環(huán)境及歷史沿革
塔兒灣石造像塔(圖1、圖2)位于慶陽市合水縣城東北部約70千米的太白鄉(xiāng)苗村塔兒灣子午嶺林區(qū)山叢中。根據(jù)塔兒灣石造像塔的風格和塔內(nèi)出土的文物推斷,此塔的建造時代為宋代。2013年塔兒灣石造像塔被評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xiàn)已移至合水縣博物館院內(nèi)。
子午嶺橫亙黃土高原腹地,地跨陜西、甘肅兩省,海拔1600~1900米,南北約400千米。子午嶺在慶陽境內(nèi)縱貫正寧、寧縣、合水、華池四縣,南北長207千米,森林覆蓋總面積497平方千米,約占全市總面積的1/5,為慶陽天然自然屏障,且文化遺產(chǎn)豐富,底蘊深厚。塔兒灣石造像塔所在的太白鄉(xiāng)苗村屬子午嶺文化區(qū),風景宜人,河水繞青山,風光蔥蘢秀麗。
自北魏尊佛教為國教以來,唐、宋、遼、金、西夏、明、清諸代都很尊崇佛教。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子午嶺地區(qū)建造了眾多石窟,說明在這一帶佛教信仰流傳時間久長,并且有著廣泛的信仰基礎。且此地正好靠近秦直道,是歷經(jīng)寧夏的必經(jīng)之地。發(fā)達的交通與經(jīng)濟、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等優(yōu)越條件,對佛教文化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從時代分布來看,該地區(qū)的佛塔以宋代居多。北宋與西夏在子午嶺一帶對抗,這里成為宋朝的戰(zhàn)略要地。頻繁的戰(zhàn)爭使民眾感到恐懼,而士兵時常戰(zhàn)死沙場,所以當?shù)孛癖姀V造佛塔或求得平安,或追懷死者。
塔兒灣石造像塔受子午嶺地區(qū)佛教文化興盛的影響,在佛教文化東西交流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是東西佛教文化傳播的重要物質(zhì)遺存,也對研究中原佛教文化與西部草原少數(shù)民族佛教交融、變化有著重要意義。
2 塔兒灣造像塔藝術形制
塔兒灣造像塔采用當?shù)厣皫r雕鑿,由大小石塊干疊成形,八角十三層,成密檐式,塔高10.795米,上有塔剎。塔基和第1層塔體為多塊石料組合,第1層特高,達2.24米,占全高的1/9。其他各層的塔體、塔檐均為整塊石料。塔體為空心環(huán)狀八面體。
①塔基:塔基經(jīng)清理為夯土,深2.3米。夯土上有4塊條石平鋪,構成邊長1.45米的正方形。塔基上為整環(huán)形八面體,每面浮雕1個天王或力士,相間雕飾。天王站立,頭戴兜,身著鎧甲,雙肩飾飄帶;力士半蹲,頭戴帽,身著短窄衣褲,袒胸露臍,一手上舉,一手按膝。塔基高0.475米,直徑1.3米,再上置厚0.2米的八角形塊石,其徑1.4米。
②第1層:第1層高達2.24米,占全高的1/9。布滿造像,共608身。塔分8面,每面9層。最下面2層為素面磚塊,構成天宮;素面磚塊之上為4層淺浮雕磚塊,共造像416身;這4層之上每面為1大塊磚體,8面共有196身。每方雕像居中者為佛,兩側各排列羅漢6~8身不等。其雕造技法細膩,疏密相間,布滿壁間。最上沿2層同底部2層一樣為素面塊石,環(huán)形八面。
素面天宮:最下兩層是素面塊石,每層8塊,厚16厘米,寬20厘米。這2層塊石構成的空間即天宮,內(nèi)有一石棺,石棺周圍有銅鏡6塊和散放的錢幣19枚。
四層浮雕:在兩層素面塊石之上為4層淺浮雕塊石,每層仍由8塊組成,起高20厘米,寬20厘米。造像內(nèi)容以佛說法為主,佛跏趺坐,禪定印。佛周圍為弟子、羅漢,或立或坐,形態(tài)各異,另有文殊、普賢兩菩薩的出行圖,還有佛游歷傳道圖和法身像等。每塊造像多為13身,4層八面造像共416身。
整塊浮雕:在4層塊石浮雕之上為一塊中空整體八面體浮雕塔體,高58厘米,徑1.3米,佛雕內(nèi)容有佛說法圖。此層面造像數(shù)一般為24身不等,八面造像共196身。
③塔檐:第1層塔體之上為八角形整塊塔檐,其高20厘米,徑146厘米。檐上為每角起豎脊,兩脊之間為6條瓦櫳。檐下為3層遞減仿木檐枋,均在檐角交叉。
④第2層至第13層:塔體均為整塊中空的環(huán)形八面體,均為素面。塔檐形制亦與第1層塔檐相似,只不過各層的塔體和塔檐向上逐層縮小。13層以上為塔剎,剎高76厘米,亦為砂巖雕鑿而成。剎桿頂部為圓尖寶珠頂,剎桿插在五層環(huán)狀相輪之內(nèi)。
3 佛造像內(nèi)容
3.1 天王、力士
塔基為環(huán)形八面體,每面浮雕1個天王或力士,自東向西,相間雕飾。主體均浮刻于1個正方形的龕內(nèi)。
天王站立,頭飾發(fā)髻,臉部渙漫不清,袒露上身。雙肩飾飄帶,飄帶穿過胳膊交疊于后背,下著長褲,一側飄動。手勢分為兩種:一種為雙手均叉腰,一種為一手叉腰、一手向上托舉。
力士半蹲,頭戴護耳帽,臉部亦渙漫不清。身著短窄衣褲,袒胸露臍。手勢分為兩種:一類為一手上舉,一手按膝;一類為兩手扶膝蓋。
3.2 佛說法圖
塔第1層自下而上有4層八面淺浮雕,造像內(nèi)容以佛說法為主,另有文殊、普賢兩菩薩出行圖。佛說法圖均有嚴格的套路和圖像傳統(tǒng):一佛居中,坐在蓮花座或方形束腰座上,有10或11弟子對稱分上下兩層相伴佛左右。在遵循嚴格的結構同時,人物姿態(tài)各異、栩栩如生、形態(tài)逼真。
佛坐姿:佛身披袈裟,有的袒露右胸及右膊,佛手印模糊不清,多施無畏印、與愿印、禪定印。佛坐式為跏跌坐或結跏跌坐。有的則雙腿自然下垂,雙手扶膝,神情親切。基座或簡,或由蓮花瓣裝飾。
佛左右:以佛為中心,佛身左、右兩面或立或坐10多身羅漢,如圖9~圖16,各個弟子、羅漢均以坐姿為主。圖11、圖14、圖16中,各弟子、羅漢均以站姿為主;圖9中羅漢、弟子或坐或立。相較佛的端莊威儀,眾弟子就較為自由活潑,各具情態(tài)。如圖13,畫面中心有1佛、2菩薩、2弟子。佛身披通肩衣,禪定印,坐于蓮花寶座,身后菩薩和弟子恭立、雙手合十,肅穆恭敬。而左上角兩僧相背倚靠,一腿屈膝,一腿盤臥。一僧將經(jīng)絹高舉額前,仿若在高聲誦讀;一僧左手撫額,拿著經(jīng)絹的右手自然垂于身側,姿勢松弛自然,好似在冥思感悟。畫面右上角盤坐的兩僧也頗有趣味,一僧側歪腦,一手握經(jīng),一手指天,高談闊論,旁人靜聽,思慮贊同。整幅畫面動靜結合,形象各異,情態(tài)傳神,體現(xiàn)了較高的藝術技巧。
3.3 菩薩出行
塔南側雕文殊菩薩出行圖和普賢菩薩出行圖各1幅。
文殊菩薩出行圖(圖17):文殊乘雄獅,右臂曲指前方,右手持金剛寶劍,能斬群魔,斷一切煩惱。左手持青蓮花,花上有《金剛經(jīng)》卷冊,象征所具無上智慧,惜臉部渙漫不清。獅子身配鞍纏、瓔絡等飾物,昂首挺胸,軀肢剛勁有力,拔步前行。兩側有牽獅奴、力士和突目豎眉力士簇擁。
普賢菩薩出行圖(圖18):普賢乘象,普賢菩薩代表理德、定德、行德,結跏趺坐于象背寶座,象征愿行的堅持。面目和手中所持之物已殘存不清。象低首向前,象牙、眼、鼻刻畫細致逼真,四足穩(wěn)健有力。象額隱見裝飾,背部覆鞍帔約有花紋。兩人御象,一人立于象背,傾仰牽鞍繩,一人立于象旁揮臂前行。在大象前站有五羅漢擊釵、鼓樂,相向或背立徐徐前行。
3.4 整塊石體佛說法圖
塔由下而上的第5層為八面中空整體浮雕塔體(圖19~圖22),高58厘米,徑1.3米,佛雕內(nèi)容亦為佛說法圖,比1至4層的長方小石塊說法圖構圖更為復雜,手法更為飄逸。每面佛居于高處中心位置,為半跏趺坐或結跏趺坐于高座上,或倚坐,端嚴無比,八面佛體手勢均有所不同,構思巧妙。弟子、菩薩、羅漢位于兩側,體型都小于佛。每面造像數(shù)一般為24身,數(shù)量略有差異。八面造像約196身,以佛體為中心從兩側分三層或四層延展開來,稍有疊層錯落。由塔底觀上,內(nèi)容繁復多樣,如臺梯層層疊疊而上,衣著飄逸靈動,更襯托佛的莊重威嚴。
4 藝術特點
4.1 構圖
4.1.1 左右對稱式構圖
在佛國世界里,神有神主,有仆,有尊,有卑。在塔兒灣石造像塔中的石雕佛造像組合中,為了表現(xiàn)這種差別,主要采用突出中心的左右對稱式構圖。以佛為中心,弟子、羅漢侍列在佛左右。佛高居其中,多為半跏趺坐或結跏趺坐于高座上,端嚴無比。弟子、菩薩侍立兩側,體型都小于佛,而且多面向佛。正是利用這種構圖方式突出佛的尊嚴,區(qū)分了佛國世界里的尊卑貴賤和地位高低。
4.1.2 立體式造像構圖
塔由下而上的第5層石雕,場面宏偉,采用了表示時空感的立體式造像構圖。佛以立體性雕塑居于最高位、最中,佛左右和下面皆浮雕小于佛的弟子、羅漢。佛面渙漫不清,在背后有彩繪背光,佛的衣袖有的隨風飄動(圖19),有的靜如禪鐘(圖20),從坐姿就能感受到端莊威儀。菩薩、弟子皆為淺浮雕,立于鏟位較深的雕巖之上,刀法順切,線條鏗鏘有力,仰望有隨風移動之感。弟子有的虔誠拜佛、俯首聽法,有的肅靜而立、仰首傾聽,他們和莊嚴的佛互益曾輝,產(chǎn)生了動靜協(xié)調(diào)的藝術效果。天上人間渾然一體,組成了一個神圣的“佛國世界”,體現(xiàn)了古代匠師高超的藝術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
4.2 風格
4.2.1 主體佛程式化
塔兒灣石造像中主體佛的面容大都風化殘缺,但在構圖、坐姿和衣飾上都體現(xiàn)出佛的端莊威嚴。如佛說法圖中佛居于中央,同兩側的眾弟子與羅漢相比,體型較大;坐姿均采用跏趺坐或善跏趺坐;站姿挺拔,一手置于腹部,一手揚起解說,淡定儒雅。相較于兩側羅漢造型,主題佛像藝術風格趨于程式化。
4.2.2 弟子、羅漢自由化
塔兒灣佛塔石造像中的弟子、羅漢造型自由活潑,手法寫意,豪放自由,極富生活情趣,通過對比突出了佛的沉靜端肅。眾弟子、羅漢動態(tài)多樣,有的安靜側首聽法,有的似在深思,有的撓頭不解,有的兩兩相對交談,甚至在激烈辯論。盡管大部分面容風化不清,但從少數(shù)存留可以依稀觀察出他們豐富微妙的面部表情。如圖23中右下角人物,五官舒展,嘴角上揚,流露參透教義的喜悅。弟子、羅漢造像在遵循佛像儀軌制度的同時,給予人物生動的性格,體現(xiàn)了工匠們非凡的藝術創(chuàng)造才能。
4.3 價值
4.3.1 歷史價值
塔兒灣造像塔歷經(jīng)時間洗滌和風沙侵蝕,盡管很多造像面部不清,但依然保留完整的形制、石雕造像、塔內(nèi)文物,可以看出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第1層塔底部構成的天宮內(nèi)出土了石函,石函內(nèi)棺床上臥涅槃佛像。函底部四角雕有4力士,蹲俯狀,一手上舉,一手扶膝。涅槃佛像雙目微閉,佛右手上曲枕于頭下,左手自然垂于側,右腿微曲,左腿伸直,整體形態(tài)自然而放松,涅槃卻猶如在夢中一般安詳。石函四周有銅鏡6面,銅錢幣19枚,最晚的則是崇宗重寶,因此推斷此塔建造時應在北宋末年,即宋徽宗崇寧年間。
北宋末年戰(zhàn)亂紛擾,民不聊生,殘酷的戰(zhàn)爭使無望的民眾需要得到心靈的慰藉。合水塔兒灣造像佛說法造像所呈現(xiàn)的佛的慈悲憫懷,信徒虔誠禮佛的場面,佛涅槃之后的祥和圓滿,都在感召民眾皈依,引導他們?nèi)淌芸嚯y現(xiàn)實,使他們相信人生能夠輪回轉生,因而佛教成為民眾的唯一精神依托。繼宋代之后,金代佛教興盛。塔兒灣造像塔是慶陽佛教文化發(fā)展歷史中的一頁,見證了慶陽作為戍邊之地,戰(zhàn)爭紛亂、人們苦難掙扎的殘酷社會現(xiàn)實。
4.3.2 藝術價值
塔兒灣造像塔石造像圖像豐富,多成組出現(xiàn),雕刻技術純熟生動,無論是構圖還是人物造型,都與慶陽當?shù)厝A池雙塔寺石雕造像極為相似,有著較高的藝術創(chuàng)作水平,對研究隴東宋末金初時期佛教藝術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構圖采用多層組合復調(diào)敘述的方式,合水塔兒灣造像塔將力士、說法圖、菩薩等所有佛造像以多人物組合,均逐次集中于塔第1層;華池雙塔寺佛造像說法圖、涅槃圖、菩薩等造像均以多人物組合的方式在塔第5層中分別予以表現(xiàn)。
塔兒灣造像塔與雙塔寺佛造像都具有人物繁多緊密、形態(tài)多樣的特點。有坐佛、有立佛,坐佛有多種坐姿,立佛組合人物線條統(tǒng)一,有較強的形式感。塔兒灣造像塔中弟子或虔誠跪拜禮佛,或誦經(jīng)吟讀,或扶額沉思;雙塔寺中的釋迦牟尼涅槃圖中的弟子或痛哭流涕,或坐地哀嚎,或捶胸,或掩面。人物造型逼真,情感豐富,合情合理,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隴東宋金時期佛造像藝術具有較高的藝術成就,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加之文獻資料少,因此該領域的研究并不完整。塔兒灣石造像塔在宋金時期佛教文化交流與藝術傳播等方面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本文對合水塔兒灣石造像塔內(nèi)容分類、構圖方式、藝術特點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并通過與華池雙塔寺石造像的造型略作比較,發(fā)現(xiàn)隴東金初佛造像與宋代晚期佛造像較為相似。塔兒灣造像塔的深入研究對建構隴東地區(qū)佛教藝術體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參考文獻
[1]劉鳳君.考古學與雕塑藝術史研究[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1.
[2]張馳.宋崇寧佛教造像浮雕“奏樂圖”及其價值[J].隴右文博,2016(3).
[3]李紅雄.慶陽歷史文化區(qū)系定位——子午文化[M]//李紅雄.考古記略.慶陽:[出版者不詳],2005.
[4]劉治立.秦直道與子午嶺地區(qū)的佛教遺存[J].敦煌學輯,2003(2).
[5]李紅雄.合水塔兒灣石造像塔被炸后搶險落架簡報[M]//李紅雄.考古記略.慶陽:[出版者不詳],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