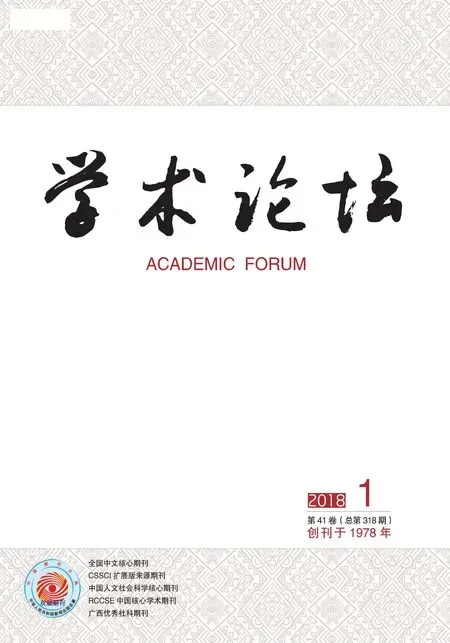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的美學重構
肖瓊
2011年4月,伊格爾頓推出了又一部力作《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書中羅列了十種最常見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觀點并一一進行駁斥,其中列舉的第四種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之間復雜關系的重新思考。西方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表現在,“馬克思主義不過是烏托邦之夢。它將希望寄托于一個完美的社會,那里沒有艱難,沒有痛苦,沒有暴力,也沒有沖突。在共產主義的世界里,沒有對抗、私利、占有、競爭或者不平等。人人平等,毫無貴賤之分。人不再需要工作,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物質財富源源不斷。……馬克思對未來的天真想法反映了他整體政治思想的荒謬與不切實際”[1]。在伊格爾頓看來,這種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過是烏托邦之夢”的觀點,是基于這樣的理由:第一,馬克思主義過于天真地相信人性的美好而無視人性的險惡,人性本來是貪婪的、自私的、好斗的、充滿競爭性的。其言下之意是,基于這樣的人性基礎上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公正社會只不過是一種烏托邦。第二,由于實踐最終導致殘酷的鎮壓,所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實踐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馬克思主義讓它的信仰者最終陷入了毀滅自由和達成不可能的烏托邦的歷史決定論中,由此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簡單的樂觀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到底構成怎樣的復雜關系?受當代激進理論家強調要以一種回溯性的視角來看待事物觀點啟發,正值托馬斯·莫爾發表《烏托邦》500周年的當際,筆者以回溯性的視角重新考察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卻發現,馬克思主義以其獨到的悲劇性視角,在現代性的美學視域中重新構筑了烏托邦的內涵及其美學意義。
一、從對立到區分: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內涵轉變
“烏托邦”一詞出自英國托馬斯·莫爾的《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一書。“莫爾生造這個詞是指一個并不存在的國家(U-topia),又指一個值得所有人追求的國家(Eu-topia)。”[2]可見,莫爾最初生造出的這個詞,應該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并不存在,也就是帶有空想的性質;但由于它是一個空想出來的美好的地方,所以有了第二層意思,值得所有人追求,從而演化為一種烏托邦精神。這種烏托邦精神可以對現實社會構成一種批判維度,以激勵人們起來改造當下的這個社會,并且不斷完善這個社會。所以托馬斯·卡伯(Thomas Kamber)總結道:“認為烏托邦是‘不存在的地方’遵循的是客觀描述現實的任務,也許這是一種想象的自由,但也只存在于他們的理念中。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為烏托邦是‘好地方’,它就成了我們已經接受的‘可能性’觀念的挑戰,是‘鼓勵重新考慮替代方案’的挑戰。”[3]
19世紀,烏托邦的內涵開始發生巨大轉變。如本尼特所言,“在經典時期,烏托邦作為原初的幻想在發揮作用,與之相反,19世紀的歷史的思想體系的發展在烏托邦思想的世俗方向中實現了一個轉變”[4]。如果說莫爾最先提出“烏托邦”時開創了一種特殊的文體,即烏托邦文學,主要指虛構出的一個文學或美學中的世外桃源,而19世紀的烏托邦內涵更多轉向更為豐富的和更具肯定意義的層面,即它的美好愿景方面。如果烏托邦意味著一個完美無暇的社會,那么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就有著同質性的關系。至此,烏托邦概念的文學虛構含義漸漸淡化,開始凸顯出它的政治含義。
不過,烏托邦最初在馬克思主義領域中是作為一個貶義詞,主要還是在空想的意義層面上進行使用,其對立面是科學。恩格斯首先將烏托邦與科學對立起來理解。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將圣西門、傅立葉、歐文歸為空想主義者,認為他們提出的社會主義只是從頭腦中產生,是一種空想的理論,這種理論的不成熟也是與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和階級狀況相適應的:“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5]而基于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這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發現,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不再被看成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成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必然產物。其任務也不再是去構想盡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斗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沖突的手段”[6],從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烏托邦”與“科學”相對的經典用法。后來的第二國際和蘇聯(尤其是在斯大林掌權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者紛紛用“科學”來標榜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以“烏托邦”“烏托邦的”來攻擊政敵,語氣中充滿了對烏托邦的輕蔑態度。
馬克思把迄今所有一切都稱為“前歷史的”。在馬克思看來,到目前為止的敘事只不過是某種潛在剝削模式單調而乏味的變體而已,“唯一真正的歷史事件是與前歷史決裂,讓歷史開始啟動”[7]。馬克思構想的歷史正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然,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構想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用伊格爾頓的話來說,因為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拿未來說事,“馬克思對那個沒有痛苦、死亡、損壞、失敗、崩潰、沖突、悲劇甚至勞動的未來根本不感興趣。事實上,他根本不關心未來會怎樣。眾所周知,馬克思根本無法描述出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究竟是什么樣子。……他或許認為社會主義必然會實現,但他很少說起這個必然到來的未來社會到底會是什么樣子”[8]。對未來的細致描摩和勾勒,必定會迫使我們為了細細研究它們的特性、特殊的原因和結果,而將它們從歷史的必然聯系中剝離出來,從而導致了對現實本身的不斷抽離。詹姆遜也強調:“烏托邦不是一種表征,而是一種作用,旨在揭示我們對未來想象的局限,超越這種局限,我們似乎再也不能想象我們自己社會和世界的變化。 ”[9]
由此,馬克思主義認為應該有很多種烏托邦。而馬克思主義也可以是一種烏托邦,但不是傳統的烏托邦,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烏托邦的積極的烏托邦。其后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有意識地區分出兩種烏托邦,以區分出馬克思主義烏托邦與傳統烏托邦的不同。恩斯特·布洛赫首先區分出“抽象的烏托邦”和“具體的烏托邦”。布洛赫的貢獻在于使烏托邦最終發展成了一個哲學概念:“在哲學領域,主要是由恩斯特·布洛赫拓寬了它的概念內容,使它上升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范疇。”[10]在布洛赫看來,烏托邦想象指的是“尚未”,不是存在的東西,而是生存的、“尚未意識到”的或“尚未成為”的。烏托邦作為一個意象可以折射出一個更美好的狀態,以與現實構成對照。布洛赫于是區分出“抽象的烏托邦”和“具體的烏托邦”。“抽象的烏托邦”是一種靜態的理想社會發展模式,它只是人們根據某種觀念、正義或上帝的啟示來構想的一種社會發展模式,而非按照社會內在的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由于缺乏對現實的生活世界的必要認識和理解,“抽象的烏托邦”最終把理想絕對架空,并與現實絕對地對立。“具體的烏托邦”則強調通向未來理想社會的動態過程。它緊貼堅實的現實基礎,始終內在于歷史的進程,因而剝去了以往烏托邦純粹的空想、補償性和逃避現實等因素,既可以作為指向更美好世界的意象折射,又是激勵人們致力于完善社會的理論參照。布洛赫于是把馬克思之前的社會烏托邦稱為“抽象的烏托邦”,而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具體的烏托邦”。在《向烏托邦告別嗎?》中,布洛赫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并非不是烏托邦,而是一種具體的烏托邦的新事物。”[11]而我們當下的迫切任務在于區分具體的烏托邦和抽象烏托邦,恢復具體烏托邦的革命實踐性,以喚起烏托邦精神。
其后的拉塞爾·雅各比也區分出傳統的藍圖烏托邦與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傳統的藍圖烏托邦”試圖精確地規劃人們的生活,并繪制未來的“藍圖”(blue-print);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則拒斥藍圖設計師對細節的癡迷,也抗拒現代圖像的引誘,他們只是用完全敞開的心靈和耳朵去靠近烏托邦,就像靠近上帝一樣。伊格爾頓則區分出 “好的烏托邦”和“壞的烏托邦”:壞的烏托邦是指超越于現實生活的基礎上通過想象來建構未來的烏托邦,它們“隨手抓住某種未來,以一種超出了約定的現存政治結構的意志行為或想象行為把自己投射出去,人們或許會稱之為‘虛擬語氣’”[12]。這種烏托邦是危險的,它并不能為我們提供某種歷史的必然性和決定論。好的烏托邦則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價值判斷和理想,是能夠直面“真實界”并值得我們為之奮斗的未來理想。在目前范圍之內,烏托邦正被一些力量或虛假線路以特殊方式發展或展開,由于它們過早地引入將來,從而導致“我們像神經病人一樣為無法遏止的渴念所困擾”[13]。好的烏托邦可以超越地解決社會發展中的“惡”的一面,通過對現實的內在批判而不是外在批判,在現實的力量中發現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伊格爾頓提出,在一個文化危機、問題叢生的世界,要回答人往何處去這個重要問題,必須在新文化引領下去構建一個“好的烏托邦”,避免傳統文化框架中的“壞的烏托邦”。這樣,從對立到區分,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的關系更趨復雜,同時烏托邦也逐漸具有了政治的意涵。
二、悲劇的視角: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政治學
馬克思認為,未來的唯一形象乃是當下的失敗。馬克思一向認為,關于未來的描述和展望,重要的不是對于理想未來的美好憧憬,而是如何去解決那些會阻礙這種理想實現的現實矛盾。未來雖說不可避免,但也并不意味著一定比現在更美好。馬克思最反對“那些烏托邦主義者相信單純憑借論辯的力量就可以戰勝對手。對于這些人來說,社會是觀點交鋒的講臺,而不是物質利益沖突的戰場”[14],而是主張,“世間男女的觀念都源自他們日常的實踐,而不是哲學家或辯論協會之間的交流。如果你想要了解人們的真實想法,就得留心觀察他們做了什么,而不是聽他們說了什么”[15]。所以,馬克思強調的不是對未來冥想的烏托邦藍圖,而是為未來奮斗的革命實踐,采取怎樣的行動讓那個美好的未來成為可能。馬克思主義這樣理解烏托邦的過程:“烏托邦來自于抗爭,不是善與惡之間(基督教精神的戰士)之間的抗爭,而是在新與舊,推演和暴力,安全性和命運性之間的抗爭,一個嚴格的規則和豐富的世界很多(來自異教徒悲劇的反抗力量)。”[16]他們強調在悲劇的框架中辯證地看待現實與未來的復雜關系,認為“只有從這個等待救贖的現實做起,以其墮落的邏輯作為擊潰它的武器,你才能寄希望于超越這樣的現實”[17]。正是在現實與邏輯的自相矛盾中,他們構想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的輪廓,不僅看到了階級斗爭作為一個巨大的悲劇,而且從悲劇中發展出一種烏托邦政治學。
早在德國浪漫派那里,人們就已經不再是僅僅將悲劇視為一種藝術體裁或類型,而是視為一種哲學觀念、審美意識、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反應或人生態度。威廉斯在《現代悲劇》中強調,悲劇既是作為現實悲劇經歷的共同名稱,又是作為特殊戲劇藝術的名稱,這兩種有關悲劇的不同含義其實相互依存,非常自然。叔本華悲劇理論的出現標志著悲劇的世俗化開端,對悲劇發生學的解釋轉向了人性的角度。悲劇災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個人犯了什么罪過,而是贖罪,贖生存本身的罪過即原罪。叔本華將悲劇與人類普遍命運聯系在一起的,從而讓以往的悲劇與倫理的關系,演變為悲劇與歷史危機之間的內在關系。受叔本華的影響,尼采也將藝術視為可以逃避痛苦現實的手段。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辯證基礎上,尼采看待悲劇并不像叔本華那么悲觀,而是透過現實中的各種生死交替,從更長遠的人類發展的層面看到了堅不可摧、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尼采對悲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概括的基礎上,威廉斯提出,在現代悲劇中,神話已經重新被作為悲劇性知識的源泉。悲劇行動的意義在于死亡和再生的循環,苦難成了死而復生中必不可少的環節[18]。
馬克思則將倫理力量的沖突放置于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框架中,將黑格爾精神歷史的客觀性替換為社會和歷史的術語,提出了一種革命的歷史悲劇學說。馬克思主義一向反對抽象的人性論,任何觀念的存在都必須產生于他們的日常實踐,而組織機構的變革確實會對人們的態度產生重要影響。因為觀念是蘊藏在日常生活行為當中,通過日常生活行為的集體形塑,我們可以改變人類看待事物的方式。威廉斯于是首先將悲劇作為一種觀念,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情感結構、直接經驗聯系起來。對于威廉斯來說,悲劇就是“一種特殊的事件,一種具有真正悲劇性并體現于漫長悲劇傳統之中的特殊反應”[19],它在“情感結構”的層面上指導我們的行動,影響并構造世界。伊格爾頓更是提出,悲劇“可以同時指藝術品、現實生活的事件、世界觀或情感的結構”[20],其最基本的共同點乃在于苦難的事實。苦難的現實總是會激起人們的憐憫和同情之心,所以基于現實經驗和情感結構的層面,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成功地將悲劇與革命進行了美學聯接。
第一,悲劇總是孕育著超越現實的力量。悲劇的視角正意味著對當下現實的一種批判。盧卡奇在《悲劇的形而上學》中最先揭示了悲劇與現代社會的關系、悲劇的烏托邦意義以及如何重建形而上學。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其實混沌一片,在工具理性的高度支配下,現代人已處于完全疏離的狀態。任何事物的價值都無法完全實現,世界和人生都變得毫無意義。悲劇的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并不知道生活的欺騙術,甚至沉迷其中不能自拔。這個時候,只有某一偶然的突發事件或騷動,才能激起人們對本真生命的渴望。這個時刻盧卡奇稱之為“偉大時刻”,通過悲劇中的死亡,激發出形而上學的思考。也就是說,只有悲劇才能獲得對現實的批判視角和現實反思。戈德曼則在《隱蔽的上帝》中提出,悲劇人必須具有兩個本質性的特征:其一,他對不可能實現的價值有一種絕對的、毫不妥協的要求;其二,作為這種要求的必然結果,他所要求的“要么是全部,要么是烏有”[21]。在戈德曼看來,悲劇人心中總有一個烏托邦沖動,他們尋求真正的善,尋求對真理的絕對要求,然而現實生活卻總不盡意,往往很難達到悲劇人所要求的絕對的真善美,這也注定悲劇人對這個令人失望的世界的拒絕態度。由此,悲劇總蘊育著烏托邦沖動,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對現實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遠景更新的憧憬。
第二,悲劇不是消極的悲觀主義。消極的悲觀主義是法蘭克福學派,他們“對大眾文本深層結構的研究,或許能夠合理地解釋我們對這個體制的厭惡,但它無法提供在這個體制內部進步的希望,它所能提供的僅僅是經由激進革命改變資本主義這樣一個烏托邦的信念”[22]。悲劇應該是一種積極的悲觀主義,潛藏著某些革命性、顛覆性的東西。悲劇為世俗的經驗世界生出了一種精神上的參照,從而否定了現狀中的人們滿足于物質利益需求的世俗性層面,升騰起一種絕對的價值和意義。這種絕對價值因為是將人們從現代的混沌世界中拯救出來而彌足珍貴。悲劇亦不是膚淺的樂觀主義。膚淺的樂觀主義只是想象界層面的盲目樂觀,不可避免地帶有幻象性質;而悲劇的希望是在失敗的經驗基礎上滋生出來的,是在絕望中仍然能夠堅持的執著信念。悲劇的悖論性邏輯在于:通過毫不退縮地服從于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人們反而超越了它。
馬克思主義一向更為關注歷史的“壞”的一面,關注有關歷史的苦難記憶,如本雅明致力于世俗狀況的絕望無助。本雅明一生都在尋找失敗與革命斗爭的記憶,其目的是為了在逝者和被壓迫者的記憶中找回革命精神,為現實斗爭注入能量。而后現代主義由于過度宣揚令人沮喪的歷史意象,反而剝奪了本雅明于頹廢意象中所寄寓的反轉的希望。伊格爾頓強調后現代主義社會中所存在的令人沮喪的現象以及在情感上給人帶來的絕望,正是可以考驗人的潛能和極限的歷史契機。“如果你不能繼續跌落,那么唯一的方向就是上升。”[12]悲劇告訴我們的是,在后現代主義時代,我們可以靜等悲劇情節的突轉。馬克思主義因此從悲劇中發展出一種烏托邦政治學,從對悲劇的讀解中援引出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現實力量。
三、從烏托邦到實踐: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
作為一個世俗猶太人,馬克思嚴格秉承猶太人的傳統而禁止預測未來,他對單純的未來憧憬不感興趣,因而無法描述出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樣貌。美好的未來不會憑空而至,而是要通過人們的實踐和革命。馬克思主義在兩個方面澄清了人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一是“社會主義革命”并不等于暴力革命;二是轉向從悲劇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革命。
馬克思主義對革命理論的最大貢獻是他們站在歷史唯物論的高度,從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系角度去解釋社會“革命”的各種潛在原因,并根據各個時代的社會現實提出的各種革命理論設想,如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到盧卡奇的“意識革命”,從法蘭克福學派的“藝術革命”到阿列西、巴迪歐、朗西埃等的“美學革命”。而英國馬克思主義更是直接提出從悲劇到“文化社會主義”的理論構想,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從文化到共同文化,從而從悲劇進入文化社會主義的具體途徑。在這里主要介紹一下阿列西、巴迪歐、朗西埃等的“美學革命”理論和英國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關于從悲劇到“文化社會主義”的理論構想。
1968年“五月風暴”的失敗,很多理論家陷入深深的思考,“認為社會的進步,除了經濟指標和物質生產這些基礎性因素之外,很重要的還要意識形態方面實現美學革命,實現新的啟蒙”[23]。馬爾庫塞強調審美可以通過改變主體而間接地改變社會,所以今后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馬克思所說的“暴力革命”,而是在意識形態的革命或美學革命的方式所進行的漫長革命。在《美學的革命》一文中,阿列西明確指出,“美學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概念。它的理論建設基礎建立在不同的“革命代理人”,尤其強調“必須破除對政治主體的本質主義理解,革命的主體必須由單數的無產階級轉變為連接女權主義、民族斗爭、種族斗爭的復數主體”[24]。而當下的革命代理人都是作為各種潛在的代理人或者隱喻而起作用,可以是我們同時代中“被排除出去的人”,可以是雅克·朗西埃所說的“沒有角色的角色”(part of noPart),也可以是吉奧喬·阿甘本所說的“犧牲人”(homosacer)[25]。
對于朗西埃來說,“革命”的目標并不是培養新感性,而在于感性的重新分配。針對席勒在《論人類的審美教育書簡》(1795年)第十五封信的結尾處提出的矛盾和作出的許諾——“只有當人在游戲時,他才是完整的人”,他認為可以這樣重新闡釋:這是一種力圖要將共同體改造成一種藝術品的極權主義做法,當下的自由社會及其商業娛樂的日常審美化生活,其作用正是在讓我們體驗到這種“生活藝術”和“游戲”的現實中,重構了我們對社會的感覺經驗和分配方式。朗西埃舉了一個例子,1848年,《工人警鐘報》報紙描述了一位為豪宅鋪設地板的細木工,用日記的形式描述了他和同伴在房間里工作的美好時光和審美幻象:只要地板尚未鋪完,他就喜歡這個房間的布置,相信自己是在家中,如果窗戶是對著花園敞開的,或遠遠望去是一幅如畫的風景,他便停下工作片刻,在想象中向著那片廣袤風景滑翔,可以說,他比隔壁住宅的主人更好地享受著這一切。但這在朗西埃看來是一種擾亂,被稱為“不是部分的部分”。它原本不屬于可感性分配的資源,現在卻通過“增補”對既定的可感性配置進行擾亂,從而建構了一種新的感性世界的方式。阿列西概括出“美學的革命”的兩個特點:第一,革命運動都是在尋找和推舉出這個歷史和社會的代理人;第二,每一個革命的事件都為其重復所替代。重復“取代”了以前的革命實踐的發生和進程,在美學革命中,事件的關注似乎更在于過程本身,更強調“做”的過程而非“創造”的目的。
同樣,英國馬克思主義也在試圖開創一條從共同文化走向社會主義的現實文化解放之路。在對共同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威廉斯提醒我們,共同文化的獲得,首先需要在共同生活的每個層次上獲得群體的生活資料,這是獲得共同文化經驗的根本原則。威廉斯于是刻意轉向對共同經驗的強調,以及對經驗的相似性的強調。在《文化與社會》中他強調:“文化的觀念是針對我們共同生活狀況所發生的普遍和重大變化所做出的一種普遍反應。其基本成分是努力進行整體性質的評估。我們共同生活的總體形態發生改變后,必然會產生了一種反應,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放在整體形態上。特定的變化會修改一種習慣法則,轉變一種習慣行為。普遍的變化在完成以后,會促使我們回顧總體規劃,使我們把它當作一個總體進行重新審視。文化觀念形成的過程即慢慢地重獲掌控的過程。”[26]而2009年伊格爾頓在《國際社會主義》上發表的《文化與社會主義》一文,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從文化的層面探討進入社會主義的途徑。伊格爾頓認為,從身體出發,如果我們軀體的感知得以改變,一個文化的社會主義不難實現。
然而,歷史的軌跡必須要穿過無數個人的悲傷與痛苦,死亡亦是不可避免。馬克思主義不僅要探索新的語境中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問題,同時還清醒地意識到社會主義實現路途上的艱難和困頓、挫折和險境。如威廉斯所說,只有以一種悲劇性的角度去認識革命,革命才能夠持之以恒。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完成對“社會主義革命”認識的澄清在于轉從悲劇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革命。最早從悲劇的角度來看待革命的又是威廉斯。奧康納評價道,“在威廉斯論文中最獨特的是《現代悲劇》中關于悲劇與革命的那部分”[27]。威廉斯在兩個層面上來看待革命:一方面革命指的是一個持續很長時間的緩慢累積形成的轉變過程,而不是暴力和混亂的方式呈現,同時這個轉變既緩慢又不穩定,甚至是難以察覺的;另一方面,革命又是關于無序混亂的更全面過程的特定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就是使潛在的、長期的無序向明確的暴力危機的轉變,“過去,我們看不到悲劇是社會危機;現在,我們通常看不到社會危機是悲劇”[28]。威廉斯肯定了革命的長期性和必然性,只要這個社會“實質上無法在不改變現有基本人際關系的前提下吸納它的所有成員(整個人類),那么這個社會就是需要革命的社會”[29],悲劇行動其實就是對這種無序的對抗和解決。然而革命行動的過程又是悲劇性的,無序、斗爭、邪惡和苦難是革命過程中必定伴隨的結果。“當我們看到結束異化的努力產生出新的自身的異化時,我們的確看到了某種悲劇的必然性。”[30]所以革命決不是簡單的行動,我們甚至在不自覺中會成為別人的敵人,以最痛苦的方式肯定了這種極度的無序。社會主義革命同樣如此。按照馬克思的思想,革命與造反不同,以往所有的革命中人的活動形式根本沒有改變,只是將這一活動在不同的人群中重新分配,從而引入新的勞動分工。而社會主義政治革命的目標是要取消勞動,消滅階級以至消滅一切階級統治。這就導致“拯救全人類”的思想難免是悲劇性的。如果從實踐的觀點來看,“拯救全人類”的思想只能是一種革命的烏托邦,因為它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可能實現的。而當我們將這個目標的虛幻性奉為一個普遍的真理,并孜孜不倦地去實踐它時,我們就已經成了自己內在的敵人。
伊格爾頓干脆將斯大林主義譏諷為20世紀一部最永恒悲劇的反映:“斯大林主義,不僅在其俄羅斯式的多樣性上,是對20世紀一部最永恒悲劇的反映:社會主義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結果卻最不可能的事實。”[31]其意圖就在于通過這些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經驗提醒我們,這種組織武裝奪取政權“暴力革命”就好像農民起義,政權變更了,而實質性的東西如生產方式、思維范式等卻根本沒有變化。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然而,斯大林主義的悲劇性意義在于,它以悲劇的形式推進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
由此可以得出,在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烏托邦不是一種對未來的描繪,而是對未來的信仰和參照。烏托邦其實就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需條件,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維度,它既是批判現存狀態的前提也是關于未來美好社會的愿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是:我們比任何時代都需要烏托邦,需要烏托邦為我們提供超越現實的希望空間和未來愿景。而當下的中國同樣需要一種積極的烏托邦,需要烏托邦的夢想和情懷來完成現實的打破和現存秩序的改變,從而拒絕盲目的、膚淺的樂觀主義。
[參考文獻]
[1][8][14][15][17]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M].任文科,鄭義,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68,70,72,72,83.
[2]Bertrand De Jouvenel.Utopia for Practical Purpose,Utopians and Utopian Thought[M].ed.Frank E.Mannuel.Beacon Press,1967:219.
[3][16]Thomas Kamber.Marx,Tragedy,and Utopia,Rethinking Marxism[J].A Journal of Economics,Culture&Society,1996(1).
[4]托尼·本尼特.文化與社會[M].王杰,強東紅,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9.
[5][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8,739.
[7]特里·伊格爾頓.我們必須永遠歷史化嗎[J].許嬌娜,譯.外國文學研究,2008(6).
[9]詹姆遜.烏托邦與實際存在[A].王逢振.詹姆遜文集:第3卷[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89.
[10]陳岸瑛.關于“烏托邦”內涵及概念演變的考證[J].北京大學學報,2000(1).
[11]E.布洛赫.向烏托邦告別嗎[J].夢海,譯.現代哲學,2008(1).
[12][13]特里·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M].馬海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310-311,311.
[18][19][28][29][30]雷蒙·威廉斯.現代悲劇[M].丁爾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35,4,56,68,68.
[20][31]特里·伊格爾頓.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M].方杰,方宸,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9,251.
[21]呂西安·戈德曼.隱蔽的上帝[M].蔡鴻濱,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84.
[22]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玨,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129-130.
[23]徐杰舜.審美人類學:從邊緣起步——訪長江學者、上海交通大學王杰教授[J].民族論壇,2015(1).
[24]莫雷.后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概念[J].學習與探索,2010(2).
[25]阿列西.艾爾雅維奇.美學的革命[J].姚建彬,譯.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10(1).
[26]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1780-1950.[M].高曉玲,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311.
[27]Alan O'Connor.Raymond Williams:Writing,Culture, Politics[M].Blackwell,198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