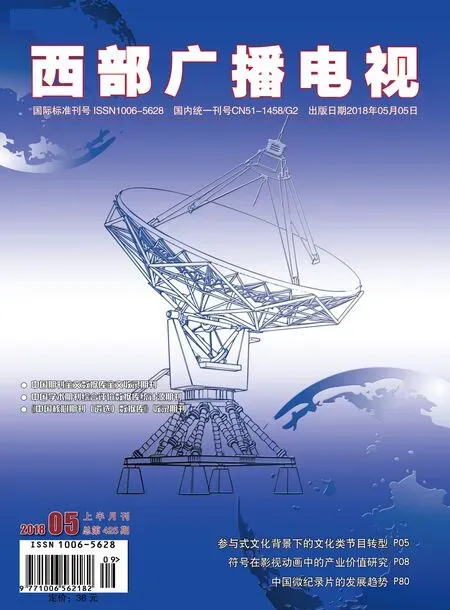參與式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類節(jié)目轉(zhuǎn)型
——以《國家寶藏》為例
陳昕悅
2017 年被戲稱為“文化類綜藝元年”,各種文化類節(jié)目的迅速崛起和火熱成為新媒體背景下逐漸分流的電視節(jié)目市場中一股引人注目的風潮。從年初的《見字如面》《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相繼刷屏,各大電視臺各種欄目紛紛效仿,一時間各種同類型節(jié)目紛沓而至呈井噴狀,卻逐漸陷入同質(zhì)化的怪圈,泥沙俱下,熱度減退,收視降低。隨著《見字如面2》的停播,這把“文化之火”也漸漸熄滅。但是在年末,有著“中國版博物館奇妙夜”之稱的《國家寶藏》卻突然殺出重圍,引爆社交媒體。筆者認為,《國家寶藏》的成功歸因于在參與式文化方面所作出的轉(zhuǎn)型,正是對參與式文化和受眾的尊重將這檔節(jié)目與傳統(tǒng)文化類節(jié)目區(qū)分開來,彌補了大部分傳統(tǒng)文化類節(jié)目的不足,因而帶來了巨大的傳播紅利。
1 新媒體背景下的參與式文化
早在1992年,亨利·詹金斯就在那本著名的《文本盜獵者》中提出了“參與式文化”的概念,他將電視粉絲看作是在節(jié)目方式上的主動消費者、熟練的參與者,是從借來的材料中建構(gòu)自己文化的游獵式的文本盜獵者,是勇于爭奪文化權(quán)力的斗士。他還頗具前瞻性地指出:當今不斷發(fā)展的媒介技術(shù)使普通公民也能參與到媒介內(nèi)容的存檔、評論、挪用、轉(zhuǎn)換和再傳播中來,媒介消費者通過對媒介內(nèi)容的積極參與而一躍成為了媒介生產(chǎn)者。生產(chǎn)者、媒介、消費者(并不僅僅是迷)以及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yún)R集在一起,使得文化工業(yè)呈現(xiàn)出一種雙向通路。
國內(nèi)有研究者對詹金斯的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界定。視角之一是將參與式文化定義為一種新型的媒介文化。李月蓮將參與式文化視為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注重其“公民性”,認為社會中每個人及每個機構(gòu),都主動或被動地卷入了這一文化之中。他指出,“參與式文化指一個社會的文化環(huán)境鼓勵創(chuàng)作和分享,促進公民參與和藝術(shù)表達。”而在本文中,我們將參與式文化定義為一種藝術(shù)表達和公民參與門檻相對比較低、強烈支持創(chuàng)造和共享創(chuàng)造作品的文化。
事實上,參與式文化在中國媒介語境中的應(yīng)用早有端倪,電影《無極》曾被中國大陸自由職業(yè)者胡戈剪輯成《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其下載率甚至遠遠高于《無極》本身。“饅頭”的出現(xiàn),引起了國內(nèi)互聯(lián)網(wǎng)改編、惡搞影視作品的熱潮,也是b站鬼畜、惡搞、再剪輯的發(fā)端,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有許多學者甚至認為這是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參與式文化的開端。而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下,傳統(tǒng)電視節(jié)目的轉(zhuǎn)型將不再是隨波主流,由受眾參與主導,而將積極迎合與改變,去適應(yīng)參與式文化環(huán)境,推動文化參與和再創(chuàng)造的形成。
2 傳統(tǒng)文化類節(jié)目的不足
近年來,文化類節(jié)目大環(huán)境非常優(yōu)良。一系列文件的出臺給文化類節(jié)目的文藝創(chuàng)作帶來了政策紅利。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2017年中國各大電視臺和視頻網(wǎng)站推出的文化類綜藝節(jié)目數(shù)量超過50檔,其中,央視和優(yōu)酷的表現(xiàn)最為突出。但是,速食化、同質(zhì)化、生命周期短等問題也隨之而來。究其原因,還是在用“老模式”做“新節(jié)目”。
曾被綜藝大臺湖南衛(wèi)視寄予厚望卻最終黯淡離場的《藝術(shù)玩家》是其中的一個反例,與《國家寶藏》相似的題材,相似的參與者,卻最終收獲了迥異的結(jié)局。在Web2.0時代,它看似創(chuàng)新實則傳統(tǒng),看似活潑實則拘泥的形式和陽春白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內(nèi)核是失敗的根源。《藝術(shù)玩家》的確在形式創(chuàng)新上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邀請著名主持人汪涵和收藏家馬未都來主持節(jié)目,瞄準古玩藝術(shù)收藏市場,采訪國內(nèi)頂尖拍賣公司……可以說,它的硬件條件,一點兒也不比《國家寶藏》差。但是,從形式到內(nèi)容,無一不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態(tài)度,教育、傳授長篇巨幅的古玩鑒賞知識,對于“快生活”“具有娛樂精神”的年輕人來說,過于傳統(tǒng)。而2017年的許多新綜藝也是換湯不換藥,照搬傳統(tǒng)節(jié)目模式,切入角度高冷,無法引起讀者同鳴,選角也無法讓觀眾產(chǎn)生認同感,更不用說參與其中了。
3 參與式轉(zhuǎn)型
《國家寶藏》在其傳播的每個階段都進行了參與式轉(zhuǎn)型。從形式上來說,《國家寶藏》是一種全新的表達。誠如《國家寶藏》制片人、總導演于蕾所言,它的定位是“從3歲到80歲,有文化到?jīng)]文化,都能覺得好”。這就注定了其敘事手段的輕松和娛樂性,以及受眾的低門檻。所以,《國家寶藏》不僅展示國寶的背景故事,還將各種藝術(shù)形式融入到室內(nèi)綜藝節(jié)目、紀錄片和戲劇中。節(jié)目中的每件珍寶都將由名人和素人扮演的“護寶人”來展現(xiàn),講述他們與這些國寶的故事,詮釋其背后的歷史奧秘,這被稱之為國寶的“前世今生”。“明星演繹歷史故事”的形式雖在學術(shù)界頗有微詞,但明星的舞臺表現(xiàn)力加上具有傳奇色彩的國寶故事改編,確實使得《國家寶藏》走入了尋常百姓家。今生故事的展示方式也因素人專家的不具備演講技巧而被調(diào)整到偏重互動,通過張國立的引導和評論,觀眾更容易意識到:“也許他們不善言辭,但他們真的做了很了不得的事,真的為國寶付出了很多。”筆者認為,這樣的“演繹”+“互動”的策劃形式是非常有創(chuàng)意的。相比以往文博類綜藝陽春白雪的基調(diào),這樣的“演繹”確實為《國家寶藏》贏得了廣泛的受眾基礎(chǔ)。
從內(nèi)核上來說,筆者認為這檔綜藝的核心精神是平等與對話,即試圖從年輕人的視角和文化來解讀文物及歷史。每一件文物的選擇、每一個故事的講述、每一層意義的開掘,都不是死板的說教,而是情感共鳴的基礎(chǔ)上建立起觀眾與文物的連接,讓文物“活”起來。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寶藏》正在逐漸擺脫早期“高冷”“不合群”的標簽,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迎合年輕人喜好的“新玩法”,邀請明星、打通娛樂模式、開啟社區(qū)討論、啟用網(wǎng)絡(luò)段子……還有觀眾評論“官方吐槽,最為致命”,表達出年輕人對嚴肅主體新傳播內(nèi)核的難以置信。后現(xiàn)代社會具有流動性和碎片性特征,這樣的“新玩法”“趣味性”相比冗長的傳統(tǒng)傳播習慣,顯然更符合青年人對消費快感的追求,也更符合他們的文化傳播方式,因而在年輕人中能夠贏得廣泛的受眾參與。至此,在新媒介參與式文化流行的大背景下,《國家寶藏》事實上完成了從文化傳播到文化參與,最后到文化再創(chuàng)造的傳播閉環(huán)。
基于創(chuàng)新的形式和對話的態(tài)度,就不難理解其在口碑上的巨大成功,第一期播出后,《國家寶藏》上了熱搜,知乎形成話題,豆瓣評分9.3,B站播放量160多萬、彈幕16萬條。《國家寶藏》在騰訊視頻上線5天播放量就突破3000萬,真正做到了許多文化類節(jié)目無法做到的事情——占領(lǐng)了年輕觀眾的高地。
4 結(jié)語
在國內(nèi)電視綜藝節(jié)目,“買版權(quán)”“爭噱頭”,進退維谷的當下,《國家寶藏》等節(jié)目的接連大熱,仿佛證明了文博領(lǐng)域如今已成為自帶流量的資源富礦,給國內(nèi)電視節(jié)目策劃帶來了一絲光亮。但是,文化類節(jié)目如何更具親和力,沖破“次元壁”的受眾局限,進行轉(zhuǎn)型,重獲新生,讓大眾感受到歷史格局和文化素養(yǎng)兼具創(chuàng)新有趣,如何打造優(yōu)秀的形式和內(nèi)核,仍然是一條漫長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梁波.大屏時代好節(jié)目特質(zhì)的比較研究[J].視聽界,2018(1).
[2]陳茜.看《國家寶藏》的“內(nèi)容與商業(yè)”平衡術(shù)[J].商學院,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