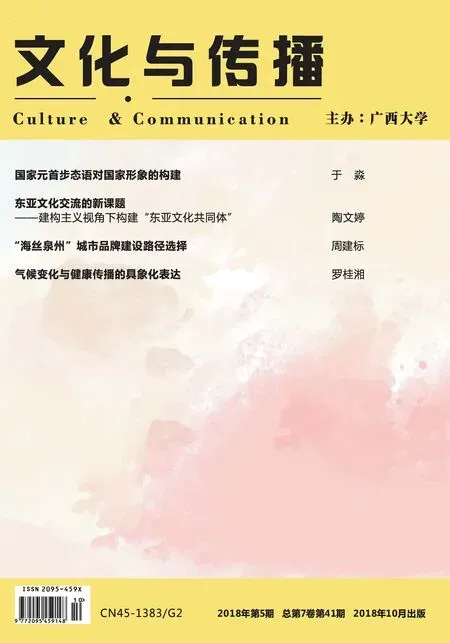翻譯傳播視域下基于模因理論的歸化翻譯研究
——以日本流行歌曲漢譯為例
鄧天奇 侯小天
引 言
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中外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在此背景下與中國文化審美較為相似的日本流行歌曲大量進入中國國內。日本流行歌曲在中國的傳播離不開翻譯,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幾乎所有的歌曲都是通過“翻唱”這一手法在中國流行開來。在此階段,歸化翻譯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通過歸化翻譯,源語文本中的異文化成分被一定程度剔除,使得目標文本變得通俗易懂,更多地賦予了中國色彩,為之后日本流行歌曲的大量傳唱奠定了重要基礎。這一現象充分反映了翻譯與文化之間存在非常緊密的互動關系。伴隨著當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的跨文化傳播機能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發現。[1]翻譯傳播學這一學說的構建也為我們研究翻譯與傳播提供了全新的范式。模因理論的導入更是為我們研究歸化、異化翻譯提供了更為開闊的視野。縱觀古今中外文化交流史,均可發現翻譯在跨文化傳播活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橋梁作用。
一、翻譯傳播學與模因理論
雖然從研究內容和形式上來看,傳播學與翻譯學各有側重,但是不可否認兩者在許多方面有著深層次的聯系。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翻譯學研究逐漸將目光投向文化領域。在這一大背景下,芬蘭學者切斯特曼最先將模因傳播理論引入翻譯學研究,主張翻譯活動是語言超越文化界限進行的模因傳播的過程,這一理論的提出使得翻譯的傳播過程更加明晰化。
(一)翻譯傳播學的構建
翻譯傳播學是翻譯學和傳播學交叉研究的結果。具體地說,是將翻譯及其傳播因素相聯系,將翻譯學和傳播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相關研究,并以其相互關系及其機理為研究對象進行探索,從系統論角度審視翻譯、研究翻譯,對翻譯中的種種現象進行傳播剖析和闡釋的學問。[2]翻譯是一種跨文化傳播活動,其過程也應遵循傳播的五要素,即傳播主體、傳播對象、傳播媒介、傳播內容、傳播效果,這些要素之間相互聯系和制約。[3]
將這一理論具體轉化到翻譯過程中來,那么譯者便是傳播者,是源文本信息的發送者,是傳播過程的第一環節,主要解決“翻譯什么”以及“如何翻譯”等問題。源文本便是翻譯所需要傳播的信息,即傳播內容。譯文則是語言符號的具體再現方式,應歸屬為傳播媒介的范疇。翻譯過程的完成、信息的傳遞均是通過譯文這一載體進行,是傳遞源文本的具體渠道。[4]讀者即為傳播對象,是譯文的接受者,是信息傳遞的服務對象,其范圍不僅僅局限于翻譯作品的受眾,還將覆蓋至全體社會成員。翻譯的本質便是一種跨文化信息傳播活動,因此翻譯只有生成、傳播并被讀者了解、實現共享,才有意義。
(二)模因傳播論下的歸化翻譯
模因是文化基因傳播的基本單位,可以被無限復制。在翻譯傳播視閾下,翻譯模因論主張將翻譯過程看作是異文化的模因通過語言向本國傳播的過程[5],并為翻譯的每一個過程進行了重新定義,對應給出了源語模因、變體模因、核心模因、共生模因、寄生模因、宿主等概念。
在該理論系統下,原作是源語模因,是一個搭載有原作者思想和文化背景的模因組合,作者的理念被視為核心模因,存在于原作中還有各種文化背景的其他模因。[6]目的語模因被稱為變體模因,變體模因的接受者即宿主,變體模因可以使源語模因更加廣泛地傳播,使翻譯有利于語言模因的傳播與發展。此外,在翻譯傳播的過程中,還存在共生模因和寄生模因這一對概念。有利于宿主生存的模因、可以在翻譯傳播過程中可以被不斷復制的源語模因是共生模因,不利于宿主生存、可能導致翻譯傳播鏈斷開的源語模因為寄生模因。同時,共生模因和寄生模因也可以視為強勢模因和弱勢模因。在這里需要注意模因的強勢和弱勢是相對的概念,根據外界環境的變化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在翻譯的傳播中,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源語模因和變體模因完全等價,但這一理想狀態很難達成。源語模因如果被拒之門外,便會失去傳播意義,因此必須拋棄一部分寄生模因完成傳播鏈。如果源語模因可以在目的語中找到相同或類似模因,并對其宿主產生相似感染,使得讀者產生類似的效果,便滿足了模因的基本生存需要。[7]這即是我們所說的歸化翻譯,歸化翻譯是翻譯模因傳播的必經階段,其強調在目的語中尋找與源語基本一致的模因,使原作模因對其讀者產生的效果被復制過來,從而達到基本忠實于源語的文本,傳播原作中的核心模因。當兩種異文化接觸時,由于文化多樣性,往往存在目的語與源語體系相差較大,目的語讀者不熟悉源語文化這一情況,所以采取歸化翻譯是較為理想的方式。雖然歸化翻譯會使部分模因丟失,但從傳播上來看意義重大,為以后模因的完整復制和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日本流行歌曲翻譯傳播中的歸化策略
流行歌曲的翻譯傳播過程是大眾文化的模因傳播過程。其最終的傳播效果與共生模因、宿主認知以及核心模因的受容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日本流行歌曲在中國傳播的初始階段曾經大量采用歸化法翻譯源語模因文本。本章將重點探討在翻唱傳播階段,譯者為了達到最大的傳播效果,所采取的具體歸化策略。
(一)選擇共生模因文本
在模因傳播過程中,每個階段都存在選擇。經過選擇,共生模因得以保存,而寄生模因則會被淘汰。[8]以此類推,在翻譯傳播中模因的選擇也是有目的的,選擇共生模因文本進行歸化翻譯,可以為變體模因傳播的擴大化奠定堅實基礎。在日本流行歌曲的翻唱階段,很多譯者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選擇了大量共生模因源語文本。下表為改革開放初期所選擇的日本流行歌曲。

表1 部分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日本流行音樂
日本流行音樂發展較早,兼具鮮明的民族性和現代性特征,其不斷根據環境的變化對其表征進行演化,實現了模因的變異與傳播。戰后日本的流行音樂史是一部日本人鄉愁的現代史,人們由于經濟的高速發展產生各種迷茫與不安,《北國之春》、《紅蜻蜓》等歌曲便在此背景下誕生。其節奏明快、曲調優美,可以說治愈系是當時日本流行音樂的核心模因。
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在探討日本流行音樂在中國的傳播時,必須充分考慮這一因素。1966年-1976年中國經歷了十年文革動亂期,當時音樂的主旋律為“高快硬響”,缺乏抒情性。經過十年動亂,中國人的心靈遭受到了非常大的創傷,急需卸下心靈的枷鎖。[9]在此背景下,文學藝術界出現了若干呼應的聲音,“傷痕文學”、“傷痕電影”紛紛出現,許多日本流行歌曲借此東風,作為源語模因被歸化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傳播開來。
一般來說,兩種文化接觸之時,如果雙方沒有共生模因,那么譯者作為特殊的宿主便無法對讀者進行感染。恰好當時《北國之春》等歌曲的核心模因與中國人當時的精神世界不謀而合,存在高度相似的共生模因。再加之,中日文化隔閡本身沒有那么大。所以當時的音樂傳播者選擇日本流行音樂而沒有選擇同時代歐美流行重金屬音樂。正是因為選擇了這一具有共生模因、適合歸化翻譯的文本,之后的翻譯過程及歌曲傳播過程才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二)避免宿主出局——闡釋性翻譯
歌曲屬于大眾文化的范疇,大眾文化是一種通俗易懂、為多數人所接受的文化。在具體翻譯傳播過程中,異文化關系紛繁復雜、難以等值,同時又需要顧及變體模因宿主的需要,達到文化傳播的目的,因此如何使外來源語模因大眾化便成為了急需解決的課題。當變體模因“宿主”無法理解變體模因中的一個新詞時,實際上信息的傳播鏈就斷開了,這時闡釋性翻譯便變得非常有必要。闡釋性翻譯的目的之一在于產生門檻較低的淺閱讀,使宿主對變體模因產生親切感進而成功感染。其對記憶水平要求不高,同時也不存在任何的認知障礙。通過闡釋性翻譯可以讓更多變體模因宿主不在這種簡單的傳播中出局。下面本文將以日本歌曲《紅蜻蜓》為例,簡單分析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歌曲漢譯過程中,所采取的闡釋性翻譯方法。

表2 《紅蜻蜓》及其漢譯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原文與譯文并不是完全一一對應的。譯文中增添了許多原文中沒有的因素。比如「夕焼小焼の、赤とんぼ」 這句譯文中增添了“請你告訴我”,「負われて見たのは、いつの日か」 這句被改譯為“童年時代遇到你”。「山の畑の、桑(くわ)の実を」這句在翻譯時增加了“拿起小籃”。「とまっているよ、竿(さお)の先」這句則增添了“是那紅蜻蜓”。如果不增加這些內容,采取完全忠實的方式進行翻譯,其變體模因的邏輯行文便很有可能產生混亂,使變體模因“宿主”產生不知所云之感。除去歌詞的音樂性這一因素外,我們可以推斷,譯者增添這些內容很有可能是出于通俗易懂,讓變體模因宿主明白日語原文的具體內涵。
翻譯作為跨文化傳播的橋梁,其功能不僅僅局限于源文本與目標文本之間的單純轉換,謀求源語模因的傳播擴大化、爭取變體模因的宿主量才是重中之重。只有盡可能地按照變體模因宿主的認知進行闡釋性翻譯,才能避免變體模因宿主因不熟悉“源語模因”的部分內容而拒絕感染、中斷翻譯傳播過程這一情況。只有使源語文本所反映的世界通俗地被變體模因宿主所理解接受,才能期待源語模因對宿主產生效果。
(三)傳播核心模因——采取本土語言審美
歌曲是審美文化的體現,在歌曲翻譯傳播的過程中必須考慮變體模因宿主的美學接受度,因此在這一翻譯過程中,必須把握源語核心模因,采取符合中國文化審美的表達對文本進行渲染處理。在上一小節中本文提到闡釋性翻譯可以讓宿主明白源語模因想表達什么,避免了部分變體模因宿主的出局,而這里所提到的本土語言審美則是更高層次的要求,主要解決傳達核心模因,深層次感染變體模因宿主的問題。本部分將以《北國之春》的第一小節為例,分析這一時代歌曲翻譯傳播在本土語言審美上所采取的若干策略。

表3 《北國之春》原文及其翻譯
對照原文,我們可以發現除去考慮歌詞的樂理性,譯文注意到中日兩國語言審美方式的不同,采取了大量的歸化策略。在原文中,源語模因即日本文化,其在審美意識上總體追求一種“物哀”之美。所謂的“物哀”,是一種在接觸到實物時,感覺到的人生微妙之處和令人銘記在心之情趣。在此種美意識的影響下,日本音樂韻律單一,詞風樸素。在本小節歌曲中的「しらかば」、「あおぞら」「みなみかぜ」這些源語模因意為“白樺”、“青空”、“南風”,均屬于單一的實物。只要在歌曲中稍微提到源語模因中的「しらかば」、「あおぞら」這些詞語,日本人腦中就會自然而然浮現出一副恬淡、靜謐的畫面。這一強調實物,追求靜態的表達方式具有典型的日本式語言審美特征。而中國人的美意識不拘泥于具體實物,更喜歡一種動態之美,因此漢語擅長表達意境,經常通過一系列華美的修飾語來烘托出宏大之畫面。
通過對比,可以看到日本的語言審美方式與中國的語言審美方式屬于異質模因。如果完全將該首歌曲源語模因復制,可能導致中國變體模因宿主無法被核心模因所感染。在本節歌曲中,這一恬淡靜謐的畫面即“核心模因”,通過在翻譯中使用亭亭、悠悠、微微等一系列符合中國本土化審美的語言,原文中表達的那種日本人所目睹的畫面即原文的“核心模因”才可以感染中國人的思維,產生基本等值的美感。這一做法雖然犧牲了源語的原有形態,但卻保留了變體模因宿主所熟悉的核心模因,更加有利于歌曲的傳播和接受,實際上源語模因的傳播完成到這一步已經為模因的完整復制打下了相當堅實的基礎。
三、日本流行歌曲傳播初期采取歸化法的原因
外來文化的傳播與接受是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需要一定的策略。歸化翻譯在翻譯傳播初期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其不僅通過保留核心模因達到了傳播弱勢模因源語文化的目的,還為之后源語模因的完整復制和傳播奠定了基礎。
(一)傳播弱勢模因的必然要求
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歌曲在中國傳播的第一階段里,一些詞語、句子只能采取歸化翻譯法才能被中國的聽眾理解和接受,這是由于模因傳播的階段性強弱特征導致的。日本流行歌曲這一龐大模因綜合體,兼具強勢模因和弱勢模因雙重性質。根據階段、背景環境的不同,其強勢模因和弱勢模因的性質可能會相互轉化。根據此定義,日本流行歌曲在中國傳播的初始階段應當歸為弱勢模因。
從模因傳播規律來看,弱勢模因理所當然地會選擇歸化翻譯。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重新引入外來文化的初期,此時日語教育程度根本無法與當今相提并論,人們對日本的了解也僅僅停留在戰爭年代。因此,鑒于當時的一些情況,只有通過歸化翻譯才能使得到的變體模因成為強勢模因。此時的這些變體模因均屬于弱勢模因,如果這些模因不能被廣泛地傳播和復制,那么最終將走向消亡,只有歸化翻譯才能滿足當時弱勢模因的基本生存需要。此時必須考慮在目的語中找出與源語相似,且能對其宿主產生相似感染的表達方式。否則將導致變體模因成為弱勢模因,無法進行復制和傳播,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日本流行歌曲在中國傳播的初始階段,譯者使用歸化翻譯方法迎合大眾,成功地將源語模因引進來,并廣泛地被變體模因宿主所接受、復制和傳播,從而成為強勢模因。通過翻譯演唱變體模因使源歌詞這一源語模因更加廣泛地傳播與發展。
(二)為完整導入源語模因奠定基礎
日本流行歌曲在中國傳播的初期,采取歸化翻譯可以滿足核心模因的基本生存需要,使得日本流行歌曲得以進入中國。通過這一階段,日本流行歌曲源語模因中的核心模因在中國大地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復制,吸引了大量中國宿主的主動感染,可以說部分中國宿主對于日本文化模因組合的受容度呈現出日漸增高的趨勢。以日本流行歌曲核心模因在中國的傳播為先導,一些在以前的傳播環境中處于寄生模因地位的日本文化弱勢模因也開始變換性質,紛紛進入中國國門成為強勢模因。一些此前不為中國宿主所了解的日式表達,日式審美文化等寄生模因也越來越被中國宿主大眾所接受,中國的傳播環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受容度。
歸化翻譯在日本流行歌曲傳播至中國的初始階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經過歸化翻譯改造后的變體模因與源語模因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不同。隨著全球化浪潮的突飛猛進,中日兩國世界觀的共生模因越來越多。日新月異的大眾傳媒和信息通訊為兩國文化模因的通暢化傳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以在以前歸化翻譯的基礎上,根據對寄生模因接受能力的不同,適當引入異化翻譯已經是大勢所趨。[10]這同時也符合翻譯模因傳播的規律,模因的本質在于盡可能多、盡可能完整地復制自己,而最優秀的翻譯便是促使變體模因對宿主產生與源語模因類似甚至完全相同的感染效果。
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一些源語模因難以完全被目的語讀者所接受,但作為譯者,我們在當前世界文化交流日趨頻繁這一大背景下,已經不能隨意尋找類似模因來代替源語模因了,應盡可能復制源語模因,將其發展為強勢模因。采用異化方法得到的強勢模因可以廣泛地傳播源語模因。
結 語
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傳播活動,是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信息共享和雙向交流的過程。從模因這個角度來探討翻譯傳播過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尺度來評判歸化和異化翻譯。
歸化翻譯在日本歌曲這一模因綜合體傳播至我國的初始階段得到了廣泛應用,同時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可以說歸化翻譯是翻譯模因傳播的必經階段,這一時期通過采取選擇共生模因文本、闡釋性翻譯方法和使用本土語言審美等手段,日本歌曲中的核心模因被轉換為中國人所廣為接受的內容。
但是,歸化翻譯在翻譯傳播中逐漸暴露出來的缺點也不可忽視,中國聽眾讀者越來越了解日本文化,已經越來越不滿足于用本國文化去了解源語文化中的核心模因。因此,可以說異化翻譯是翻譯模因傳播的趨勢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