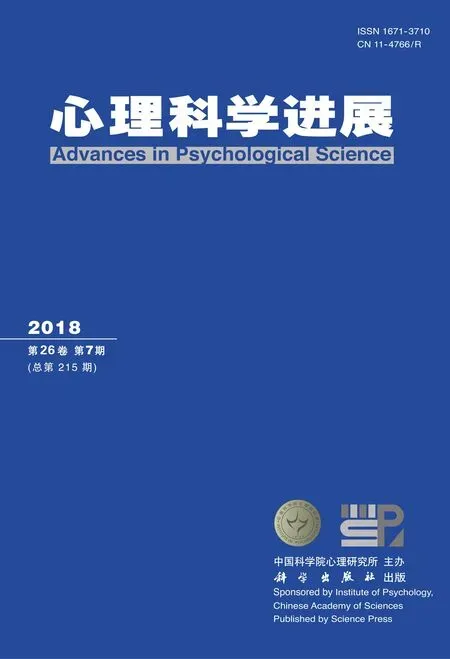基于自我錯覺的最小自我研究:具身建構論的立場*
張 靜 陳 巍
(1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心理健康研究所, 杭州 310018)(2紹興文理學院心理學系, 紹興 312000) (3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 香港)
1 引言
正如社會認知心理學家 Klein (2012)抱怨的那樣:“在心理學中恐怕沒有哪一個術語比‘自我’應用的更為廣泛卻又如此莫衷一是。”因為在日常體驗中, 我們是自身體驗的擁有者和行動的發起者的感受是如此強烈, 因而從 Decartes開始至今的自我實體論(substance theory)的擁護者, 對于一種單一、獨立和實在的實體自我的論證與尋找幾乎從未停止過。然而另一方面, 神經科學從未在人腦中找到與自我相對應的腦結構, 這導致有些研究者開始質疑自我的實在性, 有的甚至認為所謂的實體自我無非是腦創造的一種錯覺。自我的建構論者指出, 當個體仔細觀察自己的體驗世界中那些我們稱之為自我的概念及其相關應用時,他并不能發現任何固有的事物或獨立的實體, 能夠發現的是相互聯系的過程的集合。這些過程有些是身體的或生理的, 有些是精神的或心理的,正是這個過程生成了一個“我”, 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和過程本身是等同的(Thompson, 2014)。自我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建構起來的。這樣一種能基于不斷變化的身體狀態在概念上指定自己為一個自我的系統被稱為自我標明系統(selfdesignating system), 而主張自我生成于這一系統中的觀點則被稱為自我的具身建構論(embodied constructivism)立場。自我的建構論立場認為, 自我涌現自一系列遺傳的、心理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條件中, 但自我既不能被還原為一串 DNA代碼、一種心理側寫或是一個社會和文化背景, 也不能脫離這些因素而得以理解。自我的與眾不同不是因為“你”擁有某種有別于他人的形而上的品質, 而是在于“你”是從一系列獨特的和不可重復的條件和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因此自我既不是一個事物或實體, 也不是一種錯覺, 相反, 它是一個過程, 一個“我正在持續進行” (I-ing)的過程(張靜, 2017)。
為了應對為自我建立恰當的模型的挑戰, 諸多哲學家、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尋找一個核心的或“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f)的方式:“即便在所有自我的不必要的特征都被剝離之后, 我們仍然擁有一種直覺,即存在一個基本的、直接的或原始的‘某物’我們愿意將其稱為‘自我’。” (Gallagher, 2000)然而在尋找這一最小自我的過程中, 始終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避免陷入太過抽象的境地。“接地原則” (closer to the ground)被認為是一種比較好的辦法, 即要理解最原初的能夠使得自我感得以產生的主體, 我們要重視身體本身(Gallese &Sinigaglia, 2010)。因此, 理解自我是如何建構的,首先必須要理解這種最小自我是如何建構的, 而要理解這種最小自我的建構就必然要重視基于身體的自我現象。
2 具身建構的視角
認知依賴于經驗的種類, 這些經驗來自具有各種感知運動能力的身體; 而這些個體的感知運動能力自身又內含在一個更廣泛的生物、心理和文化的情境中。使用“具身”一詞時意在突出的兩點:一是關于心智嵌入身體, 二是關于身體嵌入情境與社會。如果要考察二, 必須先考察一(瓦雷拉, 湯普森, 羅施, 2010)。Damasio也指出, 身體是有意識心智的基礎, 沒有身體就沒有心智、沒有意識、沒有自我。“我”是具身化的存在, 一個由軀體和腦構成的存在。要全面地理解人類心智和自我的問題就需要一個生命的視角, 一個身體的視角(李恒威, 董達, 2015)。
但是, 自我并不等同于身體, 對自我的理解顯然也不能通過簡單地將其還原為身體實在來進行。自我產生于一個不斷進行著的過程中, 因此理解自我還需要一種建構論的視角。自我是一種過程的建構這一主張可以從包含生物學、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等眾多方面加以辯護。在所有這些方面中, 身體自我是基礎的也是最小的自我形態。
具身建構論認為, 最小的自我概念就是區別自我和非我。因為身體的自我覺知首先需要一種對自我和非我界線的標定, 正是這種區分構成了基本的自我感和非我感的區分。通過對擁有感(sense of ownership) (“我”是那個正在做出某個動作或者經歷某種體驗的人的感覺)和自主感(sense of agency) (“我”是導致某個動作產生的原因的感覺)本身, 及其不同類別和相關受損的研究來探討最小的自我、自我和他者的區別將是當前研究中卓有成效的路徑。擁有感和自主感被認為是兩類能夠幫助個體進行有效識別身體自我的重要體驗(Christoff, Cosmelli, Legrand, & Thompson, 2011)。身體擁有感賦予本體感官信號一種特殊的現象品質, 它使得自我意識變得根本上與眾不同:我的身體和“我”之間的關系與我的身體和其他人的身體之間的關系是不同的, 與我和外部對象之間的關系也是不一樣的。盡管構成個體身體的各成分會處于一個永不停息的建造和拆除的過程中, 然而我們卻有一種自我感, 有著構成同一性的結構和功能的某種持續性, 有某種被稱為人格的穩固的行為特質。身體擁有感的這種不變性正是個體將其視為最小自我的核心成分并加以研究的主要原因。
除了擁有感, 常識經驗也表明個體還會根據我是否能讓身體的某個特定部位受我的控制來判定身體的歸屬, 即自主感。較之擁有感, 自主感因其包含了更多的心理成分而更難界定。這里只關注自主感如何作為一種有助于人類進行自我識別的基本體驗。大量的研究表明, 自主感的判斷, 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預測結果和實際感官結果之間的一致和不一致程度。比較器模型(comparator model)認為在動作產生的同時會產生相應的輸出信號(efferent signals), 而當動作被執行之后又會有再輸入信號(re-afferent signals), 兩者之間的匹配會讓個體產生相應的自主感, 而不匹配則會造成自主感的降低甚至缺失(Franklin & Wolpert, 2011)。這些輸出副本機制可能就是心理上自主體驗的基礎。
本文試圖以擁有感與自主感為考察對象, 通過病理學層面上最小自我的解構以及實驗誘發正常個體最小自我的建構等兩方面的研究證據, 來論證具身建構論的合理性。
3 最小自我的病理學研究
3.1 擁有感的受損
軀體失認癥和軀體妄想癥是最為常見的也是被引用最多的擁有感受損的病例。兩者的共同點是病人會產生一種對自己的單側四肢的非歸屬的感受和信念, 即喪失對自己一側身體的覺知。有別于軀體失認癥, 軀體妄想癥還有一個典型的特征是此類病人在否認自己的身體部分屬于自己的同時往往會聲稱特定的身體部分是屬于別人的,即認為自己的手臂是屬于另一個人的, 如家庭成員或自己的醫生(Bottini, Bisiach, Sterzi, & Vallarc,2002)。這兩種病形象地展示了作為最小自我的核心成分之一的擁有感受損的情況, 同時它們的存在也提醒著個體曾經認為在關于“我的腿是我的或者我腿上的感受是我的感受”這些確認無疑的事情上我們也會犯錯。Wittgenstein (1958)曾指出,當我們以自我作為主體的方式使用第一人稱代詞時, 我們不可能錯誤地將“我”指稱于錯誤的對象。確實, 通常對于腿是自己的問題, 我們不會出錯。然而軀體妄想癥提醒我們, 要知道我們看到的腿實際上是自己的或者腿上的感受是自己的感受,腦必須以一種恰好正確的方式運作。
腦除了模擬它所棲息的身體的活動外, 它的某些部分也會記錄其它部分的腦在干什么。也就是說, 某些神經回路會模擬和監控腦的其它部分的活動。而這個監控過程的中斷則會導致自主感的缺失。近期研究顯示, 右半腦頂葉區域的損傷或突發性的梗塞都會造成了這個過程的中斷, 導致患者感覺并相信該肢體是異己的(不再屬于自己而屬于別人)或受別人控制(Demiryürek, Gündogdu,Acar, & Alagoz, 2016)。
3.2 自主感的缺失
最典型的自主感缺失當屬異己手綜合征(alien hand syndrome), 這種疾病通常被界定為一側上肢無意愿的(unwilled)、不可控的(uncontrollable)但看似有目的的(purposeful)動作(陳巍, 單春雷,袁逖飛, 2016)。異手癥所涉及的臨床表現有多種形式, 概而言之, 患者的手會表現出無法控制的行為(盡管這些動作以一種目的指向的和“有意為之”的方式而被執行), 并且患者會對這些行為產生極端的陌生感(Hertza, Davis, Barisa, & Lemann,2012)。例如, 這只任性的手會抓住門把手不放,或者拿起一支鉛筆亂涂亂畫。異己手的移動看似有意圖, 但是移動看上去的意圖和病人自己的意圖是矛盾的, 即至少自主感的最低水平(即自主性感受)是沒有發生的。因此, 異己手綜合征患者會認為上肢的活動是由它自己所導致的, 即它是一個有著自己意圖的獨立的自主體(如“我沒有那么做……”), 或者它是某個有著自己意圖的獨立自主體的一部分。然而, 即便患者喪失了目的性動作有關的自主感, 但仍表現出疏遠的擁有感(如“雖然我知道這是自己的手”) (陳巍, 2016)。
擁有感和自主感失調的病理學案例一方面說明兩類體驗在生理和現象上的可分離性, 使得研究者能夠對這兩類基本體驗分別進行研究, 另一方面也推動著研究者去思考個體視之為理所當然的自我感到底是如何被呈現出來的。作為最小自我的自我感的涌現需要有具身化的載體, 并與大腦、環境之間進行互動建構, 沒有某一樣或某一些事物可以直接等同于自我, 自我出現在各個過程的相互作用之中, 任何一個環節的紊亂都會導致自我感的異常或缺失。不過, 雖然病理學案例通過解構的方式能夠讓研究者更好地理解自我的具身建構。但是這樣的研究一來數量有限, 二來也不能直接推論至正常個體身上。就此而言, 新的研究方式的引入不可或缺(Ionta et al., 2011)。
4 最小自我的錯覺研究
4.1 橡膠手錯覺
在自我問題的探索中最為杰出的錯覺研究無疑是橡膠手錯覺(rubber hand illusion, RHI)。它是一種將人造的橡膠手感受為自己真實身體一部分的知覺體驗。因為能有效地在正常被試身上引發并檢驗擁有感體驗, RHI被認為是自我相關問題研究中一種具有重大突破的實驗方法(Suzuki,Garfinkel, Critchley, & Seth, 2013)。
在最初的實驗中, 主試在被試面前放置一只人造的橡膠手, 并將一塊擋板置于被試的真手和橡膠手之間。同時刷橡膠手和相對應的真手就能夠使被試產生橡膠手仿佛成為了自己身體一部分的感受(Botvinick & Cohen, 1998)。隨后的大量研究揭示影響錯覺產生的首要原因是視觸兩類感官輸入的同步性, 600 ms以上的時間間隔幾乎無法讓被試產生錯覺。空間一致性和特征一致性也被認為會對錯覺產生和錯覺強度造成影響。當真手與橡膠手之間的距離超過 27.5 cm時, 錯覺強度會顯著下降, 并且, 如果用與人手毫無相似之處的木塊來代替橡膠手, 錯覺也會消失(Guterstam,Petkova, & Ehrsson, 2011)。具體而言, 時間一致性所代表的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加工機制對身體擁有感的影響。即輸入反饋總是讓橡膠手和被試的真手保持同步會讓人更容易產生錯覺, 反之更不容易。而空間一致性和特征一致性則表明了自上而下(top-down)的加工機制的影響。即對于“我的手應該是怎么樣的” (如形態與尺寸)或“我的手通常在什么位置” (如不能位于解剖學上不可能的位置)被試有著較為穩定的內部表征。當外界輸入與之相匹配時, 更容易對橡膠手產生擁有感錯覺體驗, 反之更不容易(張靜, 李恒威, 2016)。
近年來, 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其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 與傳統 RHI相似度極高目前又廣受歡迎并且幾乎可以被視為傳統RHI等價范式的虛擬手錯覺(virtual hand illusion, VHI) (Ma& Hommel, 2015; Zhang & Hommel, 2016)研究也應運而生。除此以外, 還存在虛擬臉錯覺(Tajadura-Jiménez, Grehl, & Tsakiris, 2012)、全身錯覺(Petkova, Khoshnevis, Ehrsson, 2011)以及虛擬聲音錯覺(Zheng, MacDonald, Munhall, & Johnsrude,2011)。所有這些范式的原理都是以同步的視觸刺激為基礎同時根據各自研究的需要疊加其它因素而使得正常的健康被試對實際上不屬于自己身體一部分的外部對象產生擁有感或自主感。
最初的RHI實驗對于擁有感和自主感的衡量主要是基于問卷, 隨后本體感覺偏移以及皮膚電傳導反應也作為輔助測量手段出現在研究中以消解大家對于問卷缺乏客觀性的質疑(Riemer, Kleinb?hl,H?lzl, & Trojan, 2013; Zhang, Ma, & Hommel,2015)。隨著神經成像技術的發展, 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對擁有感的相關腦機制進行探索。
4.2 橡膠手錯覺中的擁有感
Tsakiris等在RHI實驗中同步的視覺?觸覺刺激之后的350 ms的時間點上通過TMS作用于右側顳頂聯合區(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結果發現同步的視觸刺激不再會引發擁有感錯覺(Tsakiris, Carpenter, James, & Fotopoulou, 2010)。這一結果說明右側顳頂聯合皮層在擁有感形成過程中的不可或缺。此外, 基于fMRI對橡膠手錯覺過程中的相關腦區進行的研究發現在產生錯覺時,大腦兩側的腹側前運動皮層、頂內溝、后頂葉、頂下小葉等區域均會產生激活(Brozzoli, Gentile,Petkova, & Ehrsson, 2011; Ehrsson, Wiech, Weiskopf,Dolan, & Passingham, 2007; Gentile, Guterstam,Brozzoli, & Ehrsson, 2013; Makin, Holmes, &Ehrsson, 2008; Limanowski & Blankenburg, 2015)。后頂葉的主要作用是整合與橡膠手有關的多感官信息。這一整合在橡膠手錯覺體驗發生之前開始,說明后頂葉所涉及的過程可能是消解視覺刺激和觸覺刺激之間的沖突, 其結果就是對視覺和觸覺坐標系的再校準。由于頂下小葉主要是處理與身體輪廓的知覺判斷有關的信息, 因此頂下小葉在橡膠手錯覺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對身體部分的空間關系的表征。此外, Tsakiris及其同事通過PET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后腦島的激活和不同條件之間的本體感覺偏移之間存在著正相關(Tsakiris,Hesse, Boy, Haggard, & Fink, 2007), 說明了腦島在擁有感的主觀體驗中可能起著重要的作用。腦島能接受軀體生理狀態的信息, 然后產生主觀體驗。因此, 腦島和錯覺過程中明顯的本體感覺偏移有關不僅為本體感覺偏移作為擁有感錯覺的指標提供了佐證, 同時也說明了擁有感的產生可能會進一步影響更高級的情感和認知加工。
基于橡膠手錯覺的這些神經成像研究的結果說明, 上述擁有感所涉及的這些腦區共同形成了一個聯合網絡, 將當前刺激與個體自己獨特的身體特征相聯系, 而穩定統一的自我感則是在這一作用過程中被建構起來的(Tsakiris, 2010)。最新的一些行為與神經電生理實驗也證實了上述猜想。例如, 張靜和陳巍(2016)通過將虛擬手呈現于不同的空間參照系來考察被試在不同情境下擁有感體驗的程度。實驗結果表明, 一方面, 無論是同步性還是距離都會對虛擬手錯覺中的擁有感產生影響; 另一方面, 不同的距離參照系對同一位置的擁有感體驗影響差異顯著。即知覺到的擁有感會受環境信息的影響, 錯覺程度的大小與相對位置而非絕對位置關系更為密切。這一發現與單模態的匹配理論認為擁有感錯覺依賴于預先存在的穩定的身體意象的假設相悖, 相反這一結果表明身體表征很有可能是基于一種較為寬泛的整合標準,因而具有相當大程度的可塑性, 說明自主體對自身身體的表征更有可能是一種概率性的聯合具身建構過程。
來自腦卒中患者身體擁有感的神經電生理學證據顯示, 相比于正常被試, 腦卒中患者接受刺激的手的皮膚電反應(GSR)、皮膚溫度與肌肉活動都顯著的降低了, 而他們卻報告體驗到了更強烈的身體擁有感。因此, 腦卒中患者與正常被試的在擁有感上的具身化差異可能是通過增強身體圖式(body schema)1身體圖式(body schema)是一種知覺-運動系統能力, 能夠持續控制姿態和動作。它是一種自動的程序系統, 無需知覺監控就可以運作。例如, 當我們穿過安檢門、在電梯上保持平衡、坐在椅子上轉圈或伸手取咖啡杯時, 身體圖式確保我們的身體具有無意識、自動化地完成上述活動的能力。的可塑性, 以及位于本體感覺之上的視覺輸入這樣一種病理性優勢所驅動的。通過抑制交感神經系統的反射活動以及前運動皮質參與身體圖式的重構, 可以促進神經生理反應的差異。這些結果可以證明, 腦損傷促進了的身體模式可塑性, 而前運動皮層在這種機制中扮演主要作用(Llorens et al., 2017)。
4.3 橡膠手錯覺中的自主感
大量的研究表明, 自主感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預測結果和實際感官結果之間的一致程度(Vosgerau & Newen, 2007; Sidarus, Vuorre, &Haggard, 2017)。預測和實際結果之間的一致性將會導致自主感的產生, 而不一致則說明動作可能是由另一個自主體所導致的。因此, 很多研究都通過操縱動作的反饋(視覺反饋或聽覺反饋)來控制自主感(Haggard & Chambon, 2012; Moore &Obhi, 2012)。空間偏差也被發現會對自主感產生影響。例如, 當光標和控制桿的移動在空間上被扭曲之后, 自主感程度的降低便會被觀察到(Farrer, Bouchereau, Jeannerod, & Franck, 2008)。對自主感空間、時間規則的研究發現自主感存在的閾值在時間上是延時在0~150 ms之內, 而在空間上則是偏移在 15~20°之內(Jeannerod, 2003)。超出這些范圍之后被試便會開始將反饋判斷為和他們的預期是不一樣的, 即不會再認為是自己的動作引起反饋。
基于腦成像技術所發現的明確和自主感有關的腦區主要包括后頂葉、小腦、輔助運動皮層、顳頂聯結與角回(David, Newen, & Vogeley, 2008;Kühn, Brass, & Haggard, 2013; Haggard, 2017)。后頂葉是重要的聯合皮層區域, 不僅在感覺與運動整合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同時也參與多種認知功能。后頂葉在橡膠手錯覺實驗產生自主感的過程中出現激活也說明對于自主感而言, 感官和運動信號之間的一致性的評估對自主感的產生至關重要。小腦在感官反饋的加工中也有作用, 它也被認為是運動控制的內部模型的基礎(Manto et al.,2012)。對小腦受損的病人的研究發現, 當要求執行的任務與內部預測控制有關時, 他們便無法很好地完成(Synofzik, Lindner, & Thier, 2008)。說明小腦不僅使得個體能夠不斷更新內部表征從更好地適應外界的變化, 而且還能夠幫助其對自我和他者所引發的刺激進行區別從而給出更恰當的反應。輔助運動皮層在對自我所產生的移動的覺知和執行中會產生激活。例如, 主導一個移動和僅僅是跟隨或者觀察一個移動相比較, 只有前者才會涉及輔助運動皮層的參與。并且, 它不僅在移動的執行過程中非常關鍵, 而且在準備階段和發起階段也很重要(Haggard, 2008)。顳頂聯結會對意外的外在感覺事件產生反應, 即在缺少自主感的狀態下, 它的激活或許反映的并非是自主性的歸因過程, 而是對這一加工的可能結果的反映(例如,判斷這一認知事件是否外在誘發的) (Haggard,2017)。
除此以外, 可能與自主感相關, 但作用并不是那么明確的區域還有顳上溝后部和腦島以及基底神經節(David, 2012)。它們分別在社會知覺和情感認知中發揮重要作用, 和主觀體驗有著密切的聯系, 并與頂葉皮層和小腦相連, 在運動控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而, 與擁有感的研究結論一致, 自主感的產生也不能被歸因為某個單一腦功能區的作用, 也不能全盤否定自我的實體性基礎而認為它就是一種“有用的錯覺”, 相反, 自我應該是在這些腦區的相互作用過程中被具身建構而涌現出來的。
這樣一種具身建構的思想同樣也有來自行為實驗的支持。張靜等通過擁有感和自主感對焦慮的影響來探討上述問題:擁有感和自主感的可塑性; 不同擁有感和自主感狀態對焦慮水平的影響;任務類型在擁有感和自主感影響焦慮水平過程中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 一方面, 擁有感與自主感是彼此相對獨立的, 在一定條件下兩者是可以進行雙向分離的; 另一方面, 擁有感與自主感之間也是存在交互作用的, 自主感能夠促進擁有感,但反之擁有感并不能促進自主感。此外, 根據上述實驗結果, 研究者還可以超越擁有感和自主感作為最小自我核心成分的作用, 進一步對最小的自我和敘事的自我之間的關系進行一些探討:不同的擁有感和自主感體驗以及不同的任務類型都會對最終所測量的焦慮水平產生不一樣的影響,這說明最小自我和敘事自我之間應該同時存在自下而上的影響和自上而下的影響。并且最小自我和敘事自我之間很有可能是通過情感這一關鍵構成要素而產生更進一步聯系的(Zhang & Hommel,2016)。
不同的條件能夠引發被試不同的身體擁有感和自主感體驗(Kalckert & Ehrsson, 2014)。這意味著自我和非我之間的界限可能并不是那么一成不變, 至少在某些條件下可以改變。RHI及其變式中所揭示出來的自我表征和自我識別的可塑性直接動搖了自我是一個單一的固定不變的實體的觀念, 相反它們暗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自我是在我們與外界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以腦的某些結構的活動為基礎基于一定的原則和規范建構起來的。當然僅憑目前橡膠手錯覺所開展的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還為時過早, 但是通過描述擁有感和自主感是如何可塑的方式, 橡膠手錯覺及其變式的研究展現了穩定而統一的自我感是如何在主客體互動的過程中動態地形成的。
5 結語
自我涉及橫向的復雜的心理內容和縱向的多層的演化?發展階段, 而通常研究一個復雜事物的最好方式就是從考察它的最簡形式開始。因此,理解自我的出發點是最小自我。通過對擁有感和自主感所構成的最小限度的有意識自我在病理學中的解構和錯覺研究中的建構, 可以論證一種自我的具身建構論。未來的研究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入手推進相關的探討, 并檢驗其合理性。
首先, 就成分建構而言, 最小自我是由擁有感和自主感兩個部分構成。一方面, 這兩部分相互獨立, 表現為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彼此分開。例如, 在個體沒有主動發出行為的意愿時如果其身體發生了移動, 他會根據擁有感和自主感之間的這種不一致快速地尋找原因并做出恰當的反應。如果僅僅是朋友開玩笑推一下, 他可能會一笑置之, 但如果是有人騎自行車不小心撞到的, 他可能會快速地躲開以避免更壞的結果發生。另一方面, 這兩部分又彼此密切聯系相互影響。正是由于擁有感和自主感之間的交互作用才保證了我們能夠以恰當的方式對某些刺激進行反應。為什么個體不能給自己撓癢癢的問題或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我們自己撓自己的時候, 擁有感和自主感是一致的, 而當別人撓我們的時候, 擁有感依舊但自主感是不存在的。當兩者之間不匹配時有所反應是滿足個體的適應性需求的, 而當兩者之間匹配時做出反應則是會令人詫異的。因此, 未來對自我建構的探索可以通過對最小自我的兩種成分是如何建構的進行研究。
其次, 就結構建構而言, 在擁有感紊亂和自主感缺失的病理性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擁有感或者自主感的失調會呈現不同的程度。即, 即便是擁有感發生了紊亂, 也不是全或無的形式。可見擁有感和自主感內部確實存在著不同的層級。有學者指出擁有感和自主感應該各自包含前反思的層面、判斷的層面和元認知的層面(Synofzik,Vosgerau, & Newen, 2008)。那么, 每種基本感受的內部層級之間如何相互影響最終導致自我感呈現呢?近期, 預測編碼模型(predictive coding model)對感官加工層級結構的解釋或許可以使用對擁有感和自主感的考察。根據所加工信息的類型, 可以將擁有感和自主感每個層級上處理的內容分為自上而下的信息和自下而上的信息, 前者反映的是關于事件的感官結果的預測, 而后者反映的則是感官事件的影響。在這一層級的最上面是加工感官輸入抽象表征的多感官的區域, 并且會有兩類不同的神經元分別處理這兩類不同的信息, 表征單元(representational units)負責加工關于即將到來的感官輸入的概率表征, 而錯誤單元(error units)則是在預期的感官事件和實際的感官事件不符時對預測錯誤進行編碼(Clark, 2013;Friston, 2005)。然而, 概率表征如何影響自上而下的預期, 從而消解自下而上的預測錯誤, 最終使得自我以穩定統一的方式得以呈現呢?其中, 在這種具身建構中, 身體意象與身體圖式是穩定的還是可塑的?仍然存在爭議有待澄清(Armel &Ramachandran, 2003; 張靜, 陳巍, 2016; Llorens et al., 2017)。
最后, 就過程建構而言, Apps和 Tsakiris(2014)認為, 對自我的表征和識別是一個將身體的單模態特征與來自其它感官系統的關于身體的信息進行概率性聯合的過程。腦就是在不斷地消解震驚和更新可能性表征的過程中建構起一個自我, 并將其以穩定和統一的自我感的形式呈現于每個人的有意識的體驗之中。自由能量原理(The free-energy principle)認為, 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的有機體有一種抵制失調的自然傾向,即面對永遠不斷變化的環境他們會盡可能保持自身原本的狀態和形式(Friston, 2010)。有機體通過避免和感官狀態關聯的震驚來達到保持穩定的目的, 而這反過來又會導致一種外部世界對它們而言需要是高度可預測的狀態。因此, 長遠而言, 腦為了減少震驚的出現就必須“學會”如何構建一個更好的模型來預測感官輸入的結果以期與實際的感官事件之間保持盡可能的一致。同樣對于自我而言也是如此, 要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保持一種穩定的自我感, 同樣需要構建一個良好的能夠對感官輸入進行較好預測的自我模型。此外, 這一模型在預測錯誤發生時也要能夠進行更新。這種解釋是否能令人信服仍然需要得到更多實驗證據的檢驗。
陳巍. (2016).神經現象學: 整合腦與意識經驗的認知科學哲學進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巍, 單春雷, 袁逖飛. (2016). 異己手癥候群述評: 現象學精神病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的雙重角度.應用心理學研究(臺灣), 64, 135–171.
李恒威, 董達. (2015). 演化中的意識機制——達馬西奧的意識觀.哲學研究,(12), 106–113.
瓦雷拉, F., 湯普森, E., 羅施, E. (2010).具身心智: 認知科學和人類經驗(李恒威, 李恒熙, 王球, 于霞 譯).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張靜. (2017).自我和自我錯覺——基于橡膠手和虛擬手錯覺的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靜, 陳巍. (2016). 身體意象可塑嗎?——同步性和距離參照系對身體擁有感的影響.心理學報, 48(28), 933–945.
張靜, 李恒威. (2016). 自我表征的可塑性: 基于橡膠手錯覺的研究.心理科學, 39(2), 299–304.
Apps, M. A., & Tsakiris, M. (2014). The free–energy self: A predictive coding account of self–recognition.Neuroscience& Biobehavioral Reviews, 41, 85–97.
Armel, K. C., & Ramachandran, V. S. (2003). Projecting sensations to external objects: Evidence from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270(1523), 1499–1506.
Bottini, G., Bisiach, E., Sterzi, R., & Vallarc, G. (2002). Feeling touches in someone else's hand.Neuroreport, 13(2), 249–252.
Botvinick, M., & Cohen, J. (1998). Rubber hands' feel' touch that eyes see.Nature, 391(6669), 756–756.
Brozzoli, C., Gentile, G., Petkova, V. I., & Ehrsson, H. H.(2011). fMRI adaptation reveals a cortical mechanism for the coding of space near the hand.The Journal o f Neuroscience, 31(24), 9023–9031.
Christoff, K., Cosmelli, D., Legrand, D., & Thompson, E.(2011). Specifying the self for cognitive neuroscience.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3), 104–112.
Clark, A. (2013). Whatever next? Predictive brains, situated agents, an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science.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3), 181–204.
David, N. (2012). New frontiers in the neuroscience of the sense of agency.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6, 161.
David, N., Newen, A., & Vogeley, K. (2008). The “sense of agency” and its underlying cognitive and neural mechanism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7(2), 523–534.
Demiryürek, B. E., Gündogdu, A. A., Acar, B. A., & Alagoz,A. N. (2016). Paroxysmal posterior variant alien hand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parietal lobe infarction: Case presentation.Cognitive Neurodynamics, 10(5), 453–455.
Ehrsson, H. H., Wiech, K., Weiskopf, N., Dolan, R. J., &Passingham, R. E. (2007). Threatening a rubber hand that you feel is yours elicits a cortical anxiety respons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4(23), 9828–9833.
Farrer, C., Bouchereau, M., Jeannerod, M., & Franck, N.(2008). Effect of distorted visual feedback on the sense of agency.Behavioural Neurology, 19(1-2), 53–57.
Franklin, D. W., & Wolpert, D. M. (2011). Computational mechanisms of sensorimotor control.Neuron, 72(3), 425–442.
Friston, K. (2005). A theory of cortical response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360(1456), 815–836.
Friston, K. (2010). The free-energy principle: A unified brain theory?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2), 127–138.
Gallagher, S. (2000).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s of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ve science.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4(1), 14–21.
Gallese, V., & Sinigaglia, C. (2010). The bodily self as power for action.Neuropsychologia, 48, 746–755.
Gentile, G., Guterstam, A., Brozzoli, C., & Ehrsson, H. H.(2013). Disintegration of multisensory signals from the real hand reduces default limb self–attribution: An fMRI study.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3(33), 13350–13366.
Guterstam, A., Petkova, V. I., & Ehrsson, H. H. (2011). The illusion of owning a third arm.PLoS One, 6(2), e17208.
Haggard, P. (2008). Human volition: Towards a neuroscience of will.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9(12), 934–946.
Haggard, P., & Chambon, V. (2012). Sense of agency.Current Biology, 22(10), R390–R392.
Haggard, P. (2017). Sense of agency in the human brai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8(4), 196–207.
Hertza, J., Davis, A. S., Barisa, M., & Lemann, E. R. (2012).Atypical sensory alien hand syndrome: A case study.Applied Neuropsychology, 19(1), 71–77.
Ionta, S., Heydrich, L., Lenggenhager, B., Mouthon, M., Fornari,E., Chapuis, D., ... Blanke, O. (2011). Multisensory mechanisms in temporo–parietal cortex support self-location and first-person perspective.Neuron, 70(2), 363–374.
Jeannerod, M. (2003). The mechanism of self–recognition in humans.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142(1-2), 1–15.
Kalckert, A., & Ehrsson, H. H. (2014). The moving rubber hand illusion revisited: Comparing movements and visuotactile stimulation to induce illusory ownership.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6, 117–132.
Klein, S. B. (2012). “What is the self?”: Approaches to a very elusive question.Social Cognition, 30(4), 363?366.
Kühn, S., Brass, M., & Haggard, P. (2013). Feeling in control:Neural correlates of experience of agency.Cortex, 49(7),1935–1942.
Limanowski, J., & Blankenburg, F. (2015). Network activity underlying the illusory self‐-attribution of a dummy arm.Human Brain Mapping, 36(6), 2284–2304.
Llorens, R., Borrego, A., Palomo, P., Cebolla, A., Noé, E., i Badia, S. B., & Ba?os, R. (2017). Body schema plasticity after stroke: Subjective and neu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the rubber hand illusion.Neuropsychologia, 96, 61–69.
Ma, K., & Hommel, B. (2015). Body–ownership for actively operated non–corporeal object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36, 75–86.
Makin, T. R., Holmes, N. P., & Ehrsson, H. H. (2008). On the other hand: Dummy hands and peripersonal space.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191(1), 1–10.
Manto, M., Bower, J. M., Conforto, A. B., Delgado-García, J.M., da Guarda, S. N. F., Gerwig, M., ... Timmann, D. (2012).Consensus paper: Roles of the cerebellum in motor control—the diversity of ideas on cerebellar involvement in movement.The Cerebellum, 11(2), 457–487.
Moore, J. W., & Obhi, S. S. (2012). Intentional binding and the sense of agency: A review.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21(1), 546–561.
Petkova, V. I., Khoshnevis, M., & Ehrsson, H. H. (2011). The perspective matters!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in ego-centric reference frames determines full–body ownership.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 35.
Riemer, M., Kleinb?hl, D., H?lzl, R., & Trojan, J. (2013).Action and perception in the rubber hand illusion.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229(3), 383–393.
Sidarus, N., Vuorre, M., & Haggard, P. (2017). How action selection influences the sense of agency: An ERP study.NeuroImage, 150, 1–13.
Suzuki, K., Garfinkel, S. N., Critchley, H. D., & Seth, A. K.(2013).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across exteroceptive and interoceptive domains modulates self–experience in the rubber–hand illusion.Neuropsychologia, 51(13), 2909–2917.
Synofzik, M., Lindner, A., & Thier, P. (2008). The cerebellum updates predictions about the visual consequences of one's behavior.Current Biology, 18(11), 814–818.
Synofzik, M., Vosgerau, G., & Newen, A. (2008). I move,therefore I am: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agency and ownership.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7(2),411–424.
Tajadura-Jiménez, A., Grehl, S., & Tsakiris, M. (2012). The other in me: Interpersonal multisensory stimulation changes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elf.PLoS O ne, 7(7),e40682.
Thompson, E. (2014).Waking, dr eaming, be ing: Sel f and consciousness in neuroscience, meditation, and philosoph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sakiris, M. (2010). My body in the brain: A neurocognitive model of body–ownership.Neuropsychologia,48(3), 703–712.
Tsakiris, M., Carpenter, L., James, D., & Fotopoulou, A.(2010). Hands only illusion: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elicits sense of ownership for body parts but not for non–corporeal objects.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204(3), 343–352.
Tsakiris, M., Hesse, M. D., Boy, C., Haggard, P., & Fink, G.R. (2007). Neural signatures of body ownership: A sensory network for bodily self–consciousness.Cerebral Co rtex,17(10), 2235–2244.
Vosgerau, G., & Newen, A. (2007). Thoughts, motor actions,and the self.Mind & Language, 22(1), 22–43.
Wittgenstein, L. (1958).The blue and brown books. Oxford:Basil Blackwell.
Zhang, J., & Hommel, B. (2016). Body ownership and response to threat.Psychological R esearch, 80(6),1020–1029.
Zhang, J., Ma, K., & Hommel, B. (2015). The virtual hand illusion is moderated by context–induced spatial reference frames.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1659.
Zheng, Z. Z., MacDonald, E. N., Munhall, K. G., &Johnsrude, I. S. (2011). Perceiving a stranger's voice as being one's own: A ‘rubber voice’ illusion?PLoS O ne,6(4), e18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