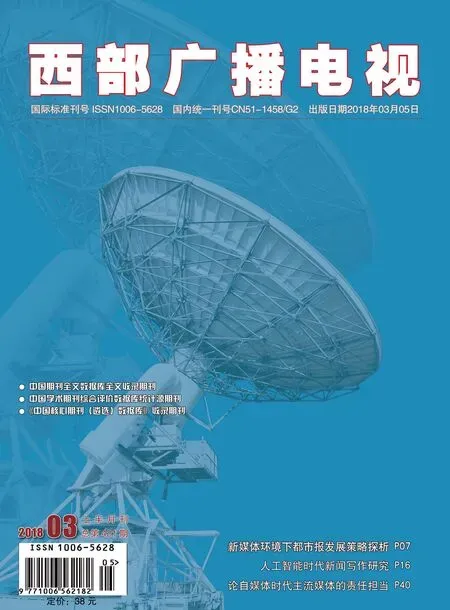賈樟柯電影中的留白之美
崔 瑩
留白思想是美學的重要理論之一,脫胎于古典哲學的虛實論,從書畫藝術中的“計白當黑”漸漸豐富擴展到了文學﹑舞蹈﹑音樂﹑建筑﹑戲劇﹑影視等藝術領域。首先在文學領域,語言不能“言征實”“情直至”,描繪景物表達情感不能過于淺白直露,細致具體,不留空白,肯定會削弱作品的審美張力。再說中國傳統戲曲舞臺,通過演員的表演動作展現劇情環境,不刻意設置復雜布景,給演員表演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也讓觀眾留有余韻。當然,音樂中的“此時無聲勝有聲”﹑中國園林藝術中的疊山理水﹑影視藝術中視聽語言的省略與懸置都體現出了留白的思想。
著名學者倪震說:“正如西方的電影理論研究,透過西方古典繪畫的雙舞臺系統,推論出西方經典電影的‘縫合’理論,并揭示其引導代碼的意識形態功能一樣,東方繪畫的編碼系統是否影響﹑如何影響電影的影像結構和鏡語系統,這是一個有待探討的課題。”[1]實際上,中國的影視藝術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傳統繪畫觀念的影響,留白的廣泛存在就是明顯的例子。與其他藝術形式相比較,影視的特性就是能帶給觀眾身臨其境的逼真感,如果再以直白淺露的方式呈現,人物臺詞﹑解說﹑情節鋪敘過實過滿,留給觀眾的想象與美感會大大減弱,使作品失去原本的意境和感染力。因此,影視藝術更應適當吸收傳統美學中的留白思想,把握好“隱”與“顯”的程度,使作品留有或濃或淡的余味,也給觀眾留下澄凈的想象空間。
1 賈樟柯電影的留白思想
賈樟柯雖然學習和借鑒了巴贊的紀實美學和德·西卡拍攝電影的觀念和態度。但不可否認,賈樟柯自身的生長經歷與文化背景也影響著他的電影創作。賈樟柯曾在接受釆訪時說:“《風柜來的人》對我影響非常大。有人說賈樟柯總說侯孝賢導演,拍的片子好像也有點像侯孝賢的電影,還說長鏡頭是學的侯孝賢。”[2]侯孝賢是追求東方主義美學的大師,他的觀念里有東方人推崇的靜態之美,在表達情感時也是克制內斂的。而賈樟柯與他在文化上又有共通性,因此在賈樟柯的電影里,表面上是現實生活的記錄,實則還隱藏著更深的意蘊,詩意地表達了不斷變遷的現實帶給我們的體驗,含蓄雋永,意味深長,與傳統美學當中的留白思想相呼應。總的來說,筆者認為在賈樟柯的電影里,留白體現出兩層含義,一層是在技法的運用上,另一層面是其風格給觀眾帶來的心理感受,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賈樟柯的電影世界。
2 電影視聽元素中的留白
法國的電影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在《電影語言》一書中將電影語言解釋為:電影語言是電影藝術在傳達和交流信息中所使用的各種特殊媒介﹑方式和手段的統稱。即電影用認識和反映客觀世界﹑傳遞思想感情的特殊藝術語言。它以現代科學技術提供的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其演進與電影技術的進步有密切聯系[3]。“電影語言”就是現代“視聽語言”的藝術形態,最能體現導演獨特的風格,故從視聽語言的角度分析賈樟柯的電影能更好地領會其表達的意蘊。
2.1 長鏡頭與空鏡頭
著名影評人巴贊提出了被大眾認可的“長鏡頭”理論,即通過較長的鏡頭時間來展現處于同一個時空中的連續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動作﹑完整的事件的鏡頭,它能夠保持時間﹑空間以及事件多樣性和統一性。基于此種特質,生活的原生態可以被長鏡頭展現出來;更重要的是,恰當運用長鏡頭,電影在記錄與寫實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種留白之韻。電影《站臺》中有個片段是尹瑞娟和鐘萍在屋內聊天,鐘萍慫恿尹瑞娟抽煙,然后又執著地要幫她描眉,畫面里的兩個人就像普通朋友一樣,鏡頭始終保持著觀察者的姿態,保持著自然隨意的氛圍,房間灰暗的環境,女孩子鮮艷的衣服﹑逆光的窗戶和縷縷輕煙形成了一幅詩意的構圖。長鏡頭建構出的留白空間,給觀眾帶來無限的韻味。同樣,在《站臺》里,中近景鏡頭里是崔明亮和尹瑞娟在城墻邊朝對方走過來,又走過去,卻始終沒有靠近。整個段落鏡頭始終沒有運動,似乎讓觀眾在一旁注視著一切。在靜靜的時間流淌中,人物若即若離地走動著,觀眾似乎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情感的微妙變化。長鏡頭給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視聽體驗,表面是在記錄,實則詩意地表達了作者的情感,也給觀眾留下回味。
空鏡頭即鏡頭下無人物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天空﹑原野﹑花草﹑樹林﹑墻壁等,或是利用鏡頭焦點虛化形成的模糊背景,這些畫面雖然不是主體對象,但卻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能將一種較為含蓄的美感置入電影中,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情緒和感受。例如,在電影《三峽好人》中,被云霧繚繞的遠山,澄澈碧綠的江水,空鏡頭的運用將三峽地區拆遷之前的場景一一記錄了下來,對比之下岸上的生活場景卻大相徑庭,熙熙攘攘的人群,凌亂的街道,無處不在的建筑廢墟。當沈紅找到郭斌原來所在的工廠時,鏡頭前景是沈紅的側身,后景是散布在山凹間高低不一的廠房;在韓三明找到跑船回來的麻幺妹時,鏡頭前景是頭頂衣服的韓三明的側身,后景是煙霧彌漫的江水和江面上零星停泊著的船只。空鏡頭將實際的空間記錄了下來,觀眾在看到此種情景時,心境必然是五味雜陳。《小武》的主人公被父親趕出了家門后,站在村口看到的景象通過一個空鏡頭表現了出來——村里的土灰色平房﹑光禿禿的山崗﹑干枯的樹木,蜿蜒曲折的土路……這些景,與小武的心境相契合,此刻生活的艱辛苦澀,迷茫且無依無靠的漂泊感仿佛與周遭的環境融為一體,霎時間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不需要過多直白鋪敘。
2.2 色彩元素
色彩是影視藝術重要的視覺元素之一,可以瞬間吸引觀眾或帶來沖擊力,“有助于深刻表達內容和從情緒上感染觀眾的造型因素”[4],并且“可以用來推動劇情的發展,直接參與環境與心理氛圍的制造”[5]。運用色彩元素能表達某種象征性含義,含蓄地體現導演意圖,形成留白的韻味。
看過賈樟柯電影的人,都會注意到畫面的色彩,“故鄉三部曲”里中的內陸小城﹑街景﹑城墻﹑火車站等,《三峽好人》中的樓房里的廢墟和廢舊的廠房,還有《小山回家》中的北京街頭,都是以灰色為主色調,這種色調不僅使事物客觀地呈現,還能表達畫面之外的意蘊。這就是留白之美,不需要過多的解說詞,或是人物對話,就有這樣的感染力,生存其中的人們仿佛都無所適從,頹廢的精神狀態能被我們清晰地感受到。除灰色之外,綠色也是賈樟柯電影慣用的色調。《站臺》開始,畫面就呈現的是以綠為主的色調,綠墻前面擠滿了等著看演出的農民,作者想表達的思想﹑想表達的情感就包含在這滿屏的﹑仿佛噴涌而出的綠色中。
2.3 音樂音響
在影視語言中,巧妙運用聲音元素在影視藝術中必不可少,但如何運用才能給觀眾帶來回味無窮的感覺?賈樟柯這樣示范,他電影中的人物,在需要做出重要決定前不是我們熟悉的大喜大悲,而常常是一言不發的沉默。《三峽好人》里有一幕是韓三明和麻幺妹兩人在江邊相見,卻相顧無言,鏡頭一直呈現他們這樣的狀態,沒有移開,雖然沒有對話,觀眾卻能感受到兩個人要重新在一起的決心。此時悄無聲息比鑼鼓齊鳴更有感染力。巴拉茲·貝拉在《電影美學》中也曾說:“靜也是一種聲音效果,但這只是在能聽到聲音的情況下才如此。表現靜是有聲片最獨特的戲劇性效果之一。”其實,這與留白的本質一致,意在用空來營造滿,用有來詮釋無,其本源是空,是無。以空﹑無的表達方式呈現,使電影呈現留白之美,具有了更遼闊﹑深遠﹑空靈的意境。
3 電影敘事層面的留白
國畫的留白講究筆法簡潔,以少帶多,廣為流傳的一幅馬遠的《寒江獨釣圖》就體現了這種特質,只畫一葉孤舟,舟上老翁俯身垂釣,四周是大面積空白的背景,只有寥寥幾筆微波,卻給人煙波浩渺之感,意境開闊深遠。賈樟柯在電影的敘事層面也實現了這種留白,沒有激烈的戲劇沖突和戲劇化的情節,展現的是人們生活最瑣碎無章的一面,因為在賈樟柯看來,一部電影最重要的是能產生一種調動觀眾精神活動的氛圍,使觀眾聯想起自己的生活經歷,產生某種獨特的體驗,而不是完美講述情節豐富﹑戲劇性強的故事,這即是留白的精髓。
3.1 情節跳躍
賈樟柯影片的敘事鏈條上常常會出現人物的突然轉變,突然出走消失,而導演從來不交代轉變的原因。《站臺》中有一幕是女主人公尹瑞娟,鏡頭切換她騎著摩托車在街上穿行,身上穿著綠色的制服,她怎么成為稅務員了?之前提到的她的父親怎么樣了?還有至今單身一人的她曾經的牙醫男友去哪了?以上內容賈樟柯在電影里都沒有告訴清楚說明,中間所有過程都留給觀眾去想象和揣測,畫面只是呈現的流逝的時光。還是這部影片,鐘萍因為和張軍非法同居被抓到了派出所,警察告訴她張軍已經交代了他們兩個并不是夫妻,之后鐘萍就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文工團,失去了聯系,不知所終。而她對這件事的態度,復雜的內心活動抑或是與張軍的情感糾葛,甚至很多具體重要的事件都被省略掉了,留下很多空白。
3.2 開放式的結局
在賈樟柯的電影里,經常沒有明顯固定的故事結尾,而是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呈現出來,給觀眾留下了無限思考想象的空間,比如早期的“故鄉三部曲”通通采用了開放式結局,主人公最后的情感歸宿和生活去向都沒有說明,給觀眾留下回味的余地。因為,在賈樟柯看來,生活本來就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同樣,在電影《小武》結尾也有用留白,民警郝有亮把小武拷在了電線桿旁,小武順勢蹲在了地上,來看熱鬧的很多群眾聚集在了小武四周,于是賈樟柯巧妙地運用了一個360度搖鏡頭對準了這些并不參與影片拍攝的群眾。在不經意間看熱鬧的群眾和演員之間就互換了位置,演員和圍觀群眾之間的界限不再明顯,此時影片便戛然而止,只留下了觀眾在回味中慢慢地品味思考。
《世界》的結尾,趙曉桃想要和成太生用煤氣中毒的方式結束生命,以此來報復用情不專的成太生,但卻沒有成功,被人得知后救了出來,最后兩個人被抬到了冰冷的雪地上,躺著一動不動,成太生問道:“我們是不是死了?”趙曉桃說:“沒有,我們才剛剛開始。”影片隨即結束,沒有明確的答案告訴觀眾兩個人究竟是生還是死?是最終重歸于好,還是毅然決然分手?同樣,在《三峽好人》的最后,一邊是工人在廢墟處拆遷,一邊是有一個人在兩個廢墟之間高空走鋼絲,并且手里還個拿著橫桿,隨著蒼涼遼遠的川江號子,背著包裹的韓三明佇立著,漠然地看著遠方,鏡頭停頓幾秒后出畫。通過鏡頭前“人物的側身佇立”的姿勢,以及層次分明的人和景創造了極目遠眺與驀然回首的詩意瞬間,結尾與敘事相融合,回味無窮。影片《山河故人》最后,音樂再次響起,垂垂老矣的沈濤一個人站在大雪中跳舞,表情安詳又平靜,它是否回憶起年輕的自己,是否記得愛過他的故人,是否惦記遠離故土的兒子,但所有的一切都消失在時間里。故鄉的山亙古不變,故鄉的水川流不息,變的是世事滄桑,物是人非,不變的是人心,是那山那河。就像張艾嘉在影片中說的那樣: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被時間摧毀。結尾的點睛之筆是如此打動人心,回味悠長。
4 結語
通過對賈樟柯電影的視聽語言與敘事層面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到賈樟柯電影在日常紀實性的光影表層下,將詩化的表現與生活原生態的再現真正融為一體,蘊含著中國古典美學中的留白之美。
參考文獻:
[1]周星.民風化境——中國影視與民族文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2]陳波.尋找電影之美——賈樟柯十年電影之路[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6).
[3][法]馬賽爾·馬爾丹.電影語言[M].何振淦,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
[4]顏純鈞.電影的解讀[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
[5][法]熱拉爾·貝東.電影美學[M].袁文強,譯.北京:商務印書局,1998.
——以《在一起》中的《救護者》單元為例
——以《山河故人》為例